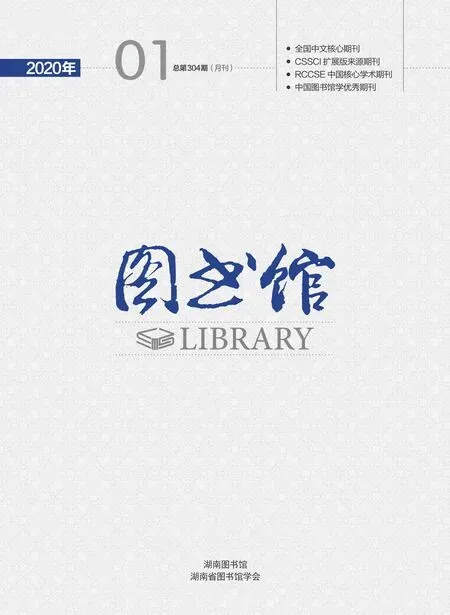經典文獻視閾下“類”的國際詮釋與文化融通*
王 進 王振國
(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與文化研究院 濟南 250355)
1 引言
“文獻分類”通常是指根據分類工具將各種文獻依其內容學科屬性或其他特征揭示出該種文獻的內容性質,并據以分門別類且有系統地組織整理文獻的一種學科方法。“方法論、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互相關聯又有所區別,從方法到理論要進行通盤考慮,才能有利于文獻學全面、系統、健康的發展。”[1]有關文獻分類的重要性,中歐學者也多有闡明,如宋代鄭樵在《通志·校讎略》指出:“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2]1806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闡述:“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3]956英國學者Maltby 主張:“文獻圖書事業的基礎是分類。”[4]希臘學者Shera 則表示:“文獻機構組織知識的基本手段是書目組織,而書目組織的基礎則是分類。”[5]另外,德國學者Richardson 也述及:“文獻研究人員最重要的工作職責是分類。”[6]上述言論說明,文獻分類是文獻研究的基礎,它不僅揭示文獻館藏的內容,同時也提供辨識學術源流的功用。了解和把握中歐文獻分類原理的最佳途徑是理解其思想根源,欲真正了解中歐文獻分類原理的異同,需要追溯其淵源與建構系統的思維方法。截至目前,探討中歐文獻分類原理及其思想淵源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嘗試搭建一條連接中歐文獻分類的橋梁,俾使對中歐文獻分類原理有進一步的認識,更期使經由中歐文獻分類的國際比較,讓圖書文獻學領域的研究得以貫穿國際化文獻分類原理,同時對于分類原理的發展有科學完整的國際認知。
2 “類”的文化思維與中歐文獻源流
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的形塑與其思維有很大關聯。早期人類原始部落的分類方式屬于具象思維,歐洲大約從亞里士多德時期開始逐漸向邏輯的科學分類發展,而具象思維在中國有很強的延續性,這樣的思維也反映在文獻分類上,遂形成了中歐文獻中不同的“類”概念。
歐洲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與知識有關的創造活動大多以抽象邏輯思維進行分類,尤其主張以事物的本質屬性歸類,事物之間的關系只有“是”與“不是”,亦即任一事物在同一時間里具有某種屬性或不具有某種屬性,并認為分類時要窮盡所有的可能性,范疇之間的區分彼此截然分明且范疇內的成員無等級區分。換言之,歐洲的“類”概念是利用二分法對事物的本質進行鑒別與選擇,各范疇之間的界線是明確的,同時所有被劃分在同一范疇的成員皆具有共同的本質屬性和同等的地位,務求做到符合窮盡性與互斥性原則。歐洲文獻分類強調同層級分類間應具“互斥性”,他們認為哲學的基本原理是文獻分類的理論基礎,歐洲現代文獻分類實源于古典范疇理論。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類、邏輯分類或動植物分類大多呈現具象思維,諸如整體性、直觀性、形象性、概括性、聯想性等都是此種思維的特性。“從廣義的圖書文獻來講,殷商時期甲骨文獻的收藏可以算作圖書檔案的萌芽時期。”[7]中國古代的“類”不強調以事物的本質屬性分類,文獻分類大多參考先哲的知識分類或本草分類,體現了具象思維。此種思維與先哲“天人合一”“主客同構”的中國傳統精神有關,即所謂的中國智慧。這種智慧表現在思維模式上重視整體性的直觀把握,不注重強調形式邏輯分析。中國文獻分類體系在演進的過程中類目雖易出現變化,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詩經等都與經部有關;同樣,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天文、歷數、五行、兵家、兵書等也都與子部有關。事實上,它們的內容涉及多種學科,之所以被分在同一范疇并非因為具有共同的屬性,而是部分屬性相似進而被關聯在一起。
總的來說,歐洲階層式文獻分類屬于“古典范疇理論”,中國文獻分類則比較傾向“現代范疇理論”,它們是影響中歐發展出不同文獻分類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3 “類”的原理在中歐文獻中的殊異與融通
3.1 中歐古代文獻分類原理
先秦至清末以前,中國提出的文獻分類原理有長孫無忌的“離其疏遠、合其近密”[5]5;鄭樵的“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2]1815;馬端臨的“以類相從”[9];祁承?提出的“書有定例,而見不盡同,且亦有無取于同者”[10];章學誠倡導的“互著別裁”[3]966與“因勢利導”[3]936等。未正式提出的潛在分類思維包括:“據書立目”“類目設置原則”“以文字立類”“總括性原則”“詳盡性原則”“類目層級原則”“類目排序原則”(如一般至特殊、人次關系序列、解釋關系序列、重要性遞減、時序排列原則等)等。其中,屬于抽象邏輯的“總括性原則”僅粗具雛型,尚未達至成熟階段。
從古希臘羅馬時期至近代,歐洲提出的文獻分類原理有Brown 的“一題一位原理”[11];Hulme 的“文獻保證原理”[12];Bliss 的“科學和教育一致性原則、邏輯從屬原則、配置原則、可擇性位置原則、標記原則”[13];Broadfield 的“相似律、歷史律、進化律”[14];Taylor 提出的“邏輯分類、互斥性、分類標準一致性、窮盡性與彈性原則”[15];Vickery 從概念層、字匯層與標記層提出分類原則,較著名的有“分析綜合原理、類目順序原理、原料轉化原則、具體遞減原理、數量遞增原則、時間從近原則、發展從近原則、復雜遞增原則、慣用序列原則”[16];除此之外,尚有引用生物學或邏輯學等領域的“整合層次理論”“總括性原則”等。
3.2 中歐古代文獻分類原理的不同之處
其一,標記原理由歐洲產出。歐洲文獻分類學者相當重視標記,提出相關主張的有Bliss、Brown、Vickery、Taylor 等。有別于其他理論,標記原理是因應文獻分類系統設計所產生,完全由文獻分類學者所提出,因此,它的發展并不是建立在哲學原理的基礎上。在中國古代,標記相關的學術觀點則相當少見。
其二,敘述性與動態性理論在歐洲呈現為先后發展,中國則展現為并行發展。Parkhi 曾將Vickery 理論提出的時間點作為劃分文獻分類發展史的依據,“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發表的理論被稱為敘述性理論,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則被視為動態性理論。”[17]Parkhi 為歐洲文獻分類理論發展所采用的分期原則在中國古代并不適用。以“類目順序”原則為例,Parkhi 將其歸屬于“動態性理論”,事實上西漢劉歆時代已經有了類目排序觀念;十三世紀的馬端臨提出了“以類相從”,十八世紀的章學誠提出了“先道后器”原則。以時間點來看,這些應是“敘述性理論”,就性質而言卻是“動態性理論”。所以,中國曾出現敘述性與動態性理論同時發展的情況,這與歐洲先后發展并不相同。
其三,中國文獻分類原理的萌芽實早于歐洲。由于中國古代并未特地為文獻分類理論著書立論,讓人誤以為中國古代不曾提出分類理論的主張。事實上,部分重要的分類理論思維在中國古代早已出現,例如,有關聚類的原理,歐洲在十九世紀末由Edwards 提出了“一題一位原理”[18],而中國早在七世紀的唐代便提出了“離其疏遠,合其近密”[8]5論點。對于一致性的共識觀念,歐洲約在二十世紀初由Bliss 提出了科學和教育一致性原則,而在十六世紀的明代,祁承?即提出了“因、益”的建議。有關定位原理,二十世紀初,歐洲的Bliss 提出了位置可替換原則,而早在十六世紀,明代祁承?就提出了“通、互”的思想。
3.3 中歐古代文獻分類原理的相同之處
中歐文獻分類原理受到哲學、邏輯學等領域的影響。中歐皆重視類目設置原則。在眾多文獻分類原理之中,類目設置的相關原則如類目選詞、類目排序等最受重視。歐洲的文獻分類須遵循“互斥性”與“分類標準一致性”原則,此原則來自Porphyry 的知識樹原理,Edwards 的一題一位原理亦是總結哲人知識分類經驗而來;類目專深層次漸進原則的分類概念來自Porphyry 的五謂詞,即種、屬、種差、固有性及偶然性。可見,歐洲的文獻分類理論大多受到了哲學家、邏輯學家的分類思維影響。同樣,宋代鄭樵提倡的文獻分類與先哲的會通思想不無關系,“其校讎學將圖書、圖譜、金石皆視為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并對文獻進行了搜求、校勘、編目、考證以及編纂等五大整理程序”[19];南北朝王儉提倡名實相符的類目順序則受到了孔孟等哲人的名實論影響;此外,清代章學誠提出的先道后器文獻排序方法也與《易經》的哲學思想有關。
4 “類”的特質在中歐文獻系統中的殊異與融通
4.1 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的特質解析
二十世紀初期以前,中歐文獻分類系統各自獨立發展,未曾出現交流情況,無論是標記、類目內容與結構形式皆有極大分野。上述差異的形成與中歐的文化傳統、學術源流等方面的影響有關。“專業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相關專業活動的深化進程。”[20]確切地說,中歐文獻分類體系的形成主要取決于其社會群體的知識觀、思維模式以及價值取向等。在此影響下,中歐文獻分類體系所體現的特質并不完全相同。
中國呈現的特質主要為重要性遞減的“價值性”、借鑒前人分類的 “繼承性”、體現整體分類思維的“具象性”、文字標記的“助記性”、類目長度的“精簡性”及法令規定文獻體制的“統一性”。同樣,歐洲的文獻分類系統也有其特性,包括重要性遞減的“價值性”、借鑒前人分類的 “繼承性”、遵循邏輯分類原則的“抽象性”、跨國交流的“國際性”、阿拉伯數字標記的“助記通用性”與類目長度的“精簡性”。
上述特質的“價值性”“繼承性”“助記性”及“精簡性”是中歐建構分類系統共有的特色,而“具象性”與“抽象性”則是中歐各自的特性,二者呈互補關系,至于“國際性”“通用性”則是歐洲的優勢,催生了全球皆在運用的杜威十進分類法。
4.2 中歐建構文獻分類系統的異同闡釋
其一,中歐文獻都以藏書為分類基礎,歐洲另具邏輯分類的類型。歐洲文獻分類系統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邏輯為基礎的分類,另一種是以實用為基礎的分類。前者是將知識范疇依邏輯方式區分排列,然后將各種文獻數據納入其分類系統之中,后者基本上是依據實際館藏所編訂的分類法。從演進的歷程來看,歐洲早期多強調以實用為基礎的分類法,十九世紀中期以后開始發展以邏輯為基礎的分類法。中國古代文獻分類系統主要是根據藏書分類編撰,從宏觀角度來看,基本皆屬于以實用為基礎的分類,不過由于中國古代的藏書情況較為特殊,因此可詳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根據既有的藏書分類(親見原書),如劉歆的《七略》;第二種是根據過去的藏書(未親見原書),以其目錄為基礎的分類法,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焦竑的《國史·經籍志》;第三種是結合上述兩種類型的分類法,亦即根據既有藏書與目錄編撰的分類體系,如阮孝緒的《七錄》等。從演進歷程來看,中國大約從六世紀阮孝緒《七錄》開始出現非單純以既有藏書為基礎的分類法。
其二,中歐應用文獻保證原理的異同。中歐以實際藏書編制的文獻分類體系,基本上符合文獻保證原理。前者如劉歆《七略》、荀勖《晉中經簿》、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長孫無忌《隋書經籍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祁承?《澹生堂藏書約》等,后者如Callimachus 分類法、歐洲國會文獻圖書分類法等。至于不符合文獻保證原理的狀況,中歐有所區別。歐洲主要以人類知識為基礎編制,會造成“有目無書”的分類體系。中國古代的大部分類例是根據藏書編纂,從宏觀角度來看是符合文獻保證原理的;但部分類例可能不符合文獻保證原理,如存書與亡書兼收無法確保“有目必有書”、未遵從書眾則立類的原則造成“有書無目”、選擇性收藏造成“有目無書”。
其三,分類系統類目的層級位置皆取決于類目本身的價值。中歐文獻分類系統類目的層級和排序皆與其是否受到重視有關。如古希臘羅馬時期,修辭學的技藝是邁向宮廷之途的先決條件,第歐根尼將演說術類目置于體例首位,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辯論技巧及演說能力的重視。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六經,并規定以通經與否為進退官吏的依據,使得日后經學大盛,當某類知識受到分類者或是大眾重視時,其類目就會被提升成大類或被排列于前。故“重要性遞減”是文獻分類法中常被應用的類目排序原理,運用類目重要性遞減原則的有劉歆、王儉、阮孝緒等。基于此,人們從歷代分類體系的層級變動與內容增刪,可以探尋知識進步的軌跡及受社會重視的程度。
其四,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的本質是減熵原理。根據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的發展脈絡,其萌發時間皆發生在公元前,爾后分類系統的時代進程則有所差異。中國自西漢以后,文獻分類體系的數量開始急劇增加。反觀同時期的歐洲,其文獻分類系統的數量卻無明顯增長,此現象與文獻存量有極大關聯。當文獻不斷增加形成無序狀態時,人們就會思考一套方法對其加以組織整理以便保存與應用。資料的整理從無序至有序,其實就是十九世紀德國物理學家Clausius 提出的熱力學定律“熵”原理的具體應用。熵是由希臘語“能量”和“轉變”合成的,熵的增加表示分子無序性的增加,熵的減少表示分子有序性的增加。因此,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的產生,本質上是一種“減熵原理”。
其五,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發展多建立在先人基礎上并與教育緊密結合。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的形成多是因循或總結前人的經驗,在借鑒的同時又有所創新,揭示出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皆具有繼承性的特質。“中國古典文獻重歷史,西方文獻重排架與檢索,二者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剛好形成互補。”[21]是故,繼承的對象包括前賢哲人的分類體系或前代的文獻分類體系。在歐洲,文獻分類系統類目綱要的設立,除借鑒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知識分類外,其分類的主要內容與學校授課內容相呼應,尤其是大學課程。如公元前五世紀以前,希臘教育幾乎完全是以詩為基礎。從古希臘及古羅馬時期開始,歐洲文獻分類系統的類目設置則以“學科”分類,這顯然受到當時教育科目及課程內容的影響。孔子確立了中國早期典籍分類體系結構“六藝”分類法,即《詩》《書》《禮》《易》《樂》《春秋》,這是教學和治學的重要工具。其中,《詩》《書》《禮》《樂》在孔子之前已成為貴族的教育材料。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增加“語孟類”是因為當時國家設科取士,《論語》《孟子》并列為經。綜上可知,中歐文獻分類體系與學校教育課程亦緊密聯系。
其六,歐洲為依類歸書,中國是因書設類。歐洲分類文獻是“依類歸書”,文獻分類法單獨設立,而中國則是“依書設類”,文獻分類與編目并存。中歐文獻分類體系首創之時皆是目錄形式,屬于“因書設類”。之后,歐洲自有文獻圖書館以來,分類者試圖制訂一套可供眾人使用的分類法,其特征是分類方法的設定獨立于分類行為之外。通常分類法設立者與利用者可以是不同的人,只要該分類法設計得宜,便可適用于各類文獻圖書館。而中國自古以來并沒有編訂一套獨立的文獻分類法。文獻分類者在編制分類法時,并非考慮天下所有各類文獻,而是就其所欲編的書籍來決定設立哪些類別。換言之,分類者在面對所要編的書籍時才開始考慮如何分類,而不是應用一套已經建構好的文獻分類法歸類文獻。
5 “類”的發展在中歐文獻中的殊異與融通
5.1 古代中歐國家的政府體制層面
中世紀時期,中國的封建政體與歐洲的封建社會有所不同。歐洲的封建社會并無共同擁戴的最高機構,通常呈現出四分五裂的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社會則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其運轉中心有各級官府。某些朝代的統治者往往喜歡強調一致性,不喜歡去認識客觀存在的多樣性,這樣的策略也延伸至對文獻分類系統建構的管理。比如西晉時期的官府規定,凡是分類的國家藏書皆要采用李充的四部分類法,并以法令形式確定為應遵守的“永制”。在制度規范及李充“經、史、子、集”分類思維的熏染下,四分法幾乎成了古代中國文獻分類法的正統和主流。反觀歐洲,自古希臘與羅馬帝國之后再也沒有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其所發展出的文獻分類不受官方法令限制。中國的“統一性”與歐洲的“分散性”特質使得中歐文獻分類系統發展差異日益明顯。
5.2 中歐文化的源流與承繼層面
中國古代學科為整合式,歐洲為分科式。歐洲在很早以前即談論學科、重視學科并以學科分類。自亞里士多德時代開始,哲學家或科學家將其對宇宙的認識區分為一系列相對獨立的學科,如哲學、邏輯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醫學、政治學、美學、修辭學等。這種以學科分類的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且巨,不僅體現在知識分類上,同時也反映在文獻分類系統上。反觀中國傳統學術及其知識系統主要集中在經、史、子、集四部框架,并無嚴格的學科劃分。雖然中國早在遠古時期已有學科的概念與著作,歷經殷周、漢唐、宋明以至近代,在哲學、史學、文學、算學、天文學等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但并不強調分科的重要性。歐洲的分類強調學術分科,中國的分類則強調和合。前者是“天人相分”“為知識而求知識”以及“分科而學”;后者則是“天人合一” “為用而求知”以及“整體而學”。
5.3 系統建構的知識規則層面
歐洲文獻分類體系主要是以“學科”分類方式呈現,如哲學、邏輯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等;中國則主要是經、史、子、集的四分法。“文獻學術研究范式的變革這個主題涉及文獻學、歷史學和學術史等諸多領域。”[22]中歐文獻分類的部分觀念來自哲學、邏輯學或生物學的分類思想。由于中歐哲學、邏輯學或生物學的分類觀不同,因此,中歐文獻分類發展分歧的重要因素也與之有關。歐洲傳統知識分類的方法主要是以物作為對象,基本上是以事物的客觀本質及其相互關聯的邏輯作為分類的主要依據。中國古代知識分類的特征主要是以人而不以物作為出發點,亦即以事物相對于人的關系作為區分它們的準則。這在文獻分類及百科全書類目中得到印證。前者如劉歆《七略》中的“諸子略”分為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等,即是以人為主體進行分類。后者如《太平御覽》等古代類書亦是從人的角度去思考進行分類。中歐哲人所建構的知識分類體系數量、提出的范疇理論或分類的對象,皆存在著差異。在歐洲社會,哲人熱衷于對宇宙知識進行分類,所創建出的知識分類系統數量眾多;反觀中國古代,雖曾出現荀子“大共名與大別名”、墨子“達名與類名”等類似歐洲知識排序理論,但中國哲人普遍不重視抽象知識的演繹,不以萬事萬物的知識為范疇進行科學分類,如老子主張絕圣棄智,莊子也主張自然放棄知識,僅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曾為知識分類,所以中國知識分類體系的產量相當匱乏。先哲“天人合一”整體觀的智慧對文獻總論的傳承有著深遠影響。
歐洲的文獻分類學者通過學習邏輯學精確推論的規則,如“演繹法”“歸納法”“矛盾律”“排中律”等邏輯原理,了解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相互間的關系,進而衍生出“互斥性”“總括性”“周延性”等文獻分類的準則。反觀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除鄭樵等少數目錄學者外,鮮有學者依據邏輯推演程序,通過知識架構的方式表達對知識的見解。如中國古代對動植物的分類主要是依據其外部形態,呈現直觀的思維,此思維不僅反映在當時類書(百科全書)的分類,同時也體現在文獻的分類上。而在歐洲,古希臘時期的學者已洞察出單純從現象入手進行分類是不夠的,必須依據事物的內在聯系和本質屬性的異同進行分類。
歐洲目錄學與文獻分類體系獨立發展,中國則相依發展,如《七略》可謂是早期的文獻分類系統,其編纂方式皆屬于目錄分類形式。爾后,歐洲的文獻分類體系與目錄分別獨立發展,中國的文獻分類體例則持續與目錄學以依存方式共生。歐洲不僅將分類發展成為專門學科,又發行專業性期刊和設立分類課程,因此其在分類理論方面的研究更為普及,成果豐碩。而中國的目錄學雖持續發展并提出相關主張,但其特性是目錄學者在編訂文獻分類體系時,也在著錄書目,致使所提出的主張往往著重于編書的實踐層面,所以中國分類原理的發展不似歐洲興盛。
中歐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人們的思維方式也存在著差異,進而影響文獻分類的設計。一般而言,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偏重于形象與整體性思維,而歐洲文化比較注重邏輯與分析性思維。歐洲思維講究分析,注重普遍性,偏于抽象邏輯的思維方式。邏輯思維方式通常體現為有順序地推下去,通過分析、比較而識別。因此,歐洲的文獻分類系統基本是遵循一定的邏輯關系,被歸納為某種樹狀層次結構,也是現代學科分類的基本模式,依此模式,人類的知識領域在分類系統中都有可能找到適當位置;中國思維則偏于直觀形象思維的方式,形象思維對事物的識別、判斷沒有推理的程序,因此大多數是屬于平面與二維的結構。
6 結語——文獻“類”的國際化學科準則建構
6.1 文獻分類原則需有兼收并蓄與文化融通的學術氣派
從亞里士多德時期開始,分類須遵守“窮盡性”“融通性”等邏輯原則,被歐洲社會普遍接受,并成為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建構文獻分類系統的主要思考模式。當然,在現代范疇理論觀念下,文獻研究者未必皆具有共同的本質屬性,且范疇之間也未必有明確的區分,因此,“融通性原則”面臨極大的挑戰,執行的困難度可能比預期要高出許多。雖然目前所應用的文獻分類系統已趨成熟,但使用者仍不易檢索到其所需數據,這可能與分類未完全符合融通性原則有關,未來我們應對此多加關注。
6.2 文獻分類思維需有編目具體與邏輯抽象的學術特色
現代的科學分類強調遵守邏輯學的形式構架。所謂邏輯就是正確推論的規則,推論是一種從某些前提得到結論的思考方式。事實上,邏輯學主張的以事物本質屬性為分類的依據,并不是人類原始的分類思維,也非人類普遍運用的分類方式,如古代文獻“經、史、子、集”和類書“天、地、人、事、物”即不是所謂的形式邏輯分類。完全以歐洲邏輯分類原則設計的文獻系統仍有不足之處,具象思維的劃分方式也是人們對文獻分類的貢獻之一。“一體化是世界編目的發展趨勢,國際化是任何一個國家編目規則的必由之路”[23],建議未來文獻信息檢索系統的建構應顧及上述兩種分類思維。由于所有邏輯分類伴隨著判斷行為,判斷與推理并非人人可用,有時需要經過訓練才能熟稔,而具象性思維的分類通常是一種直觀投射的反映,邏輯思考的多層次性需要多種投射才能成形。故系統建構者可以思考兩種層次的設計,以一般使用者比較容易形成的具象分類思
維作為表層設計,進而將其引導至正確的邏輯分類結構。
6.3 文獻分類建構需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脈絡
中國古代文獻分類系統的特色之一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理論方面,鄭樵在《通志·校讎略》提到:“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2]1806,同時也指出古代文獻分類為的是使書籍“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 雖亡而不能亡也”[2]1804,讓治學者能“即類求書,因書究學”,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在系統方面,無論書目分類體系有無提要,皆致力于達成此目標,如《通志·藝文略》沒有小序,沒有解題,形式上與一般藏書目錄無異,但猶能顯示學術源流的專門之學。
6.4 文獻分類系統需注重古典原理與現代范疇的學術融通
“中國的古代文獻整理,以其悠久的歷史而積淀了豐富的學術思想,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優良的學術傳統。”[24]但反觀當下,中國現行的文獻分類法卻大都仿自歐洲的文獻分類法,因此,長期以來多以歐洲文獻分類的系統或原理為研究重點。中國古代的文獻分類原理有其傳統特色,這種特色與歐洲的文獻分類原理互補,前者相當于現代范疇理論,后者形同為古典范疇理論。此二者系不同思維下形成的分類觀念。唯有同時重視,才能獲得完整的文獻分類原理。應用文獻保證原理與修訂類目是中歐編訂文獻分類系統的共同特色,顯示此兩項工作有其重要性,由此,建議文獻分類的系統建構應持續加以重視。除依據文獻保證原理之外,在用詞方面可參酌古代教育內容以及百科全書,因為歐洲古代的文獻知識分類、百科全書的排列漸次與歐洲大學的教育內容趨向一致,中國古代文獻雖未與百科全書同時更新,也是與當時的學習教育互為表里,因此亦可作為修訂的參考。
綜上所述,經典文獻“類”的國際化詮釋與學科建構首先要解析 “類”的文化思維,其次要厘清“類”在文獻學科中的理念源流,再次要從“類”的原理、“類”的特質、“類”的發展來闡釋經典文獻的殊異與融通,通過“類”的國際化闡釋,冀望能夠為國際文獻分類體系提供科學的參照,進而對文獻學界的國際交流有所助益。由古籍而文獻,由比類而詮釋,由學科而國際,應是一條科學研究經典文獻的妥適路徑。
(來稿時間:2019 年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