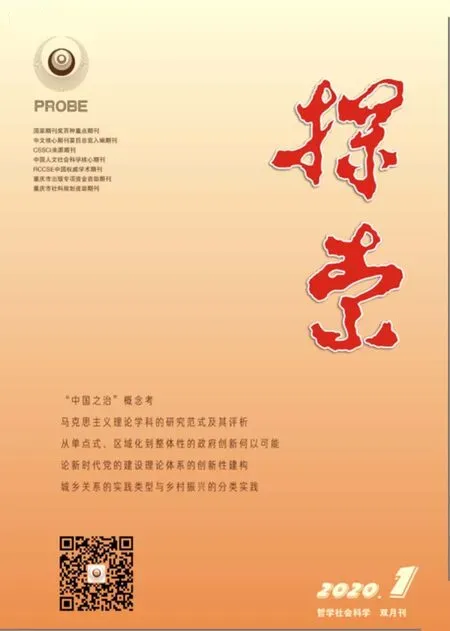“中國之治”概念考
葉娟麗,范晨巖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1 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總結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家治理的制度成就和歷史經驗,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既把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頂層設計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實踐推向新的歷史階段,也助推關于“中國之治”的理論探討成為學界的熱點。但綜觀現有研究,學者們基本上將“中國之治”這一概念直接拿來使用,鮮有人追溯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也沒有對概念本身進行界定。王義桅的長文系統論證了“中國之治”的內涵與特點,但并沒有對“中國之治”進行學理的概念界定[1]。在查證的文獻中,唯有一處涉及對“中國之治”的直接定義,即石國亮提出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欣欣向榮的有序治理景象”稱為“中國之治”[2]。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從中西比較的視角來認識“中國之治”的。如張新平等人認為,“中國之治”是一個與“世界之亂”“西方之亂”相對的概念[3],“中國之治”是指在世界局勢不確定性增強的背景以及世界局勢變化對中國發展形成沖擊的情況下,中國仍能保持經濟穩健增長、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穩定和諧的狀態。這里的“中國之治”強調了政治秩序的有常和社會整體的安寧,是一個與“亂”相對的概念。除了與西方對比,也有將“中國之治”與中國古代、近代對比,認為“中國之治”是一種與近代破敗凋敝、民不聊生相對的社會狀態。基于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之治”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總之,既有研究的“中國之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突出“治”與“亂”的比較,而“中國之治”就是中國貢獻給世界上其他欠發達國家一個可資借鑒的發展模式。這些對“中國之治”的認識確實為我們厘清“中國之治”的內涵指明了方向,但“中國之治”這一概念的使用正日益顯現出泛化的趨勢。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國之治”,歷史上的“中國之治”指的是什么,根據這一概念在十九大后被“啟用”的具體語境,今天的“中國之治”又應當是什么?為了澄清當下學術界與輿論界關于“中國之治”的一些誤讀和誤用,本文擬從梳理“中國之治”的歷史淵源出發對其概念內涵與現實意義進行系統分析。
2 傳統語境下的“中國之治”
“治”在漢語中既有“安定、太平”的含義,也有“治理、管理”的意思。自古以來,中國君主與傳統知識分子都有追求“天下大治”的理想,而其手段可能是儒家的人治,也可能是法家的法治。總之,通過手段之“治”來實現目的之“治”是傳統中國語境下“中國之治”中“治”的基本含義。但與對“治”的理解基本達成共識不同,關于“中國之治”這個四字組合的使用,在不同朝代有著不同的理解。
2.1 華夷之辨與“中國之治”
“中國之治”一詞最早出現在何時何處,現在無法考證。根據目前掌握的文獻搜索結果來看,至少在宋朝大文豪蘇軾那里就開始用“中國之治”這個概念來表達華夷論。在《王者不治夷狄論》中,蘇軾明確提出,“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于《春秋》”[4]84。很顯然,蘇軾認為他的華夷論是繼承了《春秋》的傳統。
《春秋》是否明確提出過“中國之治”不可考,但春秋時期,中原諸侯國對“華夷之別”的強調可以在史家和文學家的著述中窺見一斑。《左傳》中,晉國名臣魏絳在向國君陳述“和戎”的利弊得失時,就蔑稱“戎,禽獸也”[5]273。戎部落的首領駒支反駁晉國權臣范宣子時亦自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5]281所謂的“華”,就是指代周禮治下的中原諸國。除了文化上接受周禮的熏陶,地理上,這些國家星羅棋布分散在華夏文明的核心區域內,在風土、習俗、衣著、飲食、語言文字等多個領域都與周邊的少數民族迥異。由此,先秦時期,“中國”不僅是一個文化概念,也是一個地理概念。唐代韓愈繼承了這一觀點,提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6]19顯然,韓愈認為周禮文化是使華夏民族區別于蠻夷的根本原因。正是這種文化的長期熏陶,使中國古代形成了內中國外夷狄、貴中國賤夷狄、內外不同、華夷有別的觀念。
“中國”的概念一經形成,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也就漸漸得以形塑。正是從先秦時代開始,中國人就在自己的經驗與想象中建構了一個“天下”,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中心之外是華夏或者諸夏,諸夏之外是夷狄。在這種華夷觀念下,地理空間越靠邊緣就越荒蕪,那里的民族就越野蠻,那里的文明就越低級。這種華夷觀成為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基礎。在那些族際對立尖銳、“夷狄之患”嚴重的朝代,比如說宋代,正統(或道統)觀念就尤其突出,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之學格外興盛[7]。而蘇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了“王者不治夷狄”之論,并且在提出其華夷論時明確使用了“中國之治”這一概念。根據蘇軾的華夷論,夷狄是不配適用“中國之治”的。顯然,這里的“中國之治”應當強調的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華夏禮儀之治。關于蘇軾的華夷論,尤其是他關于“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的論斷,在中日韓的學術圈論者較多,在多篇相關文獻中都有所涉及,在此不贅述。
宋代開始,傳統的朝貢體制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主義遭遇挫折,刺激了“中國”意識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興起[8]41-42。在思想史上,北宋的《中國論》和《正統論》表達了非常強烈的民族情緒。在《中國論》中,石介嚴格區分了中國與四夷的文明差異,認為君臣、禮樂、冠婚、祭禮等體現的是文明的中國,而被發文身、雕題交趾、衣毛穴居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空間上雜處、文章上混同,則“國不為中國矣”。因此,必須在空間上“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9]116-117。很顯然,華夷論并非僅僅是文人的一種思想觀念,它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政治實踐。同樣,與蘇軾華夷論一起提出的“中國之治”也開始出現在中國古代的政策主張中。
如在明朝嘉靖年間,皇帝下令征安南,戶部左侍郎唐胄毅然上疏請求罷兵。唐胄的理據是《春秋》中華夷之別的核心主張是“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他也明確使用了與蘇軾意義相同的“中國之治”,認為華夷有別,安南不配有“中國之治”,因此也沒有發兵的意義。在這里,唐胄華夷有別的思想表露無遺。他甚至還提出:“外夷分爭,中國之福。”[10]3569不單是對作為藩屬的安南,即使是明朝治下的云南也被分成“內”“外”兩部分。其中,所謂的“外”,即是對少數民族聚居且擔任地方官員(土司)地區的一種稱呼。而這些由土司掌管的“外夷衙門”也是未得“中國之治”的蠻荒之地。萬歷年間,云南白井鹽課提舉司提舉江丞默在《重建文廟碑記》中就寫道:“蓋滇南遠在天末,古唯羈縻勿絕,聽其自為聲教,未嘗以中國之治治之。”[11]即是說,云南的蠻夷之地未能有幸得到中原王朝的“中國之治”。
相較于此前,明朝時“蠻夷之地”的范圍從傳統地理位置的西南、西北、東北,擴大到了被海盜和倭寇長期盤踞的東南沿海。由于未有“中國之治”,東南沿海的海盜、倭寇之患異常嚴重,并因此使得蘇軾意義上的華夷論大行其道。嘉靖時期總管浙閩海防的朱紈就認為對倭寇、海盜等“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則震之以威,謂之化外”[12]46。秉承這一理念,朱紈對倭寇、海盜等海上蠻夷勢力的打擊異常嚴厲,對俘獲的蠻寇以剿滅斬殺為主,安撫為輔[13],因此在史書上留下“倭寇克星”之名。
到了清朝,華夷論有增無減。清初被發配到邊遠寒冷寧古塔地區的張縉彥,至死秉持著這種頑固的華夷論,并通過各種形式抒發其家國情懷,且不忘重復提醒“中國之治”不可治蠻夷。他曾經寫道:“昔者,許行為神農之言,子輿氏非之,以為不知時變也。今觀塞外之土俗,乃知古道未始不可復,神農、巢、燧,未始不可作,圣人未始不可齊民而治,中國之治斷不可施之荒遠也。”[14]52至于清朝末年,孫中山所提出的“驅除韃虜”則是這種理念在晚近中國的又一體現。
但是,隨著清末國門慢慢打開,第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放眼了解世界;同時外國人逐漸進入中國,促使中國傳統的華夷觀開始有所改變。如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多次論說西洋人不是野蠻人,更不是禽獸,西洋人和中國人一樣知曉禮義。郭實臘直接反駁了蘇軾的“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的理念,指出蘇軾所謂的“夷狄”是對“殘虐性情之民”的一種稱呼,而到訪中國的外國人“知禮行義”,怎么可以與“禽獸”比較。因此,他建議:“待人必須和顏悅色,不得暴怒驕奢,懷柔遠客,是貴國民人之規矩,是以莫若稱之為遠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國的人,或以各國之名,一毫也不差。”[15]23
事實上,到了清朝,蘇軾“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被翻譯成拉丁語和英文等多種語言在西方得以傳播,英國等發達國家因為被稱之為與野獸相提并論的蠻夷而大為惱火,郭實臘和東印度公司的胡夏米(Huyh Hamilton Lindsay)在其中都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而中國傳統的華夷之別的理念,尤其是清朝外交文書中的“夷”字,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引發了中英之間多次外交話語的沖突,最后清政府以“英國商人”取代原公文中帶有侮辱性的“夷商”二字[16]60。
2.2 專制落后與“中國之治”
傳統帝制時代中國主流的華夷論到了清代開始面臨挑戰。這種挑戰既來自對中國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也來自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而與華夷論密切相聯系的“中國之治”這個概念,其內涵與外延也相應地發生了重大改變。
最先從否定意義上用到“中國之治”這個詞的是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政治思想的第一人嚴復。在翻譯《法意》(即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時,對于孟德斯鳩認為中國一切宗教、法律、習俗與生活方式全部建立在“禮”的基礎上這一論斷,嚴復深以為然。他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往往禮、俗、法三者混而不辨,中國之治尤其如此。“中國政家不獨于禮法二者不知辨也,且舉宗教學術而混之矣。吾聞凡物之天演深者,其分殊繁,則別異哲,而淺者反是。此吾國之事,又可取為例之證者矣。”[17]992“中國數千年間,賢圣之君無論矣,其叔季,則多與此書所以論專制者合。然中國之治,舍專制又安與歸?”[17]948在當時預備立憲的背景下,受西方三權分立思想影響較深的嚴復認為,自古以來的中國政治制度禮、俗、法不分,也就是法律的制度與法律的精神不分。而這樣一種治理模式,正與孟德斯鳩書中提到的專制政體如出一轍。因此,在嚴復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在嚴復的語境中,“中國之治”就是專制制度的代名詞。
盡管在西方政治制度與思想傳入中國的近代,對“中國之治”持負面理解的不只嚴復一人,很多近代思想家都開始反思“中國之治”,但在文中直接對“中國之治”展開批判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魯迅。在1907年的文論《摩羅詩力說》中,魯迅站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一邊,對“中國之治”展開了猛烈的抨擊。他寫道:“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意異于前說。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18]63意思是,“中國之治”,講究的是不冒犯。一方面,皇帝嚴厲禁止別人觸犯他,這樣才能保護其統治千秋萬代。因此,在“中國之治”下,天才一出來,皇帝會竭盡全力地毀掉他。另一方面,人民也反感被人冒犯,他們只希望平安地活著,寧愿蜷縮著也不思進取,他們對待天才的態度也一樣,也會竭盡全力地將其毀滅掉。
總之,在嚴復那里,“中國之治”是一種禮法不分的治理體制,接近于孟德斯鳩筆下的專制;而魯迅眼中的“中國之治”,不僅代表了皇權的專制,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寬容不進取的象征。正是認為傳統文化將一切都禁錮,不思進取,魯迅才提倡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革命。
2.3 清明盛世與“中國之治”
與嚴復和魯迅同時代,“中國之治”還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含義,這就是康有為所理解的“中國之治”。1898年6月,康有為代內閣學士闊普通武所擬“請定立憲開國會折”中指出,立憲乃治強之本,今變行新政,應從根本做起。康有為把春秋改制附會為立憲,認為西方各國正是得了中國先圣的精義才得以致強。在康有為看來,立憲和議院可以統合人民的力量,使國家上下一心。中國的問題是“蓋吾國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無國會以維持之耳”。“蓋自三權鼎立之說法,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只要皇帝陛下“上師堯舜三代,外采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19]338-339。
這里的“中國之治”開始取接近“貞觀之治”“文景之治”之意,指代某一時期國家治理出現的盛世景象,體現為政治清明、經濟復蘇、文化繁榮等特點,是積貧積弱的中國在近代面對與西方國家越來越懸殊的發展差距時,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政治理想,即通過先進的制度來實現中國的富強,也就是實現“中國之治”。那時,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同時也已經意識到,實現“中國之治”僅靠學習模仿西方的制度是不夠的,還應當“防共弊”,要效法“東西政法”而不僅僅是西方制度。如清末桐城派著名作家賀濤曾提及,“日本維新之初,醉心歐化,幾經沖突,乃成為今日之日本。中國風氣初開,正所謂醉心歐化之時,乘其機而利用之,而慎防其弊,使東西政法皆得效用于我,以自成為中國之治”[20]658。
可見,康有為和賀濤等人所謂的“中國之治”是借由西方先進制度與中國自身經驗而實現的一種國家富強狀態,是一種政治上的清明盛世,是歷朝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此后,“中國之治”概念的運用主要是基于歷史的視角,偶然出現在對歷史人物或者歷史文化事件的分析中。直到十九大前夕,差不多同時出現了三篇以“中國之治”為主題的文獻,分別是張維為的《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的制度原因》、石國亮的《比較視野下的“中國之治”》和袁廷華的《中國政黨制度的世界貢獻》①這三篇文章分別載于2017年的《求是》第15期、《前線》第7期、《北京青年工作研究》第7期。。這三篇文獻都采用了與“西方之亂”或者“世界之亂”相對應的視角,論述“中國之治”體現出來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十九大召開期間以及閉幕之后,陸續出現了一些與上述三篇文獻觀點相同或者接近的期刊論文和報紙宣傳文章。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將“中國之治”的理論研究與輿論宣傳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至此,“中國之治”這一概念脫離歷史語境,開始走入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語境。
3 現實語境下“中國之治”的內涵
對“中國之治”這一概念的解讀離不開“治”和“治理”兩個關鍵詞。前已述及,“治”在漢語中與“亂”相對應而具有“安定”之意,也有“管理”之意而與西方傳入中國的“治理”這一術語相對接。而關于“治理”這一概念在中國引入、演變歷程的研究,文獻已經實在太多,在此不再贅述。在大多數的解讀中,“治理”由英文Governance翻譯而來,但正如“中國之治”的內涵與“治”“治理”既相聯系又不完全等同一樣,在英文中與“治”“治理”相對應的英文單詞也并不只有governance一個。只有對照比較這些互相關聯的單詞才能理解“中國之治”內涵的全貌。
一是governmentality,相當于治理技術、治理制度或治理方略,總之更側重于治理之術。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治”“治理”的英文文獻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21-24]。
二是governable和governability,原本有“可治理”“達成治理”之意,接近于中國歷史上與“亂”相對應的“治”的意義,是一種美好的良善的治理狀態。有文獻專門梳理governability這個概念的含義,認為它是治理主體、治理對象以及治理技術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不像傳統理解的治理概念那樣只片面強調治理主體的質量,而是被定義為整個社會系統的總體治理能力。“治”“治理”(Governability)的形成既受治理對象的影響,同時也與治理主體密切相關,更受制于治理主體、治理對象這兩個系統之間的互動。正是因為受制于這么多的因素,“治”“治理”又是一種動態的存在,同樣的治理形式面對不同的治理對象,可能治理效果并不一樣[25-26]72-84。在一篇關于南亞地方分權研究的文獻中,作者夏爾瑪(C.K.Sharma)比較了Governance、governmentality和Governability這幾個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地方一級的分權治理,不僅需要Governance(一種非等級的、橫向的、基于網絡的管理方式),還需要Governmentality(旨在塑造和引導個人或團體行動的措施或方略)和Governability(互動視角的治理體系的管理能力和質量)[27]。
從英文中使用Governance、Governmentality和Governability三個單詞的情形看,“治”“治理”既可以是技術形態,也可以是一種理念;既可以是現實的治理經驗,也可以是一種遠期的目標。再結合“治”的漢語意義與“中國之治”的歷史淵源及其在當前“復興”的時代背景,本文認為,“中國之治”這個概念的內涵,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解讀:
3.1 “中國之治”意味著中國式治理理念,即中國之智
首先,“中國之治”的定語是“中國”,歸根結底是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立足于社會主義中國這一大前提。所以,我們需要從中國本土尋找問題的答案,從中國文化中挖掘資源,從中國實踐中提煉經驗。因為,治理制度作為外在的強制性行為規范,它歸根到底是文化的產物,它的形成是本土文化長期潤物細無聲的內在演化與積淀,它的存續與運行更要依賴于特定文化潛移默化影響著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脫離本土傳統與文化語境的制度終究是無源之水與無本之木,即使被硬造出來了也無法運轉。中國的國家治理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依據本國國情,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成功地解決了近當代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誠如習近平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斗基礎上的,是由我們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國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接力探索取得的。”[28]77中國的成功向世人說明,一個國家若想突破發展困境,打破發展瓶頸,必須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照搬他國制度未必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制度嫁接也可能引起“排異反應”。這是“中國之治”給世界上所有面臨發展困境的國家提供的“中國智慧”。
其次,“中國之治”的背后是以人民整體利益為歸依的制度優勢,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堅守。“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29]1與許多西方國家的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對群眾工作的重視并不是為了吸引選票,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信仰使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調整民生工作的力度和深度,中國政府在掃盲、疾控、扶貧等諸多民生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的十九大將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直面人民群眾溫飽問題解決后呼喚精神、價值等更高層次追求的現實,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群眾心聲的敏銳觀察,再一次有力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把解決群眾困難當作執政黨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爭取群眾支持,同群眾打成一片,是中國共產黨能夠贏得民心、保持長期執政的重要“法寶”,也是“中國之治”的重要“訣竅”。對人民,依靠而不是收買,服務而不是利用,是“中國之治”展示給世人的另一個“智慧”。
最后,兼收并蓄、開放包容是“中國之治”提供給世界的又一個“智慧成果”。“中國之治”雖然是中國本位,但并非與世隔絕。“中國之治”不是閉門造車,也不是孤芳自賞。“中國之治”既是立足中國也面向世界;既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新中國成立伊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就在重視吸收蘇聯等社會主義制度優點的同時,努力擺脫其弊端,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指出:“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30]64大膽吸收和借鑒世界其他國家在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有益經驗,使之與中國的制度、文化相融合,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快速進步,提高民生福祉,給人民群眾更多獲得感和幸福感,是“中國”何以“治”的重要原因。“中國之治”是“兼容之治”“開放之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28]258伴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持續深化,中國也將參與更多的全球事務,為解決人類發展問題提供思路。一些西方學者就認為:“如果中國崛起為世界最強國,她就會試圖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中國未來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將可與20世紀的美國媲美,甚至有可能會超越美國。”[31]13“全球秩序的未來可能不再在西方的統治下,因為西方秩序通常被視為混亂、無序與危險的。”[32]6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問題頻發,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社會危機,全球風險因素提高。在這種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之治”不僅讓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煥發了更大的生機,也增加了全球的穩定性,給人類制度和文明的演進提供了另一種可能[33]。
總之,從理念的層面看,“中國之治”是中國特色的,又是人民本位的,同時它內在地蘊含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不僅強調中國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也提倡為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期盼發展的人民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既讓中國更好地利用世界的機遇,又讓世界更好地分享中國的機遇,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之治”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動的當下,正向世界釋放一個積極的信號,展示著中國的責任與擔當。
3.2 “中國之治”意味著中國式治理方略,即中國之制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中國之治”不僅是一種治國理念,更意味著中國式治理制度體系、中國式治理方略。簡言之,即中國之制。關于“中國之治”的制度層面,《決定》第一次將“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多方面的顯著優勢”概括為13點,涵蓋了經濟、政治、行政、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外交、黨的領導等諸多領域的全方位優勢和疊加優勢。有學者將中國的制度優勢歸納為“三合”,即“中國之治”具有合實際、合規律、合目的的制度邏輯。合實際,是指中國制度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國情實際和時代實際;合規律,是指中國制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制度發展規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充分發揮優勢和潛力;合目的,是指中國制度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34]。
在中國的制度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就是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28]16。《決定》創造性地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制度”,探索性地用制度保障和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通過構建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將黨的理想信念宗旨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讓黨的理想信念看得見、摸得著、做得到。
此外,在中國的制度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相并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決定》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這一概念,改變了以往在黨的文件中出現的“行政管理體制”或“行政體制”“行政體制改革”概念。行政體制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創造性與活力的基本保證,承擔著按照黨和國家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與美國模式相比,也有人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行政推進模式,它更能有效地應對風險、收入分配不公和環境挑戰[35],更好解答“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關系問題,從而能夠有效兼顧制度優勢與國家治理績效。
在人類開始步入智能化時代的今天,治理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革,國家治理的對象復雜多變,治理的內容豐富多元,“中國之治”既要妥善解決中國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要積極應對全球治理的共同難題,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世界安全與地區沖突風險有增無減、全球金融風險與債務危機困擾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還要未雨綢繆人工智能時代可能帶來的風險與挑戰。為了有效地以“中國之治”應對“時代之變”[36],中國正在進入一個“頂層設計”的治理時代[37],力圖通過頂層設計使我們的治理手段與治理方式更加精細化、智能化、現代化,以期早日建立起有機的、協調的、動態的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3.3 “中國之治”意味著中國式治理愿景,即中國之志
“中國之治”不僅是一種現實的制度存在,更是一種美好的治理愿景。“中國之治”的愿景首先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戰略任務”和“總體目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說法首次出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隨著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升到戰略層面,構成了總體目標[38]。亨廷頓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它涉及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里的變革。”[39]25可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是多個領域協同變革的過程,需要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以及對應的治理行動,兩者合力是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打破了多個既有制度的條條框框,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治理行動上都將中國向現代化方向推進。
“中國之治”的愿景還是《決定》第一次提出來的“三步走”——第一步,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第二步,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當然,“中國之治”的愿景不限于治理層面,它也是中國共產黨現階段奮斗的愿景,這就是“兩個十五年”的階段性目標。第一階段是2020—2035年,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繼續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是2035—2050年,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繼續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理,“中國之治”的愿景也不限于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它同時跟中國夢是一體的,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核心目標即“兩個一百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并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真正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這正是歷代知識分子夢想中的清明盛世,是中國人民理想中的“中國之治”。
綜上,從理論層面,“中國之治”可進行多種解讀。它可以是一種理念,體現的是“中國之治”的人民本位、中國特色與世界價值;它也可以是一種制度體系,體現的是以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為核心的治理之術與中國式治理方略;它還可以是一種發展愿景,體現的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追求的天下大治和清明盛世。它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探索出來的中國方案,也是中國奉獻給世界的中國智慧;它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學中的“民治、民有、民享”理念,實踐的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來的人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愿景。
4 結論與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華大地發生了巨變,世界格局更是出現了深刻變化。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政治上舉足輕重,文化不斷推陳出新。中國的持續繁榮與穩定有序,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衰退、政治動蕩形成了鮮明對比。最近幾年,民粹主義運動在西方發達國家愈演愈烈,而英國脫歐、法國國民陣線興起與特朗普上臺被認為是這一現象的典型后果。經濟上,近30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多數人的實際收入下降與普遍的收入不均,正在侵蝕著戰后持續的經濟增長所帶來西方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之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強勢“復蘇”的,它是對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近100年來歷史經驗總結的產物,是基于中國的今天與中國的昨天的縱向比較,更是基于今天的中國與今天的世界的橫向比較。囿于“中國之治”這一概念的特殊歷史淵源與現實語境,我們在使用與宣傳“中國之治”時既要避免落入傳統意義的窠臼,也不能忽略它與歷史的關聯;既要關照“治理”概念產生的西方語境,更要體現“中國之治”的中國身份。具體地,對這一概念的解讀與運用,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分清“中國之治”的應然形態與實然形態。作為治理理念與治理愿景的“中國之治”,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應然的治理哲學;而作為治理方略與治理制度的“中國之治”,體現為一種實然存在的制度現實。“中國之治”可能是一種對過去40年中國成功經驗的總結,也可能是對未來中國清明盛世的一種預期。因此,在使用“中國之治”時就必須區分它究竟是回顧過去的,還是面向未來的;是已然存在的事實,還是一種美好的期許。就目前而言,國家治理現代化仍在建設過程中,盡管中國的治理績效已經為世人所矚目,但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仍然任重而道遠。如果我們誤將作為愿景的“中國之治”當作既成事實,就有可能滿足于目前的成績而止步不前,那結果可能會使當前的“中國之治”原地踏步,同時使預想中的“中國之治”也遙遙無期。
二是處理好作為工具的“中國之治”與作為目的的“中國之治”的關系。在具體形態上,“中國之治”可以體現為一系列政治、經濟、法律制度體系,也可以體現為一整套治國理政的文化理念與價值文化。前者是作為工具的“中國之治”,是治理之術;后者是作為目的的“中國之治”,是治國之本。很顯然,作為工具的“中國之治”并非一成不變的,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和治國理政任務的變化,這些具體的制度體系與治理策略是可以不斷發生改變的,是需要逐漸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現階段,盡管相對于西方國家的治理亂象,中國這邊風景獨好,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治理體系已經十全十美,事實上,在一些具體的環節,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多成功的做法可供我們借鑒。而對這些治理之術的拿來主義,并不會否定或者損害我們作為治國之本的“中國之治”。只是我們在借鑒時,需要關注具體制度與根本政治制度、制度外在形態與制度內在哲學之間的區別,始終堅持一切工具的“中國之治”最終都要服務與服從作為目的的“中國之治”。
三是注意將“中國之治”的中國特色與世界價值相結合。毋庸置疑,“中國之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即中國特色,它是扎根于中華大地上的治理哲學與治理方略,符合中國國情,是“中國之治”的本質特征。但同時,“中國之治”也是中國奉獻給世界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和中國理念的總和,已經或者正在為解決全球治理難題提供一個又一個中國方案,因此“中國之治”又必然地區別于歷史上狹隘的華夷之辨,具有其普遍適用的世界價值。而基于歷史傳統、政治制度與發展程度的不同,在國家治理方面的中國特色與世界價值必然有不同步的地方,有時甚至會有矛盾沖突的地方,因此,正確認識與處理“中國之治”這一概念體現出來的中國特色與世界價值,就顯得尤為必要。在使用與傳播“中國之治”概念時不能為了中國特色而中國特色,不能為了突出“中國之治”的中國身份而刻意淡化或者否定“中國之治”蘊含的世界價值。在何種程度上強調中國特色,在何種意義上倡導其中國身份,這需要擁有足夠的理性與智慧。只有把握好了這個度,才能真正做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國之治”才能既成就中國,也造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