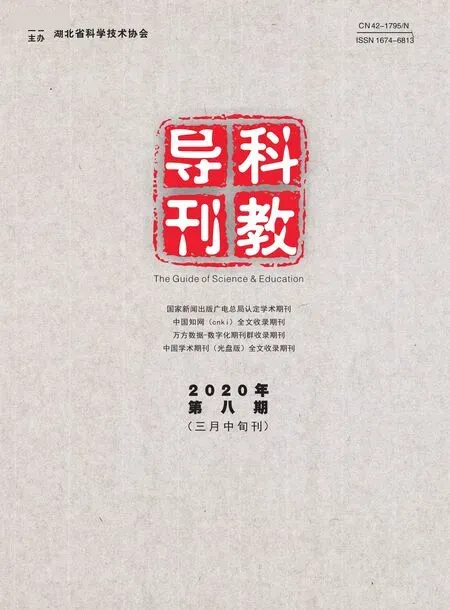“i+1”輸入假說對應用型本科院校大學英語分級模式聽力教學的啟示
鄧亞丹 侯檢菊
(湘南學院外國語學院 湖南·郴州 423000)
0 引言
《大學英語課程要求》頒布以來,全國高校紛紛探討和實踐各種適合自身情況的英語教學方法和模式,其中大學英語分級教學,秉承分類指導、因材施教的原則,頗受到高校教師的關注,并成為大學英語教學的理想教學組織形式之一。湘南學院從2013級本科生開始,全面進行了英語分級教學,取得了階段性的成績和效果,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如分級教材使用管理問題,C級學生學習消極怠懈等問題。筆者在此期間一直承擔分級教學的工作,對分級教學也逐漸有了一些心得和體會,尤其是聽力分級教學。本文運用克拉申i+1輸入理論,分析大學英語聽力分級教學中現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個人想法和見解,借此對其他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和分級教學的推動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1 克拉申“i+1”輸入假說
1.1 “i+1”輸入假說的主要內容
美國語言教育家克拉申(Stephen D.Krashen)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二語習得提出了一系列假說。1985年在其著作《輸入假說:理論與啟示》中正式歸納出習得與學習假說、自然順序假說、監控假說、輸入假說、情感過濾假說等五個系列假說,總稱為輸入假說理論。克拉申的二語習得理論是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中影響最廣,效果最好的的理論之一。克拉申的輸入假說理論,即“i+1”輸入理論,“i”代表習得者現有的語言水平,“1” 則表示略高于習得者現有水平的語料。根據克拉申的觀點,只要習得者能理解輸入,而他又能達到一定量,就自動地提供了這種輸入。如果語言輸入遠遠超出學習者的現有水平即“i+2” 或者低于現有水平“i+0”或“i+1”,學習者就不可能獲得理想的學習效果。學習材料太難或者太易都引不起學生的興趣,達不到好的效果。
1.2 克拉申“i+1”輸入假說的特點
輸入是可理解的。語言材料必須是可理解性的,能被學習者所理解的。如果語言材料太難或>i+1甚至更高,就將超出學習者理解能力,那這個學習就是無效的。
足夠的輸入的量。語言輸入必須是大量的。要習得新的語言結構,僅僅靠幾道練習,幾篇短文閱讀是不夠的,它需要外語學習者的輸入量達到一定程度時才能奏效。
既有趣又有關。語料越有趣、越有關聯,學習者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就越高,這樣就能在不知不覺中習得語言。
2 大學英語聽力教學存在的問題
在英語學習中,聽力位于聽、說、讀、寫四項基技能的首位,由此可見聽力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但也是許多外語學習者感到難以提高的一部分。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都忽視了聽力的重要性,最終導致學生聽力水平得不到提高。
(1)以總成績為標準的分級模式難以保證聽力輸入的可理解性。學生的聽力語料輸入主要來自課堂的教師話語、聽力課以及課外自主學習。當前,很多高校采取了大學英語分級教學模式,即按照新生入學分級考試和高考成績的總分為原則編排為A、B、C三個等級班級,這種分級模式的編排也受到國內諸多學者的質疑。比如來自邊遠地區的學生高考取得的成績都不錯,但聽力和閱讀技能水平呈兩極化,差異較大,他們很少接受專項聽力訓練,所以聽力能力相對薄弱。對比之下,來自沿海地區的發達城市的學生普遍聽力技能明顯略高于閱讀技能。一些國內學者的研究表明,相當部分的學生聽力和閱讀技能發展不均衡,按總成績為標準的分級模式,忽略了這些學生對不同技能的學習需求的差異。目前,我們學校使用的聽力教材均采用的是《新視野大學英語》聽說教程,并沒有根據學生聽說能力的差異因材施教。尤其對C級班的學生,《新視野大學英語》聽說教程二、三往往超過其認知水平和理解能力,即>“i+1”甚至達到“i+2”,最終導致學生對聽力產生抵觸情緒、情感負面、無法實現有效地語言習得。
(2)語言的輸入量不夠。目前,大學英語課程正普遍面臨壓縮課時的危機,大學英語的地位正在邊緣化。以筆者所在的高校為例,英語作為高等教育必修基礎課程,課時量從228學時(四個學期)逐步削減至120學時(兩個學期),其中聽力課的安排每單元僅僅為兩個課時,導致教師的教學主要集中在課程的精讀和寫作上,從而弱化了聽力。這勢必會減少學生可獲得的語言輸入量。另外,聽力教學模式較單一、缺乏多元化,一般教師上聽力課,不外乎一錄音、一聽力課本,教學模式即是“聽錄音、做題、對答案”,單一枯燥,激發不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這種純聽力課的形式讓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忽略了學生聽力技能和文化素養的培養。學生課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很難做到每天進行一定量的語言輸入,最終導致學生能看懂聽不懂,聽力技能得不到提升。
3 克拉申i+1輸入假說與大學英語聽力分級教學
(1)創建“聽說技能”的分級教學模式。因為各地區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的差異以及個體語言學習差異都可能導致學生的聽說和讀寫技能發展不同步,不均衡,顯然,唯總分為標準的分級教學模式并不能將學生按照其聽力能力的強弱區分開來。針對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按技能分級”的教學模式。即根據學生聽說、讀寫技能的強弱將學生分別編入相應的“聽說”和“讀寫”班級。按技能差異循序漸進,逐步提高各項語言技能。筆者所在學校按照英語分級模式把大學英語部分成A、B、C三個教研室,每個教研室都承擔了各個等級的教學任務,這種劃分其實與分級模式之前的傳統模式并無二致,并沒有體現分級理念與實踐的統一。一些學者也建議,根據技能差異把大學英語公共部分為“聽說”和“讀寫”兩個教研室,每教研室分別負責相應的模塊。筆者認為這種模式更能體現分級理念與實踐的統一,能讓每位教師專注某一項技能的教學,提升教學水平。同時,學生也能在與其技能相對應的教學班,能在他所理解的“i+1”的語言環境下進行高效地學習。此外,分級后的班級也能根據學生的技能提升情況采取升、降的滾動管理機制,允許學生在不同級別之間合理滾動。每學期或學年結束時對學生所學知識進行考核,考核通過的學生可根據自己需求升到不同技能級別學習。同時,考核未通過的學生會自動降入較低級別。這種“按聽說技能”的分級教學模式符合學生實際,也符合當代大學英語教學的發展和潮流。
(2)建立聽力分級材料庫,增強課外輸入,加大聽力語料的輸入量。鑒于當前大學英語課程課時的壓縮和傳統單一的聽力教學模式,僅靠有限的課內聽力肯定提高不了學生的聽力能力。在如今網絡資訊信息發達的時代,高校英語教師更應該充分地利用多媒體和網絡技術,采用新技術,結合課外輸入,從互聯網、視聽APP等現代工具上篩選語言地道、內容豐富的視聽材料,并按照其難易程度進行分級,建立聽力語料庫,供學生課內與課外學習,同時也要注重及時更新語料內容。筆者學校目前擁有網絡信息中心、網絡自主學習中心,外語角活動室,每天晚上和周末都專門安排大學英語老師在英語自主學習室值班,輔導答疑,要求大一所有學生自主學習時間的每期不少于16學時。課外的聽力輸入主要以泛聽為主,聽力形式可以多樣化,在保證內容豐富性和趣味性的同時,難度應盡量控制在“i+1”水平,確保語言材料的可理解性,讓學生在輕松的語言情境中習得語言。例如,我們學校的網絡自主學習平臺滿足了各個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有簡單的基礎語法知識,也有國外權威媒體的報道和刊物,形式多樣化,此外,學習也開展形式多樣的英語口語活動,比如外語節、英文歌唱比賽、電影配音等,這些活動能有效培養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營造輕松的學習氛圍,更能幫助學生做有效地聽力輸入,自然而然的提升了學生英語習得能力。
4 結語
綜上所述,盡管大學英語分級教學方面現階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效果,但因學生的聽力和閱讀技能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勢必會影響到學生對“i+1”語料的可理解性輸入。根據克拉申“i+1”輸入理論的特征,我們有必要創建新的聽力分級教學模式,建立聽力分級材料庫,增強課外輸入,加大聽力語料的輸入量,同時創設低情感過濾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最大限度地習得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