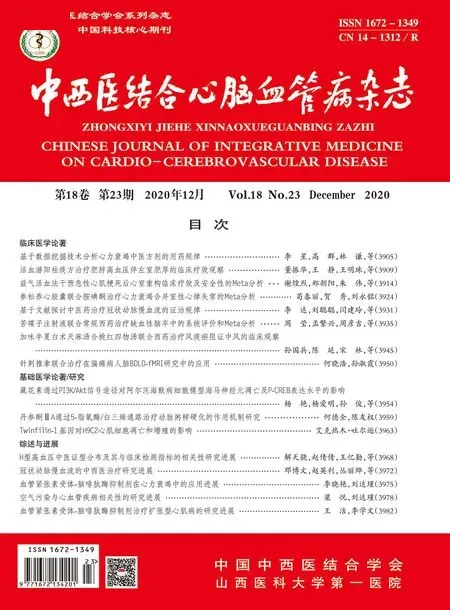H型高血壓中醫證型分布及其與臨床檢測指標的相關性研究進展
解天驍,趙倩倩,王憶勤,李媛媛,燕海霞
H型高血壓即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hyperhomocysteinemia,HHcy)的原發性高血壓。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是一種含硫的非必需氨基酸,是蛋氨酸代謝的中間產物,且其結構與半胱氨酸相似。H型高血壓有著極大的風險,是引起腦卒中、缺血性心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中醫學具有全面調節機體功能的特點,在改善癥狀、平穩降壓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近年來,對H型高血壓的中醫證治研究越來越深入。本研究對近年來H型高血壓的辨證分型及其與臨床檢測指標的相關性研究進展進行概述,以期為H型高血壓的中醫臨床診治提供依據。
1 H型高血壓的概念及發病機制
1.1 H型高血壓的概念 H型高血壓即伴有HHcy的原發性高血壓。正常情況下,人體空腹血漿Hcy水平為0~15 μmol/L,Hcy水平>15 μmol/L時,稱之為HHcy。當HHcy聯合原發性高血壓時,可被定義為“H型高血壓”[1]。HHcy與高血壓協同作用引起血管疾病的風險比達到1∶1.3,H型高血壓病人心腦血管意外發生率超出單純高血壓病人5倍。目前我國高血壓病人為1.6億人[2],其中有約75%伴有HHcy。調查報告顯示,腦血管病是我國居民首位死亡原因。相關研究顯示,血漿Hcy與原發性高血壓、免疫性疾病、2 型糖尿病等多種疾病密切相關[3]。
1.2 H型高血壓的發病機制 Hcy是人體內蛋氨酸代謝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含硫氨基酸,是腺苷蛋氨酸酶水解后的反應產物,由Devgneaud于1932年發現,人體內70%~80%的Hcy以二硫鍵形式結合于血漿蛋白,20%~30%自身結合成二聚體Hcy,還有1%的Hcy以自由形式存在于機體循環中。血漿中游離Hcy和結合Hcy的總和稱為總Hcy,即通常所說的Hcy血漿濃度。研究表明,Hcy與血管疾病有緊密聯系,是動脈粥樣硬化的一個危險因子,其與高血壓在增加心腦血管病發生率中具有協同作用[4-5]。
有研究表明,血清中Hcy水平升高與高血壓的發病密切相關。Hcy是一種含硫氨基酸,屬于蛋氨酸和半胱氨酸代謝循環中的重要中間產物,主要通過再甲基化途徑、甲基化的替代途徑、轉硫化途徑、Hcy直接釋放到細胞外液、Hcy在Fe3+或Ca2+等重金屬離子的催化下自身氧化形成等途徑在人體中代謝產生[6]。HHcy引起高血壓致病機制尚未十分明確,可能與血漿Hcy在血管內皮細胞內過分蓄積時直接或間接導致血管內皮損傷有關。Hcy可以促進內皮細胞合成內皮素,還可能通過產生一系列活性氧中間產物抑制一氧化氮(NO)的合成并促進其降解,造成血中內皮素與NO水平比例失衡,使血管舒張反應異常,擴血管物質減少,縮血管物質增加,總外周血管阻力增加[7]。HHcy的原因有以下幾種[8-9]:①遺傳因素,β胱硫醚合成酶、γ胱硫醚酶和N5,N10-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N5,N10-MTHFRC)的基因突變及內皮一氧化氮合酶(G894T)基因突變。先天遺傳因素導致編碼甲烯四氫葉酸還原酶、胱硫醚縮合酶、甲硫氨酸合成酶的基因缺陷,從而造成相應酶缺乏或活性降低,Hcy轉化環節受阻形成蓄積。②營養相關因素,吸煙、大量飲酒和咖啡以及葉酸和維生素B攝入過少,都會提高H型高血壓的發病概率。③性別與年齡,研究提示男性血漿Hcy濃度高于女性,女性絕經后高于絕經前,可能與雌激素影響代謝有關;隨著年齡增大,血漿Hcy濃度升高,可能與一些重要酶生成減少及活性降低有關。④疾病,腎功能不全是影響Hcy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
2 H型高血壓的中醫病因病機研究
中醫學雖無H型高血壓的病名,但根據其臨床表現可屬于中醫學“眩暈”“中風”“頭痛”等范疇。關于中風,《醫學綱目·論中風》認為“中風皆因脈道不利,血氣閉塞也”。《丹溪心法·中風》則認為“肥人中者,以其氣盛于外而欠于內也”。近代醫家張山雷等繼承前人經驗,并結合西醫學知識來探討中風發病機制,認為中風發生主要在于肝陽化風,氣血并逆,直沖犯腦[10]。眩暈的病因較多,病性為虛實兩端,然屬虛者居多,臟腑虧虛、命門火衰發為眩暈[11]。《素問·至真要大論》認為“諸風掉眩,皆屬于肝”。《靈樞·衛氣》認為“上虛則眩”。張子和《儒門事親·頭風眩》指出:“夫婦人頭風眩運,登車乘船,亦眩暈眼澀,皆胸中有宿痰之使然也”。《丹溪心法·頭眩》指出:“頭眩,痰加氣虛并火,治痰為主,夾補氣藥及降火藥。無痰則不作眩,痰因風動,又有濕痰者,有火痰者”。
從H型高血壓本身來看,中醫學認為先天稟賦不足和后天精微物質缺乏是本病的主要病因,肝、脾、腎三臟在其形成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肝主疏泄,喜條達,若氣郁化火,肝腎陰虛,肝陽偏亢,上擾頭目;腎為先天之本,藏精生髓,若先天不足,腎精虧損,不能生髓,而腦為髓之海,髓海不足;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虛則氣血生化乏源,津液代謝障礙,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H型高血壓的發生[12]。可見,H型高血壓中醫病因多與肝、脾、腎虧虛有關,與眩暈、頭痛、中風的病因相吻合。H型高血壓病機多為本虛標實、虛實夾雜,且病位以肝、脾、腎為主,病理變化為肝、腎陰陽氣血失調,導致風、火、痰、瘀;其發病機制為肝陽上亢和或肝腎陰虛,H型高血壓在高血壓病的基礎上具有自身特點。唐娜娜等[13]將200例H型高血壓病人分為腎虛血瘀、痰濕壅盛、陰虛陽亢、肝火上炎、氣血虧虛及肝腎陰虛等證型,測定各證型血漿Hcy水平,認為腎虛血瘀是H型高血壓最具危害的證型。
3 H型高血壓病人中醫證型分布特征
3.1 H型高血壓病人的中醫體質特征 現代中醫學多遵循9種基本中醫體質類型的分類方法,分為平和質、氣虛質、陰虛質、陽虛質、濕熱質、痰濕質、氣郁質、瘀血質、特稟質。王燕麗等[14]對222例H型高血壓病人(其中男100例,女122例)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體質類型的分布中前4位分別是濕熱質(31.98%)、痰濕質(20.72%)、血瘀質(15.76%)和氣虛質(12.16%);氣郁質、陰虛質、陽虛質居中;最少的為平和質(1.30%)。趙榮[15]研究發現,214例老年H型高血壓病人中醫體質主要以痰濕質為主(30.84%),其次為瘀血質(26.17%)和氣虛質(27.10%)。
3.2 H型高血壓病人中醫辨證分型及其分布特征 H型高血壓的發病多與風、痰、火、瘀、虛相關。根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中藥新藥治療高血壓病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高血壓病可分為痰濕壅盛證、肝火亢盛證、陰虛陽亢證和陰陽兩虛證4型,很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H型高血壓的中醫辨證及其分布特征進行了深入研究。
帕力旦·吾布爾等[16]對144例H型高血壓病人中醫證型進行分析,各證型分布情況為:痰濕壅盛證86例(59.72%)、肝火亢盛證25例(17.36%)、陰虛陽亢證19例(13.19%)、陰陽兩虛證14例(9.72%)。張雪峰等[17]觀察了226例H型高血壓病人的中醫證型分布情況,發現痰濕壅盛證72例(31.86%)、陰陽兩虛證70例(30.97%)、肝火亢盛證50例(22.12%)、陰虛陽亢證28例(12.39%)及其他證型6例(2.65%)。張騫等[18]研究發現70例H型高血壓病人中痰濁上蒙證最多,占40%,且以男性為主要群體。邢齊樹等[19]研究了120例H型高血壓病人的中醫證型分布,發現陰虛陽亢型與肝火亢盛型病人居多;痰濕壅盛型病人Hcy濃度最高。陳暉等[20]對300例H型高血壓病人進行中醫辨證分類,發現痰濕壅盛型的占比較高(49.7%),陰陽兩虛型最少(5.0%)。以上研究均提示痰濕壅盛證是H型高血壓的最重要病因。
年齡及性別可能影響H型高血壓的辨證分型。閆翠等[21]對144例H型高血壓病人進行中醫辨證分型,發現年齡為7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多以陰虛陽亢型為主,年齡60~70歲病人以肝火亢盛型為主;痰濕壅盛證H型高血壓病人男性所占百分比高于肝火亢盛證、陰虛陽亢證(P<0.05)。
閆翠等[22]研究發現H型高血壓病人陰陽兩虛證比例(29.2%)和肝火亢盛證比例(22.2%)均高于非H型高血壓病人;H型高血壓病人陰虛陽亢證比例低于非H型高血壓病人。李眴澤[23]觀察了205例腦卒中合并H型高血壓病人的中醫證型分布情況,發現風痰阻絡證114例(55.6%)、風火上擾證41例(20.0%)、氣虛血瘀證21例(10.2%)、陰虛風動證17例(8.2%)、痰熱腑實證12例(5.9%)。如前所述,風邪是H型高血壓的病因之一,風痰蒙心神,閉清竅;風火則擾心神,并引發頭痛,因此,臨床病人出現偏癱、神識昏蒙、語言蹇澀或不語等癥狀時,辨證應考慮風這一因素。
4 H型高血壓中醫證型與臨床檢測指標的相關性
4.1 H型高血壓證型與血液指標的相關性研究
4.1.1 證型與Hcy的相關性研究 Hcy作為診斷H型高血壓的重要指標,其與中醫證型的相關性應予以關注。H型高血壓最常見的中醫病機為痰和瘀,常見證型有4種。朱志揚等[24]檢測了1 795例H型高血壓各證型病人的血Hcy,發現痰濕壅盛型H型高血壓病人Hcy濃度最高,為22.07 μmol/L,肝火亢盛型H型高血壓病人Hcy濃度較低,為17.08 μmol/L,提示Hcy的升高可能與“痰”有較為密切的關系,痰濕壅盛型為H型高血壓的高危證型之一,其發生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性較高。
4.1.2 證型與血脂的相關性研究 曾潔[25]研究了255例H型高血壓痰瘀互結型和非痰瘀互結型病人血液Hcy與血脂指標的相關性,研究結果提示H型高血壓痰瘀互結證主要與血脂代謝異常相關,尤其表現在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水平改變,不同Hcy水平與總膽固醇(TC)、三酰甘油(TG)、24 h血壓、脈壓有關。何佳等[26]研究發現H型高血壓痰瘀互結證病人的血脂指標TC、LDL-C水平均高于非痰瘀互結證病人;HHcy的H型高血壓(Hcy>25 μmol/L)病人多合并代謝綜合征,以血脂代謝紊亂最為明顯。束秉鈞等[27]研究發現H型高血壓病人中醫證型與血脂水平具有相關性,TC水平與痰濕壅盛密切相關,TC可作為H型高血壓痰濕壅盛證的辨證依據之一。痰濕壅盛可能影響脂質代謝以及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提高動脈硬化的發生率。
4.1.3 證型與超敏C反應蛋白(hs-CRP)的相關性研究 hs-CRP是預測動脈粥樣硬化的重要指標,hs-CRP直接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等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其增高是心腦血管事件重要的預示及危險因子。劉莉等[28]研究發現H型高血壓病人hs-CRP明顯高于非H型高血壓病人;H型高血壓各證型病人間hs-CRP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陰虛陽亢型H型高血壓的hs-CRP更高,達到平均8.72 mg/L,提示hs-CRP可作為H型高血壓中醫辨證的客觀指標。孫建春[29]觀察了80例H型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的hs-CRP水平,結果發現不同證型病人血漿中hs-CRP表達有差異,陰陽兩虛證>陰虛陽亢證>痰濕壅盛證>肝火亢盛證(P<0.05)。
4.1.4 證型與血小板參數的相關性研究 H型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在凝血功能及血小板參數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張云枝等[30]檢測了160例H型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的凝血酶原時間(prothrombin time, T)及血小板參數(thrombocyte parameters,TP),發現腎虛血瘀證病人的PT和TP均高于其他證型,提示血瘀證對人體凝血功能有影響。
4.2 H型高血壓證型與動脈硬化相關指標的相關性研究 頸動脈超聲指標主要包括頸動脈內中膜厚度(intima media thickness,IMT)、頸動脈斑塊、斑塊個數等指標。杜文婷等[31]比較了90例H型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的頸動脈超聲指標,發現肝火亢盛型H型高血壓病人的頸動脈斑塊更大,平均大小為6.97 mm;陰虛陽亢型的斑塊數量最多,平均1.96個;從斑塊分級情況來看,無論何種證型,都為3級斑塊數量最多,其中痰濕壅盛型H型高血壓的3級斑塊最多,提示H型高血壓證型與頸動脈超聲指標有相關性。張雅文[32]研究發現,H型高血壓痰瘀互結證病人不同Hcy水平者LDL-C、TG、血清尿酸(UA)及頸動脈斑塊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IMT也是頸動脈超聲的重要指標之一,IMT增厚提高了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病率,可反映動脈粥樣硬化程度。孫建春[29]比較了80例H型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的IMT指標,發現痰濕壅盛型病人IMT明顯高于其他證型病人,平均為1.45 mm。
動態動脈硬化指數(ambulatory arterial stiffness index,AASI)是一種檢測動脈硬化的指標,反映整體動脈彈性功能。董陽[33]檢測了120例老年人H型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的AASI,發現陰陽兩虛型病人的AASI明顯高于其他各型,說明陰陽兩虛型H型高血壓病人血管彈性較差,且患冠心病、中風等的風險明顯高于其他證型。
4.3 H型高血壓證型與血壓指標相關性研究 血壓升高雖然是各型高血壓的基本特征,但高血壓不同證型病人的血壓指標仍有不同。常用的血壓指標包括24 h平均舒張壓、24 h平均收縮壓,最高收縮壓及舒張壓、最低收縮壓及舒張壓等。何一婷[34]研究發現痰濕壅盛型H型高血壓病人的24 h平均收縮壓、最高收縮壓、收縮壓變異系數均高于其他證型;而肝火亢盛型、肝郁型H型高血壓的24 h平均舒張壓均高于其他證型;H型高血壓病人的血壓晝夜節律變化與Hcy水平相關,提示Hcy濃度可影響晝夜血壓變化幅度,隨著Hcy的升高,晝夜血壓呈現上升趨勢。
5 小結與展望
H型高血壓中醫證型的分布與非H型高血壓有所不同,主要為痰濕壅盛證和陰虛陽亢證。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研究者對于H型高血壓的證型是痰濕為主亦或是陰虛證為主仍存在爭議,且辨證標準尚未統一,缺乏客觀化指標的支持。H型高血壓中醫證型與臨床檢測指標的相關性研究顯示,證型與Hcy水平、血脂、hs-CRP、頸動脈IMT、AASI、血壓等指標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對證型與臨床檢測指標相關性的機制闡釋不足。
下一步應開展H型高血壓辨證規范化、標準化研究。此外,還需要擴大研究樣本量,進行規范研究設計,應用更合適的統計方法,結合臨床檢測指標,開展H型高血壓的中醫證型客觀化、標準化研究,為H型高血壓中醫證治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