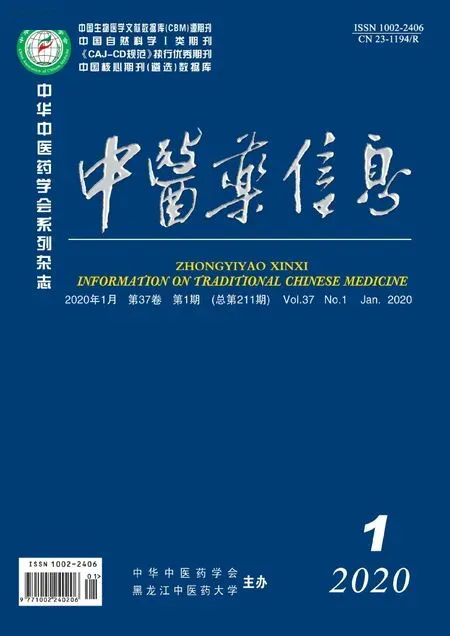從調神止痛理論探討內關穴治療痛癥
吳召敏,顧一煌
(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46)
疼痛是不愉快的主觀情感體驗感受,呈現出一系列復雜的生理心理活動,可見于各種疾病中,該癥狀在臨床上稱為痛癥。關于痛癥,《內經》在諸多篇章中均有論述,導致疼痛的原因不外六淫侵襲,七情所傷,情志不暢,臟腑機能紊亂,其病機是經絡阻滯不通,不通致痛[1]。“不通”是其致病原因,然“諸痛癢瘡,皆屬于心”,痛的感覺在于心,故其病機演變關鍵在于心神,心神內動是其根本原因,無論何種病因導致疼痛,其病理機制只有一個,即心神在痛癥病機中的決定因素。針刺治痛主要有以下三種方法:一是從病因入手,直接解除導致使氣血運行不暢的原發因素;二是從病機入手,通過調節經絡、氣血的運行,使經絡氣血恢復正常狀態;三是從疼痛本質入手,通過移神寧心,從源頭解除疼痛的感覺[2]。
1 調神止痛
1.1 理論依據
1.1.1 血、脈、心、神一體論
《內經》對于疼痛作了詳細的記載,其中《舉痛論》是痛癥的專題論著,認為產生疼痛的機制主要為“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明確指出了疼痛發生的部位在脈,即血脈,而“心主身之血脈”,滋養人體的氣血,是經心的搏動輸送至全身,內養臟腑,外濡四肢百骸,保證了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3]。心主生血及血液在脈道中正常循行,血液充盈,脈道滑利,心氣充足,保證了整個血液循環系統的完整性,正如《靈樞·營衛生會》所說“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而“心主藏神”,神掌控著人體的生理及心理活動,總領和主導著人體意識思維活動,“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血是精神活動的物質保障,神正常功能的發揮有賴于血液的滋養,心主神明是“通”功能的體現,是心主血脈的功能滋養整個臟腑體系及四肢百骸,從而發揮以氣血為物質基礎的神的功能,故血—脈—心—神形成了完整的生命循環體系[4]。
1.1.2 經絡、血脈、心、臟腑相關論
《靈樞·本臟》曰:“經絡者,所以行氣血而營陰陽,濡筋骨而利機關”,經絡是氣血運行的通路,通過經絡這一通路系統傳遞各種信號,從而內聯臟腑,外絡形體官竅,溝通人的整體,是人體結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衛、氣、營、血是通過經絡運行全身,營氣為水谷精微化生的精華,進入經脈內生成血液,在經脈中流行不已,發揮其營養作用;衛氣是水谷精微的懾悍滑利物質,分布于經脈之外而司溫養臟腑,固護肌表,抗御外邪。營衛相隨,循環無端,周而復始。營衛充盛,則經脈具有正常的功能活動,人體健康;反之則經脈功能失常,人體發病。心主血脈,在心氣的自然搏動下將血液輸注到全身,而經絡是氣血運行的通道,可見經絡是心的自然延伸。除了氣血,心的精氣亦通過心神的傳感由經絡輸送到全身,《內經》說道:“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針刺傷及脈道,影響氣血的運行,則心神亦受影響,故經絡循行氣血流注所到之處可直接影響心神。在心—經絡這個密閉相通的系統中,經絡、血液及心神相互影響。
經絡臟腑相關理論是針灸的重要部分,經絡通過其特殊結構把五臟六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確保人體是完整一體的,《靈樞·海論》中記載:“夫十二經脈者,內屬于臟腑,外絡于肢節。”十二經脈為臟腑氣血的發源地,為臟腑提供精氣以保證臟腑正常機能的發揮,而“心者,君主之官”,心是五臟六腑的大主,氣血通過經絡到達各臟腑是以心臟為中心的,故心和臟腑經絡在機能上就具有多種調節作用,在物質和功能上既源于心又源于臟腑的多源關系[5]。《素問·靈蘭秘典》記載“主不明,使道閉塞不通”,所以當外邪侵襲經絡,或瘀血、寒濕等病理產物停留于經絡,或臟腑功能失調,致經絡阻滯,氣血不通,“不通則痛”,經脈氣血的運行與心、神聯系緊密,局部氣血通過經絡這個通道向心臟傳導,由心神感知疼痛,故曰“痛則神歸之”;因血、脈、心、神是統一的整體,氣血的異常狀態會導致心神受損,反之,心神也可調節氣血的運行,通過調神來調節氣機,如此可使氣機條暢,血脈調和,氣血通暢,通則不痛,從而到達“心寂則痛微”,這是調神止痛的本質。
1.2 臨床應用
1.2.1 調神之穴
在取穴方面,從神由心、腦所主出發,使用調神止痛時一般選擇心、腦的經脈,主要選取督脈、心經、心包經的腧穴,如石學敏院士在治療頑固性疼痛時,會選擇內關、人中以行氣調神,通過調神來使氣機通暢;武連仲教授擅長針刺止痛,他使用12種方法來治療疼痛,其中“調神止痛法”位于第1位,主要取內關、水溝、少府、郄門等穴[6]。
1.2.2 調神之法
《靈樞·本神》記載:“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針刺治療疾病,無論何種疾病都需要“治神”,治神與否決定了臨床療效,“粗守形,上守神”,《小針解》解釋到:“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余不足可補瀉也。”張景岳對此深有體會,他解釋到“醫必以神,乃見無形,病必以神,血氣乃行,故針以治神為務。”[7]可見只有通過守神,才能感受到不可見氣血的運行狀態,因此調神止痛治療痛癥必須通過治神來調節氣血的運行,氣血運行通暢,通則不痛。
關于治神,是從醫者和患者兩個方面入手。首先要求患者定神,《素問·痹論》說道“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針刺時要求患者保持安靜,精神集中,這樣更易使氣至,“氣速至而速效,氣遲至而不治”,患者的主動配合能促進針刺發揮最大效應。其次是醫者守神,《標幽賦》記載:“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氣隨,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醫者進針時必須心無旁騖,一邊仔細關注患者的神情,一邊感受針下的反應,誠如竇漢卿所要求的“目無外視,手如握虎,心無內慕,如待貴人”。通過患者和醫者的合作,進針后醫者感受針下的反應,患者想著疼痛的部位并體會針刺的感覺,所謂“醫者,意也”,醫患二者之間心意相通,通過針刺來調動正氣,將針刺的效應最大化以驅除疾病。
2 內關治療痛癥
2.1 理論基礎
調神止痛重在調心神,《靈樞·邪客》謂:“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心包是心的門戶,凡外邪侵襲心,心包先受之,從而保護“生之本”的心臟,故調心神多選取心包上的腧穴。內關歸屬于心包經,內關穴第一次被記載在《靈樞·經脈》:“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循經以上系于心,包絡心系。”內關是心包經的絡穴,同時循經以上系于心,故內關穴是調神止痛針法必選穴,可見內關治療痛癥是基于調神止痛理論。
除了通過調神以止痛,《標幽賦》中記載了“住痛移疼,取相交相貫之徑”,此處指出了止痛的取穴原則,即選擇各經相交叉的穴位。因為經絡相交的穴位歸屬于多條經脈,如此能調節多條經脈的氣血運行,可一穴調多經,這也是臨床上常用的穴位,譬如絡穴,絡脈在此從經脈別離以加強本經與表里經的聯系,故絡穴可將表里兩經聯絡起來,所以有“一絡通兩經”的理論,因此絡穴既可以治所屬經脈上的疾病,又可以治與之相表里之經的疾病。再如八脈交會穴,一共有8個穴位,是八條奇經和十二條正經中的8條正經相交的部位,所以可調節奇經和相關的正經的氣血運行。因為絡穴和八脈交會穴可一穴調多經,治療范圍廣泛,故可選擇絡穴、八脈交會穴來治療疼痛類疾病。而內關穴是手厥陰心包經的絡穴,與手少陰三焦經相表里,又是八脈交會穴之一,與陰維脈相通,因此針刺內關穴,可“一穴調三經”,有寧心安神、寬胸理氣、調暢氣血、鎮靜止痛的功效[8]。
內關穴治療痛癥,不僅可調節經絡、氣血的運行,使經絡氣血恢復正常狀態,還通過移神寧心,從源頭解除疼痛的感覺,此穴從疼痛病機及本質上治療疼痛,止痛效果好,可治療各類疼痛類疾病。
2.2 臨床應用
《針灸大成·八法交會八穴歌》曰:“公孫沖脈胃心胸,內關陰維下總同”,內關穴治療疾病廣泛,可治療心、胸、胃部的疾病。關于痛癥,臨床應用較多,通過檢索文獻發現[9],內關單穴或配合其他穴位,可治療心痛、腹痛、痛經、痹證、咽喉腫痛、目赤腫痛等痛癥。張盛之[10]針刺內關配合外關治療急性痛癥,其中包括冠心病心絞痛、胸脅痛、外傷痛、岔氣痛、急性腰扭傷、受寒、頸肩痛和腿痛等痛癥,結果總有效率達100%。經查閱文獻發現,現代內關治療痛癥多用于治療冠心病心絞痛、胸部扭傷、胃痛、腹痛、痛經、泌尿結石疼痛、癌性疼痛、術后疼痛、腰痛和咽喉腫痛等。
2.2.1 冠心病心絞痛
心絞痛與“胸痹”“真心痛”相當,皇甫謐所著《針灸甲乙經》曰:“心系實則心痛肘攣,腋腫,實則心暴痛,虛則為煩心,取之兩筋之間”,兩筋之間即指內關穴。張安東[11]將72例冠心病心絞痛患者分為兩組,一組進行針刺內關穴,另一組予服用山海丹膠囊,比較兩組的療效,最終顯示針刺內關的有效率達97.22%,而服用藥物的則為83.33%,表明針刺內關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療效突出。向蓉[12]以內關穴為主針刺冠心病心絞痛患者41例,并將服用丹參滴丸41例設置為對照組,觀察心絞痛緩解時間,并通過心電圖監測心肌缺血情況,結果發現針刺內關穴縮短心絞痛緩解時間,改善心電圖缺血型改變情況等優于對照組。
2.2.2 胸部扭傷
胸部扭傷,中醫稱為“岔氣”,是在搬取重物時用力不當而出現的突然的疼痛,疼痛部位多出現在胸脅部,疼痛劇烈,隨著深呼吸而加重。《醫宗金鑒》有云:“內關主刺氣塊攻,兼灸心胸脅痛疼”;《標幽賦》載:“陰蹺、陰維、任沖脈,去心腹脅肋在里之疑”。胸部扭傷,病位在胸脅,為心肺等重要臟器所處之處,臨床上多采取遠端取穴。盛世寬[13]采用繆刺法治療急性胸部扭傷疼痛,具體方法為左側病針刺右側內關穴,右側病針刺左側內關,針刺時配合運動,醫者進針時讓患者深呼吸,進針后讓患者留針做雙臂抬舉,彎腰等運動。結果共治療75例患者,總有效率達94.6%。劉萍等[14]運用繆刺內關透外關來治療急性胸部扭傷患者,有效率為94.7%,療效滿意。
2.2.3 胃痛、腹痛
胃痛及腹痛是因消化系統功能紊亂導致的,多出現于胃潰瘍、胃痙攣、闌尾炎等疾病,其癥狀為突發胃脘部、腹部的劇烈或隱隱疼痛,有時還會出現惡心、嘔吐、腹瀉等癥狀。《標幽賦》曰:“胸腹滿痛刺內關”;《席弘賦》載:“肚疼須是公孫妙, 內關相應必然瘳”。選取內關配伍公孫治療胃痛、腹痛,療效明顯。侯志鵬等[15]選擇30例腹痛患者,一半患者運用強刺激公孫、內關,另一半則采用普通電針針刺公孫、內關,觀察兩組疼痛改善情況,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3.33% ,對照組為86.67% ,可見針刺公孫、內關治療腹痛效果明顯,強刺激后效果更顯著。
2.2.4 痛經
當人體被外邪侵襲,或出現七情失常,或先天不足導致沖任、胞宮不暢或失養,會出現痛經。古代著作里關于痛經的治療有:“女子胞中痛,月水不以時休止,天樞主之”;《針灸則》曰:“經水未行,臨經將來作痛,血實郁滯也,針:天樞、陰交、關元”。針灸治療痛經多選用脾經及任脈上的穴位或者選用經驗穴如十七椎等,趙因[16]選擇30例原發性痛經患者,辨證為濕熱瘀阻型,平均分組,一組選擇“絡穴止痛方”(列缺、豐隆、鑫溝)加地機、氣沖穴進行針刺,另一組則采取應急止痛,觀察各項評分及疼痛持續時間,結果顯示針刺治療療效明顯優于應急止痛。黃慧玲[17]采用內關加公孫、天樞、中極、地機、足三里,根據疼痛時間進行分期治療,凡經前或經期疼痛者用毫針瀉法,在月經來潮前的3~5 d開始針刺,月經來臨停止針刺;經后疼痛者進行針刺補法,在月經快結束的前幾天進行治療。治療2個月經周期后觀察療效,共15例患者,總有效率為86.7%。在治療痛經的選穴上,可在基礎選穴上加用內關穴,以加強止痛之功。
2.2.5 泌尿結石疼痛
由于結石劃傷或堵塞泌尿道,患者會出現劇烈的腎絞痛,似刀割樣,疼痛呈持續性或間歇性,疼痛部位從腰部或上腹部向腹股溝或者外陰部放射,可伴有冷汗、嘔吐等[18]。對于泌尿系結石急性發作,通常采用注射阿托品達到鎮痛的目的,史春娟[19]對泌尿系結石疼痛患者進行針刺治療,并設置藥物組,肌注阿托品1 mL,黃體酮注射液40 mL,結果針刺組止痛所需時間短于藥物組,可見針刺止痛效果較好。尉國勤[20]用針刺足三里、內關、三陰交等穴治療該病引起的疼痛,共治療15例,顯效13例,2例配合局部熱敷也取得滿意療效,有效率100%。現代泌尿系結石多采用碎石手術治療,無論是術前發病時的疼痛,術中麻醉時疼痛,還是術后排石反應出現的疼痛,疼痛貫穿始終[21],因此針刺可以在發病時干預,其選穴可在常規選穴上加內關以達到調神止痛的效果。
2.2.6 癌癥疼痛
隨著癌性疾病的發生率的增加,由癌癥及治療癌癥期間所導致的疼痛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癌癥疼痛劇烈且持續不解,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陳愛文等[22]統計分析出針刺治療癌痛的穴位使用頻率最高的穴位為足三里,內關排第二,其次為三陰交、合谷、阿是穴等穴。昝慧敏等[23]選取晚期癌癥疼痛患者16例,使用艾條灸結合針刺治療,治療穴位從中院、內關、公孫、足三里、梁門、膈俞、肝俞、合谷、梁丘中選擇,每次選穴3~5個,總有效率為85%。居晨霞[24]將晚期惡性腫瘤合并癌痛患者進行鎮痛藥物合并內關、足三里穴位按摩與單純使用鎮痛藥物進行對照,觀察癌痛緩解情況,結果顯示藥物結合針刺的有效率(93.6%)明顯優于單純藥物組的有效率(79.2%),可見按摩內關、足三里穴位可以緩解晚期惡性腫瘤患者癌痛癥狀。
2.2.7 術后疼痛
術后疼痛是人體經過手術治療后出現的不可避免的組織損傷,從而導致的一系列復雜的身體和心理反應,除了給患者帶來痛苦,還會影響患者的預后恢復情況。術后止痛方法有口服鎮痛藥、肌內注射、經皮膚或直腸黏膜給藥,靜脈自控鎮痛、硬膜外患者自控鎮痛等,針灸也逐漸被用于術后鎮痛[25]。趙喜波等[26]選取擇期食管癌手術患者120例,其中60例進行電針內麻點和內關穴,剩余60例患者予靜脈自控鎮痛治療。治療后發現,電針刺激內麻點和內關穴對于食管癌手術后患者的鎮痛效果優于使用靜脈自控鎮痛的患者。肖剛等[27]選擇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患者120例,將其隨機分為兩組,針刺組采用針刺合谷、內關、足三里、陽陵泉、膽囊穴、三陰交、阿是穴等主穴,止痛泵組給予止痛泵持續靜脈滴注鎮痛,觀察疼痛分級及不良反應。結果,針刺組有效率67%,止痛泵組有效率47%,可見針刺用于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后鎮痛有效。
2.2.8 肢體疼痛
針刺內關穴可用以治療肢體等部位的疼痛,顧彥冬[28]選擇94例急性腰扭傷患者,平均分為兩組,一組給予理療結合針刺內關,另一組僅予理療治療,結果顯示理療加上針刺組總有效率93.6%,理療組總有效率80.9%,針刺內關穴治療急性腰扭傷療效確切,易于操作。鄧伯影選擇33名膝關節疼痛患者,采用針刺內關進行治療,總有效率達90.9%。柳洪盛等[29]對50例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患者進行針灸治療,取內關穴,在進行及留針時結合運動。結果治療后,50例患者骨性關節炎指數和疼痛視覺評分表評分較治療前均下降,患者關節疼痛及運動功能明顯好轉,可見內關穴用于治療膝關節炎顯效。賀麗萍[30]采用單純針刺內關穴配合運動療法治療落枕,其中男性32例,女性18例,治愈率為100%,1次治愈者占96%,2次治愈者占4%。
3 現代理論機制
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末首創針麻手術以來,針刺鎮痛得到了廣泛應用,國內外對于針刺鎮痛機理從神經-免疫-內分泌等方面展開了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研究發現,針刺鎮痛的一大機制是通過促進內源性阿片肽的釋放,達到止痛的效果。此外,針刺通過刺激炎性反應,使局部的內啡肽分泌增加和上調外周阿片受體從而發揮消炎止痛的功效;針刺還可能通過減少內源性致痛物質的生成、干預脊髓背角神經元的細胞內信號轉導通路、抑制痛覺敏化,從而發揮鎮痛作用[31]。對于內關穴的應用,目前研究熱點多為其作用于心血管系統,但對于鎮痛的機制研究較少,主要是因為針刺鎮痛的研究頗為完善,具有普遍性,針刺內關穴可通過以上途徑達到鎮痛的效果。葉德寶[32]認為針刺內關穴可刺激正中神經,而正中神經神經元在脊髓節段分布與支配頭顱內外血管的交感神經所在的脊髓節段分布位置接近,因此,刺激內關穴是通過刺激正中神經元以調節交感神經,改善異常顱腦血管,從而到達即可止痛的效果。郭虹憶等[33]發現,足三里穴位注射聯合指壓內關穴后可促進血清β-EP分泌,減少SP分泌,可阻斷初級感覺神經元將疼痛信號傳至中樞系統,同時SP的減少可抑制炎性因子釋放,減少傷害性信息被輸送至中樞,達到鎮痛效果。此外,內關穴治療心血管疾病的臨床研究較多,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心絞痛均會出現疼痛癥狀。經臨床和實驗研究證實,針刺內關穴可緩解毛細血管內皮細胞損傷的現象明顯減少,改善微循環,促進血液循環,緩解心絞痛;可通過降低心肌缺血小鼠心肌組織TNF-α、IL-1β、IL-8蛋白表達水平,抑制炎性反應,減少炎癥刺激以緩解疼痛;高頻電針內關穴治療后,可促進NO的分泌,從而調節心血管系統,達到止痛的效果[34-36]。李夢等[37]對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內關穴進行電針治療,結果大鼠的脊髓背根神經細束電活動的頻率與波幅均明顯下降,其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濃度含量均明顯升高,多巴胺在外周組織發揮著舒張平滑肌的作用,發揮止痛作用,而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與人類的精神和情緒活動關系密切,這有可能是針刺內關穴可以緩解痛情緒的機制之一。
4 小結
痛癥是針刺擅長的疾病之一,而針刺最重視調神,在治療痛癥疾病不能忽視“神”這個重要概念,調神除了運用穴位以調神,還要在刺法上進行調神,對醫者和患者均要求守神。臨床上除了使用“以痛為腧”取穴方法治療痛癥,還要依據中醫基礎理論辨證取穴,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選擇內關穴治療痛癥即從本質上治療疼痛,單獨或者配伍使用內關穴對于治療痛癥療效確切,臨床上可廣泛使用。《九針十二原》曰:“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臨床上遇到難以治療的疾病,是因為未得其術所致,因此要從《內經》等經典著作出發,尋找治療疾病本質的理論依據并將其運用于臨床,才能成為一名“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