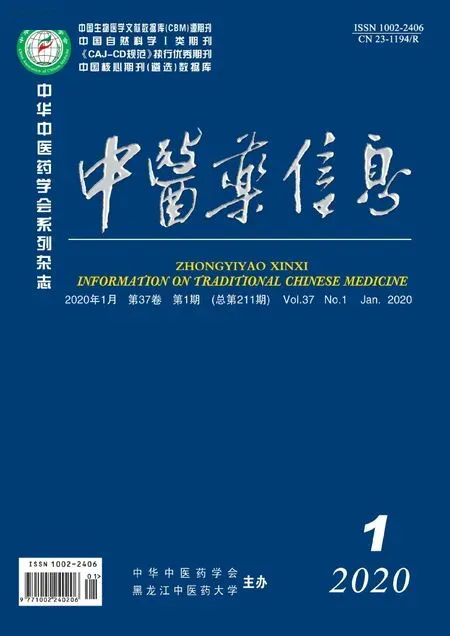周慎齋脾胃學術思想研究概況
馬駿,段永強,2*,鞏子漢,白敏,王斑,李小忍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20;2.敦煌醫學與轉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20;3.河北大學,河北 保定 071002)
周之干(約1508—1586年),字元干,號慎齋,明代嘉靖年間著名醫學家,宛陵(今安徽宣城)人。慎齋醫術高明,重視脾胃,在醫界享有盛譽,故嘗有“自明以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慎齋”[1]1之說,《周慎齋醫學全書·吳序》更是高度評價其“獨得仲景之精髓,直駕李、劉、朱、張而上,有非季俗醫所能仿佛二三也”。周慎齋生前忙于診務,無暇著書,今所存著作皆為后人整理,現存有《慎齋遺書》與《醫家秘奧》兩種。
1 周慎齋學術源流考鏡
1.1 周慎齋生平及學術傳承關系
周之干(約1508—1586年),號慎齋,明代嘉靖年間著名醫學家,宛陵(今安徽宣城)人。關于周慎齋學術傳承私淑關系,《醫家秘奧》[2]《周慎齋醫學全書》[1]1均報道如下:周慎齋中年深研軒岐之精髓,私淑張元素、李東垣,參以劉河間,后求正于薛己之門,問難數月,于是豁然貫通。
趙仁龍等[3]報道,周慎齋歸主查源溪家10余年,從學者甚多,其中成業者有胡慎柔、石鎮、查萬合等。查氏又為慎柔恩師,正如《慎柔五書》中石震所撰“慎柔師小傳”明確指出:“了悟先生涇縣人,為太平周慎齋先生高座”“(查了悟)先生懼其學過己,乃令往從慎齋先生”。因而,究其三者與周慎齋的關系為,周慎齋承薛己之學,一傳胡慎柔、查了悟,再傳石震。慎齋醫術十分高明,在醫界享有盛譽,故嘗有“自明以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慎齋”[4]之說,《周慎齋醫學全書·吳序》更是高度評價其“獨得仲景之精髓,直駕李、劉、朱、張而上,有非季俗醫所能仿佛二三也”[1]4。
1.2 著作爭議
周慎齋生前忙于診務,無暇著書,今所存著作皆為后人整理,現存有《慎齋遺書》與《醫家秘奧》兩種。趙仁龍等[3]通過檢索《中國古籍總目》與《全國圖書聯合目錄》收錄的以周慎齋命名的傳世書目有《周慎齋醫書》《周慎齋三書》《周慎齋醫案稿》《周慎齋先生經驗秘傳》及《醫家秘奧》五種。通常認為[5],周之干生前著有《脈法解》《周慎齋三書》,又有由門人記錄并經后人整理之《慎齋遺書》《醫家秘奧》《周慎齋醫案稿》等傳世。不同的是,趙仁龍等[3]認為《周慎齋醫案稿》為周之干傳學之秘本,系周之干晚年總結平生醫療經驗之所集,由門人錄其言談整理而成,并有所增益。趙氏經比對發現,《周慎齋醫案稿》約2/3論述見于《慎齋遺書》《醫家秘奧》《慎柔五書》,且醫文如出一轍。此外,筆者通過對照《醫家秘奧》目錄,發現其中涵蓋《脈法解》《周慎齋三書》等著作,加之《慎柔五書》“慎柔師小傳”云:“慎齋先生名滿海內,從游弟子日眾,師隨侍,每得其口授語,輒筆之。先生初無著述,今有語錄數種行世,多師所詮次也”及《中國醫學大辭典》厘定《周慎齋醫案稿》“當亦后人或乃門所集”,認為署名周慎齋的《周慎齋醫書》《周慎齋三書》《周慎齋醫案稿》等著作,其原書或被合并,或被篡改,或一書多名,現今諸書應經整理核定為《慎齋遺書》與《醫家秘奧》兩種。
2 周慎齋脾胃思想研究
2.1 理論研究
2.1.1 “亢害承制”與脾胃理論相結合
“亢害承制”最早記載于《素問·六微旨大論》:“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張介賓注曰:“亢者,盛之極也。制者,因其極而抑之也。……所以亢而過甚,則害乎所勝,而乘其下者,必從而制之。”此處,亢害承制指的是自然界力圖維持平衡的自穩調節現象,機體也需要與外在環境一樣通過自我調節保持相對的平衡狀態,才能維持自身的正常生理活動[6]。
金露露等[7]指出,周慎齋將“亢害承制”與脾胃理論相結合,以脾土為中心進行考慮其他五臟疾病的病機。周慎齋認為“五臟和則能互為生克,相生相克,相制相化,而無過與不及之病,所謂氣得其平也;不能平者,或因六氣之感,則外傷而不平,或因飲食勞倦欲事七情,則內傷而不平,不平于先天者,必傷于后天,傷于后天者,必害于先天,一有所傷害,則多氣不納腎之患”[1]13,強調了調理脾胃的方法,就需要理解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張其成[8]對“五臟調節模型的意義與不足”進行討論,周慎齋的“脾之五臟”“腎之五臟”揭示了脾腎各自互藏五臟的觀點,認為“心之脾胃虛,肺之脾胃虛,肝之脾胃虛,腎之脾胃虛,脾胃之脾胃虛,因其虛而調理之,即治病必先脾胃之說也”“百病皆由胃氣不到而不能納腎”所致,因而每一臟都有類似脾胃的功能。
周慎齋將“亢害承制”與脾胃理論相結合的思想,在臨床運用中也有體現。蒙木榮等[6]指出,隔二隔三之治等治法就是根據五行亢害承制的規律演化而來,是中醫治療學中獨具一格的精華部分。周慎齋在治療脾胃疾病時常用此法,他說:“然補法之中又有奧妙焉……故善用補法必先補脾,脾陰足則精微運化,而泄瀉自止矣,此東垣所謂隔二之治。且脾能生肺,肺又生腎,循環而生,子母相顧,此古圣賢補腎不如補脾之妙”[1]228,“用四君加山藥,引入脾經,單補脾陰,再隨所兼之證而用之,俟脾之氣旺,旺則上能生金,金轉能生水,水升而火自降矣,此合三之治法也。”[1]101周慎齋將“亢害承制”與脾胃理論相結合,論述甚詳,且倡導隔二隔三療法,對指導臨床應用具有重大意義。
2.1.2 諸病不愈尋脾胃
周慎齋繼承并發揮了李東垣“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思想,提出“諸病不愈,必尋到脾胃之中”“治病不愈,尋到脾而愈者甚多”的學術觀點,認為“脾胃一傷,四臟皆無生氣,故疾病日多矣。萬物從土而生,亦從土而歸”,“諸病不愈尋脾胃”對指導臨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周銘心等[9]認為“諸病不愈尋脾胃”理論可用于其他諸多病癥,但實為權宜之計,不得已而用之。楊志明[10]報道,運用該“諸病不愈尋脾胃”理論,從脾胃著手治療眩暈、水腫、肺癆等多證,取得了顯著療效;楊氏還指出,有些慢性病久治療效不顯著,如果從調理脾胃的角度出發,則可另辟蹊徑。張春光[11]報道,運用該“諸病不愈尋脾胃”理論,在臨床實踐中,治療多種頑癥,多從脾胃入手,方取取三仁湯,治療脂肪肝、陽痿、頑咳等患者,取得良好的效果。
2.1.3 脾陰學說
脾陰就是脾氣中陰的活力部分,表現為濡養、向下的作用[12]。周慎齋對脾陰虛臨床癥狀表現做了描述,例如華信[13]總結了脾陰虛的癥狀,除“久熱不退,虛熱勞損,中消,嘈雜,噎隔,聲啞,口瘡,納差,泛惡,不食,食后腹脹,腹痛或便秘等癥”外,還包含周慎齋所指“一人尿血,此脾陰不足也”(《周慎齋遺書·尿血》)。
而脾陰虛治療方面,黃一卓[14]通過數據分析的方法,對中醫脾陰學說古今文獻梳理發現,《慎齋遺書》《本草述鉤元》中關于脾陰內容均達21條之多,占所對比書目之最,《慎齋遺書》中主要論述了“胃陽全賴脾陰之合”“單補脾陰以養胃氣”“白術水煮爛成餅曬干,能補脾陰之不足”“用四君子湯加山藥,引入脾經,單補脾陰”等與脾陰相關的理法方藥。黃一卓還列舉了《慎齋遺書》從脾陰論治痰飲、汗證、吐血、尿血等的典型醫案。
張利靜[15]認為,周慎齋尤其具有特色的是明確指出脾陰虛脈象,他說“肝脈弦長,脾脈短,是為脾陰不足”,又認為脈者血之府,脾統血,血枯則脾陰虛,脈象則易多變,言“脈或大、或小、或浮、或數、或弦、或濕,變易不常,知其脾陰虛而脈失信也。”因此認為,周慎齋對脾陰之脈深入的觀察體會,補充了脾陰虛臨證診斷空白,為后人準確診斷脾陰虛證提供了依據。
此外,周慎齋對脾陰不足之消渴證也作了論述:“蓋多食不飽,飲多不止渴者,脾陰不足也,專補脾陰不足,用參苓白術散”。
2.1.4 先天、后天互根
周慎齋非常重視脾腎之間的關系,認為脾胃化生五臟之氣必到達于腎,如《慎齋遺書·用藥權衡》云:“人之生死關乎氣,氣納則為貴。氣納則歸腎,氣不納則不歸腎,氣不歸腎者,謂脾胃之氣不得到腎也。其不到有五,心之脾胃,肝之脾胃,肺之脾胃,腎之脾胃,脾胃之脾胃,不到者,由先后天不能相生故也。”周氏還認為脾腎之間相須相濟,具體表現在“腎傷則先天傷,而后天之胃無根,亦必受害。凡久病而不死者,腎傷未及胃也,及胃立死矣”,因此預測疾病時,要“在此二天,一傷則病,兩傷則死。既兩傷矣,尚欲救之,愚人也;兩不傷而醫者死之,醫人之罪也。見病不先察此二天,不知醫者也;能醫者,專以此二天為務。此醫門之秘談也。”
胡泉林[16]指出,周慎齋并非把脾、腎分為兩個部分,而是以先天、后天關系為軸心,論述五臟病機,以脾胃生發之氣,論述五臟之脾胃虛,這不僅擴展了李東垣的脾胃論述,亦明顯不同于乃師薛立齋“或重脾胃”“或重腎命”的觀點,更不再囿于前人的“補脾不如補腎”“補腎不如補脾”之爭,可謂別出心裁。后世李中梓“先后天根本”論,葉天士“心、肝、脾、腎之脾胃虛”論,亦無非承周氏之緒余而已。
2.1.5 重視胃陽
周慎齋繼承并發展了脾胃學說,重視脾胃同時,尤重“胃陽”,誠如《慎齋遺書·望色切脈》云:“總之,治病以回陽為本,乃要法也……回陽者,回胃陽也。何臟無胃陽則治何臟”。修成奎等[17]指出,周慎齋善于調脾胃,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慎齋“人身以陽氣為主,用藥以扶陽為先”的理論中,非常重視扶陽(胃陽),這與其重視脾胃的學術思想有關。
2.2 臨床研究
2.2.1 化裁補中益氣湯
周慎齋尊崇李東垣,善用補中益氣湯化裁,其論治脾胃內傷發熱、內傷雜病的治療經驗無疑擴大了補中益氣湯的應用范圍,特別是運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經驗,對后世較有影響。閆玉冰[18]指出,周慎齋基于補中益氣湯升清陽散陰火的組方特點,在臨床使用中有所創新。周慎齋認為補中益氣湯“補中者,補中氣也。參、術、草所以補脾、五行相制則生化,廣皮以疏肝氣,歸身以養血,清氣升則陽生,故用柴胡、升麻以升提清氣,清氣既升則陽生,陽生而陰自長矣”,強調了補中益氣湯升清陽以陽氣為主導的特點。閆玉冰還通過對《慎齋遺書》驗案分析,說明周氏運用補中益氣湯加減的獨到見解,形成了補中益氣湯加附子的用藥經驗。佐藤田實[19]報告3例熱病患者,其中2例先后使用補中益氣湯與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治療,結果表明加入少量附子后可使治療效果更加顯著,認為這源于附子與其他藥物間的相乘作用。此外,還有報道[20]運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治療低血壓,連續服用6個月后患者低血壓病痊愈,且精神乏力和足腰冷等癥明顯改善。
2.2.2 根據脈象制方
周慎齋諳熟醫理,首重脈理,善于根據脈象制方。劉銳等[21]指出周慎齋根據脈象制方特色十分鮮明,從其用方規律來看,說理簡明,規律突出。《醫家奧秘·脈法》僅列78條,但所用方卻達到31方,出現頻率高者可見10余次,如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八味丸等,臨證運用六味地黃丸與八味地黃丸的規律是:兩尺旺,用六味地黃丸;兩尺微細,用八味地黃丸。依據“脈法”的說明,凡尺脈沉細或微,用八味地黃丸,但見旺、數或有力方可用六味地黃丸。朱景智等[22]指出,周慎齋對八綱辨證運用靈活,善于用脈象隱言辨證,誠如“左尺浮緊有力,傷寒宜解表,汗出即愈;但有力不緊,清心蓮子飲或五苓散以利之;無力則為虛,六味地黃丸;沉實為寒宜溫;沉遲為虛宜補,故紙、肉蓯蓉、鎖陽、大茴之類,當消息用之;沉弱微則為虛不宜直補,所謂補腎不若補脾,正與此同。或十全大補湯佐以補腎之味;沉數陰中無陽,八味地黃丸。”還還列舉周慎齋根據脈象辨證制方的案例,如:“寸脈細微,陽不足,陰往乘之,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兩尺洪大,陰不足,陽往乘之,補中益氣湯加黃柏。”“尺脈大于寸脈,陰盛陽虛,宜汗。寸脈大于尺脈,陽盛陰虛,宜下。尺脈浮而有力宜表,無力補中;沉而有力滋陰降火,無力地黃丸之類”“欲使人體氣機升提,用羌活、防風等辛溫發散之品;降陰氣,需用黃柏等苦寒斂降之品;由內向外出,用發表的汗法;欲使人體氣機由外向里收,用斂降的下法。”指出周慎齋根據脈象判斷人體氣機升降出入,然后運用相應方劑治療,在臨床時有運用,可資借鑒。
2.2.3 脾胃內傷虛損病癥
周慎齋在前人的基礎上,取得了較大成就,特別是對脾胃內傷虛損學說的闡發,于中醫臨床有許多的裨益。何緒屏[23]指出,周慎齋對脾胃內傷學說的發揮主要有三:其一,詳述脾胃氣機的生發與氣血、陰火的關系;其二,提出脾胃內傷虛損責之氣血兩虛,并使用甘淡平補脾陰之品以生陰血;其三,強調“久病后,全以脾胃為主。”因此不論內外感傷及雜病,均應從脾胃著手。江珂鋟等[24]指出周慎齋在論治內傷虛損病癥時主要基于對脾腎與命門真陰真陽在機體發生疾病產生變化的認識,進一步闡發了“補腎不如補脾”,提出兩種補腎陰的方法:補脾陰以滋腎陰、補脾升陽以滋腎陰。
2.3 其他研究
傅維康[25]指出,“辨證施治”術語首見于《慎齋遺書·卷二》,且有專列標題“辨證施治”一節。
李浩然[26]在論述肺陽具有化生陰血的生理特點時引自《醫家秘奧》曰:“宗氣,即膻中之陽,此陽屬肺……此氣降下,即為陰血,所謂‘金能生水’是也。”因此認為,肺陽所衍生的宗氣,下降于腎,便能化為陰血。”
洪必良[27]在論述探病法時指出,《慎齋遺書》將探病法視為治療大法,將“探”并列于“寒、熱、補、瀉、逆、從”諸法,并評價曰:“初驗雖分真偽,欲施攻補狐疑,全憑一探虛和實,此是醫家妙計”。
闞廣迪等[28]在論述麻木的治法時引《慎齋遺書》曰:“麻木須分左右上下,左因氣中之血虛,歸脾湯;右因血中之氣虛,黃芪建中湯;左右俱麻木,十全大補湯;上身麻木,清陽不升也,補中益氣湯;下身腳軟麻木至膝者,胃有濕痰死血,妨礙陽氣不得下降,故陰氣漸逆而上也,四物湯加人參、牛膝、薏苡仁,引陽氣下降;下身麻木,脈豁大無力,宜八味湯加人參;十指麻木,脾不運也,宜溫脾土”。
呂艷[29]探討了道教的經典學說發展過程,認為周慎齋受到內丹學說、丹田學說和命門學說的影響,指出《慎齋遺書·陰陽臟腑》所述:“心腎相交,全憑升降,……夫腎屬水,水性潤下,如何而升?蓋因水中有真陽,故水亦隨陽而升至于也,則生也中之火。也屬火,火性炎上疫如何而降?蓋因火中有真陰,故火亦隨陰而降至于腎,則生腎中之水,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之真陰真陽也。真陰真陽者,也腎中之真氣也。”就明顯借鑒了內丹學說。
3 小結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對周慎齋的研究較少,且多是簡要介紹或某一方面的研究。周慎齋為明代末期著名脾胃大家,臨床經驗豐富,其脾胃學術思想及臨床應用值得進一步深入系統地進行探討。因此,對周慎齋的脾胃思想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總結其脾胃學說理論及應用規律,符合當今中醫事業的發展趨勢,對提高臨床診療水平,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