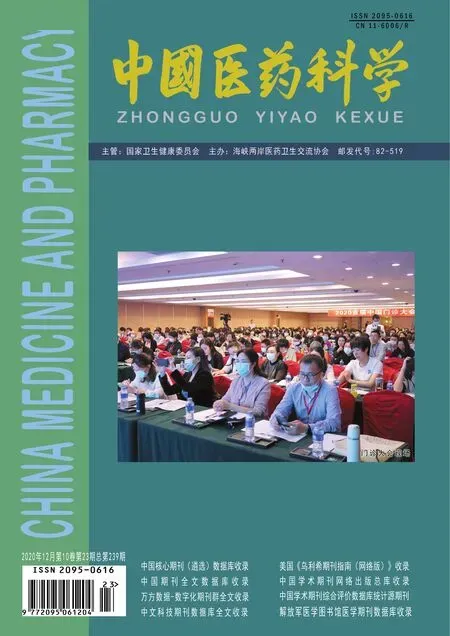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的研究進展
梁春耕 肖定洪
上海市嘉定區中醫醫院脾胃病科,上海 201800
慢性萎縮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是以胃黏膜上皮及腺體萎縮,數目減少,胃黏膜變薄,黏膜基層增厚,伴有或不伴有幽門腺化生、腸腺化生,甚至不典型增生為特征的常見消化內科疾病,為胃部疾病炎-癌轉換中重要的一環。但其病因及發病機制仍不甚清楚,治療上缺乏確切的治療措施。中醫藥在治療CAG的過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將中醫藥治療CAG的研究成果作一綜述。
1 病因病機
1.1 歷史沿革
CAG臨床上無明顯特征性表現,多表現為胃脘部疼痛,以隱痛為主,腹脹,噯氣吞酸,嘔吐呃逆,嘈雜痞滿等不典型癥狀。傳統醫學中無其病名的提出,但根據其臨床表現多歸納為“胃脘痛”“呃逆”“嘔吐”“吞酸”“痞滿”“嘈雜”,但總屬脾胃病范疇。《素問·舉痛論》:“寒邪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引急,故痛”,《素問·痹論》:“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肝胃氣痛,痛久則氣血瘀凝”“不榮則痛”,該病病機與外感邪氣、飲食失宜、氣滯血瘀等密切相關。《靈樞·經脈》:“肝足厥陰之脈……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靈樞·四時氣》:“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指出嘔吐之病與肝膽脾胃密切相關。張仲景提出外感病下之過早致損傷脾胃,正虛邪陷,中焦氣機升降失常而致痞的病機,至李東垣進一步闡明脾虛濕困、濕阻中焦、脾胃虛弱等均可致痞滿。
1.2 現代學者的認識
不同學者根據自身臨床體會,對該病的病因病機有著不同觀點。馬輝等[1]認為CAG的病機以脾胃虛弱為本,陽虛為本,同時局部出現津液虧虛,胃腑失以濡潤,氣血瘀滯,進一步產生濕阻、痰飲、寒凝、火郁等病理產物,本愈虛而標愈實,病勢纏綿難愈。才艷茹等[2]通過總結李佃貴教授治療CAG治療經驗指出李教授非常重視“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提出五志過極、肝失疏泄、脾失健運、胃失和降,氣機逆亂,終致氣滯、血瘀、濕阻、濁聚、蘊毒而成濁毒,濁毒日久耗傷胃陰,絡脈受損,氣血失布,腺體萎縮,黏膜破壞,最終形成CAG-不典型增生-胃癌病變發展。何善明認為食飲不節、肝木乘土、脾胃虛弱、疫毒傷胃(幽門螺桿菌)是該病的主要病因,并提出脾胃虛弱與脾胃虛寒是CAG的病變之本,郁熱、瘀血、疫毒是慢性胃炎反復復發之標[3]。李世增教授認為飲食不節、脾胃虛弱是CAG的重要因素,同時外感六淫、情志所傷、勞逸失度在CAG發展過程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4]。脾胃虛弱是發病的根本,其中又以脾氣虧虛、胃陰虛較多,熱度內蘊、肝郁化火為標,病久入絡,氣血功能失調,氣滯血瘀在疾病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許蘭蘭[5]提出“胃陰虧耗”為 CAG 基本病機,燥熱之邪侵襲人體,耗傷人體津液,胃體失養是其主要病理基礎。胃歸陽明屬土,喜濡潤而惡燥。長期嗜食辛香燥烈、肝郁日久化火均可損傷胃之津液,胃失濡潤,終致CAG的發生。潘華峰等[6]根據多年臨癥經驗,重視正虛、瘀血、濁毒在CAG中的重要作用,脾胃同居中焦,脾升胃降,斡旋氣機升降,此外脾主運化水谷,胃主受納腐熟,脾胃升降、運納功能正常,則水谷精微化生正常,使之能夠濡養四肢百骸、臟腑經絡。一旦脾胃功能出現異常,則運化不利,升降失司,病久不愈則氣血不循常道化而為瘀,致中焦濕困,壅滯氣機化熱成毒,脾虛益甚,虛瘀濁毒相互影響,共同促進CAG病變的發展。綜上所述,眾多學者普遍認為CAG多因飲食不節、情志不遂、外感六淫等致脾胃功能失司,中焦運化失常,致濕阻痰凝、氣滯血瘀等共同促進病變的發展,其中氣滯血瘀貫穿病變始終。
2 中醫藥治療
2.1 辨證論治
《慢性萎縮性胃炎中西醫結合診療共識意見(2017年)》[7]將CAG分為肝胃氣滯證、肝胃郁熱證、脾胃虛弱證、脾胃濕熱證、胃陰不足證、胃絡瘀血證六型,分別采用柴胡疏肝散、化肝煎合左金丸、黃芪建中湯、連樸飲、一貫煎合芍藥甘草湯、失笑散合丹參飲加減治療。但由于學者間學術觀點、理論思想、臨床經驗不完全一致,故在臨床治療中亦存在不同策略。單兆偉教授按中醫辨證分為5種證型治療:脾胃氣虛證,治以益氣健脾,方用參苓白術散加減;中焦郁熱證,治宜和胃泄熱,方用平胃散合二陳湯加減;肝胃不和證,治宜疏肝和胃,方用柴胡疏肝散加減;胃陰虧虛證,治宜滋養胃陰,方用沙參麥冬湯加減;氣虛血瘀證,治宜益氣活血化瘀,方用補中益氣湯加減,亦取得較好治療效果[8]。王國斌認為本病以脾胃氣(陽)虛,陰虛為本,氣滯、食滯、痰濕、瘀血為標。脾胃氣機升降失常,治宜六君子湯加減;若為胃陰虧虛者,治用芍藥湯或一貫煎加減;肝郁氣滯明顯者多加用佛手、郁金等疏肝理氣藥;痰濕內盛多選用二陳湯加砂仁行氣化濕,薏苡仁健脾利濕,厚樸花理氣,甘松醒脾開胃等;若胃絡瘀阻者,則治以失笑散酌加刺猬皮、丹參、莪術等活血化瘀;飲食停滯,治當消導化積,多選用枳術丸或枳實導滯散加減[9]。徐景藩教授主張胃陰不足證,當滋養胃陰,兼以行氣。方用沙參麥冬湯或益胃湯加減;脾虛氣滯證,需健脾和胃佐以理氣,方用六君子湯加減;肝胃不和證,治宜疏肝和胃,方用柴胡疏肝散或逍遙散加減;夾飲食積滯者,宜加消積導滯、調節胃腸,方用保和丸加減;夾濕熱、痰飲者,治宜祛濕化痰,藥用二陳湯、四妙散加減等;兼夾瘀血者,治宜益氣活血化瘀,可選桃紅四物湯加減[10]。毛阿芳等[11]總結黃穗平教授治療經驗時指出該病病機主要為脾胃虛弱、氣機逆亂、痰瘀互結,治療上多重視補虛扶正、斡旋氣機、化痰行瘀,補虛常選用四君子湯、理中湯、歸脾湯等;理氣行氣多用枳殼、陳皮、木香,同時遵“肝主疏泄”,喜用柴胡、香附、玫瑰花、合歡皮等疏肝理氣之品;脾虛不運或濕邪困脾者,常選茯苓、薏苡仁、半夏等祛濕化痰之藥,病變日久絡脈瘀阻者酌加三七、延胡索活血化瘀止痛。任順平亦指出CAG病位在胃,與肝脾密切相關,基本病機為脾胃虛弱,運化失司,濕邪內生,壅遏氣機,常兼見氣滯、血瘀、熱郁、痰濕、食積等,其中飲食、情志、濕邪為重要因素,善用柴平湯加減,辨證或健脾化濕、養陰益胃,或調和肝脾、理氣通降,或活血化瘀、祛瘀生新。在柴平湯基礎上,見食后飽脹,口淡乏力,脈弱者,加黨參、炙黃芪、炒白術益氣健脾;見胃脘灼痛,舌紅苔少脈細者,加沙參、麥冬、玉竹、石斛等益胃生津;兼見肝氣不舒,痰氣交阻者,酌加茯苓、蘇梗、玉蝴蝶等行氣開郁,降氣化痰;兼見胃脘及脅肋部脹痛,口苦口干,脈弦數者,加元胡、川楝子、郁金、旋復花、代赭石等疏肝瀉熱、和胃降逆之品;兼見胃部刺痛,部位不移,舌質紫暗或有瘀斑,脈澀,胃鏡提示胃黏膜中重度萎縮伴腸化等,即考慮絡脈瘀阻,加用三七、丹參、莪術等[12]。
2.2 針灸治療
針灸治療作為中醫學重要成員,在治療CAG方面亦發揮著重要作用。李佳佳[13]通過針刺中脘、內關、中脘、三陰交、公孫等穴位,能夠顯著改善CAG患者腹痛腹脹,惡心嘔吐,噯氣反酸等癥狀,同時升高胃泌素(GAS)、胃動素(MTL)水平,影響胃酸及胃蛋白酶源的分泌,促進胃黏膜修復和改善胃腸蠕動,加速胃排等。曾慶婷等[14]發現針刺背俞穴配合穴位埋線治療可明顯減輕CAG患者胃脹痛、愛腐吞酸、食欲減退等癥狀。洪武漢等[15]在研究滋胃飲聯合穴位注射對胃陰不足型CAG療效中發現滋胃飲聯合雙側足三里穴位注射可以調節脾胃經氣,增加胃腸黏膜血液分布,改善胃部微環境,增加胃黏膜、胃腺體的抗損傷與自我修復能力,抑制腸上皮化生。另有學者[16]通過動物實驗觀察艾灸對CAG癌前病變大鼠胃黏膜細胞增殖因子的影響發現,與正常組相較,CAG模型大鼠胃黏膜細胞EGF、PCNA、Ag-NORS、TGF-α、VEGF等表達均明顯升高,提示胃黏膜細胞出現異性增生性改變。同時艾灸大鼠胃經穴位能夠抑制CAG癌前病變大鼠胃黏膜細胞增殖因子的表達,抑制異性增生,促進胃黏膜的修復。王薈清等[17]通過針刺雙天樞、上脘、中脘、下脘、氣海、足三里、內關等治療CAG伴腸上皮化生患者,發現針刺能夠緩解其臨床癥狀,同時可以緩解胃黏膜腺體的萎縮及腸上皮化生程度。張迪等[18]通過艾灸中脘、足三里探討合募配穴在治療CAG的療效觀察中發現通過艾灸患者足三里、中脘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同時增加了幽門螺旋桿菌的清除率,并有效預防了其復發的發生,進一步深入研究發現其可能與調控胃蛋白酶原及受體、胃泌素水平有關。此外唐志純教授團隊研究成果證實針刺聯合穴位埋線對脾胃虛弱型CAG患者的臨床癥狀、炎癥程度、腸上皮化生、腺體萎縮甚至異型增生均有較好的治療作用,為慢性萎縮性胃炎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治療方法[19]。有學者對針刺足三里治療CAG的機制探索發現,針刺足三里可以降低CAG患者體內的內皮素同時增加降鈣素相關基因肽、一氧化氮的水平,從而改善胃黏膜供血,促進胃黏膜自身修復功能;與此同時降低患者體內表皮生長因子水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腸上皮及異性增生,延緩病變發展的進程[20]。代二慶教授團隊借鑒朱良春、董建華等大家結合自身的臨床經驗多認為CAG脾氣虧虛、氣虛血瘀貫穿疾病始終,善用針刺、穴位埋線、中藥相結合治療,臨床研究表明該法能夠改善患者胃部黏膜微循環,促進損傷胃黏膜修復,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胃黏膜萎縮與腸上皮化生[21]。吳春燕[22]在探討針灸聯合參苓白術散治療脾虛濕盛型慢性萎縮性胃炎療效分析的研究發現針藥聯合能夠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改善患者胃黏膜炎癥程度、腺體萎縮及腸上皮化生等。張蕊等[23]通過針刺大鼠脾俞、胃俞配合貞芪扶正膠囊治療1%氨水誘導的大鼠慢性胃炎的實驗發現針刺及藥物均能夠有效提高抗炎因子IL-10的表達,同時降低促炎因子TNF-α的表達,減輕胃黏膜炎癥水平,針藥聯合具有一定的協同作用。
3 結語
我國人口眾多胃癌的發病率仍居高不下,CAG是胃部惡性腫瘤的基礎性病變,是淺表性胃炎-萎縮性胃炎-腸化皮化生-胃癌發展過程中較為關鍵的一環。隨著人們對CAG認識的逐漸深入以及中醫藥在其治療方面的不斷成熟,中醫藥在治療CAG中獲得了較為不錯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1)眾多學者對該病的辨證論治仍存在一定的分歧,需要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盡快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2)中醫藥的藥物成分復雜多樣,如何全面深入的了解其作用機制仍是廣大科研工作者亟需解決的問題;(3)臨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學依據,臨床療效評價方法不一等。盡管中醫藥在治療CAG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確切的療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相信在廣大學者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終將能夠更加科學、合理、規范的服務于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