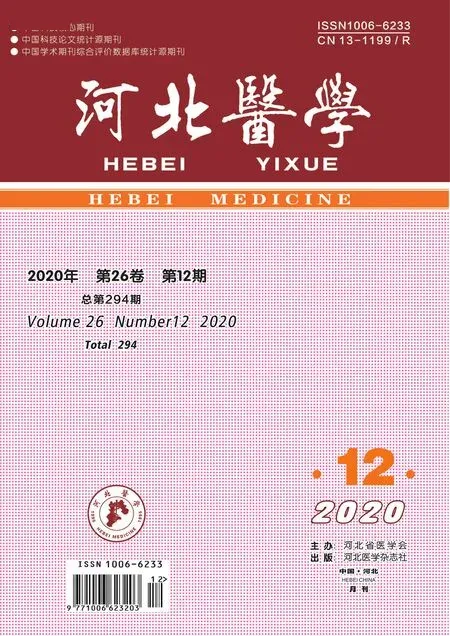乳腺癌患者發生靜脈血栓栓塞癥診療過程和風險評估相關研究新進展
吳楊凡, 劉 明, 趙 波, 趙亞男, 郝清智
(1.山東中醫藥大學, 山東 濟南 250014 2.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周圍血管科, 山東 濟南 250011)
乳腺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據GLOBOCAN估計,2018年全球女性約有210萬新乳腺癌病例和60萬乳腺癌死亡病例[1]。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us embolism,VTE)包括深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embolism,PE)。VTE是乳腺癌患者的常見并發癥之一,而肺栓塞是VTE中最為嚴重的表現,有致死風險,成為了僅次于乳腺癌本身的第二致死因素。乳腺癌并發VTE的概率相比其他癌癥低,但是乳腺癌患者的基數大,所以乳腺癌并發VTE的影響也大。目前已知乳腺癌本身、乳腺癌相關治療以及乳腺癌患者自身因素都能夠影響VTE的發生。近些年來,乳腺癌在腫瘤方面有了新的認識,也涌現出新的診療手段,這些新認識與新診療手段有的與VTE密切相關,本文通過總結乳腺癌患者在腫瘤方面和診療方面與VTE的新進展,以期待為乳腺癌患者的VTE風險評估和VTE預防提供新的參考。
1 腫瘤與VTE的新關系
腫瘤是VTE的誘發因素,在過去的很多年里已經得到證實。腫瘤發生VTE的機制比較復雜,通常由多個因素共同作用。從微觀角度來看,腫瘤細胞可直接或間接介導觸發血小板黏附、聚集和釋放反應,促進凝血發生。腫瘤細胞釋放的膜狀小囊泡(Microparticles,MPs)能夠結合血管損傷部位,增強血栓形成;腫瘤細胞產生的組織因子(Tissue Factor,TF)和癌促凝物質(Cancer Procoagulant,CP),兩者分別啟動外源性和內源性凝血途徑來導致血栓形成;腫瘤細胞還可以激活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和2,減低纖維蛋白溶解作用。另外腫瘤細胞可與單核-巨噬細胞發生相互作用,釋放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1b(IL-1b)等細胞因子,通過下調內皮細胞反調節機制,導致蛋白C的肝合成減少,加強凝血酶產生。從宏觀角度而言,腫瘤壓迫血管可導致血流滯緩,腫瘤侵襲可直接損傷血管內皮細胞。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癌癥患者處于VTE的高風險位置。
癌癥能夠誘導血液呈高凝狀態,同時促凝環境又能夠促進腫瘤的發展,促凝環境中的TF和凝血酶分別通過激活蛋白酶激活受體(protease activated receptor,PAR)2、激活PAR1及產生纖維蛋白來促進腫瘤的生長、遷移和血管生成。最新數據已經證實乳腺癌表型與基質成纖維細胞的外源性凝血途徑(TF、凝血酶、PAR1、PAR2)表達相關,浸潤前和浸潤性癌中的基質成纖維細胞中的外源性凝血途徑表達增加[2]。癌癥與凝血的相互關系還表現在抗凝血酶與腫瘤的關系,抗凝血酶是人體的主要抗凝物質,而抗凝血酶作用于腫瘤,能夠抑制腫瘤細胞遷移和侵襲。最近研究已經證明乳腺癌患者中TNM分期越高,血漿中的抗凝血酶Ⅲ活性越低[3]。這可能由于癌癥環境下產生的次氯酸能夠修飾抗凝血酶,使抗凝血酶產生新的表位,從而誘發腫瘤進展中血栓的形成和促進血管的生成。
2 手術相關VTE風險新“踩點”
機器人輔助乳房切除術是新興的乳腺癌手術方式,2015年,Toesca等第一批報道了機器人進行乳頭保留、乳房切除術后立即實施假體乳房重建的手術[4]。近幾年,機器人輔助乳房切除術的模式也呈現多元化,不同的診療手段與機器人手術相結合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乳腺癌的外科手術中,比如機器人進行的背闊皮瓣重建術和乳房切除術的相結合、機器人輔助乳房切除術與顯微外科手術游離皮瓣重建術的相結合,內窺鏡單口技術與機器人乳房手術的相結合等,研究的結果也證實了這類手術在不同類型的乳腺癌手術中技術上的可行性[5]。機器人輔助乳房切除術操作精細、微創美觀,可以減少術中部分并發癥,同時也能夠縮短術后恢復時間,這也是機器人輔助乳房切除術備受關注和期待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這類手術進行的數量太少,最多的樣本量才達到100例,所以一些重大并發癥并未報道過,另外這類手術由于操作程序和熟練程度的局限性,麻醉和術中時間普遍較長,大多在3h以上,比起常規乳腺癌外科手術,術中制動時間明顯延長,減緩了血流速度,增加了VTE的風險。
3 靶向藥物相關新風險
3.1他莫昔芬、芳香酶抑制劑與VTE的新進展:他莫昔芬和芳香酶抑制劑等靶向雌激素治療應用于乳腺癌患者可有效降低乳腺癌的死亡率。他莫昔芬是一種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可有效預防雌激素陽性腫瘤患者的乳腺癌復發。最早關于他莫昔芬與血小板的關系是他莫昔芬促進血小板活化,從而進一步促進凝血。而近些年的一些研究結果卻是與前面研究相矛盾的。Johnson等利用接受他莫昔芬輔助治療的患者中分離出的血小板進行研究證實,他莫昔芬直接抑制腫瘤細胞誘導的血小板活化,并顯著抑制血小板的促血管生成和促轉移作用[6]。他莫昔芬與血小板關系研究的差異可能是由于激素劑量、使用的激動劑、血小板分離實驗的差異引起的[6,7]。Pather等最近通過使用全血而不是洗滌過的血小板進行阿那曲唑和他莫昔芬的體外實驗,這也是阿那曲唑最早的體外實驗,證明了阿那曲唑能夠增加血小板活化,同時也為他莫昔芬促血小板活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7]。阿那曲唑是第三代非甾體芳香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AI)。AI通過抑制雌激素生成,降低血液中雌激素水平達到治療乳腺癌的目的,與接受他莫昔芬治療的患者相比,長期使用AI的患者發生的VTE的風險更低,并且至少能夠降低41%的VTE風險率[8]。
3.2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抑制劑與VTE的風險:細胞周期調節已被確定為靶向藥物治療的標靶,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抑制劑(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s,CDKIs)是治療激素受體陽性轉移性乳腺癌的一種新方法。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了三種CDKI(palbociclib,ribociclib,abemaciclib)均與芳香酶抑制劑或氟維司群合用,2017年Abemaciclib也被批準成為單一治療藥物,而將abemaciclib添加到內分泌治療中會導致VTE發生率增高。藥物聯合應用可以增強乳腺癌治療效果,減輕毒副作用,同時也可能加強某些副作用,一項對3159名乳腺癌患者進行薈萃分析的研究表明,在來曲唑或氟維司群中添加CDK 4/6抑制劑會增加VTE的發生率[9]。然而不管是CDKI類藥物,還是雌激素受體抑制劑或者是芳香酶抑制劑,本身就具有誘導血栓的風險,聯合使用很有可能使兩者發生協同作用,增加VTE的風險,因此可能是不安全的,需要特別注意。
3.3免疫抑制劑與VTE的相關性:除了傳統的化學療法和激素療法外,一些新型抗腫瘤藥也與VTE風險密切相關。用于治療各種癌癥的免疫調節劑和抗血管生成劑沙利度胺和來那度胺均與VTE密切相關。除此之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目前最有希望的抗癌免疫療法,它的出現改善了與多種癌癥相關的臨床結局,然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也能夠引起異常免疫,產生一些與自身異常免疫相關的不良反應,VTE是其中不良反應之一。Tsukamoto等報道了首例沒有VTE病史的患者,在使用抗PD-1檢查點抑制劑派姆單抗后,出現了多發性動脈和靜脈血栓栓塞的事件[10]。另外一些文獻中也報道過沒有其他并發癥和VTE病史的患者,在使用免疫抑制劑后出現了靜脈血栓栓塞事件,并且大多集中表現為PE[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應用免疫療法后發生PE的事件大多是個案報道,并沒有大數據支持,而所有抗腫瘤療法都可能導致組織損傷和組織因子釋放,引起內皮損傷,誘導血小板活化,本身就具有促凝風險。關于免疫檢查點與VTE關系的進展有待于大量數據或實驗的支持。
4 與中心靜脈導管相關的血栓新發現
乳腺癌患者反復進行多療程大劑量化療時,需要多次反復靜脈給藥,留置中心靜脈導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CVC)可以保證化療過程的順利進行,同時越來越多地植入持久性CVC,另一個原因是方便支持性護理措施。CVC包括經外周靜脈置入中心靜脈導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經皮穿刺中心靜脈導管、完全植入式靜脈輸液港及隧道式導管。最近Chopra等對23000名PICC住院患者進行分析,接受PICC交換的患者與未接受交換的患者相比,PICC血栓形成的頻率更高,靜脈血栓形成的風險增加近兩倍[12]。這可能與頻換更替PICC導管,導致PICC導管與血管內皮頻繁摩擦,從而增加了血管內皮損傷的機率有關。
5 討 論
乳腺癌與VTE的新關系,為我們提供了逆向思維,腫瘤誘發凝血,而外源性凝血又能夠促進腫瘤生長,那么通過適當阻斷外源性凝血途徑也可以抑制腫瘤的生長和侵襲,目前正在實施將口服抗凝劑利伐沙班用于抑制乳腺癌干細胞活性的試驗[13]。抗凝血酶能夠抑制腫瘤生長和遷移,癌癥環境下產生的次氯酸又能夠改變抗凝血酶的表位,誘發血栓,所以減少次氯酸的產生,或者阻斷抗凝血酶的表位的改變,也是一種既能夠抑制腫瘤發展又能夠減少VTE發生的新途徑。
隨著操作程序的熟練和改進,機器人輔助乳腺切除術相信在將來的某一天會克服麻醉和手術時間長等問題,成為未來乳腺外科的主流。關于手術患者抗凝方面,2019年國際血栓形成和癌癥倡議臨床實踐指南對癌癥患者手術預防性VTE建議每天使用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1次(當肌酐清除率≥30mL/min時)或低劑量普通肝素每天3次,以防止癌癥患者術后發生VTE。術前2~12h應開始藥理預防,并持續至少7~10d;具有高VTE風險和低出血風險的患者應進行LMWH的長期預防(4周)以預防癌癥患者大手術后的VTE。
乳腺癌治療中很多新藥物和新組合與VTE的關系隨著大數據的支持被反復驗證。他莫昔芬與血小板的關系將來可能會從不同的分子機制進一步推證。在藥物聯合使用方面,特別注意與CDKI類藥物聯合使用,可能會增加VTE的風險,同時當藥物重新組合聯合應用時,一些本身具有促血栓風險的藥物,進入藥物組合時,很有可能增強藥物的協同作用,增加VTE的風險,聯合使用此類藥物時需要特別注意。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能夠解除癌癥細胞對免疫系統的抑制,促使免疫系統對癌癥組織發起攻擊,除此之外,免疫系統還可能對正常的組織發起攻擊,引起自身免疫性反應,作用到血管,引起血管的炎癥,從而促發血栓,這可能是免疫抑制劑誘發VTE的一種解釋。然而癌癥和癌癥相關治療本身就能夠促進VTE的發生,加之免疫檢查點與VTE的相關文獻大多是個案報道的存在,缺乏大樣本的考證,所以癌癥患者應用免疫抑制劑治療期間發生VTE是否與免疫抑制劑有直接關聯尚未達成統一意見,但是依舊可以為我們提供參考,應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時也需要防范VTE的發生。
關于CVC的使用,指南不建議使用抗凝劑常規預防導管相關的血栓形成,導管應插入右側頸靜脈,中央導管的遠端應位于上腔靜脈和右心房的交界處,建議在外圍插入的中央導管線上使用植入端口[14]。同時盡量減少或避免與含氟尿嘧啶藥物聯用,或改用其他藥物替代,高血壓患者需口服降壓藥。留置PICC后的患肢應該盡量減少更換導管的次數,以減少導管與血管的摩擦引起的血管壁損傷,達到減少血栓形成的風險性。另外可以改變PICC導管的浸泡方法,采用肝素鈉鹽水浸泡,可以降低了置管后導管相關性血栓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