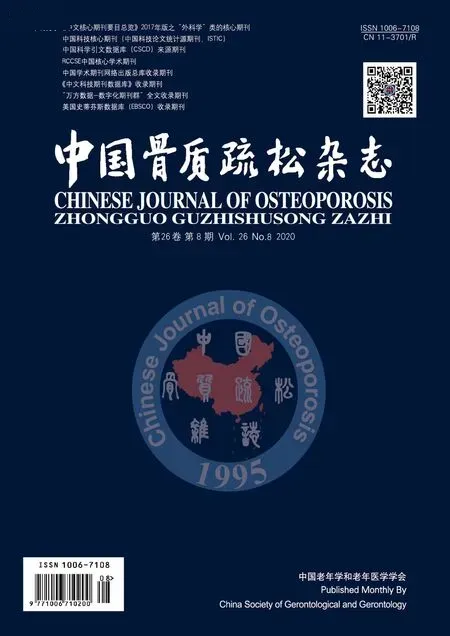穴位貼敷治療原發性骨質疏松癥的研究進展
康石發 李少華 孫堅鋼 袁一峰 黃小生 史曉林
1.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3
2.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浙江 杭州 310005
骨質疏松癥是一種骨代謝性疾病[2],從微觀角度分析[3],已經發生骨質疏松的骨微觀結構惡化,骨小梁減少,且小梁骨總體積減少,在外則表現為疼痛、變矮和駝背[4]等。據數據統計分析[5],骨質疏松癥的患病人數每10年男性和女性分別將增加約15%和20%,年齡大于40歲的人群中患病女性遠多于男性。我國是人口基數大國,老齡化面臨嚴峻的形勢,而骨量會隨著年齡的增加逐漸丟失,60歲以上人群占總人口的10.1%。50歲以上的男、女患病率分別約為14.4%、20.7%,且呈上升趨勢[6],因此防治骨質疏松不可小覷。隨著患病人數的增多,給我國骨質疏松的預防工作帶來了更高的挑戰。近些年來,穴位貼敷成為防治原發性骨質疏松癥的一種新的中醫療法,綜合了腧穴、經絡、藥物等因素,對內分泌、骨代謝等方面均產生影響。本文將從中醫的視角綜合各醫家相關研究剖析穴位敷貼在防治骨質疏松癥方面的特點,以期為臨床提供理論參考。
1 骨萎的發病機制
骨質疏松癥屬于中醫學骨痿的范疇[7],中醫學認為臟腑虛衰和瘀毒是該病發生的重要原因。
1.1 責之于臟腑
臟腑虛衰是發生骨痿的根本原因[8],五臟藏精神血氣,六腑化谷行津,若臟腑虛衰,百病則生[9],其中腎虛時最常見的病因,腎主藏精,精生髓化血以養骨,腎與骨有著密切聯系,腎精充足則骨骼強健,若腎精不足骨髓便為無水之源,髓不養骨。有研究[10]表明,辨證為腎虛證者其骨密度明顯較低,腎虛則鈣磷代謝受影響,導致骨質疏松的發生;脾胃化生氣血,為后天骨髓之本[11],若脾虛不運,氣血乏源,血無以化精,先天之精得不到充養,則骨髓失養。現代醫學通過對中醫中的脾臟研究后發現[12],脾發揮著消化系統的功能外,還參與物質代謝、人體免疫、神經調節,通過這些途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骨鈣、磷等礦物質的吸收誘發骨質疏松的發生;肝、肺、心三臟,雖在醫學古籍中關于骨痿的記載頗少,但從其功能上分析亦可見其與骨痿的的發生有一定的關系,如肝腎同源,腎虛可引起肝藏血不足;肝血虛亦能導致腎中精氣虧虛[13],肝主疏泄,又可調節氣血津液的運行;肺朝百脈,全身氣血通過百脈流經于肺;心主血脈,可化赤為血,三臟均均通過精氣血影響骨生長發育。
1.2 責之于虛、瘀、毒
年紀越大者骨痿的發病率越高,這與老年人虛、瘀的體質有關,虛、瘀都是骨痿發生的關鍵病機[14]。虛和瘀互為因果,若臟腑虛衰,則無力行血,血滯則瘀成,脈絡瘀阻,新血不生,使虛更虛,致筋脈、肌肉以及骨髓得不到營養而出現疼痛、痿廢日漸骨痿,在虛、瘀相互作用下,久之將導致“毒”的產生,即“虛瘀致毒”論[5,7]。毒[15]是指氣血津液不循常道,臟腑失調,使體內的生理病理產物排出不利,導致氣虛、氣滯、血瘀等,蓄久化為瘀毒之邪,虛、瘀、毒可相互交織,形成惡性循環,影響骨及周圍組織細胞物質交換,骨的微循環障礙。細胞學上表現為骨細胞肥大、痿縮,或變性、凋亡[16]。
2 穴位貼敷的基礎認識及選穴
2.1 穴位貼敷的概念及作用機制
腧穴是人體之氣集中的部位,與經絡之氣相通,而經絡內屬臟腑,外絡肢節,將人體各組織器官聯系在一起[17],是氣血運行的通路。正如《靈樞·本臟》[18]指出,“經絡行氣血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也”。穴位貼敷法是一種將藥物碾粉加入酒精、姜汁和醋調配成藥餅或藥膏敷在穴位上進行透皮吸收的方法,有著悠久的歷史,豐富的臨床積累[19]。藥物用于穴位通過刺激經氣的的集中點而作用于全身的經脈,達到調節經氣、疏通經絡、調和氣血等作用,在藥物和穴位雙重作用下,可將藥物的療效最大化[20]。隨著對經絡的不斷探索,張維波[21]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經絡低流阻通道論,他認為經絡是一種多孔介質通道,因其低流阻特點,組織液、化學物質和物理量可通過該途徑運行。陳傳江等[22]發現該通道有利于藥物刺激腧穴激發經氣,另外穴位貼敷后由于腧穴局部汗水難以蒸發,皮膚水化后皮膚角質層疏松,藥物更加穿透后,進入人體后通過該通道可使中藥的藥理作用充分發揮而達到調節人體的作用。
2.2 穴位貼敷防治骨痿的選穴
李慧敏[23]經過對各醫家臨床研究進行分析,發現經絡選用偏向于足太陽經和督脈,選穴則常用足太陽經上的腎俞、脾俞;督脈上的命門;骨之會穴之大杼;髓之會穴之絕骨。此外足三里、關元、太溪等腧穴也可選擇。需注意的是穴位貼敷的運用注重特定穴,可擬腎俞、脾腎、足三里為基礎方,功在調理先天之本,補益氣血之源。吳亞東等[24]認為取穴以足太陽經、督脈為主,亦可取足太陰經、任脈、足少陰經等。其中以命門、腎俞、志室、關元等運用居多。王珊璽等[25]拜讀近10年相關文獻后發現,常用穴以腎俞、關元、足三里、脾俞、命門為主,除督脈和足太陽經外還可選用足陽明經、足少陽經、任脈等。在臨床運用上以脾俞、腎俞、命門等為主,多考慮足太陽經和督脈,足太陽經屬膀胱絡腎,經行臟腑之精氣所輸注的背俞穴,又如《黃帝內經》中記載 “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表明足太陽經與督脈皆與骨聯系密切。
3 穴位敷貼的臨床運用
近年來,我國骨質疏松癥的患病率逐年增加,西醫在治療上多選用鈣劑、雙膦酸鹽、活性維生素D等常規藥物進行防治[26],但需長期用藥,弊端較多。中醫的外治法如穴位敷貼具備療效顯著、無痛或少痛等特點,在骨質疏松防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在慢性病治療方面優勢獨特[27]。
LIN XS等[28]采用天歸散穴位貼敷研究對去卵巢大鼠骨質疏松的影響。實驗將60只去卵巢雌性大鼠隨機分為4組,A組和B組灌胃給藥1 mL/100 mL生理鹽水;C組給予天歸散,組成為肉蓯蓉、牛膝、杜仲、柯拉玉米等配成藥貼敷于大鼠腎闕穴,一天一次;D組喂予碳酸鈣VD3和阿法卡爾西多,觀察12個月。通過檢測BMD、BALP、TRAP-5b和BGP水平及骨組織形態學變化得到實驗數據。統計分析后發現干預后C組和D組的骨密度與A組和B組相比均有明顯改善,而在BALP、TRAP-5b和BGP水平上均顯著下降,最終得出天歸散穴位貼敷可以顯著改善骨密度的結論。高靜等[29]采用子午流注納支法對肝腎不足型患者進行穴位敷貼,方選獨活寄生湯加減,藥用獨活、杜仲、牛膝,桑寄生等補腎強骨,草烏、川芎、細辛、防風、川烏(炙)、赤芍、肉桂、白芥子、當歸、延胡索等活血溫經,打粉后用姜汁糊成膏狀。按時選穴組定為酉時(17:00~19:00)貼敷于陰谷、太溪和大鐘;戌時(19:00~21:00)貼于復溜,非按時選穴組選在巳時(9:00~11:00)貼敷于上訴諸穴,連續貼敷5 d停2 d,2月后進行療效評估,臨床癥狀、體征按消失、明顯改善、稍好轉、加重或無變化對應臨床愈合、顯效、有效、無效等4個級別;證候積分減少率按≥95%、70%~95%、30%~70%、小于30%與這4個級別進行對應。發現按時取穴組和非按時取穴組在SOP治療上均有效、顯效或臨床愈合,但是前者療效明顯優于后者,前者在緩解疼痛,改善功能障礙,消除中醫證候、提高生活質量等方面療效更為顯著。同年,胡陽等[30]做了相同的研究并發文指出采用獨活寄生湯加減配成穴位敷貼治療該病還可改善功能障礙,緩解焦慮,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呂文靜[31]認為采用穴位貼敷的方法可以顯著緩解患者腰部疼痛的癥狀,研究如下。方用杜仲、紅花、伸筋草、川斷、透骨草等,意在活血化瘀,補腎健脾,將藥物打粉加醋汁配制成小顆粒狀用于貼敷,穴位取腎俞、脾俞、肝俞及阿是穴,評價采用6級評分計算疼痛積分,從0級~5級依次為無疼痛、負重后疼痛、活動后疼痛、休息痛、運動受限、需服藥止痛,級數即為分數,每級疼痛按輕、中、重依次記為1分、2分和3分,二者分值乘積為最后得分。該項研究療程為2年,將所得結果統計分析后發現穴位敷貼法在疼痛的緩解方面優于“鈣劑、維生素 D”組,疼痛積分明顯較低,且疼痛緩解時間明顯縮短。馬俊義等[32]利用肉桂、淫羊藿、狗脊等三位中藥研成粉末后進行提取,制成巴布膏貼敷于關元,命門、腰陽關,三焦俞、大腸俞、膀胱俞、腎俞、氣海俞等腧穴,療程一年,分別在治療前、治療后檢測OPG、RANKL含量,采用雙能X線測定髖關節BMD值。通過與“鈣爾奇D片和善美片”組比較后結論如下:穴位貼敷療法在緩解疼痛和肌痙攣癥狀方面效果顯著,各觀察指標如髖部骨密度和血清中 OPG含量正向改變更加明顯。張柱基等[33]就牛萸散治療骨質疏松癥進行觀察性研究,將組方中牛膝、干姜、吳茱萸、肉桂、丹參等幾位藥打粉調配成膏狀,取適量于輸液貼覆蓋在懸鐘、氣海、涌泉、大杼、腎俞、關元、命門等腧穴上,療程為6個月,治療后搜集疼痛、骨代謝生化指標、FPG、2hFPG水平、BMD值等結果進行分析,得知牛萸散穴位用藥聯合西藥治療要遠遠優于單純西藥治療,可使骨質疏松性疼痛感降到更低、使ALP骨吸收標志物水平更低,骨量提升更高。何康宏[34]使用肉桂、狗脊、露蜂房,腧穴取命門、氣海俞、三焦俞、大腸俞、腰陽關、關元俞、腎俞。每貼敷3個月停1個月,1年后將治療前的BMD值、VAS疼痛評分、各骨轉換指標和 生活質量評分分別和治療后第4、8、12月的對應值進行比較來分析治療效果。研究發現中藥穴位藥貼可提升腰椎BMD值,明顯緩解骨質疏松性疼痛,調節骨轉換負平衡,改善生活質量。
4 穴位敷貼使用的的注意事項
穴位貼敷在臨床上廣泛運用于內外婦兒,其安全性高,但是以下情況應當注意[35~36]:局部皮膚有破損、瘡瘍者或感染者禁用;位于頭面五官和孕婦下腰、少腹部等穴位禁用;治療期間應清淡飲食,避食生冷、魚鮮、辛辣等;貼敷后皮膚局部出現過敏反應,如水泡、破潰,全身性風團、斑疹、紅腫、瘙癢者禁用;皮膚局部出現發紅、灼熱、癢痛者應在醫生評估下使用。
5 小結與展望
抗骨質疏松治療的最終目的是要緩解骨質疏松性疼痛,預防患者駝背畸形而影響心肺功能,降低骨折的風險,以維持患者的生活質量。抗骨質疏松治療雖取得了很好的療效,但防治周期漫長,造成經濟、精神上的負擔。中醫和西醫都在不斷的投入研究,現代醫學認為該病的發生罪魁禍首是人體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另外與丘腦-垂體-性腺軸[37]功能紊亂也有關系。至今為止,各醫家對穴位敷貼法的臨床療效做了大量的研究,證實了其在治療骨質疏松癥并緩解癥狀、預防并發癥等方面療效顯著。中醫學認識到“骨痿”的發生不僅與各臟腑尤其是與腎、脾胃的關系密切,還與虛瘀毒密不可分,因此方藥選用當以補腎強骨、健運脾胃,益氣補血以及活血化瘀為主,如天歸散、牛庾散和獨活寄生湯等。藥物可選淫羊藿、伸筋草、透骨草、杜仲、紅花、川斷、桑寄生、桃仁、肉蓯蓉、獨活和肉桂等。穴位貼敷是將配制成膏劑的藥物敷貼于腧穴上達到治療效果,因此除了藥物本身的作用外,選取的腧穴也會影響該病防治的療效。骨質疏松的發病與足太陽經、督脈、足少陰經、任脈等經脈關系較為密切,在臨床運用時當靈活選用,可取其背俞穴、原穴,募穴等,腧穴可選用足三里、腎俞、脾俞、命門、關元、志室、大杼、絕骨和太溪等。本文所討論的穴位敷貼作為一種中醫的外治療法,其選穴定經,選方用藥離不開中醫理論的指導,在臨床上運用需辨證論治進行個體化治療,其安全性高、成本低廉,發展趨勢光明。但也面臨著諸多問題,例如:運用穴位敷貼法需辨證后進行個體化治療,中醫的診斷和治療因醫生水平差異難以統一,因此無法形成大規模的使用,阻礙了該法的推廣;臨床醫師往往低估穴位敷貼的療效,只是將其作為骨質疏松癥治療的可有可無的輔助療法,沒有得到臨床上的重視;穴位敷貼藥物的劑量、干預頻度、干預時間和個體差異目前尚無統一標準;有關細胞、激素水平的作用機制研究不足,文獻報道缺乏。
穴位貼敷作為中醫藥外治療法,可作為防治原發性骨質疏松的一種新的中醫藥方案探討,以期發揮更好的骨質疏松防治效果,可研究空間大,學者們可通過動物實驗和臨床觀察進一步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