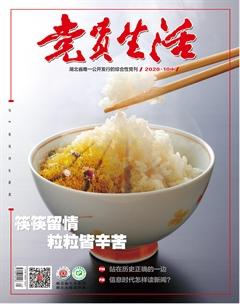古人如何節儉過日子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周易》);“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千百年來,這些耳熟能詳的經典名句奠定了中國文化豐厚的節儉傳統。在國家治理與國家建設中,在千家萬戶的家風家訓中,這種節儉傳統代代傳承,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成由勤儉破由奢”
歷史表明,中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過“緊日子”過出來的。
西漢“文景之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提倡節儉,嚴禁浪費。文帝在位20多年,宮室園林、車馬侍從,均無增加。文帝想做一個露臺,預算下來,要百金,相當中產人家10家的財產總和,便放棄了。景帝也不斷減少自己的開支,從不接納也不許地方送奢侈品,否則以盜竊論,并要求各級官吏“務省徭費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宮宮女也不準穿拖地長衣,帷帳不準用貴重的絲織品。皇帝帶頭節葬,遺詔治喪期間不準影響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不準用貴重的物品陪葬。這樣,國家的開支縮減,官僚貴族不敢濫取民財、鋪張浪費,人民負擔大為減輕,社會上出現了流民還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說就是治奢、治軍、治霸,貴粟積貯,休養生息。
東漢“光武中興”同樣如此。光武帝有鑒于西漢后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成風等積弊,格外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唐代的“貞觀之治”正是得益于厲行節儉的警鐘常敲,給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樣。李世民親身經歷隋朝興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時,說:“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因而,“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偉者皆令毀之”。
在唐太宗的倡導、力行“戒奢從儉”下,“茅茨土階”“惡衣菲食”成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貞觀年間出現了一種好風氣,戴胄一生所住為舊房,死后無祭祀之所;魏徵家無正堂,死后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感嘆道:“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很特殊的一個時期,一方面經濟文化比較繁榮,另一方面對外關系一直表現得較為軟弱。然而,有一點不容置疑,宋朝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崇尚節儉,并且生活上使過“緊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數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種節儉的天性,有著節儉國用、不敢奢侈的傳統。趙匡胤出身于軍人家庭,從小家教較嚴,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習慣。甫一建國就開始帶頭過起了“緊日子”,宮室內一切從簡,“皆尚質素”,窗簾用廉價的青布,平日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沒有多大差別,宮女太監也只有300余名,后來覺得浪費,又遣散出宮50余人。
宋初不僅對官員的服飾有嚴格規定,而且皇室對子女也不例外。有一次,永慶公主回宮省親,趙匡胤發現女兒身上的衣服非常華美,一面繡有貼花,一面鑲了翠羽,光鮮靚麗。他很不高興,對女兒說:“你把這件衣服脫下來,以后也不要再穿這樣華麗的衣服了。你生在富貴之家,千萬不可給這樣的壞風氣開頭。”
在趙匡胤的影響下,此后歷代皇帝都將過“緊日子”制度化。宋代的節儉國用形成了制度,其宮廷開銷、祭祀支出、賞賜大臣等方面都要求節儉。宋朝的宮廷宴會,據宋史記載,分幾個級別,但并不奢侈。頭二盞酒是沒有菜肴的,第三盞時才提供下酒菜。
到宋徽宗時,這一傳統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綱,從浙江等地運往開封供觀賞的花木和石頭,光運費就耗資巨大:“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其結果呢,不僅出現秦檜等生活奢侈的權相,很快又迎來“靖康之恥”。
“從來簡儉是家風”
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歷史上有很多有識之士都以節儉為榮,以奢侈為恥。他們認識到儉有四利,可以養德、養壽、養神、養氣(《鶴林玉露》)。至于具體到家庭,無論是盛世還是亂世,古代中國家庭更是有著一股久遠的過“緊日子”的傳統。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其儉與奢直接關系到社會風氣的好壞,官員之家尤其如此。
《史記·魯世家》載,春秋時期魯國正卿季文子,出身于三世為相的貴族家庭,掌管國政和兵權30多年,輔佐魯宣公、魯成公、魯襄公三代君主,可謂位高權重,他一生忠貞守節,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
歷代名臣巨宦中不少人的家訓,大都以倫理道德為主體,以勤儉持家為根本,彰顯了辯證的節儉觀。
晚清名臣曾國藩以善治家著稱,不僅自己過“緊日子”,一餐只吃一葷,一件衣服穿30年,而且其家訓就倡導過“緊日子”,“能勤能儉,永不貧賤”。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張之洞、梁啟超等大批近代人物都是如此。
因而,會過“緊日子”的人基本上與廉潔可以畫等號。至于歷史上那些世家大族如浙江鄭義門、山西王家大院、福建永定客家人、湖南張谷英村等幾乎家家都是過“緊日子”的好手,他們明白,要想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唯一的辦法就是過好“緊日子”了。
“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
歷史表明,千百年來,過“緊日子”的傳統無關窮與富,到了困難時期,過“緊日子”更是化解困難的良法。從井岡山到延安時期,共產黨的紅色基因里面就有“勒緊褲腰帶”的傳統,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帶頭過“緊日子”。毛澤東常穿打著大補丁的褲子,蓋三斤半的舊棉被,晚上睡覺用禾草做枕頭;“要想著國家,能節約一點就節約一點”的朱德,人稱“時人未識將軍面,樸素渾如田家翁。”
抗戰中,根據地一直是以過“緊日子”挺過來的,1943年《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規定有五點,處處針對過好“緊日子”:(一)不急之務不舉,不急之錢不用,且須在急務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經濟;(二)提倡勤儉樸素,避免鋪張浪費;減少公差公馬,提倡動手動腳;實行糧票制,免去雙重糧的浪費;注意一張紙、一片布、一點燈油、一根火柴的節省;愛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經濟事業,實行經濟核算制;并加強管理和監督,開展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四)愛惜民力,節制動員,不浪費一個民力、一匹民畜;(五)堅持廉潔節約作風,嚴厲反對貪污腐化現象。新中國成立后,朱德曾寫詩道:“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黨和國家多次遇到困難時期,每一次都度過來了,而勤儉建國、過緊日子的方針發揮了重要作用。
“畫棟不久棲,雕梁有壞期;膏粱不久吃,珍饈有斷時。”居安思危,新時代同樣需要發揚古人過好“緊日子”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