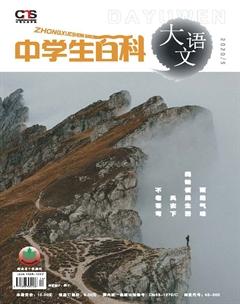呼吸——一個宇宙的毀滅
[美]特德·姜

正是在一座氣體補給站,我第一次聽說了促使我進行調查并導致我最終發現的那些謠言。很簡單,事情始于我們區公告員的一番話。按照傳統,在每年頭一天的中午,公告員要朗誦一段很久以前為這樣的年度儀式而創作的詩文,這個過程需要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公告員提到,他最近一次朗誦的時候,鐘樓在他結束之前就敲響了整點報時的鐘聲,這可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另一人說這是一個巧合,因為他剛剛從附近的一個區回來,那里的公告員也對同樣的事情提出了抱怨。
沒有人過多地思考這件事,只是把它當作看似正常的簡單事實。僅僅過了幾天,有人再次提到了一個類似的情形,又一位公告員的朗誦與鐘樓的時間不符,有人認為這種異常情況也許體現出所有鐘樓共有的機械缺陷,比較奇怪的是,缺陷導致了時鐘變快而不是變慢。鐘表匠檢查了出現問題的鐘樓,但是沒有發現任何缺陷。其實,經過與那些在新年慶典中走時正常的鐘樓相比較,人們發現這些鐘樓后來都一直在準確地計時。
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有些蹊蹺,然而我的精力過多地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面,沒法更多地思考別的事情。我一直都是一名解剖學學生,為了提供后來一些事情的背景信息,我先簡要介紹一下我與這門學科的聯系。
因為我們的生命力旺盛,致命的災難也不常見,所以死亡很少發生。這是一件幸運的事,然而這令解剖學研究難以進行,尤其是很多非常嚴重的事故導致的死者的遺體受損,從而不能用于研究。假如充滿空氣的肺破裂,爆炸的威力可以撕碎我們的金屬鈦軀體,仿佛那是錫做的一樣。過去解剖學家把精力都用來研究四肢,因為這是最有可能完整保留下來的部分。一個世紀之前我上了第一堂解剖課,講師為我們展示了一條完整的斷臂,為了露出里面密集的連桿束和活塞,外殼已經被除去。回想起來,當時的情形我仍然歷歷在目。講師把那只手臂的動氣管連接至掛在墻上的肺,這是他儲存在實驗室里備用的,然后他就能操縱從手臂的殘端伸出的操縱連桿了,那只手也斷斷續續地隨之張開與合攏。
從那以后,解剖學的發展已經達到了可以將殘臂修復的程度,偶爾還能實施斷肢再植的手術。同時,我們也開始有能力研究世人的生理學。我也給別人描述過我親身參與的第一堂解剖課,在描述的同時,我打開自己手臂的外殼,指導學生在我移動手指的時候仔細觀察縮短和伸長的連桿。
盡管有了這些發展,在解剖學領域的核心仍然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巨大難題:記憶。雖然我們了解一些大腦的結構,但是由于它極其精密復雜,腦生理學研究的艱難盡人皆知。在一些典型的死亡事故中,顱骨被打破,大腦噴出一股金粉,里面除了少量破碎的細絲和箔片幾乎沒留下什么,留下的東西卻一點用處也沒有。幾十年來關于記憶的主導理論認為,一個人的所有經歷都被刻在了金箔上,腦部破裂時氣體的沖擊力撕碎了這些金箔,形成了后來發現的那些微小碎片。解剖學家收集起這些小塊的金片——它們薄得可以透過光線,只不過光的顏色會變綠——花上好些年的努力把碎片拼成原樣。他們希望最終能夠破譯死者最近的經歷在金箔上留下的記號。
經過仔細的觀察和不斷增加顯微鏡的放大倍率,我發現空氣管分生出微小的毛細管,與毛細管交織在一起的是一張由金屬絲編織成的致密的格子網,網上掛著金質的葉片。毛細管逸出的氣流使葉片各自保持著不同的狀態,它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開關,因為沒有氣流的幫助,它們就無法維持自身的狀態。但是我猜這些葉片就是我所尋求的開關,存儲記憶的媒介。我看到的漣漪一定就是回憶的表現:葉片的排列方式被讀取出來并傳送回識別引擎。
擁有了這樣全新的理解,我就可以再將顯微鏡對準識別引擎了。在那里我也觀察到了金屬絲網格,不過上邊承載的金葉沒有固定在哪個狀態,而是在迅速地前后撲動,快得我幾乎都看不清。實際上,整個引擎似乎都在運轉,它所包含的網格多于輸送空氣的毛細管,我奇怪空氣如何能連續不斷地吹動所有的金葉。我對葉片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的仔細觀察才發現,它們自身也起到了毛細管的作用,葉片組成臨時的管道和瓣膜,在短暫的時間里使氣流轉向,依次吹向其他的葉片,最后管道和瓣膜還會消失。這是一臺連續變化的引擎,它的一部分作用其實就是改變自身,網格結構還算不上一臺真正的機械,因為它相當于一張紙,識別引擎不停在上面書寫。
可以這么說,我的意識被編碼成這些微小葉片的狀態,不過更準確的描述是不斷改變方向并驅動葉片的氣流。看著這些不停擺動的金葉,我明白了空氣不像我們通常所想的那樣,僅僅為實現思維的引擎提供動力。其實,空氣恰恰就是我們思維的媒介。我們的思維就是一種氣流的模式。我的記憶被記錄下來,不是通過金箔上的刻痕甚至開關的位置,而是依靠持續不斷的氬氣流。
我領悟了這種網格結構的性質之后,一系列結論接二連三地反映在我的腦海里。第一個也是最普通的一個,我明白了為什么造就大腦的唯一成分是金這種最具延展性和韌性的金屬。只有最薄的葉片才能滿足這種機制對于移動速度的要求,只有最精致的細絲才能充當葉片的轉軸。我用筆在銅板上刻下這些文字時會產生一些銅屑,每刻完一頁,我就會把它們掃下來,相比之下,這些銅屑簡直就是粗糙笨重廢料。只有金質媒介才能實現記憶的快速擦除和存儲,而且比任何開關或齒輪的組合要快得多。
接下來我明白了為什么缺少空氣致死的人在安裝充滿空氣的肺之后仍然無法恢復生命。持續的氣流形成氣墊,使網格結構中的葉片在它們之間維持平衡狀態,也使得它們來回的擺動非常迅速。這也就意味著,一旦氣流停止,一切就都丟失了,所有的葉片都垂下來,呈現同樣的懸掛狀態,它們所代表的思維模式和意識都被擦除了。恢復空氣供應無法復原失去的一切。這也是速度的代價,存儲思維模式的媒介越穩定,意識運作的速度就越緩慢。
隨后我查清了時鐘異常的原因所在。我看出葉片移動的速度取決于吹向它們的空氣,充足的氣流幾乎可以使葉片無摩擦地移動,要是它們移動得比較緩慢,那是因為它們受制于較大的摩擦力,只有在支撐它們的空氣墊比較薄和吹過網格的氣流比較弱時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鐘樓的時間沒有變快,其實是我們的頭腦變慢了。鐘擺驅動鐘樓的節拍從不會改變,流過管子的水銀也沒有加快速度,但是我們的大腦依賴空氣的流動,空氣流動得越慢,我們的思維就越慢,從而使我們覺得時鐘變快了。
我曾害怕我們的頭腦可能會變得緩慢,正是這樣的擔心激勵著我進行自我解剖。然而我認為我們的識別引擎——盡管由空氣驅動——最終的本質還是機械式的,這臺機器的某個部分會逐漸疲勞變形,從而造成速度減慢。這本來是一件可怕的事,不過至少我們還有希望能修復這臺機器,把我們的大腦恢復到它最初的速度。
然而,要是我們的思維純粹是氣流的模式,而不是齒輪的運動,這個問題就嚴重得多了,有什么因素可能導致流經每個人大腦的氣流變慢呢?不可能是氣體補給站的配送器壓力降低所致。我們肺部的氣壓特別高,所以空氣必須經過一系列的調節閥降壓后才送到大腦。我覺得思維能力的減弱一定源于反方面的因素:我們的環境氣壓在升高。
怎么可能呢?這個問題一出現,唯一可能的答案也變得明確了:我們天空的高度一定是有限的。在我們目力所及的范圍之外,環繞我們的這個世界鉻墻向內傾斜,形成一個穹頂;我們的宇宙如同一座密室,而不是一口開放的井。空氣逐漸在密室中積累,直到氣壓與地下氣槽中的相同。在這篇銘文最初,我說空氣不是生命之源,這就是原因所在。空氣既不會創生,也不會消失,宇宙中的空氣總量保持恒定。假如我們的生命只需要空氣,那么我們永遠不會死。然而真正的生命之源是氣壓差,空氣從稠密的地方流向稀疏的地方。我們的思維和活動,以及我們所造的每一臺機器的運轉都是靠流動的空氣來驅動的,不同壓力間的相互平衡產生了這種動力。一旦宇宙間各處的壓力達到相同,所有的空氣將不再流動,變得毫無價值。總有一天,我們將被靜止的空氣所圍繞,無法從中獲得半點能量。
其實我們消耗的不是空氣。每天我從新換的肺中獲取的空氣完全從我的肢關節和身體外殼逸出,就是說這些空氣被我排放到身體周圍的大氣中。我只是把高壓的空氣轉換成低壓的空氣。我身體的每一個動作都對宇宙氣壓的平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所考慮的每一個想法,都加速了那個末日的到來。
起初我給別的解剖學家講述我的發現時,他們不相信我。不過,在我進行自我解剖實驗之后的幾個月里,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了我。人們對大腦又進行了一些檢查,對大氣壓力實施了多次測量,結果都證實了我的斷言。我們這座宇宙的背景氣壓的確在升高,從而減緩了我們的思維速度。
這個真相被廣泛了解之后,恐慌開始大范圍傳播,這是因為人們第一次審視“死亡不可避免”這個想法。為了抑制我們的大氣變得稠密,很多人號召嚴格減少活動,對于浪費空氣的譴責逐漸升級為憤怒的謾罵,甚至在有些區,出現了死刑懲罰。考慮到許多世紀之后我們的大氣壓才會同地下氣槽中相同,恐慌平息下來,因此死亡的懲罰也就令人蒙羞。我們不確定這個過程到底要經歷多少個世紀,有人在進行和討論進一步的測量和計算。同時,大家開始廣泛地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度過余下的時間。
有一個團體致力于實現逆轉氣壓平衡并發展了許多信徒。他們之中的機械師制造了一臺機器,它從大氣中獲取空氣,用外力使之體積變小。他們將這個過程稱之為“壓縮”。機器把空氣恢復到儲氣槽的氣壓,那些逆轉主義者興奮地宣布這為一種新型補給站的建造打下了基礎,這種補給站——和它填充的每一個肺——不僅為個人賦予了新生,而且也激活了整座宇宙。唉!仔細檢查一下這臺機器,你就會發現它致命的缺陷,機器本身由儲氣槽中的空氣提供動力,充滿一個肺要消耗更多的空氣。它不能逆轉氣壓平衡,反而和世上萬物一樣,只能加劇這個過程。
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信徒在這樣的挫敗之后幻想破滅,但是逆轉主義者作為一個團體卻沒有躊躇不前,而是提出新的設計,用展開的發條或落下的重物為壓縮機提供動力。機械師沒有獲得更好的結果,每一根旋緊的發條都意味著上發條的人要釋放空氣,每一個高于地平面的重物都表示舉起它的人要釋放空氣。在這座宇宙中,所有的動力源最終都由氣壓差產生,總而言之,沒有什么機器的操作能增大氣壓差。
逆轉主義者繼續從事他們的工作,他們確信總有一天會造出一臺機器,使產生的壓縮空氣比消耗的多,那將是一個永恒的動力源,補充著宇宙失去的生命力。我不像他們那么樂觀,我相信氣壓趨于平衡的過程是不可動搖的。我們宇宙中所有的空氣最終會均勻分布,不會有哪個地方更稠密或更稀疏,活塞無法驅動,旋翼無法轉動,就連頭腦中的金葉都不再運動,氣壓消失、動力枯竭、思維凝固,宇宙達到徹底的平衡。
有人會對這樣的情況感到諷刺,我們的腦研究沒有為我們揭示過去的秘密,反而展現了我們最終將走向怎樣的未來。然而我堅持認為,我們其實了解到一些有關過去的重要事實。宇宙的開端仿佛是深吸一口氣,然后屏住了呼吸。沒人知道為什么,然而不管原因如何,我很高興宇宙以這樣的形式誕生,因為我的存在也要歸因于此。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正是我們的宇宙緩緩呼出的氣流。在這漫長的呼氣結束之前,我的思維將一直存在。
所以我們的思維也許會盡可能地被延長,解剖學家和機械師們正在研制腦部調節閥的替代品,作用是逐漸提高大腦內的氣壓,使它保持高于環境的氣壓差。一旦這種閥安裝到體內,即使我們周圍的空氣變得稠密起來,我們的思維速度大體上也會保持不變。可是這并不意味著生活不會改變,氣壓差最終會降低到令我們的肢體虛弱、行動遲緩的地步。到那時我們也許得減緩自己的思維,這樣身體的遲鈍才不那么明顯,不過這還是會導致外界的一些過程看上去像是在加速。隨著鐘擺瘋狂地擺動,嘀嗒的時鐘好像變成了叫個不休的鳥兒,墜向地面的物體似乎受到了彈簧的推動,舞動的繩索仿佛成了噼啪作響的皮鞭。
我們的肢體將在某個時刻完全停止活動,我無法確定末日臨近時各種問題出現的正確順序,但我想,情況會是這樣:我們的思維將繼續運作,所以我們像雕像一樣無法動彈的同時還保留著意識。也許可以說話的時間還要更長一些,因為我們的聲匣工作時需要的氣壓要比肢體小。但是由于無法前往氣體補給站,每次講話都會消耗思維所需的空氣,思維完全停止的結局就離我們更近了一步。為了延長思維能力而保持沉默和在交談中走向最后的終結,哪個選擇更好一些呢?我不知道。
在我們停止活動的前幾天里,也許有一些人可以將大腦調節閥直接連在補給站的配送機上,其實就是用偉大的世界之肺代替了自己的肺。要是這樣的話,那些人直到氣壓完全平衡的最后一刻都能夠保持清醒。我們這座宇宙中所剩的最后一絲氣壓也將在驅動一個人思考的過程中消耗殆盡。
隨后,我們的宇宙將進入絕對平衡的狀態,所有的生命和思維都將停止,時間也因此而失去意義。
不過我還懷有一點渺茫的希望。
盡管我們的宇宙是封閉的,不過在無窮大的固體鉻中,它也許不是唯一的氣室。我推測別處可能還有一個,不同于我們的另外一個,甚至體積更大呢。這個假想的宇宙可能有跟我們一樣或者更高的氣壓,然而,假如它的氣壓比我們的更低甚至是絕對的真空呢?
把我們同那個假想宇宙分隔開的金屬鉻厚得我們都無法鉆透,所以我們不能憑借自身力量到達那里,也就沒辦法從我們的宇宙中釋放掉過剩的大氣并以這種方式重新獲得動力。但是我想象這個宇宙鄰居有它自己的居民,他們的能力超過了我們。假如他們可以在兩個宇宙間開拓出一條管道,并安上閥門從我們這里向那邊釋放空氣,那我們該怎么辦?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宇宙當作儲氣槽,開動配送機充滿他們的肺,用我們的空氣發展他們的文明。
為我提供動力的空氣還能驅動別人,助我刻下這些文字的空氣有一天會流過別人的身體,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欣慰。我沒有欺騙自己,認為這會是我再生的方式,因為我不是那些空氣,我只是空氣流動模式的體現。
然而我還懷有更加渺茫的希望:另外那個宇宙的居民不僅把我們的宇宙當作儲氣槽,而且一旦用盡了這里的空氣,他們哪天也許能開辟出一條通道,親自來我們的宇宙探險。他們可能會在我們的街道上徜徉,觀察我們僵硬的身體,研究我們的財產,驚異于我們的生命。
我作這篇說明的原因即在于此。我希望你就是其中的一位探險者,我希望你發現這些銅板并破譯表面上的文字。不論你們的大腦是否由我思考時消耗的空氣所驅動,通過閱讀我的文字,你的思維模式就模擬了我曾經的思維模式。以這種方式,我從你身上獲得了新生。
你的探險者同伴們將會讀到我們留下的其他書籍,通過你們合力思考,我的整個文明重獲新生。當你們走在我們寂靜的街道上,想象著這里曾經的樣子,鐘樓鳴響,補給站里到處都是閑聊的鄰里,公告員在公共廣場朗誦詩文,解剖學家在教室里上課。下一次你觀察周圍這個靜止的世界時想象一下我描述的這一切,這樣它就會在你的腦海里重新變得充滿活力、生機勃勃。
探險者,我希望你一切順利,不過我懷疑,降臨在我們身上的命運會不會同樣也在等待著你們?我能想象得出平衡的趨勢不僅僅是我們這個宇宙才有的特征,而是所有宇宙的內在性質。也許我的目光短淺,而你們的人已經發現了一個真正永恒的壓力之源。然而我的思索已經是異想天開,我會假設你們的思維有一天也會停止,不過我無法弄清那將是在多遠的未來。你們的生命將和我們的一樣終結,沒有人能逃脫。不管需要多久,最終的平衡一定會達成。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知道了這樣的結局就感到悲哀,希望你們的探險不僅僅是搜索充當儲氣槽的其他宇宙,還希望你們是在求知欲的激發下,渴望見識宇宙呼出一口氣能產生什么。因為即使一座宇宙的壽命可以預測出來,宇宙中生命的多樣性卻無法統計。我們蓋起的建筑,我們創作的美術、音樂和詩句,我們各自的生命:沒有一個可以預測,因為這些都不是必然的。我們的宇宙在滑向平衡點的過程中也許只能靜靜地呼氣,而它繁衍出我們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卻是個奇跡,只有誕生了你們的宇宙才能與之媲美。
探險者,盡管你讀到這里的時候我去世已久,但我還是要送你一句臨別贈言。仔細想想,得以存在便是一個奇跡,能夠思考就是一件樂事。我覺得我有權告訴你這一點,因為在刻下這些文字的同時,我就是這樣想的。
(節選,有刪改)
賞析
本期的《今聲》欄目,我們節選了來自中國和美國的兩篇科幻小說。同在科幻的范疇里,兩則故事的立意和表達手法大相徑庭,這印證了小說可以帶來無限可能;作者同是華人,享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卻表達出不一樣的情懷。特德·姜曾數次獲得雨果獎和星云獎,他創作了一系列構思精巧、腦洞大開的短篇小說,其獲獎作品《你一生的故事》被拍成電影《降臨》,還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本期選的是相較而言略顯復雜的《呼吸——一個宇宙的毀滅》,文中對復雜機械的細致描寫乍一看來仿佛天書,閱讀起來有一定的困難。但這篇小說就像夏威夷果,營養豐富、風味卓絕的果肉被包裹在精密儀器和陌生名詞之下,等待讀者拎著名為耐心的小錘子將它砸開。讀完之后再回頭,又會發覺每一段看似過于冗長的背景交待都有其存在的意義,節選起來也格外難以取舍,真正做到了用不長的篇幅傳達恢弘的立意。在你翻開這篇小說的時候,恐怕很難想到以空氣和社交開頭的故事,能在閱讀中帶領讀者參透宇宙的秘密,最后故事以宇宙毀滅告終。這或許是科幻小說引人入勝的原因,知道了開頭,往往無法猜出結尾。又或許因為我們難以參透自己宇宙的奧秘,所以采用上帝視角鉆研虛構的宇宙顯得特別的激動人心。當然,沒有什么完美的設定,哪怕是文中精巧靈活、強健聰明的異星人也有阿喀琉斯之踵。且不論殘缺是否為他們的文明披上凄美的面紗,不盡完美的設定恰好能突顯宇宙中最不可思議的奇跡——能夠存在、思考、延續。
特德·姜令人十分佩服的一點是,每次寫作都在挑戰全新的領域——語言學、熱力學等——每次能做到對不同領域的條條框框如數家珍,不會因為只是寫作幻想小說而放松對真實性的要求。雖然說作家的工作是寫作,但為了寫出真實可信的故事,塑造能引人共情的角色,必須跳出身為作家的舒適圈,做足調查研究,同時還要完全從筆下人物的角度出發,讓人物的言談舉止符合他們的身份——或者像在這篇文章中一樣,使角色符合他們的宇宙規律。一個從基礎到規則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宇宙,會有什么樣的文明,會有什么樣的價值觀,與我們在不同之外或許還有相似之處……讓人不禁對未知充滿了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