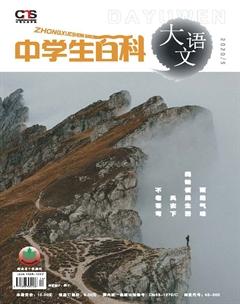且觀野草生新芽
袁嘉璐

繼“野草書店”告別北大,許多網友對實體書店的發展表示了擔憂。在我看來這實屬多慮,對于自有生命力的“野草”,野火不盡春風生,但觀野草抽新芽。
觀之當下中國經濟現狀,野草書店的暫時退出并不是沒有原因。“互聯網+”經濟形態發展勢頭迅猛,在書店經營領域也早已遍地開花。當當、亞馬遜等電商大行其道,眾多電子書產品也改變著人們的閱讀習慣,大部分書商、出版社都已采用“互聯網+”形式,采取線上主打、線下供應的鏈條模式。可以說,實體書店作為銷售平臺和閱讀平臺的功能已不再突出,基本優勢正在不斷喪失。
而在這個更新速度提高百倍、行業形態日新月異的時代,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誰無疑就把握住了未來。一部野草書店的興衰史,基本反映出產業發展的普遍規律。“野草書店”在新文化運動后成立,對魯迅先生雜文集《野草》名字的繼承恰好展現了北京大學作為青年革命陣地的時代特點,此之謂“生逢其時”。而如今,互聯網對實體經濟提出了更高要求,野草書店卻固守幾個書架、一桌一椅,局限于學生閱讀銷售功能,此之謂“夾縫求生”,終被淘汰。
然而,今天的野草也并非一無是處,實體書籍、具有文化氛圍的線下空間,是其最大的優勢。如何找準實體書店的時代定位,如何打造實體書店的新形象,這才是時代對實體“野草”提出的根本性問題。
《周易》有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既已同為書界同仁,線上書店滿足人們閱讀的物質需求,實體書店便應擔當起文化載體之責,打造一方承載文化的精神角落。
書店中不只有書,就像森林中不只有樹。森林能涵養起一片生態,實體書店也能憑借其實體文化產品構建起文化生態空間。教育部指導意見指出,高校要創辦與本校特點相適應的校園實體書店,即是貼近教育、學術要求,打造校園學習、文化研討的生態空間;西安啟味閱己書屋藏身城墻遺址公園,造型設計新穎,集文創、咖啡、文化活動于一體,打造了城市居民精神棲居的生態空間……實體書店既要跳出傳統閱讀平臺、銷售中間商功能的限制,又要以自身“行走的文化”優勢為依托,做好店內規劃設計,找準各店優勢特點,做文化生態的打造者,做精神需求的服務者。
白紙一尺室一方,留得人間草木心。藏書何必千萬卷,且觀野草生新芽。
點評
作者對書店的意義、實體書店在現代社會的生存之道進行了深入辯證的思考,從“野草書店”的名字想到了魯迅先生的散文集,進而想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思路靈活又將討論對象放到更廣闊的歷史空間去評價,格局開闊,這是本文的一大亮點。從魯迅到《周易》,再到結尾的小詩,文章文采飛揚,作者是看書人、愛書人,也是善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