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條捷徑永遠存在
張引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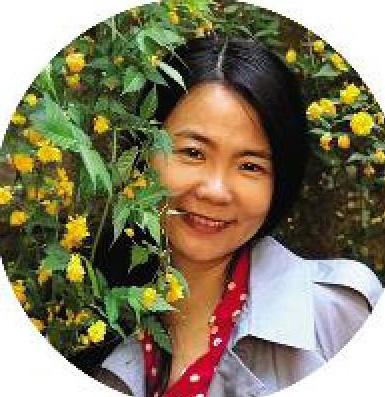
我家住在中央美院附近。臨近考試時,我經常看見背著畫夾的學生在小區附近進進出出,想必他們是在學院附近的培訓班強化訓練。
有一天下午,我去美院看畢業展,很偶然地和站在我旁邊的一位正在讀大二的油畫系學生聊了起來:
“什么時候開始學畫畫的?”
“5歲,上幼兒園大班時,父母給我報了畫畫的課外班。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已經畫了15年了。”
“15年?不煩嗎?畫了這么久。”
“不煩,每天都能畫畫,挺開心的!”
我想起木芽風提到學長告訴她高三一整個學期都要參加美術集訓,得從早上7點畫到晚上12點,她覺得太辛苦了。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一部分競爭對手是從5歲就開始畫畫,與她同時間考試時,已經比她多花了10年時間練習。
木芽風知道選擇美術要整日整夜地練習,也知道學習編導要在文化課上非常努力。所以,她可能不是不知道該選哪一條路,而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有勇氣豁出命地去努力——或徹底提高學習成績,或拼命提高繪畫技巧,這兩條路選擇哪一條都可以,但無論選擇哪一條,看起來都不太容易。她想在這兩條路里找一條捷徑,可惜這里沒有;況且捷徑都特別短暫和不牢靠,讓人心虛。最重要的是,捷徑不會永遠存在。
一位心理學家說過一個關于“吃苦”的觀點,我是非常認同的。他說:“今天我們談到吃苦,不再是吃不飽穿不暖,而是能不能耐心地只做一件事,并且做到最好。”我們已經不能忍受當下的枯燥和乏味,對于刻苦和努力也很不屑,總覺得無須這些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東西。但是,這真的不行,每個目標的實現都要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三個腳印也是一種妄想。
日常的生活中,想得太多做得很少的時候,我經常會想起陳丹青在賈樟柯的一本書的序言里寫到的一段話:什么叫作救自己呢?就是忠實自己的感覺,認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煩,不要放棄,不要敷衍。哪怕寫文章時弄清楚標點符號,不要有錯別字——這就是所謂的自己救自己。我們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筆一筆地畫畫,賈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膠片。
其實木芽風同學面臨的處境和陳丹青、賈樟柯是一樣的,若選擇了畫畫,要一筆筆去練習;若選擇了編導,要一道道去做題,一天天提高考試成績。就這樣,沒有別的辦法。選擇了什么,最終都是要靠自己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完這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