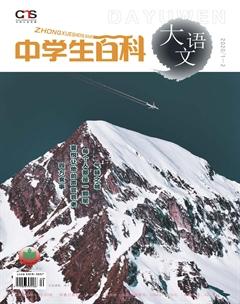成為演員的安藤櫻
陳竹

我只能責怪自己太不識泰山,直到去日本第三年,學戲劇的我才知道有一位叫作Sakura Ando(安藤櫻)的演員在日本影視作品里多么千姿百態。若是她沒有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中演繹一位冷暖有情的媽媽,那么我與她只會是“相見更晚”。平時不太關注某個演員的我也開始留意這朵“櫻”,在何時何處如何綻放。
再看她是《百元之戀》,一部完全以她飾演的喪女為視角展開的作品。她把自己胖成滿身肥膘,扮演一位寄生于家庭、不工作整天打游戲等飯擺上桌的“家里蹲”。外出做的唯一的事是騎腳踏車去百元商店買一大堆的零食,回來繼續填補空虛的自我。她的活動距離是從家到百元商店的區區幾百米,人生意義是在與家人的相處中,永遠可以做到讓對方和自己一樣不爽。日本電影里有很多這樣的人物,并非杜撰。因為不愿意面對一個規則嚴密充滿壓力、注重人際關系的社會,有一部分中青年會選擇拒絕或盡量少與外界接觸,過著最低成本的生活。
《百元之戀》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同樣是描繪都市里的落魄者,但區別在于后者是靠戲劇沖突和情節來建立語境,而前者是專攻角色的外在行動與內心顫動。
這種內心顫動的表現在于,安藤飾演的一子在和家人鬧翻離家出走之后,看到拳擊手男朋友如何被打倒在拳臺上,同時開始思索——什么是“痛”。這種感受是曾經那個成天好吃懶做閉門不出,只會在拳擊游戲里充當勝利者的她所完全無法了解的。在那個晚上,習慣了傷害親人的她,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什么是“被傷害的痛”——被熟悉的人侮辱。這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受傷必定是離家獨立需承受的代價。在經歷被動的傷痛后,她選擇主動出擊——參加拳擊練習,且一心想打拳賽。不是要贏,更不為咸魚翻身。她真的不知道再怎么努力訓練,打得再像那么回事,上去就干得過別人嗎?做事只憑直覺從不計后果的她也許真的不知道。但她知道只有像那個甩掉了自己的男朋友一樣走上拳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痛”,而不只是像練習時總有教練在身旁保護,“1、2、3、4”地出拳只知“累”不識“痛”。電影不落俗套的地方在于沒有讓安藤做“女洛基”,不走入小人物實現夢想的結局。最后,當和前男友和解手牽手,兩個比賽失敗者走出拳館時,時間是否已經在兩人身上發酵?
看到安藤在電影里完成從外型到內心的蛻變,我無法不成為她的影迷。我懷疑立志做演員的年輕女演員少有會以安藤拓展的人物作為奮斗榜樣,因為:不夠好看。“看起來好看”對于安藤來講重要嗎?至少從她呈現的銀幕形象來說,“好不好看”“漂不漂亮”這個問題不是所有,而只是一部分。或者說,是在努力追求“美”的那個過程,即使凸顯出了人性的丑惡或窘態,那亦可能是美。
回頭看我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安藤櫻呢?好像數不出來。前一段時間,姚晨在網絡上發出“控訴”,期望新生代的導演們也可以考慮考慮像她一樣的中生代女演員。仔細一想,到底是我們沒有像安藤櫻這樣的演員,還是沒有這樣的電影(角色)給她們來演繹?又或者,再問一問坐在銀幕前的我們:作為觀眾,是否允許銀幕上的那個角色以一個“不夠好看”“不夠圓滿”的人幫我們進行自我欲望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