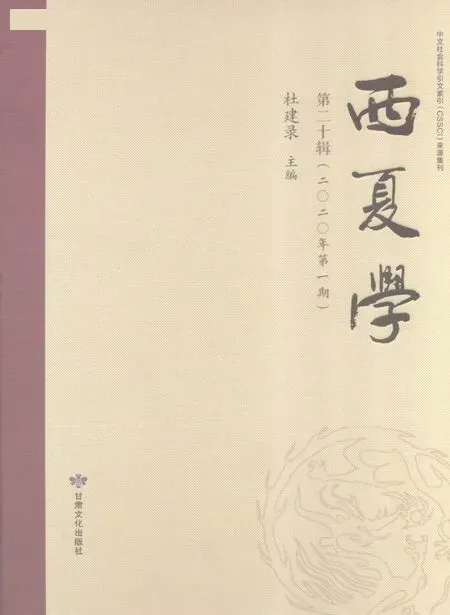《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的西夏譯本
麻曉芳
一
《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系密宗佛經。這部佛經短小精悍,結構簡單,講述的是佛與諸菩薩在日月天宮,東南西北四佛各從本國來此集會,應日月天子之請,由佛說出兩則陀羅尼。該佛經的西夏譯本1909年出土于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黑水城遺址,今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以及英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已知的編號有兩個:俄藏著錄中存編號Инв.No.607孤本文獻一件,為5葉經折裝殘片;英國國家圖書館另藏有一葉殘片,編號Or.12380-2289(K.K.II.0237.p)。《佛說智炬陀羅尼》已知的存世文獻僅此兩種6葉殘損經卷,因此并未引起學者注意,也未曾被釋讀與研究。
西夏文《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經題首見于克恰諾夫和戈爾巴喬娃的《西夏文寫本與刊本》第149號《佛說智炬破壞阿鼻地獄陀羅尼經》,俄藏編號為Инв.No.607,對應梵文佛經①З.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cтр.102.。西田龍雄先生在《西夏文佛經目錄》第208號也記錄了此佛經。對于這部佛經是否為漢傳文獻,他持懷疑態度,并在目錄中同時列出了于闐三藏法師提云般若所譯大正藏第1397號《智炬陀羅尼經》及藏文佛經Hphas-pa ye-shes ta-la-la shesbya-bahi gsungs hgro-ba thams-cad yongs-su sbyong- ba(《圣智炬陀羅尼能凈一切趣》)兩種對應佛經①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Ⅲ,京都大學文學部,1977年,第43頁。。克恰諾夫在《西夏佛典目錄》中詳細記錄了版式與內容,即:寫本,麻紙經折裝。9.7厘米×7.4厘米,板框高12.2厘米。殘存卷首5折,每折5行,行8字②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cтр.446.。內容為卷首至“我等云何從諸如來及……”,殘卷尾。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Or.12380-2289(K.K.II.0237.p)號文獻,僅存一葉殘片,刊布于《英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冊,原題“佛經”③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英藏黑水城文獻》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頁。。張九玲定名為《佛說破壞阿鼻地獄智炬陀羅尼經》殘片并描述其版式為:刻本,上下雙欄,行8字,存5行④張九玲:《〈英藏黑水城文獻〉佛經殘片考補》,《西夏學》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0頁。。英藏殘片存佛經尾部一葉40字,內容為陀羅尼頌畢后普賢菩薩對日月天子所說之言。
英、俄兩地所藏《佛說智炬陀羅尼經》殘片分別對應佛經卷首及卷尾,中段陀羅尼部分卻不見于各地所藏西夏文獻。在考察俄藏Инв.No.6806號文獻時,我們發現這個編號文獻由一系列佛經殘葉拼湊而成,其中就有《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的陀羅尼部分。本文將探討6806號文獻,對不同殘片予以定名,并將《佛說智炬陀羅尼經》陀羅尼部分與此前已知兩種殘片綴合,旨在還原整部佛經原貌。俄藏Инв.No.6806在此前的研究成果中均被定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關于此文獻最早的著錄見于克恰諾夫和戈爾巴喬娃的《西夏文寫本與刊本》第381號《金剛經》。克恰諾夫《西夏佛典目錄》將其歸入《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系列文獻中,并描述其版式為:刻本,經折裝。9.5厘米×7厘米,板框高13厘米,共存74葉,殘卷尾。上下雙欄,每頁5行,每行8字。核查上海古籍出版社蔣維崧、嚴克勤二位先生20世紀末在圣彼得堡拍攝的照片,Инв.No. 6806號共25頁照片圖版,各葉版本形制十分接近卻略有差異:前14頁每行10字,刻板字體筆畫較細,字間空白處有補花多種。第15頁圖版之后字體筆勢與前者略有不同,筆畫較粗,每行8字,字間空白處偶見“二”“三”“六”等漢文數字。
二
日本學者荒川慎太郎在考察《金剛經》的西夏譯本時,確定Инв.No.6806號圖版第1—14頁為《金剛經纂》一卷,第14頁后二折為《金剛般若真心》及咒語。他懷疑圖版第15頁后可能混入了《大莊嚴寶王經》①荒川慎太郎:《西夏文〈金剛經〉的研究》, 東京松香堂,2014年,第50頁。。荒川慎太郎疑存的《大莊嚴寶王經》,經對照實為《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第四卷內容的摘抄。這段摘抄前是一段完整的《釋迦牟尼滅惡趣王根本咒》,全段咒語此前未見于已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僅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拔濟苦難陀羅尼經》中有一句近似的陀羅尼②聶鴻音:《俄藏西夏本〈拔濟苦難陀羅尼經〉》,《西夏學》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頁。。《釋迦牟尼滅惡趣王根本咒》錄文如下,漢文本參照西夏智廣編集的《密咒圓因往生集》③本文使用【】指示圖版頁次,【1】—【5】為俄藏Инв.No.607號;【19-1】為俄藏Инв.No.6806號圖版19第1葉;【2289】為英藏Or.12380-2289號。:

此外,Инв.No.6806文獻共涉及五種不同的佛經殘片,即《金剛經纂》《金剛般若真心》《佛說智炬陀羅尼經》《大莊嚴寶王經》和《釋迦牟尼滅趣王根本咒》。佛經文獻與圖版頁次對應如下:
1.《金剛經纂》 【1-1】 ——【14-2】【25】
2.《金剛般若真心》 【14-3】——【14-4】
3.《佛說智炬陀羅尼經》 【15-1】——【19-2】
4.《大莊嚴寶王經》摘抄 【19-3】——【20-3】【21-3】——【24】
5.《釋迦牟尼滅惡趣王根本咒》【21-1】——【21-2】
Инв.No.6806文獻圖版經多次拼合,內容次序錯亂。這些殘葉中還包括《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的咒語部分,無論是筆體還是版本形制都與英藏Or.12380-2289十分一致,應為同一文獻散斷而成。經與英藏及俄藏殘片綴合后,基本可還原整部佛經原貌,尤其是還原了完整的陀羅尼部分。
三
下面將俄藏Инв.No.607,Инв.No. 6806以及英藏Or.12380-2289三種西夏文殘片進行綴合,并做全文解讀。漢文參照《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第914頁提云般若譯漢文本《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為清晰對照,我們省略了漢文陀羅尼原文中煩瑣的語音標注。陀羅尼部分夏漢不一致之處以陰影標注。




說明:
(1)漢文本經題作《佛說智炬陀羅尼經》。
(2)“超哄”,西夏文常譯作“發生”,這里與漢文本“從”對譯。
(3)恭敬頂禮,漢文本作“頭頂禮敬”。
(4) 此處西夏本缺“及菩薩所,而得發起一切眾生光明破諸黑闇滿十方智炬陀羅尼耶。以是陀羅尼力故,當令我等能為眾生作大明炬。”
(5)西夏文“翬”,擬音為pja1,與漢文陀羅尼“迦”及藏文kā對音不符,疑誤。
(6)此段陀羅尼據提云般若漢文本對譯。
四
一般認為,漢文《佛說智炬陀羅尼經》凡兩譯,流傳最廣的版本由于闐高僧提云般若在唐代譯出。他在洛陽譯經時間短暫,唯有六部佛經,《佛說智炬陀羅尼經》就是其中一部。到了北宋時期又有施護所譯《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見大正藏第1398號。實際上,這部經還有更早的譯本,就是百余年前隋代阇那崛多譯出的《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智炬陀羅尼經》是這部經第三卷的部分節選。西夏譯本題為《緽銅慶繆恥笗履牡箎溝綒茸碃瞲其》(《佛說阿鼻地獄破壞智炬陀羅尼經》),雖然經題與三種漢譯本都不一致,也不同于藏譯本經題《圣智炬陀羅尼能凈一切趣》,但是內容可以與漢文本相對應。
下面我們將西夏譯本分別與阇那崛多、提云般若及施護的三種漢譯本作以對照,西夏文文選擇陀羅尼后佛告日月天子之言。

?
根據相應片段對照,西夏譯本可以與提云般若譯本最為接近,詞句可以嚴整對應。另外,從陀羅尼在佛經中出現的位置來看,《佛說智炬陀羅尼經》中的陀羅尼雖為連綴在一起的大段,但是實為兩段不同的咒語,即《大藏全咒》中“護眾生咒”第一咒與第二咒。在存世的漢、藏及西夏譯本中,西夏譯本、提云般若譯本中的“護眾生咒”兩咒合二為一,連綴成一段,沒有分隔。而施護譯《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阇那崛多譯《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及藏文《圣智炬一切趣清凈陀羅尼》將兩段咒語分開,陀羅尼前后分別有其他經文。因此我們判斷西夏譯《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的翻譯底本為于闐三藏提云般若的漢譯本。
五
在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原則中,第一種不翻的原則“秘密故”往往指陀羅尼。陀羅尼咒語只能音譯,念誦發音要求非常準確。因此佛經的陀羅尼常常間隔一段時間就要校正或重譯。在西夏仁宗時期就曾對前代佛經進行了大規模的校正工作,西田龍雄、聶鴻音、孫伯君、孫穎新等在對照《法華經》《仁王經》《圣曜母陀羅尼經》《無量壽如來會》等佛經的初譯本與校譯本時發現,重新審定陀羅尼用字是仁宗時期校經的重點之一。仁宗時期新確立了一套陀羅尼翻譯規則,與西夏早期陀羅尼對音規則多有不同。最顯著的特點是校譯本中的陀羅尼開始使用大小字組合,盡可能表現梵文的復輔音和塞音收尾的音節,力求使誦經人在念誦咒語時最大限度地接近梵文①聶鴻音:《〈圣曜母陀羅尼經〉的西夏譯本》,《寧夏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第86—90頁。。孫伯君將西夏時期新譯佛經陀羅尼標音用字規則歸納為:自造陀咒語專用譯音字;梵語復輔音聲母使用大小雙字表示;加注“剩”表示長元音;使用小字表示部分輔音收尾的音節等②孫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經實踐》,《寧夏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第89—98頁。。
西夏譯《智炬陀羅尼經》是典型的漢傳密教佛經,雖無初校譯本可用以對勘,但是從陀羅尼部分能夠明顯看出參照梵藏本陀羅尼校正過的痕跡。咒語對音用字的特征可與仁宗校譯佛經咒語的諸多特點相合。例如:
第一,西夏譯本使用雙字表示梵語中的復輔音聲母或輔音韻尾,后一個西夏字多為小寫,復輔音和輔音韻尾與藏文本一致。梵文kur,西夏譯本作“窾蝚”ku1rjur2,漢譯本作“屈”。西夏本中使用“蝚”rjur2對應輔音尾-r,漢文本中無相應對音字。
第二,西夏本對梵文頂音和齒音不做區分,使用相同西夏字對音。t和t都使用硯tji2對音;漢文本中則頂音使用知組字,齒音使用端組字對音,如使用端組字“底”“替”等與梵文t對音,使用知組字“徵”與梵文t對音。
第三,梵文腭音五母中的c、ch、j、jh四個塞擦音,西夏譯本中使用舌尖前塞擦音對音,與梵藏對音一致。漢文本中的對音字“遮”“斫”等都是章組的正齒三等字,在中古切韻音系中應為舌面前音。
在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體合璧大藏全咒》中,此經的一些咒語段落出現了“以上一句番經缺,依漢文咒語音入”或“以上一句漢經缺,依番經咒語添入”等藏、漢無法對應之處。漢文佛經缺失咒語的地方,西夏文咒語往往可以與藏文咒語一一對應。(見文中陰影標注之處)如漢文咒語“羯摩羯摩”在《大藏全咒》中可以與梵文kamakama對應,西夏文與藏文一致,均無此句。因此,從咒語的對應關系上看,西夏文咒語與藏文咒語的對應更為契合。
以漢文佛經為翻譯底本的《佛說智炬陀羅尼經》的西夏譯本,陀羅尼對音特征卻顯示出與梵藏對音規則一致的特征,而與提云般若漢譯本的陀羅尼對音用字不甚契合。我們可以推測《佛說智炬陀羅尼經》雖在漢文佛經基礎上譯出,但是在仁宗大規模校經時,陀羅尼部分又經過重新校正。西夏時期譯經原典的來源主要有漢傳、藏傳兩種,很難見到梵文佛經原本,因此結合某些特定的用字特征可以判斷出該佛經陀羅尼帶有藏傳佛教的背景或經過精通藏文的僧人重新校對。仁宗校譯本佛經的判定,學界多以經題前后標注的“御譯”或“御校”一類的題款為基礎,而少有依據佛經內容判定的實例。《佛說智炬陀羅尼經》西夏譯本的陀羅尼用字特征可為判定佛經是否具備藏傳佛教背景提供內容上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