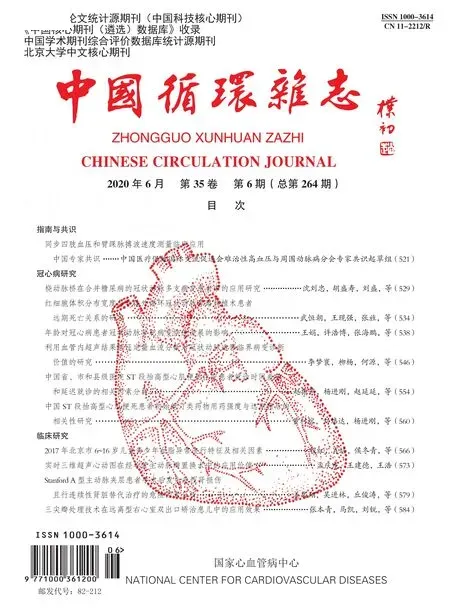主動脈瓣二瓣化畸形合并主動脈病變的研究進展
孫境 綜述,鄭哲 審校
主動脈瓣二瓣化畸形(BAV)是最常見的先天性心臟畸形,人群中的發病率在1%~2%[1],男女發病比例在3:1,其引起的死亡及相關并發癥所造成的醫療負擔超過所有其他先天性心臟病的總和。雖然BAV導致的主動脈瓣狹窄及關閉不全是最常見的心臟并發癥,但是與BAV相關的主動脈病變日益引起臨床醫生的注意,表現為從主動脈根部至近端主動脈弓的全程或部分擴張[2]。本文旨在將近幾年BAV合并主動脈病變在病變特點、發病機制、治療指征方面的研究進展做綜述。
1 BAV主動脈病變特點
1.1 BAV分型
正常的主動脈瓣由三個等大的半月型瓣葉組成,而BAV患者由于先天的瓣葉發育異常表現為兩個不等大的瓣葉[1],根據發育不良的兩個瓣葉之間是否存在融合嵴及融合嵴的位置分為若干亞類。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是2007年的Sievers分型[3]。另外一種應用較多的布魯塞爾分型是基于BAV瓣膜修復進行的分型,根據BAV兩個發育正常的交界角度進行分型[4]:A型為交界角度160°~180°,B型為140°~159°,C型為120°~139°。兩種分型各有側重點,Sievers分型側重于解剖分類,布魯塞爾分型側重于交界角度及功能分型。
1.2 BAV主動脈病變分型
BAV主動脈病變的分型類型較多。2006年Della Corte等[5]首次對BAV主動脈病變進行分類,試圖找出其中的特點,最終他發現BAV主動脈病變多種多樣,但根據擴張位置可大體上分為升主動脈中部擴張型與主動脈根部擴張型。2008年,Schaefer等[6]根據主動脈竇部直徑、竇管交界直徑及升主動脈直徑將BAV主動脈分為三型:N型,正常型;A型,升主動脈擴張型;E型,竇管交界消失型,文章同時發現Sievers分型的左右融合型合并N型較多見。2008年,Fazel等[7]根據近端升主動脈擴張位置的不同分為四型:Ⅰ型,主動脈根部擴張;Ⅱ型,升主動脈擴張;Ⅲ型,升主動脈擴張及主動脈橫弓擴張;Ⅳ型,主動脈根部、升主動脈及主動脈橫弓部均擴張。并且主動脈病變分型與瓣膜病變分型之間沒有發現明顯的相關性。綜合既往報道的BAV主動脈病變分型系統,目前比較公認的主動脈病變形態主要分為三型[2]:1型,升主動脈擴張型(大彎側為主),合并不同程度的主動脈根部擴張;2型,僅升主動脈擴張,不合并主動脈根部擴張,可以合并不同程度的近端主動脈弓擴張;3型,主動脈根部擴張,也稱為根部型。其中 1型最常見,多出現在50歲以上老年人,合并主動脈瓣狹窄及BAV左右融合型,2型多出現在BAV右無融合型患者中,3型少見,多出現在40歲以下年輕男性患者中,常合并主動脈瓣反流,病因多與遺傳相關。
雖然過去20年間針對BAV主動病變的分類及病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分型,但是目前仍然沒有一種確定統一的分類方案覆蓋所有患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BAV主動脈病變的臨床表現異質性。
2 BAV主動脈病變發病機制
2.1 BAV主動脈病變的組織病理學改變
大約一半外科手術切除的BAV主動脈病變患者主動脈壁表現為中層的過早退化,類似于馬凡綜合征患者的主動脈壁病理改變,過去稱為中層囊性壞死。細胞外基質(ECM)在保持主動脈壁的結構完整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BAV主動脈病變患者表現為彈力纖維及膠原纖維等ECM的降解、平滑肌細胞(SMC)的丟失[2]。在這個病理過程中金屬基質蛋白酶(MMP)及其組織因子抑制物(TIMP) 的平衡失調發揮重要作用[2,8]。
MMP是一個鋅依賴性的蛋白酶大家族,在心血管疾病、肌肉骨骼疾病、炎癥反應及癌癥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有大量的研究顯示在BAV主動脈病變中MMP的活性增加導致ECM降解,這其中以MMP-1、MMP-2、MMP-9、MMP-12及MMP-14報道較多。Rabkin[9]在2014年通過Meta分析發現MMP-9在胸主動脈瘤患者中表達顯著增高,而在BAV與主動脈瓣三瓣(TAV)對比時發現MMP-9在兩者中的表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相反MMP-2在BAV主動脈病變患者中表達顯著增高,而其他的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結果[10]。得出這些有爭議的結果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測定MMP的組織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動脈壁組織,一類為血液,又稱為循環標志物,組織來源不同可能造成結果差異;第二,BAV主動脈病變的異質性,不同類型的主動脈病變的機制不同,可能導致MMP表達的不同[11]。TIMP作為MMP活性最重要的調節因子,在BAV主動脈病變中也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文獻研究顯示TIMP-1、TIMP-2、TIMP-3及TIMP-4表達增高與BAV主動脈病變相關[12]。
MMP與TIMP之間比例失衡導致主動脈壁彈性纖維降解,平滑肌細胞丟失,并最終導致動脈瘤的形成,這一理論基本得到大家的認可[2]。Mohamed等[12]將MMP及TIMP的檢測進一步細化,發現二者的比例在BAV主動脈病變大彎側與小彎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Ikonomidis等[13]對比不同融合類型BAV之間主動脈組織MMP與TIMP的表達差異,發現左右融合型與右無融合型及左無融合型相比更容易出現動脈壁纖維組織的降解。具體是什么原因導致BAV主動脈病變表現出這樣的組織病理學改變,目前爭議很大,主要的理論集中在基因學說、表觀遺傳學說及血流動力學說。
2.2 BAV主動脈病變的基因遺傳機制
2.2.1 BAV主動脈病變的基因學說
BAV被認為是一種遺傳性疾病,已經發現的與BAV相關的基因包括:NOTCH1、MATA2A、TGFBR2、MATR3、SMAD6、GATA5等[14-16],目前在GeneCards網站(www.genecards.com)上查詢BAV相關基因已經達到453條。能夠說明BAV遺傳特性的基于家系的突變基因研究顯示BAV在家系中的遺傳度能達到89%。雖然升主動脈與半月瓣具有共同的胚胎學起源,均來自心臟神經嵴細胞及第二生心區,但是其在基因遺傳方面與BAV似乎不具有同源性,目前僅有少數的研究發現與BAV主動脈病變相關的突變基因:NOTCH1、SMAD6、FBN1、MYH11等[17]。目前在GeneCards網站上查詢BAV主動脈病變相關基因僅有21條。Gould等[18]在2019年通過研究兩個BAV主動脈病變的家系,發現內皮細胞中ROBO4基因突變或著表達沉默導致內皮屏障功能受損及內皮-間充質轉化(EnMT)。這些發現說明基因學說在BAV主動脈病變的發病機制中尚存在一定的地位,但是基因突變導致的病變僅能解釋很少部分的BAV主動脈病變,大多出現在具有先證者的家系,對于大部分散發病例無法用基因突變來解釋。
2.2.2 BAV主動脈病變的表觀遺傳學說
表觀遺傳是指DNA序列不發生變化但基因表達卻發生了可遺傳的改變,這是近年來研究較多的方向,主要集中在DNA甲基化及非編碼RNA兩方面。Pan等[19]在2017年通過分析21例升主動脈壁組織的DNA甲基化,發現在主動脈夾層及BAV患者主動脈壁均出現非CpG位點的DNA甲基化缺失,而在CpG位點,BAV患者表現為EZH2靶點的高甲基化。非編碼RNA包括微小RNA(miRNA,簡稱miR)、長鏈非編碼RNA(lncRNA)、小核RNA(snRNA)等,這其中miRNA與主動脈瘤及主動脈夾層密切相關,既往文獻報道的有miR-21、miR-26、miR-29及miR-143/145等。Boon等[20]在2011年發現miR-29b在BAV主動脈病變患者表達明顯增加。Ikonomidis等[10]在2013年發現miR-1和miR-21在BAV與TAV患者的主動脈壁組織中表達明顯不同,但是血漿中的濃度無明顯差異。Wu等[21]在2016年發現針對同一患者不同擴張程度的主動脈壁進行分析,發現miR-17相關的miRNA在BAV主動脈病變發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輕度擴張的主動脈壁(動脈瘤形成的早期)中,miR-17表達上調,抑制 TIMP-1和TIMP-2的表達,增加了MMP-2的活性,進而促進ECM降解、動脈瘤形成。Martínez-Micaelo等[22]在2017年研究循環中的miRNA發現miR-718高表達與BAV主動脈病變明顯相關。后續的多個研究均將重點放在的循環miRNA上[23]。
2.3 BAV主動脈病變的血流動力學機制
BAV主動脈病變的血流動力學機制是一個古老而新穎的學說,因為在基因研究之前,大家就發現主動脈瓣狹窄的患者容易在狹窄后出現主動脈的擴張,稱為“狹窄后擴張”。該理論發展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種有效、可靠的影像學手段來評估大動脈的血流,20世紀末21世紀初4D Flow MRI的發展促進了BAV主動脈病變血流動力學的發展與完善。4D Flow MRI可以準確測量掃描范圍內各位置血流的方向、速度、剪切力等重要參數。其在速度分析的準確性上明顯優于相位對比MRI,與多普勒檢測結果無明顯差異。
主動脈內的血流狀態紊亂導致不同區域的血管壁所受的壁剪切力(WSS)不同,促進血管壁的惡性重構進而出現動脈瘤樣擴張,這是BAV主動脈病變的血流動力學理論基礎。近幾年,在4D Flow MRI的幫助下,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該機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Manka等[24]在2014年通過可視化的血流分析,模擬主動脈內的血流速度、方向及血流狀態,發現BAV患者主動脈內的血流呈颶風樣改變。Mahadevia等[25]在2014年發現BAV的瓣膜融合方式改變主動脈內的血流方式、WSS進而影響主動脈病變的分型。BAV左右融合型在竇管交界水平高WSS主要集中在主動脈的右側區域,而右無融合型主要集中在主動脈的后側區域,在升主動脈中段及近端主動脈弓水平,右無融合型在各個方向均承受更高的WSS,因此,右無融合型容易出現升主動脈及近端主動脈弓的彌漫性擴張。另外他們還發現了一種新的血流動力學量化指標-血流移位,其在不同BAV主動脈病變分型中的敏感度最高。Guzzardi等[26]在2015年將血流動力學改變與組織學改變相聯系,術前通過4D Flow評估高WSS區域位置,術中留取相應位置動脈壁標本進行組織病理學檢驗,發現高WSS區域ECM失調,表現為彈力纖維降解,MMP-1、MMP-2及MMP-3表達上調,這提示血流動力學改變可能介導BAV主動脈病變的形成。雖然在4D Flow MRI的幫助下,血流動力學理論從定性研究轉變為定量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但是目前也有許多尚不能滿意解釋的問題:BAV瓣膜功能正常的患者也容易主動脈病變,即使BAV瓣膜病變很重的患者也不出現主動脈病變,TAV瓣膜病合并主動脈病變患者少等等。
目前對于何種機制導致BAV主動脈病變還沒有定論,或許幾種機制都或多或少發揮作用。
3 BAV主動脈病變的外科干預指征
所有的基礎與臨床研究均為了回答一個問題,即BAV主動脈病變的患者何時是最佳的外科干預時機?因為主動脈的擴張容易出現主動脈瘤破裂或主動脈夾層,這些主動脈事件的發生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找到一個明確的干預指征非常重要,但是臨床上很難判斷出這么一個最佳的干預時機,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積極外科干預與密切隨訪觀察。近20年來兩種觀點的力量此消彼長,爭論不斷,這在指南上的反映尤為明顯。從1998年至2017年,共有11部國際指南對BAV主動脈病變的外科干預指征做出過推薦。主動脈直徑的切除閾值從1998年的的55 mm降至2010年的40~45 mm,2014年及2017年的美國的瓣膜疾病治療指南再次將該閾值提高至55 mm。為了全面說明BAV主動脈病變相關的爭議,美國胸外科學會(AATS)在2018年聯合全世界的該領域專家發布了專門針對BAV主動脈病變的專家共識[27]。共識中推薦對于沒有相關危險因素(例如:主動脈根部型、合并主動脈瓣反流、不能控制的高血壓、主動脈夾層或猝死的家族史、合并主動脈縮窄、主動脈直徑增長大于3 mm/年等)的BAV主動脈病變患者的切除指征為55 mm(I/B),對于合并危險因素的切除指征為50 mm(Ⅱa/B),對于低手術風險患者及有經驗的心臟中心,動脈瘤的切除指征也可以為50 mm(Ⅱb/C),而對于同期心臟手術的患者,如果BAV主動脈病變的直徑達到45 mm也應該同期切除(Ⅱa/B)。該共識是目前世界范圍內各主要心臟中心普遍采用的標準,但是在歐洲的一些心臟中心,對于同期心臟手術的患者,BAV主動脈病變的干預更積極,將標準定為43 mm[28]。目前這些干預指征的制定依據均為回顧性研究,證據級別較低,未來需要更高級別的證據為指南的制定提供支持。
4 總結
BAV合并主動脈病變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臨床問題,對于它的基礎與臨床研究充滿了困難與挑戰,目前無論在發病機制、病理分型及干預時機等方面均存在巨大的爭議。未來的研究方向是進行不同亞型之間的分組研究,這樣可能會得到一致的研究結果。另外一個急需解決的臨床問題是如何對BAV主動脈病變患者進行危險分層,這可能需要從細化的臨床分型、發病機制、影像學檢查、血液學檢查等多方面綜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