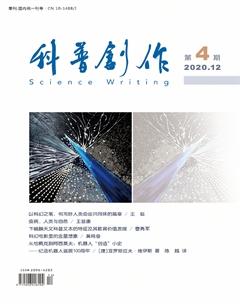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述評
陳方齊 張巖泉
劉慈欣,中國科幻小說代表作家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起,他一邊在山西省陽泉市的娘子關發電廠擔任計算機工程師,一邊利用業余時間出版了13本小說集。他的創作時間并不算長,1999年6月才首次在《科幻世界》發表兩篇作品《鯨歌》和《微觀盡頭》,但他很快憑借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豐富的想象力確立了自己在科幻小說界的地位:連續數年獲得中國科幻文學最高獎銀河獎;2015年,其長篇科幻小說《三體》獲得科幻文學最高獎項雨果獎;2018年,更是以1800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榜首。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稱他“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文學提升到了世界級的水平”[1]。
新世紀以來,學界對劉慈欣的評價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發展變化過程。筆者于2020年5月20日嘗試以“劉慈欣”為主題關鍵詞在中國知網(cnki. net)搜索,共檢索到文獻711篇,且很大一部分是在 2015年之后發表的(如圖1);而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以“劉慈欣”為主題關鍵詞檢索到文獻24篇,2015年之前發表的僅2篇。從研究視角看,對劉慈欣的研究也逐漸從早期書評式推介深入到對其重要文本的美學風格與藝術手法研究、思想性與創作理念的研究、海外傳播與接受的研究等,同時亦有超越其個人寫作而指向科幻小說重要命題的討論。而隨著《三體》三部曲英文版、日文版的相繼出版,討論其作品翻譯策略的成果也逐漸增多。2019年電影《流浪地球》的火爆也使得電影學領域對中國科幻電影的討論增多,這些成果雖然都會提及劉慈欣及其作品,但實際上討論的問題已超出了文學研究的范疇,本文將聚焦于文學研究領域。
一、美學風格與藝術手法研究
(一)美學風格的研究
新世紀對劉慈欣小說的研究是從對其美學風格的研究開始的。盡管人們對“科幻小說”的定義仍爭論不休,但對“‘驚異感是科幻小說最突出的特征”這一命題的認知似乎都沒有疑義。英國學者法拉·門德爾松(Farah Mendleshn)在《劍橋科幻文學史》(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中指出:“如果說最具科幻小說特色的東西,那就是‘驚異感了。”[2]40與西方對科幻的研究一樣,中國對科幻小說最早的討論似乎也來自科幻迷①,李兆欣的《對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宏細節——“大尺度”意象的思考》[3]正是從驚異感出發分析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章認為劉慈欣科幻小說中所描寫的“大尺度”意象與“驚異感”存在某種聯系,并嘗試利用所謂“科技美學”的概念來解釋這種“驚奇感”產生的原因。可能由于《邊緣》是科幻迷和研究者自辦的網絡雜志,對學術規范要求并不嚴格,所以我們很難考證支撐“科技美學”理論的材料是否存在。不過我們應該肯定作者試圖從審美的角度去分析科幻小說中的科學描寫的意圖,只是囿于有效理論的缺乏,導致了文章的不成功。
學院派最早的研究成果可能是吳巖、方曉慶的《劉慈欣與新古典主義科幻小說》。這篇論文到今天幾乎是研究劉慈欣必讀的文章,文章將美國“黃金時代”的科幻小說與蘇聯科幻小說置于同一系統中觀照,認為兩類科幻在對現代化的看法上相當一致,并稱此類堅信技術能引導人類走出愚昧的科幻小說為“科幻文學中的古典主義流派”[4]37。劉慈欣的作品恰在敘事、人物、情感取向上繼承了某些科幻古典主義的特征,但同時又創造性地使用了“密集敘事”“時間躍進”、抽象人物等手法實現對古典主義科幻小說的超越。在這個意義上,“劉慈欣扭轉了以破壞性為主潮的中國科幻文學的當代走向,并把它引向積極的建構方向”[4]37,也即新古典主義的方向。這一觀點在很長時間內影響著評論者對劉慈欣科幻小說的判斷。不過也有不同的聲音,宋明煒就認為劉慈欣應被視為是中國科幻“新浪潮”的代表作家,并提出了反對將其歸為黃金時代作家的理由:“首先,劉慈欣的科幻想象已經明顯超越了通常以冒險和征服為目的的太空漫游的敘述模式;其次,劉慈欣的寫作風格既有崇高的面向,也有詭奇的方面,在宇宙宏大的背景上指向數字化的后人類未來。”[5]34嚴鋒的《創世與滅寂——劉慈欣的宇宙詩學》[6]將劉慈欣的科幻創作納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坐標中進行考察,指出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不僅具有新古典性,更具有一種先鋒性,即:1.回到啟蒙卻又超越啟蒙,在消解宏大敘事的“小時代”中重塑宏大敘事;2.將傳統革命英雄塑造成“超英雄”;3.超越宗教的創作特色,解釋了21世紀以來科幻文學勢頭強勁的原因,實際上也確認了劉慈欣科幻小說對古典文學與先鋒文學的超越。高亞斌從劉慈欣短篇科幻所描繪的科幻景觀出發,分析其背后潛藏的美學價值。他的《宇宙重生的恢宏頌歌——劉慈欣〈坍縮〉中的科幻景觀》[7]和《微觀意識與翻轉乾坤的敘事奇觀——劉慈欣小說〈微觀盡頭〉管窺》[8]都是從單篇小說中所描繪的令人驚異的現象出發,分析其背后蘊含的宗教情感(只不過劉慈欣信奉的是“科學神”),進而在微觀層面發掘出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美學價值。陸威的碩士學位論文《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美學研究》[9]比較全面地討論了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美學價值與審美機制。文章分析了劉慈欣科幻小說中出現的幾類審美意象——種族形象、世界形象、科技形象、科學神、超英雄以及非理性的類群形象——所展示出的奇異且迷人的審美魅力,以及這種魅力產生的原因。文章由表及里、層層深入,是比較全面、系統的關于劉慈欣科幻小說美學特點的研究成果。
(二)藝術手法的研究
對藝術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敘事學、形象學和語言學的分析上。楊宸的《“歷史”與“末日”——論劉慈欣〈三體〉的敘述模式》[10]從敘事學角度分析了《三體》系列存在的兩種敘事模式——歷史模式和末日模式,指出歷史模式的敘事還原了消退的時間意識,而末日敘事實現了對人類整體性的呼喚,從而使《三體》系列在當代文學中具有了獨特的價值。吳寶林的《論劉慈欣“大藝術系列”科幻小說——以〈詩云〉為中心》[11]聚焦劉慈欣未完成的“大藝術系列”①科幻小說的敘事特征、文體特征和美學特征,由此看出它們對劉慈欣后來科幻創作的影響,從而確定其在劉慈欣創作譜系的位置。文章材料充分,論證有力,拓展了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的視野。
劉慈欣小說中人物形象分析也是劉慈欣研究的一大熱點,而其80萬字的巨著《三體》系列更是因塑造了眾多人物形象而成為評論者關注的焦點。方曉楓的《試析〈三體〉三位女性形象的倫理意義》[12]抓住“女性”“倫理意義”兩個關鍵詞,成為這一類評論的代表性文本。文章分析了《三體》系列中葉文潔、莊顏、程心三個女性形象,從倫理學角度闡釋了《三體》系列。這樣運用傳統研究視角研究劉慈欣的作品忽視了對《三體》三部曲的整體把握,也并未顯示出劉慈欣作品的宏大特征和科幻文學與其他題材文學的差異。
劉慈欣自己曾在《從大海看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文學要素的反思》[13]中提出宏細節、種族形象、世界形象和科學形象等說法,并指出中國讀者和評論家對這樣的說法并不認可。但今天越來越多的年輕評論者開始從這樣的“宏”角度去分析劉慈欣科幻作品中的形象。郭凱的《劉慈欣科幻作品中的科學形象研究》[14]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研究“宏形象”的論文。文章引入了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的視角分析劉慈欣小說中的科學形象。在科學史的視角下,作者總結出了劉慈欣在其科幻小說中塑造科學形象的三種路徑:重寫科學史、將西方已有科技構想中國化和虛擬科技革命。在科學社會學的立場上,分析劉慈欣科幻小說中作為一個社會領域的科學的特點,闡明了科幻小說獨特的審美價值。當然,文章在論述上還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諸如以幾個物理學研究生對科幻文學的期待推衍出某個具有特定審美趣味的科幻讀者群的存在,這樣的論證可能比較缺乏說服力。
針對劉慈欣科幻小說語言特征的研究相對較少,高翔的《從劉慈欣作品看中國科幻小說的語體特點》[15]是這方面較早的成果。文章選擇了語體分析這個角度分析以劉慈欣為代表的中國新科幻具有的特點,指出科幻小說“形象性、情意性、創新性”的語體屬性,并通過對劉慈欣小說語言進行詞匯、語法、辭格等方面的分析,總結出其語體特點,歸納出形象描繪、社會功能、審美功能三方面的語體功能。陳薇薇的《劉慈欣〈三體〉中的修辭特色研究》[16]采用語料統計法、文獻研究法、描寫與解釋等研究方法對《三體》三部曲中出現的修辭現象進行了分析,圍繞語音修辭、詞匯修辭、句子修辭及辭格研究四方面對《三體》三部曲進行了描寫與闡釋,是針對《三體》三部曲比較全面的語言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思想性與創作理念的研究
對劉慈欣科幻小說思想性與創作理念的研究稍晚于對其小說美學風格與藝術手法的研究,這部分成果主要圍繞劉慈欣的長篇小說《三體》三部曲展開,小說講述了人類文明和三體文明的生死搏殺以及兩個文明在宇宙中的興衰歷程。對其小說思想性及創作理念的研究主要涉及劉慈欣小說主題意義和創作理念的研究。
(一)技術與倫理
劉慈欣的技術觀是其主題研究中頗受關注的一個方面。盡管劉慈欣曾不止一次說明自己“是一個瘋狂的技術主義者,我個人堅信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17],但情況卻似乎未必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并沒有將科學或技術作為一種價值評判標準,而是始終把技術作為一種讓人們生活得更好的工具,在作品中反復探討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人們帶來的兩難處境。《地火》《地球大炮》《三體》系列都是典型例子。不少研究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闡釋劉慈欣科幻小說背后的“技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糾纏。劉珍珍的《后現代主義視野下的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18]對劉慈欣的作品做了比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作者站在比較文學研究的立場上,通過文本細讀法討論了兩個問題:劉慈欣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提出的“零道德”與后人道主義的契合性,以及劉慈欣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前一部分將劉慈欣的作品與西方人道主義思潮的發展演變相結合,在后人道主義的視野中定位了劉慈欣的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確實對劉慈欣的作品非常熟悉,論證也很有力。但當涉及到從后工業社會對科學技術的批判角度解讀劉慈欣作品時,理論和闡釋就似乎有些脫節,我們并不能看到劉慈欣的“技術主義”如何體現了后現代內涵。這不只是本文所存在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研究者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當用文學、文化理論研究劉慈欣作品的“科學”時,現有的方法難免有些力不從心。
除了從整體上把握劉慈欣小說的成果,以劉慈欣單個或部分創作成果為研究對象的作品論也不在少數。這類成果大多聚焦劉慈欣小說背后的理性與人性的矛盾。屈菲的《從黑暗森林到生活世界——論〈三體〉系列小說中的話語意識》[19]站在文學社會學的立場上,分析了《三體》系列背后的話語意識,即對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都保持一定的距離,正是從這樣的話語意識中傳遞了作者生活至上的價值取向。相比其他從“作者—作品”出發闡釋《三體》系列成果,這樣的分析還是比較新穎的。王瑞瑞的《論科幻文學的宇宙倫理——以劉慈欣的“三體系列”為中心》[20]則從《三體》系列中宇宙倫理的建構中探討劉慈欣的倫理態度。文章認為劉慈欣的《三體》系列通過構建一個“零道德”的宇宙使人類的倫理道德失效,進而通過“歸零者”形象的塑造構建起一個新的道德烏托邦。但仔細閱讀文本會發現,小說結尾程心在小宇宙留下了五公斤物質,而這一行動則可能會影響宇宙重啟。也就是說,劉慈欣在《三體》系列中并沒有毫不猶豫地構建出一個道德烏托邦,更像是留下了無盡的追問:宇宙能否順利重啟?重啟后的高維宇宙會不會重蹈“黑暗森林”的覆轍?從這個角度看,劉慈欣還是在冰冷的理性與人道主義的溫情之間搖擺,這也是文章值得商榷的地方。李廣益的《羅輯的決斷:〈三體〉的存在主義意蘊及其文化啟示》[21]站在存在主義的立場上對《三體》系列后兩部的主人公羅輯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與重構,并從中窺見《三體》系列中這些存在主義式的英雄在當下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意義及其背后所隱含的劉慈欣重塑英雄主義時的糾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開拓了思路。而王衛英、徐彥利的《劉慈欣科幻小說〈贍養上帝〉中的三個設問》[22]通過《贍養上帝》隱含的三個設問,看出了作家思想中技術至上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劉慈欣作品中技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矛盾,既顯示出劉慈欣科幻創作的特別之處,也體現了科幻小說作為一種呈現新認知的文類所承載的功能。
(二)現實主題與思想實驗
科幻小說總是站在“今天”去展望未來,即使書寫對象是“科學”與“未來”,目的卻仍然是激發讀者對現實的重新思考,這也就是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所說的“認知疏離”(cognitive estrangement)——“蘇恩文認為科幻小說通過一個新的角度向讀者‘暗示一套新的準則,從而使讀者對現實的經驗認識‘變得陌生,這種對熟悉事物的重塑有一個‘認知目的,那就是激發讀者對現實的認識,從而獲得對社會現狀的理性理解”[2]230。那么,討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現實意義就是可行且必要的了。這方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三體》系列上,這部80萬字的長篇科幻包含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確實讓人們重新認識了現實。學者對它的闡釋也涵蓋了政治、文化、歷史、哲學等諸多方面。
納楊的《從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談當代科幻小說的現實意義》[23]探尋了《三體》三部曲的現實意義——對倫理和技術的反思——是如何通過其整體構思、人物形象、宏大想象三個方面表現出來的。趙柔柔的《逃離歷史的史詩:劉慈欣〈三體〉中的時代癥候》[24]從劉慈欣《三體》系列所引起的轟動效應出發,通過對《三體》系列敘事方式、情節內容、敘事模式的分析,得出其引起轟動的原因在于隱喻了某種時代癥候——逃離歷史、逃離創傷性經驗。陳頎的《文明沖突與文化自覺——〈三體〉的科幻與現實》[25]通過分析劉慈欣《三體》系列的敘事視角,總結了劉慈欣在科幻與現實之間的文化自覺:劉慈欣以“硬科幻”的方式介入現實,通過對未來人類可能面臨的文明災難的幻想,推動當代精英反思人類道德、文明與歷史,而在這之中又可以看到劉慈欣對精英與大眾罅隙的思考。作者緊扣“知識分子”與《三體》三部曲敘事的關系,視角獨到,很有洞見。歐樹軍的《“公元人”的分化與“人心秩序”的重建——〈三體〉的政治視野》[26]是為數不多的從政治角度對《三體》三部曲進行解讀的文章。作者從近30年現實中地緣政治、國際格局的劇烈變化出發,看出了《三體》系列對現實政治的強烈隱喻:地球三體組織的降臨派似乎是現實世界中恐怖分子的化身,幸存派是現實中出賣同胞茍活于世的叛徒寫照,拯救派則是現實中宗教勢力的隱喻,就連主人公葉文潔、史強、羅輯也都是現實生活中面對終極危機的人的鏡像。而《三體》系列對人心秩序重建的啟示就在于不能忽視生存與死亡的抉擇。王靜靜則關注到了《三體》中對于“文革”的書寫,她的《論劉慈欣〈三體〉中的“文革”敘事》[27]討論了“文革”敘事對《三體》系列情節發展的作用,并關注到了劉慈欣對“文革”的書寫更多地聚焦于自然,從而反映出作者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文章指出了《三體》中歷史敘事對科幻真實性以及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作用,觀點新穎。
《三體》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以黑暗森林為核心的宇宙社會學以及劉慈欣的科技觀和認識論,有不少學者對此表示了相當的興趣。趙汀陽的《最壞可能世界與“安全聲明”問題》從黑暗森林這一極端設定出發,指出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中的“零道德”宇宙給傳統哲學研究提出了理論上的挑戰——“一是突破了‘霍布斯極限”,“二是提出了人類處于被統治地位的政治問題”[28],進而檢討了傳統哲學思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而“安全聲明”將使文明陷入對自身的重復。吳飛的《黑暗森林中的哲學——我讀〈三體〉》[29]從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出發,勾勒并揭示了《三體》所構建宇宙社會學背后隱含的哲學關懷。這篇文章也成為其稍后專著《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解讀》的一部分。專著從黑暗森林、人性、心靈(自我)和死亡幾個維度對《三體》三部曲做了哲學闡釋,這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劉慈欣研究專著。楊立華的《科技紀元與三體〈春秋〉》[30]則揭示與檢討了《三體》呈現科技世界觀下的宗教隱秘。這些成果無疑彰顯了中國學者對人類未來的憂患意識和人文關切。
三、超越個人寫作的研究
新世紀以來,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或者說當代中國科幻小說研究中似乎總隱含著一種焦慮,即關于科幻小說“文學性”的焦慮。對這一焦慮的回應包括對科幻小說“文學性”的討論、對劉慈欣科幻小說寫作立場的分析以及對劉慈欣科幻小說文學史意義的定位等方面。
(一)科幻小說“文學性”的討論
科幻小說作為一種類型文學,在中國長期被歸入“兒童文學”的范疇,而劉慈欣獲獎以來,不少論文開始關注作為一種類型文學的科幻的“文學性”。這里涉及到兩種態度:一種是在所謂經典文學的框架內談科幻小說的文學性,也即用評判經典文學文學性的標準評價科幻文學,以期達到提高科幻文學地位的目的;另一種則是對在經典文學史中已形成的文學性標準提出挑戰,認為科幻文學應該有自己的文學性標準,這種態度顯然更為激進,因為它在提高科幻文學地位的期待中還包含了對科幻文學獨特品質的強調。較早研究科幻文學的學者或青年學生大多持前一種態度,因為在科幻文學還沒有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的時代,人們不得不采取一種“歸順”的姿態以期達到對主流文化和學界的和解。
但隨著以劉慈欣為代表的中國新科幻作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科幻文學開始逐漸自信,劉慈欣本人一直認為作為一種類型文學的科幻不必獲得主流文學的承認[31],不少論文也開始重構科幻文學的“文學性”。王峰的《科幻小說何須在意“文學性”》[32]是這方面的代表。文章從理論上分析了文學性的概念,指出“文學性”的內涵應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科幻小說在當代中國的繁榮為重構文學性提供了一種可能,并進一步指出科幻文學如果改造了文學性概念,那將是對想象性、幻想性的強化和抒情性、辭采形式的弱化。文章論證邏輯比較嚴謹,也為科幻文學文學性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王瑤的《鐵籠、破壁與希望的維度——試論劉慈欣科幻創作中的“驚奇感美學”》[33]指出劉慈欣科幻小說美學上的新穎之處在于“驚奇感”,并進一步指出其小說的“驚奇感”產生于對“現實世界”和“科幻世界”這兩個世界的塑造。文章認為劉慈欣的小說通過描摹高于現實的科幻世界及那個世界中的常人與英雄,打破現實對人的束縛,給人以希望,從而使讀者產生“認知陌生化”,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劉大先的《總體性、例外狀態與情動現實——劉慈欣的思想試驗與集體性召喚》[34]看到了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在后純文學時代以思想試驗的方式對世界整體性的把握,而其思想試驗又與政治緊密相關——通過對“例外狀態”的肯定將個體命運融入集體,通過對宇宙尺度下的極端環境的描繪隱喻現實。陳舒劼的《“長老的二向箔”與馬克思的“幽靈”——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由《三體》系列中“歌者”向“長老”索要二向箔打擊太陽系這一普通情節說開去,指出當代科幻小說中存在兩類社會形態的想象:典型的高科技水平與低社會形態錯位的社會形態想象以及其他社會形態想象。這兩類社會形態想象都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檢視中顯出自身的破綻和局限[35],由此確認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形態想象方式的重要意義。這幾篇文章可以說在重構以劉慈欣創作為代表的科幻文學的文學性上層層深入,對后來的研究者而言有較大的啟發。
上述兩種態度的目的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打破“主流文學”對科幻文學的“隔離”,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區分孰優孰劣。只是要警惕兩種錯誤傾向:對前者而言,要避免一味以純文學觀點分析科幻小說而導致的輕視;對后者而言,要避免一味拒絕其他標準,使科幻小說自我隔離于主流文學之外。
(二)寫作立場與文學史意義
劉慈欣作為一位中國科幻作家,其作品必然帶有本民族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而關注作家的寫作立場并從中窺見其對于中國(科幻)文學史的意義,也是超越劉慈欣個人寫作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賈立元(飛氘)的《光榮中華: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中國形象》[36]從對具體形象的分析中透視劉慈欣“地球往事”前兩部中所體現出的對未來中國的想象。文章從劉慈欣小說的技術主義的理性和藝術的“崇高”入手,以“地球往事”前兩部的人物為例,分析了劉慈欣小說對未來中華復興的暢想,深化了對科幻文學構建民族國家形象的認識。但文章同時也指出了劉慈欣小說中冷酷的科學與文學的熱情之間的分裂,認為這可能會造成未來中國科幻敘事上的困境,從而揭示出劉慈欣在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羅雅琳的《新穎的劉慈欣文學:科幻與第三世界經驗》進一步討論了劉慈欣小說的新穎性背后的文化政治資源,即“以第三世界立場反抗啟蒙主義式的‘人之形象,從而挑戰西方話語所攜帶的‘普遍性霸權,申明自身生活方式的正當性與合法性”[37]。而這種新穎性的表征就是劉慈欣科幻小說對以弱勝強的反復書寫,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就是第三世界身份,這也是其小說中出現帶有“游擊隊員”品性的知識分子形象和“先鋒隊”豪情的重要原因。李廣益的《中國轉向外在: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38]著眼于劉慈欣科幻小說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文章梳理了中國20世紀初以來書寫本土之外世界的文學歷程,指出在作家們已對用世界眼光表現、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外向型文學感到陌生的今天,劉慈欣以其創作實績為中國文學再一次“向外轉”提供了佐證和思考。作者看到了劉慈欣科幻小說承接20世紀初救亡的民族意識、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一面,同時又認為不應囿于“民族寓言”的視角而低估劉慈欣作品中對人類的普世關懷。毛孟啟則關注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文化精神,其《娘子關頭窺皓月——谫談劉慈欣小說與中國文化精神》[39]對劉慈欣中短篇小說中所體現的中國文化精神做了比較全面的概括,文章指出了以《朝聞道》《鄉村教師》等為代表的中短篇科幻至少表現出了中國文化精神的以下幾個方面:求道、殉道精神,傳承精神,擔當精神,詩性精神以及神話思維。其立足傳統、開放兼容的品格既體現了中國科幻的“文化自信”,也為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了寶貴借鑒。
四、比較研究、影響研究與海外研究狀況
(一)比較研究、影響研究與文化交流
從比較研究角度研究劉慈欣的論文相對較少。陳海琳的《災難·抗爭·救贖:劉慈欣和王晉康的末日書寫——以〈三體〉系列小說和〈逃出母宇宙〉為中心》[40]比較了劉慈欣與王晉康在對末日描寫、道德思考方面的異同,認為劉慈欣對末日的書寫帶有瑰麗宏大的古典主義氣質,而王晉康則偏重冷峻的寫實主義。同時,文章認為王晉康在《逃出母宇宙》中放棄了將科技發展與道德倫理的沖突作為核心主題,對人類傳統的道德觀進行大膽顛覆的做法,似乎與《三體》背后的道德思考有趨同傾向。但遺憾的是,作者并沒有繼續挖掘兩位科幻作家在這兩部作品背后的道德思考具體有何異同性。范軼倫的《劍與詩:古典文化帶來未來救贖——〈詩云〉和〈斷章〉中的身份認同比較》[41]從“民族寓言”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內地科幻作家劉慈欣科幻短篇《詩云》和香港科幻作家譚劍《斷章》中“詩”與“劍”這兩種象征中國古典文化的意象的內涵,闡釋內地與香港在面對“文化身份”時的差異:前者指向西方入侵背景下人文主義與科技主義的認同搖擺,后者指向香港回歸前港人的身份焦慮。這種站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視角,無疑是對劉慈欣研究的補充。
英國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是英語世界“硬科幻”的代表作家,也是劉慈欣十分崇拜的作家,劉慈欣在許多場合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因此,研究克拉克對劉慈欣創作的影響成為劉慈欣研究的一個課題。研究者多從劉慈欣對阿瑟·克拉克作品的接受、二者創作的比較展開,這方面的論文多以年輕學子的學位論文為主。李云的《阿瑟·克拉克對劉慈欣〈三體〉三部曲創作的影響》[42]、張曉妮的《劉慈欣對阿瑟·克拉克科幻作品的接受研究》[43]及其他學位論文大多是從內容(題材)、形象、美學風格切入,采用比較的方法闡釋克拉克對劉慈欣的影響。而關于劉慈欣如何將克拉克科幻小說中的元素進行創造性轉化,以及轉化的具體路徑為何的問題,則并未得到更為充分的整理。可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陷入困境,需要后來者對相關論題進行深度拓展。
劉慈欣與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相對薄弱,為數不多的論文也基本上是從“傳播與接受”角度切入。顧憶青的《科幻世界的中國想象:劉慈欣〈三體〉三部曲在美國的譯介與接受》[44]和付筱娜的《攜想象以超四海——〈三體〉的海外傳播之鑒》[45]基本都是從譯介過程、翻譯策略和接受效果三個方面探究了劉慈欣長篇科幻《三體》系列在海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過前者更側重相關事實的收集展示,從現象中提煉出的經驗稍有不足;后者已能從相關事實中作出經驗性總結。劉舸、李云的《從西方解讀偏好看中國科幻作品的海外傳播——以劉慈欣〈三體〉在美國的接受為例》[46]采用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劉慈欣《三體》系列在美國廣受歡迎的原因,為中國科幻文學創作及海外傳播提供了一些參考。
(二)海外研究成果述要
國外對劉慈欣的研究還不多,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系副教授宋明煒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他近年來主要研究中國科幻小說,已發表相關中英文論文50余篇,其有關劉慈欣的討論中最著名的無疑是《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47]。文章結合劉慈欣的幾部代表作品對其科幻世界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文章首先回顧了科幻文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并確定了劉慈欣在中國科幻文學特別是新科幻發展史上的坐標。隨后,文章分析了劉慈欣科幻小說藝術魅力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指出正是由細節化的“寫實”帶來的崇高美感,使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區別于克拉克等外國科幻作家。文章接著從理性和人文主義兩方面分析了劉慈欣科幻世界的雙重意義,并透過《三體》系列進一步闡釋了劉慈欣通過塑造一個“完整的”科幻世界所帶來的驚異感。宋明煒在另一篇論文《中國當代科幻的烏托邦變奏》①中也涉及到了劉慈欣的創作,認為劉慈欣對“硬科幻”的提倡源于其小說中的技術烏托邦。而其在稍后的《1989年以后: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②中更加詳細地闡釋了劉慈欣小說對這種變奏的體現。文章將劉慈欣未出版的《中國2185》③看作是中國科幻新浪潮的開山之作,認為其創作代表了“一種更復雜、更有反思性和顛覆性的文學,其中包含著希望與絕望、烏托邦及其惡托邦反思、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混合雜糅”[5]33。文章同時指出,劉慈欣的這種烏托邦/惡托邦辯證的思想在其后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續。這兩篇有關中國科幻新浪潮的文章討論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共同構成了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烏托邦/惡托邦想象的思考。
除宋明煒的相關成果外,李樺的“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Liu Cixins Critical Utopia:China 2185”(《劉慈欣批判烏托邦中的政治性想象:〈中國2185〉》——筆者譯)[48]在海外也有一定影響。文章借助了湯姆·莫伊蘭(Tom Moylan)的“批判烏托邦”這一范疇,從“標志性記錄層面”(iconic level)、“離散記錄層面”(discrete level)和“一般形式”(generic form)分析了《中國2185》中的政治元素,并把這部小說同劉慈欣的其他作品以及當代中國其他科幻小說中的政治隱喻聯系起來考察,是劉慈欣海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成果。2016年,《紐約客》(The New Yorker)發表了約書亞·羅斯曼(Joshua Rothman)的“Liu Cixin - Chinas Arthur C. Clarke”(《劉慈欣:中國的阿瑟·C.克拉克》——筆者譯)[49],這篇文章指出了劉慈欣在中國科幻的地位,并對其科幻作品進行了具體分析,贊嘆劉慈欣科幻作品的豐富想象力及技術細節。同年,“劉慈欣科幻小說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研討會在海口召開,日本學者上原香在會上發表的《劉慈欣科幻小說的角色小說化:從〈超新星紀元〉到〈三體〉》詳細討論了劉慈欣小說中的女性角色,但文章選取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從角色小說的視角詮釋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文章通過梳理劉慈欣的幾部代表性作品在科幻小說、中國現代小說和角色小說間的運動軌跡,認為劉慈欣在《三體》系列創作中逐漸“增加了角色小說性這一新的張力”[50]。
2019年3月,頂尖科幻學術期刊《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137期(第46卷第一部分)開辟了“劉慈欣專號”,發表了李廣益 、藹孫那檀(Nathaniel Isaacson)、關首奇(Gwenna?l Gaffric,《三體》三部曲法語譯者)、斯蒂芬·道格蒂(Stephen Dougherty)的三篇學術論文。其中,關首奇的“Liu Cixins THREE-BODY TRILOGY and the Statu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與科幻小說在當代中國的地位》——筆者譯)[51]根據自1949年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歷史及其在政治領域的重新闡釋,考察了中國及海外《三體》三部曲的生產過程和接受條件,并對其引發的當今評論、學術甚至是政治熱潮做了詳細闡述。斯蒂芬·道格蒂的“Liu Cixin,Arthur C. Clarke,and ‘Repositioning”(《劉慈欣,阿瑟·克拉克和“重新定位”》——筆者譯)[52]首先借用翻譯理論家艾米麗·阿普特(Emily Apter)所說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概念討論了劉慈欣小說對克拉克小說的繼承與發展,以及翻譯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接著討論了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對中國現代化的矛盾回應,最后分析了劉慈欣的科幻理論中的“超越自戀”這一觀點,可以說是比較全面新穎的劉慈欣分析。
五、結語
綜觀新世紀以來的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我們在美學風格和藝術手法研究、思想性和創作理念研究、超越個人寫作的研究以及比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就研究對象而言,多數成果主要圍繞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展開。這固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三體》三部曲作為長篇小說,可闡釋的空間自然比中短篇小說要廣闊),但長此以往則容易導致一個雙重性問題:從縱向上看,對《三體》過于集中的闡釋容易使我們忽略《三體》系列之前的創作,從而對劉慈欣科幻創作的動態過程失察;從橫向上看,冷遇《三體》三部曲之外的作品亦不利于我們把握劉慈欣科幻創作的全貌。
其次,本土科幻文學理論的構建雖已起步,但較西方仍有差距。一方面,由于從事西方科幻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譯介的學者不多,我們本土的學者自然也很難提出自己的理論;另一方面,學界對科幻作家所提出的理論也重視得不夠,例如劉慈欣所說的“宏細節”與“宏形象”的理論,幾乎沒有相關的論文(著)對其在文學理論上做進一步闡釋。而理論武器的缺乏會使得包括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在內的科幻文學研究難以取得創新性成果,也無法指出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創作的獨特性。
再次,對其文學史意義、比較研究和影響研究的忽視。目前有關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對其作品主題、敘事、結構等的討論,而少有將其放在中國科幻文學史及世界科幻文學史坐標中進行研究。比較研究的意義就在于通過比較看似相似的對象顯示出其獨特性。同樣,劉慈欣不止一次提到克拉克對他的影響,那么探討這種影響產生的路徑、劉慈欣如何對克拉克的作品進行創造性轉化就顯得很有價值。
最后,科幻文學研究者需要開闊自己的研究視野,這同樣有助于緩和科幻小說“文學性”的矛盾。科幻文學是科學與未來雙重入侵現實的敘事性文學作品[53]。“科學”與“未來”常常在科幻小說中出現,而現階段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大多自高中開始就學習文科,大學學習的也多為人文社科專業,這樣的知識背景在面對劉慈欣這類“硬科幻”作家時難免會顯得局促;而有理工科知識背景的大學生則會因為文學理論知識的缺乏而難以進入文學研究領域(即使他們自身對科幻文學的創作與評介很有興趣)。這樣的尷尬就會產生前述研究者從文學角度分析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科學”元素時的力不從心。
或許,開闊研究視野,積極提出、使用新理論,不限于對作品本身的分析,而是通過比較,在社會歷史的語境中讀解和闡發文本(間)的意義,才有可能突破現有研究的局限。
□ 作者簡介
陳方齊,華中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
張巖泉,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1] 嚴鋒.創世與滅寂——劉慈欣的宇宙詩學[J].南方文壇,2011(05):74.
[2] 愛德華·詹姆斯,法拉·門德爾松,等.劍橋科幻文學史[M].段從軍,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8.
[3] 李兆欣.對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宏細節——“大尺度”意象的思考[J].邊緣,2005(5).
[4] 吳巖,方曉慶.劉慈欣與新古典主義科幻小說[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02):37.
[5] 宋明煒,王振.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J].南方文壇,2017(03):33-41
[6] 嚴鋒.創世與滅寂——劉慈欣的宇宙詩學[J].南方文壇,2011(05):73-77.
[7] 高亞斌.宇宙重生的恢宏頌歌——劉慈欣《坍縮》中的科幻景觀[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1):111-114.
[8] 高亞斌.微觀意識與翻轉乾坤的敘事奇觀——劉慈欣小說《微觀盡頭》管窺[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02):70-74.
[9] 陸威.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美學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9.
[10] 楊宸.“歷史”與“末日”——論劉慈欣《三體》的敘述模式[J].文藝研究,2017(02):29-37.
[11] 吳寶林.論劉慈欣“大藝術系列”科幻小說——以《詩云》為中心[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1(04):33-38.
[12] 方曉楓.試析《三體》中三位女性形象的倫理意義[J].文學教育(上),2016(09):28-31.
[13] 劉慈欣.從大海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文學要素的反思[J].科普研究,2011,06(3):64-69.
[14] 郭凱.劉慈欣科幻作品中的科學形象研究[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2010.
[15] 高翔.從劉慈欣作品看中國科幻小說的語體特點[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7(S2):255-258.
[16] 陳薇薇.劉慈欣《三體》中的修辭特色研究[D].云南:云南師范大學,2018.
[17] 王艷.為什么人類還值得拯救?科幻文學的對話[M]//劉慈欣. 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劉慈欣科幻評論隨筆集. 四川: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173-182.
[18] 劉珍珍.后現代主義視野下的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9:1-36.
[19] 屈菲.從黑暗森林到生活世界——論《三體》系列小說中的話語意識[J].文藝爭鳴,2015(09):143-148.
[20] 王瑞瑞.論科幻文學的宇宙倫理——以劉慈欣的“三體系列”為中心[J].江淮論壇,2018(05):175-180.
[21] 李廣益.羅輯的決斷:《三體》的存在主義意蘊及其文化啟示[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12):1-16.
[22] 王衛英,徐彥利.劉慈欣科幻小說《贍養上帝》中的三個設問[J].科技視界,2018(29):10-13.
[23] 納楊.從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談當代科幻小說的現實意義[J].當代文壇,2012(05):83-86.
[24] 趙柔柔.逃離歷史的史詩:劉慈欣《三體》中的時代癥候[J].藝術評論,2015(10):38-42.
[25] 陳頎.文明沖突與文化自覺——《三體》的科幻與現實[J].文藝理論研究,2016,36(01):94-103.
[26] 歐樹軍.“公元人”的分化與“人心秩序”的重建——《三體》的政治視野[M]//李廣益.中國科幻文學再出發.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50-61.
[27] 王靜靜.論劉慈欣《三體》中的“文革”敘事[J].小說評論,2016(03):170-175.
[28] 趙汀陽.最壞可能世界與“安全聲明”問題[J].哲學動態,2019(03):8.
[29] 吳飛.黑暗森林中的哲學——我讀《三體》[J].哲學動態,2019(03):16-25.
[30] 楊立華.科技紀元與三體《春秋》[J].哲學動態,2019(03):26-31.
[31] 劉慈欣. 類型文學沒必要獲得主流文學的承認[EB/OL]. (2013-4-6)[2019-10-31]. http://www.chinanews. com/cul/2013/04-06/4704841.shtml.
[32] 王峰.科幻小說何須在意“文學性”[J].探索與爭鳴,2016(09):124-127.
[33] 王瑤.鐵籠、破壁與希望的維度——試論劉慈欣科幻創作中的“驚奇感美學”[J].現代中文學刊,2016(05):95-101.
[34] 劉大先.總體性、例外狀態與情動現實——劉慈欣的思想試驗與集體性召喚[J].小說評論,2018(01):49-58.[35] 陳舒劼.“長老的二向箔”與馬克思的“幽靈”——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J].文藝研究,2019(10):77-87.
[36] 賈立元.“光榮中華”: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中國形象[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3(01):39-45.
[37] 羅雅琳.新穎的劉慈欣文學:科幻與第三世界經驗[J].現代中文學刊,2016(05):84.
[38] 李廣益.中國轉向外在: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08):48-61.
[39] 毛孟啟.娘子關頭窺皓月——谫談劉慈欣小說與中國文化精神[J].當代作家評論,2020(02):122-129.
[40] 陳海琳.災難·抗爭·救贖:劉慈欣和王晉康的末日書寫——以《三體》系列小說和《逃出母宇宙》為中心[J].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33(4):50-55.
[41]范軼倫.劍與詩:古典文化帶來未來救贖——《詩云》和《斷章》中的身份認同比較[M]//李廣益. 中國科幻文學再出發.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116-132.
[42]李云. 阿瑟·克拉克對劉慈欣《三體》三部曲創作的影響[D].湖南大學,2016.
[43]張曉妮.劉慈欣對阿瑟·克拉克科幻作品的接受研究[D].貴州大學,2017.
[44]顧憶青.科幻世界的中國想象:劉慈欣《三體》三部曲在美國的譯介與接受[J].東方翻譯,2017(01):11-17.
[45]付筱娜.攜想象以超四海——《三體》的海外傳播之鑒[J].當代作家評論,2018(01):174-179.
[46]劉舸,李云.從西方解讀偏好看中國科幻作品的海外傳播——以劉慈欣《三體》在美國的接受為例[J].中國比較文學,2018(02):136-149.
[47] 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J].上海文化,2011(03):17-30.
[48] Hua Li.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Liu Cixins Critical Utopia:China 2185[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15, 42(3):519-540.
[49] Joshua Rothman. Liu Cixin - Chinas Arthur C. Clarke[EB/OL].(2015-8-24)[2019-10-31]. http://www. chinadaily.com.cn/interface/toutiao/1139302/2015-8-24/cd_21688078.html.
[50] 上原香.劉慈欣科幻小說的角色小說化:從《超新星紀元》到《三體》[M]//石曉巖.劉慈欣科幻小說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90.
[51] Gaffric, Gwenna?l, and Will Peyton. Liu Cixins Three-Body Trilogy and the Status of Science Fi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19, 46 (1): 21-38.
[52] Dougherty, Stephen. Liu Cixin, Arthur C. Clarke, and “Repositioning”[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19,46 (1):39-62.
[53] 吳巖.科幻文學論綱[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1.
①根據《劍橋科幻文學史》的說法,在坎貝爾時代,“一些科幻迷寫信闡述他們對科幻歷史和未來發展可能性的理解,他們的討論代表了建立針對科幻的批評理論的首次嘗試”。
①指劉慈欣目前已發表的《夢之海》(2002)、《詩云》(2003)和《歡樂頌》(2005),以及計劃中的雕塑藝術篇、繪畫藝術篇和行為藝術篇。
①英文論文“Variations on U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原刊于美國Science Fiction Studies雜志第40卷第1期,2013年3月。中文翻譯《中國當代科幻的烏托邦變奏》,發表于《中國比較文學》2015年第3期,譯者畢坤。
②英文論文“After 1989:The New Wa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發表于China Perspectives,2015年第1期。中文翻譯《1989年以后:中國科幻新浪潮的烏托邦變奏》,發表于臺灣《中國現代文學》2016年下半年刊,譯者王振。刪節后的簡體版《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發表于《南方文壇》2017年第3期。
③文本見科幻小說網:http://www.kehuan.net.cn/book/2185.html(最后查閱于2020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