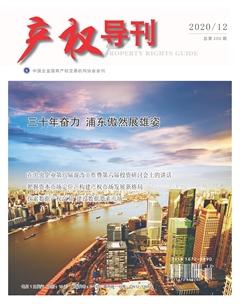尋找極端經濟下的“先頭部隊”
禾刀
經濟,如同一個社會煙火氣的晴雨表。著名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曾描述了這樣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場景:敵人用火和劍把一個國家夷為平地,摧毀了這個國家幾乎所有可移動的財富,所有的居民都被消滅了,然而幾年之后,一切又都和以前一樣繁榮。
穆勒描述的戰后經濟,正是本書作者、英國央行經濟學家理查德·戴維斯關注的極端經濟現象之一。理查德指出,在經濟領域,“極端”并不僅僅用來描述我們熟悉的股市崩盤、住房危機或金融丑聞等現象,也可以用來表述難民營、監獄、災害突發地、工業革命發源地、不平等地區、老齡化地區、科技前沿地區等經濟體。
春江水暖鴨先知。凱恩斯把那些生活在塑造經濟趨勢的極端情況中的人稱為“我們的先頭部隊”。 為了尋找“先頭部隊”,理查德通過16萬公里的行程,以及對500多名當地官員、居民、罪犯等的采訪,以了解和還原當地的經濟、市場和生活的真實面貌,闡述了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人們如何生存、重建社區、恢復經濟和市場;在極端優質的條件下經濟為何會走向失敗;在代表未來趨勢的極端經濟體,人們如何應對老齡化、高科技和不平等。跟隨理查德的追尋腳步,我們隱約發現了經濟韌性背后的特殊力量。
極端之中有韌性
眾所周知,當前全球“大多數國家都面臨三種趨勢:人口老齡化、新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不平等的加劇”。理查德尋找應對這些極端問題答案的動機來自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28年提出的一個觀點:如果我們知道看向哪里,我們今天就能瞥見未來。其訣竅是找出一種持續的趨勢,以及大多數人都在遵循的道路,并觀察那些經歷過這種極端趨勢的人的生活。這種觀察當然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理查德反復強調的極端經濟中的韌性。
在理查德看來,這種韌性主要有三大要素,即人們的思想、技能和知識的力量。三大要素中,思想是第一動力,正所謂“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技能和知識就像人們逆勢上攀的左右腳,缺一不可,否則就只有一腔夸夸其談的抱負。
陸游有詩云,“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世人們以此詩形容極端情況下或許蘊藏另一種重生希望,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理查德筆下的極端經濟,描述經濟觸底過程中,往往也蘊藏著一種類似的反彈韌性。
在理查德尋訪的全球9個地區中,韌性無處不在,越是極端條件下,這種韌性表現得越強烈越明顯。在遭遇印度洋海嘯之后,印度尼西亞的亞齊人放下失去親人的悲痛,迅速投入到復工復產的重建中,當地旅游經濟很快重煥生機;約旦扎塔里難民營,人們充分發揮個人聰明才智,把那里打造成一個擁有各類初創“企業”3000多個、就業率高達65%的經濟體;路易斯安那州監獄的囚犯創造出一種完全區別于高墻外經濟的“數字貨幣”——整個過程看不到貨幣,雙方交易只需要報個數字;日本秋田充分發揮老年人余熱,實現了老有所“勞”、老有所“入”,為解決老齡社會問題趟出了一條新路;剛果金沙薩市場里的人們面對無處不在的腐敗,創新出應對監管腐敗的地下市場……
其實,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經濟韌性同樣無處不在。澳門大學教授王笛在《消失的古城》一書中寫到,1917年,成都先后遭遇川滇、川黔軍閥混戰,民眾苦不堪言。然而,每次巷戰尚未完全停歇,小販們就冒著生命危險出來兜售貨物和食品。葉曙明在新近推出的《廣州傳》一書中亦多次提及,廣州城歷史上每次戰爭剛歇,街頭很快便會出現小攤小販的身影,有時這條街在打仗,另一條街卻還有人在賣東西。
中國有句老話,富貴險中求。險,其實就是一種極端的經濟環境。理查德指出,極端經濟可以“分配稀缺資源,幫助人們定義角色和身份,并賦予他們生命的意義”。把僅有的資源發揮至極致,與其說這是經濟的韌性,不如說是生命的韌性。在極端環境的“倒逼”下,人們不得不窮盡思維,放低身段,只要能生存,過去那些不愿想,不愿做的都會被迫進入選擇視野。
韌性之中存利弊
分析理查德的9個案例不難看出,經濟韌性雖然落腳點無一例外都是個人,但成功又不僅僅因為人。
亞齊的成功,縱然有當地人喜歡儲備黃金的傳統,但政府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幕后角色。比如積極請求國際援助,對當地旅游設施重新規劃,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在扎塔里難民營,那里的極端經濟之所以活力十足,得益于聯合國難民署人手不足“管不過來”;愛沙尼亞之所以能夠快速步出前蘇聯解體后經濟嚴重下行的泥淖,是因為政府審時度勢,及時抓住了依托互聯網的創新發展思路;日本秋田的老齡社會之所以朝氣蓬勃,是因當地民間機構活躍,并且形成了一種接受、支持乃至鼓勵老年人力所能及的社會文化價值觀……
9個案例并不全都是正面典型。理查德也列舉了約旦的阿茲拉克難民營死氣沉沉、巴拿馬達里恩當地政府柚木樹補貼計劃反倒使百姓從貧窮走向新的貧窮、曾在全球首屈一指的蘇格蘭格拉斯哥造船業因循守舊如今一落千丈、剛果金沙薩充分展示了建立在非正規經濟基礎上人類韌性的局限性、曾享有拉美經濟明星美譽的智利因嚴重不平等已經影響到公共空間的使用……
成功的原因只有一個,失敗的原因則各有各的不同。理查德相信,“許多復蘇的崩潰都是善意的結果”。像阿茲拉克難民營表面看井井有條,實際上扼殺了難民的初創熱情;達里恩的問題是因為政府應對外部負效應失策導致當地經濟和環境陷入惡性循環;格拉斯哥造船業的衰落是因為政府介入過度未能順應潮流;金沙薩的沒落折射出政府決策違背了市場基本現實;智利深陷的不平等困局,本質上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率的結果。
對照利弊,理查德得出結論,好的經濟需要好的政策環境。好的政策環境當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并非完全沒有規律可循。在理查德看來,政府最應做的,就是堅決捍衛環境等社會底線,同時又不能大包大攬、越俎代庖。雖然強勢行政力量在某一時段雖可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走向深入,個性化需求越來越多,過于強勢必然遏制個性化。金沙薩和智利歷史上都曾出現過“鐵腕”人物,改革之初,也都曾經歷經濟快速發展的高光時刻,但又都深陷發展“中年危機”無以自拔。
日本秋田應對老齡社會的積極做法,顯然是一個值得可資借鑒的案例。那里就像是一個老人社會,無論公交車駕駛員、商店服務員等,隨處可見老年“職人”的忙碌身影。日本秋田趟出的老齡社會新路,不是政府照單全收,而是區分年齡和身體狀況,在稅收以及公共建設政策等方面予以傾斜,方便老人力所能及地體現更多社會價值。最近在網上還看到一條視頻:日本有一個餐廳服務員幾乎每次都會上錯菜,其原因就在于服務員都是阿爾海默茨氏綜合癥(老年性癡呆)患者。盡管如此,食客仍舊絡繹不絕,樂此不疲,相互包容,相互尊重。
秋田構建的良好社會關系,背后是個人與政府力量的完美契合。雖然任何走出極端經濟的國家,都離不開政府的作用,但行政力量到底該扮演何種角色,這也是包括凱恩斯和哈耶克在內,無數經濟學家反復交鋒,又難以完全說服彼此的關鍵所在。
利弊之中見未來
不難看出,凱恩斯意義下的“先頭部隊”,其實就是在極端條件下最先嗅到“商機”的那些人。這些人很可能代表走出極端經濟的未來模式。未來并不是另起爐灶,現實社會中常常隱藏未來發展的蛛絲馬跡。這一點,我們亦有成功體會。十一屆三中全會率先吹響了農村土地責任承包制的號角,而在此前,肇始于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已悄然破繭,并收到良好效果。
應對極端經濟,理查德著重論述了經濟中的左右派之分。無論是采取激進還是保守舉措,無論是推行政府主導還是市場自由主義,理查德都不認為是最優方案。過左,其結果很可能步達里恩、金沙薩和格拉斯哥等地的后塵,過右,則易蹈智利那樣的覆轍。
理查德指出,“好的市場會創造價值,不好的市場會摧毀價值”。這里的“價值”,既包含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也包括社會意義上的。理查德這里所指的創造價值,顯然既不完全屬于個人,也不完全歸功于政府,而是二者的完美配合。這也就是理查德所力推的,走出極端經濟的“中間道路”。
理查德意義下的“中間道路”,當然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市場和政府二者相互配合,產生最大的經濟合力。像達里恩的森林保護,顯然需要政府力量守住底線。而在格拉斯哥,顯然是政府介入過度,導致當地造船業面對國際市場新形勢反應遲鈍。
理查德的9個極端經濟案例表明,沒有任何一種成功模式可以生搬硬套。但所有案例又同時指向同樣的結論:未來方向很可能本就隱藏于極端經濟的各種韌性之中。也就是說,對于未來方向,許多時候我們不必絞盡腦汁推陳出新,只需練就一雙尋找韌性,并甄別“先頭部隊”的慧眼,然后因勢利導,順勢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