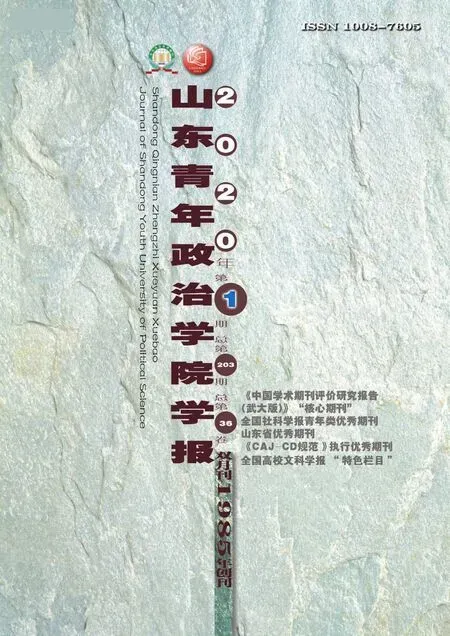受壓·失控·表演:青少年自殺行為歷程研究
胡沈明,鄭 丹
(江西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南昌 330022)
一、研究緣起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1]顯示,每年有80萬以上的人死于自殺,更有不少于10倍的自殺未遂者。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過去16年的統計數據,中國青少年自殺率雖持續下降,但情況依舊嚴峻,已成為繼交通事故、溺水和白血病之外的第四大致死因素。
對于自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殺的現狀以及自殺原因的探尋上。1897年,涂爾干就認為,社會形成的集體力量,決定著自殺人數的變化,并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解釋自殺的原因。[2]此后,莫里斯哈布瓦特、卡爾門林格爾、施納曼德等國外的學者不斷在迪爾凱姆基礎上豐富理論,相繼提到了社會鼓勵、沖動行為、判斷錯誤等觀點。我國關于青少年自殺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自殺現狀研究多關注“北上廣深”等經濟發達地區、以及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研究認為自殺原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有遺傳、心理和人格三大因素組成,其中遺傳因素引起的病理現象包括狂躁癥、抑郁癥、精神分裂[3]等;心理因素主要包括抑郁程度[4]、焦慮感[5]、生活滿意度[6]、孤獨感[7]、壓力感、絕望感[8]等;人格因素包括偏執和敵對[9]。外部因素則主要包括家庭環境、學校教育和社會環境。家庭環境主要與青少年所成長的家庭中關系親密度[10],家庭矛盾的沖突性[11],父母養育方式[12]以及童年創傷經歷等相關。近期研究表明,被人打罵、被壓迫感、缺乏成就感、學習不適應,以及老師、同學、戀愛等人際關系不適應等現象是我國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的主要原因。
已有理論研究表明,青少年自殺行為的產生與所處環境以及自殺意念的形成密切相關,但相關研究缺乏對青少年自殺既遂和未遂者生命歷程的關注,詳細描述其在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中的表現,對于認識了解和防止青少年自殺行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二、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對何為青少年,界定并不一致,但總體而言落在10-25歲的年齡區間內。在我國,青少年大學畢業年齡一般到25歲左右,大部分人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接觸社會較少,其思想相對單純。根據大眾認知、獨立生活能力以及心理學的界定,本研究主要關注“10-25歲”的青少年群體。
為充分了解自殺青少年自殺前的生命歷程,課題組選擇了八個有代表性的案例進行深度訪談,成功完成七個案例的訪談工作。我們充分考慮到自殺青少年的年齡、身份、性別、社交媒體使用情況以及自殺直接原因等方面因素,力求案例具有最大的代表性。

表 1 調研采訪案例詳情
為保證調研所獲取的材料真實可靠,課題組充分培訓了5位組員,赴多地調研,重點訪談自殺者的近親以及其他主要社會關系,力圖還原其自殺前的相關經歷。訪談記錄將近40萬字,一般每個案例花費時間在兩周左右,每個案例訪談人數約在10人左右,訪談時間在2-10小時。在找到訪談對象之前,需花費大量時間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尋找、聯系并說服訪談對象接受訪談。對于部分拒絕面談者,在確定身份真實性后,通過社交媒體訪談。針對自殺研究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調研組員之間相互督導,避免移情效應,同時貫徹不傷害原則,積極傾聽各方意見,弱化獵奇心,強調公益性和幫助受害者。
三、自殺歷程分析
研究發現,由于青少年經濟尚未完全獨立,其生存高度依賴家庭,其學習高度依賴學校,戀愛中的青少年關系高度依賴戀人,因此他們所處的結構高度封閉,更易遭受結構的壓迫。由于身處單一封閉結構之中,青少年往往不具備逃出結構的思維能力,因此其認知往往容易失控,造成用身體解決問題的思維,從而形成自殺意念。他們往往將自殺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自覺地加以“表演”,進行抗爭。
(一)日常生活遭遇壓力
結構猶如一張大網,讓生于其中的人無處逃脫。人無時無刻不是處于某種社會結構之中,大至宏觀政治結構,中至工作場所生成的結構,小至家庭環境甚至是戀人之間所營造的結構。在各種社會結構中,因結構形態不一,其對個體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形成的壓制不同。相對而言,社會和政治結構與個體關系較遠,而工作場所和家庭則直接與個體生存相關,它深刻地影響著個體的生存方式。在宏大社會結構中,因結構而生成的“怨恨”最終往往會以“集體行動”[13]結束,這種結構誘因最終反而導致社會關系更加緊密,從而形成集體行動。在工作場所或學習場所中,結構性緊張如有家庭結構做支撐,個體反抗的力度也會較大,一般也不易產生自殺傾向。但是一旦結構緊張源自于家庭、學校甚至是戀人之間,則個體社會關系極易斷裂,從而形成社會關系斷裂型自殺行為。
1.生活結構壓迫
對近6年83起見諸新聞報道的青少年自殺事件進行統計發現,青少年自殺多與家長、教師、同學霸凌、失戀等相關,部分案例則與學業無成和工作失敗相關,亦有少部分與網貸等經濟層面的原因相關。
在當代家長與子女的關系中,學習和聽話成為家長評價子女行為的重要方式,部分家長“物化”子女的眼光非常嚴重,有時甚至使其成為唯一的方式而不自知。從青少年的角度來看,如其未形成正確的學習觀,則非常容易形成“為父母讀書”的價值觀念。在南昌和九江出現的兩例優秀高中生自殺事件中,當事學生成績優秀,僅因一次考試失利,一次家長責罵,便憤而跳樓/湖。在校園內,由于升學的壓力,教師無論是精力還是“鼓勵資源”都傾向于優秀學生,從而無形之中對一般學生形成壓力,也使得優秀學生陷入到普通學生、教師和家長織就的群體壓力之中。在眾多學生與教師形成矛盾導致的自殺事件中,“檢討”“懲罰”等往往成為重要的誘因。雖然將原因僅歸結為一點有失偏頗,但是深度訪談的結果表明,對學生尊嚴和人格的不尊重是一個重要的誘因。在湖南唐云思自殺事件中,家長與教師的“合謀”則使得青少年失去最后的依靠,從而產生對他者強烈的不信任感。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家庭中父母占據主導地位,在學校中教師占據主導地位,在這兩種封閉結構中,評價標準主要源自于父母和教師,從而形成事實上的威權結構體系,他們或采取暴力手段逼迫,或采取經濟手段制約,或采取電腦游戲時間控制,或利用親情壓迫。在學校中,不少教師采用群體壓力的方式區隔學生,這些使得青少年無力反抗,無處逃遁。在山東“殺魚弟”自殺事件中,“殺魚弟”的父親早就為其規劃好了“殺魚”的一生,“殺魚弟”行為稍有偏頗即招來惡打,一次惡打甚至能將眼睛打傷。在江西南昌某高中生自殺事件中,家長看到學生玩手機游戲,直接上升到品格問題。在“袁嘉辰”自殺事件中,事件起因僅僅是教師未履行諾言。而戀人之間由于結成了相對緊密的關系,結構更加封閉,一旦一方拋棄另一方,結構雖然消失,但壓迫感非常強。總之,無論是重視、歧視還是漠視,其對處于結構中的個體都會產生巨大壓力。
2.社會關系壓迫
理論上來說,個體性格、價值理念和社會關系是導致自殺的重要原因,從既有研究成果來看,自殺行為又具有較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因此任何一種對自殺原因的探討僅是提供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并不具備完全的演繹特性。從青少年的成長來看,父母、同學、教師、網友、男/女友都可成為支撐其生存和發展的社會關系。在相關自殺案例中,自殺者往往顯著地選擇一種社會關系而排斥其他社會關系,或者說沒有選擇其他支撐性社會關系來作為自己生活下去的理由,這點令人費解。
對案例的深入發掘表明以下幾點:個體在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尤其是“男/女友”關系之后,往往排斥或忽視其他社會關系;相關社會關系主體對自殺者的社會評價高度一致;自殺者往往忽視對最親近關系的信任和維護,遇見問題后與相應社會關系的交往欠缺。
近年來,高校學生自殺多與失戀相關,中學生自殺多與學業壓力和教師評價相關,無業人員自殺多與自身價值理念遭遇壓制相關。在大學生進行戀愛之后,其社會關系具有典型的排斥行為,具體表現在大學生對學業、同學以及家長的疏遠上。中學生在遭遇學生壓力之后,往往想當然地認為家長和教師的評價高度一致,從而喪失進行社會交往的信心。
在王建成案例中,無論是兄弟、父母還是同學和教師,大家對其一致的評價就是邋遢,不上進。相關社會關系評價高度一致使得自殺主體一旦接受其他社會關系,非常容易形成評價幻象,進而產生過激行為。如王建成在女網友同意不再“分手”之后,依然選擇了自殺。
在一些校園霸凌事件、網貸事件以及教師性搔擾事件中,當事學生往往選擇獨自面對困境,不主動走出自己的思維怪圈,不主動交往,進而造成精神壓力或出現自殺行為的比比皆是。
3.職業行為壓迫
對工業化時代工人的自殺行為研究表明,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致,人們的社交行為變得更加簡單,工廠和家庭甚至是工廠宿舍“兩點一線”式生活使得多數人形成相對單一的行為和交往體系,從而容易導致自殺行為。青少年由于多處于學習階段,其行為場所多為學習、家庭或宿舍“兩點一線”,行為模式高度單一,且持續時間多達十余年。在這么長的時間內,家長的評價、學校的評價相對單一,他們對青少年行為的真實意義解讀存在偏差,且易受青少年行為和情緒的影響,雙方極易形成對立。一旦學生未能趕上社會評價的節奏,則非常容易導致心理問題,甚至產生自殺行為。
在選取的案例中,王建成、殺魚弟和胡靖并非處于學校環境之中,但依然產生自殺行為,王建成死于自我想象的網戀,胡靖死于創業失敗,而殺魚弟則因長年殺魚、心生怨恨而自殺。三人實際也形成了單一行為和單一評價。
(二)思維方式出現失控
處于一定結構之中的青少年,結成了特定的社會關系,最終在社會關系中形成失控的思維方式。調研表明,逐步邊緣、爭取主流、逃避現實、暴力反抗是青少年形成極端化思維的四個階段。進入暴力反抗階段后,青少年將身體作為執行思維的基本工具,容易出現傷害他人或傷害自我的行為。
1.階段一:遭遇排斥淪為邊緣人群
青少年所處結構一般分為四大類:家庭結構、校園結構、戀人結構以及其他關系結構。與成人相比,觸發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一般較小,如教師父母責備、遭遇欺凌、成績下降、失戀、承諾未兌現、遭遇詐騙、經濟危機等。但這類事件普遍具有被結構排斥的特性。如家庭結構中,子女與父母的評價體系產生不一致,在校園中未能保持良好成績,在同學關系中被欺辱,在戀愛關系中被拋棄等等。作為一種被評價的客體,一些青少年喪失了自主建構自我的能力,在遭遇排斥之時,他們逐步邊緣化。
2.階段二:錯用方法力圖融入主流
米德的“境中我”理論表明,人的社會存在源自他人,追求他人認同是一種本能。因此,在被邊緣化的過程中,青少年存在一種爭取主流的過程,但對自我被邊緣化的原因、過程以及應對措施缺乏清晰的認識。同時,一部分青少年由于無法通過努力和提高成績的辦法獲得關注,往往采用一些令人生厭的方式追求認同,從而與正常社會認知之間產生偏差,最終導致越來越邊緣。
自殺者胡靖家庭條件優渥,家庭成員經濟成功者眾多,自小便渴望自己賺錢,獲得家庭認可,在創業失敗后選擇集體“燒碳”自殺。王建成性格內向、成績較差,他用“臟”和“吹牛”吸引同學。濮陽的高三男生袁嘉辰向學校提出換宿舍的申請,并按照規定考進全級前30名,但校方未兌現承諾,最終選擇自殺。同樣,衡陽的初三女生也想用服用大量處方藥的方式來恐嚇老師,她認為自己只能用這種方式去懲罰對自己態度不好的老師。2018年慶陽女生跳樓自殺,原因僅是班主任未得到她想象的懲罰。
調研發現,自殺青少年都有一段較長時間的爭取主流,回歸正常生活的經歷,但由于他們形成的解決問題路徑與既有正常解決問題的路徑存在較大差距,從而不僅使得其問題未能解決,他們反而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部分青少年甚至發展為精神疾病患者。
3.階段三:進行消極抵抗逃避現實
當已有的想法無法實現之時,青少年往往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逃避現實的過程,采用各種消極抵抗的方式抵消結構對其施加的壓力。不交流、不積極、不主動、個人生活習慣變糟等是常見的表現。在傳統社會中,隨著生活場所的變化、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逐步成年結婚成家等,其生活可能獲得一定支撐。但在網絡時代,隨著虛擬場景全面介入生活,部分青少年以此為解脫,沉溺網絡、游戲和社交,獲得另外一種關系。
人們一般認為逃避是一種對結構抵抗的重要方式,當他們選擇逃避之時,意味著其自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青少年的逃避可能被封閉結構中的權威視為極大的威脅之時,其結果很可能就是悲劇。如殺魚弟被父親視為懶惰,王建成從一種結構中進入了另一種“結構”——網戀。前者與父親產生激烈爭吵后選擇“喝藥”,后者在網戀失敗后徹底喪失生活的信心。事實上,從已有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一種規律,逃避現實、進行消極抵抗之時,也就意味著青少年的思維被逼至“角落”,再進一步便是“死亡”。
4.階段四:養成極端思維以命抗爭
消極抵抗讓青少年暫時獲得了思維的寧靜,獲得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由于這種解決問題的模式與社會既有解決問題的模式存在較大的偏差,因此其遭到否定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們或與父母爭吵、或創業失敗、或被忽視、或被否定,或被網絡不良情緒引誘,總之,沒有一種路徑能滿足他們的訴求。從這個層面來看,從思想或認知層面解決問題的路徑似乎已經斷裂,剩下的便是人的本能——暴力。這種暴力既包括對自己的暴力,也包括對他人的暴力。對他人的暴力表現為積極尋求生命的意義,證明自己最后的存在價值。而對自己的暴力則是一種表達,胡靖用進入自殺群約死方式表達,孟志濤則藏好百草枯以備與父親沖突,慶陽女生用公共場所跳樓進行表達。
(三)社會行為開始異常
青少年所遭遇的危機事件在成人的眼里極容易解決,但卻成為導致青少年自殺的“稻草”。這實際上表明,青少年認知模式與成人認知模式存在巨大差別。一般認為心智成熟者的自殺多源于自我認知層面的生命意義消失,但青少年自殺多源自社會承認的消失,其生命意義建構并非來源于自我,而是源自于其親密接觸者。從對多個自殺案例的訪談和分析發現,集體參與、恐嚇、反抗和泄憤型自殺在青少年中所見較多,身體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其行為和思想表達的一種工具。
戈夫勒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著表演,它是“一個特定的個體在任何特定的場合所表現出的全部行為,這種行為可以以任何方式對其他參與者中的任何人施加影響。”[14]與藝術表演虛假性不同的是,青少年自殺行為卻是真實意念的表達。如果行為所表達的意義能充分被他人認同,則表演會停止,如果未被理解甚至遭受質疑,則表演會淪為現實的行為。這個意義上來看,青少年的自殺表演行為,更多的是一種表達行為,目的在于獲得意義和理解,不過從大多數情況來看,他們的表達并未得到應有的理解。然在社交媒體時代,青少年的這種表演獲得了媒體的支持,他們提供了三個重要的功能:一是推遲自殺的時間,二是強化自殺的意識,三是提供自殺表演的空間。
在形成自殺“表演”的真實行為之前,青少年一般經歷了疏遠親人和尋找知音兩大歷程,當兩者均無法滿足其“平等交往”和“對話”欲望之時,尋找更為廣闊的表演空間便成為必然。
1.逐步疏遠“親人”
通常情況下,代際之間交往困難。傳統社會中,由于知識主要從上一代向下一代傳播,代際之間矛盾相對較少。如今的社交媒體時代,青少年媒介技術的使用能力或者某些方面的見解相對強于上一代。在民主家庭,家長會接受子輩的知識傳播,然而,在絕大多數家庭,尤其是子女尚處學習階段,控制媒介使用時間和頻率是家長的必修功課,從而使得代際之間的信息流動急劇減少,部分青少年與虛擬空間中群體交往大于與父母或教師之間的交往。不但如此,青少年對虛擬空間中信息的信任度也大于對家庭成員或教師的信任度。在親近群體無法走進青少年內心之時,無論是遇到戀愛問題、工作問題、學習問題還是經濟問題,青少年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與父母交流、尋求幫助,而是傾向于獨自解決問題,這種“自我想象性獨立”是導致青少年出現自殺及其它心理問題的一個重要誘因。
親近群體無法走進青少年內心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家長過分以職業角色規范青少年行為。在唐云思案例中,其母親要求女兒寫檢討書,實際上“檢討書”這一文本多用于公開正式場合,具有一定的侮辱性。而唐云思在QQ群中明確表示了厭惡之情,“媽的,說我數學考得不好,還說我其他科目考的什么東西,讓我寫檢討”。
在“殺魚弟”案例中,“殺魚弟”經常遭到父親的毆打。無論是“檢討書”還是“毆打”,其本身與父母的角色表現具有較大的差距,難以走進青少年內心便成自然之事了。
二是家長與青少年在人生目標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國父母與西方父母在兒童教育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區別,中國父母以是否成才為標準,而多數西方父母則以是否成人為標準。中國父母考慮較為長遠,往往將小孩一生考慮到自己的年齡為止甚至更遠,西方父母則重視培養小孩的獨立性。父母以成年人的眼光看待未來,而青少年群體則很難以成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即便以成人的眼光看待世界,也會以少年老成、喪失青少年樂趣為代價。
三是父母與子女間的儀式性交往較少,而目標性交往過多。近年來,“逼婚”一詞的產生就帶有典型的這種特征。由于父母對子女了解甚少,儀式性交往過于簡單,子女的學習、工作業績和成就便成為交往和詢問的主要內容,雖然帶有一定的儀式性,但是對子女而言,則具有實質的內容,容易產生侵犯其私人領域的感覺。目標性交往過多,使得子女與父母間的關系變成了職業關系和工具關系,子女有明顯的“被物化”的感覺。
2.尋找陌生“知音”
人們之間的交往有工作學習等的職業性交往,家長與子女間的儀式性交往以及同類群體間的日常生活或娛樂性交往。職業性交往體系中,人們很難形成親密的關系。家庭儀式性交往體系中,往往受到各自角色定位的影響,交往難以發自心靈深處。而同類群體的日常生活交往,由于具備較多的共同話語,彼此具有一定的平等性,容易取得滿足感。同時,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往有時往往要多于學生與家長、學生與教師的交往。這種“多”并非單純指時間上的“多”,而是指雙方交往的平等性、協商性和崇拜性。
已有案例中,自殺者在尋求自殺意見、方式時往往會在同類群體內發表意見,尋求幫助。湖南的唐云思在被母親罰寫檢討書時,就在班級QQ群中表達了自殺的想法。此時,群中雖有勸說者,但更多的同學表達了不相信,亦有部分同學扮演鼓勵者的角色,還有不少同學將此事當做一個簡單的知識探討問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居然有兩位同學陪同自殺。
從自殺群聊天記錄的內容判斷來看,準備自殺者確實能夠在這類社群中獲得短暫的精神支持和安慰。在激情自殺之外的自殺案例中,我們都能發現這種與同類群體順暢交往的痕跡。但是作為一個正常的青少年,他們很難區分玩笑與真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他們在一起僅僅是因為很偶然的因素,很多時候他們之間并不能夠真正了解對方,亦無法判斷事情的嚴重性。在唐云思的班級群里,沒有一個學生將聊天記錄告訴家長或老師,自殺與其它信息一樣被當作毫無意義的信息,一種聊天的主題。
這就是一種悖論,自殺者真心想傾訴的群體是對其生活和情感漠不關心者,是對其意義表達不進行具體解讀的人。不過,我們無法否認的是,同儕群體是這類自殺群體感情的真實和廉價支持者。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同儕群體交往圈的封閉性和情感的過分支持是自殺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青少年群體中簡單的“義氣感”,簡單的“抗爭模式”也是自殺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群體交往中,由于情感迅速累積,結構性怨恨被凸顯,觀點非常容易極化,最終部分群體成員產生“以命抗爭”的心理。
3.嘗試自殺“表演”
日常生活中,“表演”帶有一定的貶義,強調其虛假性,但戈夫曼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種表演。在社會學中,表演帶有明確的“抗爭”意味,是個體調用各種社會資源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在社會抗爭模式中,“以法抗爭”,“以媒抗爭”和“以命抗爭”所見較多。但無論是“以法抗爭”還是“以媒抗爭”,抗爭主體都占有身體之外的資源,通過調動這些資源,有效地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是在青少年群體以及一些社會資本缺失的群體中,不擁有知識和金錢導致其選擇面較窄,從而將身體作為媒體,進行表演和抗爭,最終力求獲得一些收益。
就青少年自殺而言,其表演場所集中在兩個層面:一是現實場景,表現為公共場所;另外是虛擬社交平臺。如湖南學生集體自殺的吃藥地點選在教室內,公共場所跳樓自殺者往往會有較長時間的思考等。
江西南昌王建成在自殺前21小時,給16歲的網友文文發來信息:
“我打算離開了,離開這個世界,就明天。”“不信我明天可以給你拍視頻。”“我已經選好地方了,夢時代。”(王建成自殺前QQ聊天記錄)
但文文看到手機屏幕上這些“蠢話”,只是簡單地責備了王建成。她沒有過分在意,猜想只是“玩笑”而已。
在虛擬社群中,支持、點贊、夸獎越來越盛行,人們不分對錯,不論好壞,在群體中體驗自身想法正確的幻象。每個人也不管內容真假對錯,交流、互動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在這類群體中,對“技術”“技巧”和“情感支持”的重視遠遠大于對事實后果的重視,即便是在探討自殺的方法,人們也會點評各類自殺方式的優劣,而不會關注某些人正準備自殺。調研表明,虛擬群體間如不加以管制,其對知識技能的挖掘、情感的支持會遠遠超越法律界限和倫理界限,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群體可以一哄而散,不用負責。
在現實公共場所中,由于圍觀人群都是匿名群眾,不少人帶著旁觀和起哄的心情觀看,而未真正關注到生命的消失,從而也不太明白自殺的表演性質,反而激化表演行為,諷刺其非真實性,進而使得部分表演性自殺演變為激情自殺。
四、對策與建議
傳統研究往往簡單將自殺歸結于家庭與學校教育,從而導致較難防止自殺。根據調研,我們發現青少年自殺的結構思維問題、渴望交流問題以及行為表演的意義傳遞問題,我們嘗試從新的視角提出幾點緩解自殺的辦法。
(一)改思維:避免結構體內解決問題
無論是成語“坐井觀天”,還是日常用語“屁股決定思維”,都表明了一個關鍵問題,人思考問題很難脫離其所處結構,或者說社會位置與社會結構決定著人的思維模式。已有調研表明,由于年齡的原因,青少年對結構的依賴度遠高于成人,結構壓迫對其行為的影響極其深遠。從青少年的行為模式來看,自殺既具有反抗的意味,又具有突破結構、遠離結構的意味。但是他們采用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卻依然是處在結構之內,沒有采用有效的思維方式突破結構。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防止青少年自殺首先應該改變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讓他們逐步形成超越結構思考問題的取向。具體表現為:首先要了解結構對人思考問題方式的影響;其次應該培養青少年多重結構意識,讓他們了解自己所處世界并非只有一元結構,而是具有多元結構特征,處理問題時能夠在不同的結構中進行轉換,從而避免在結構中“以命抗爭”;最后,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無論是教師還是家長,都應該培養青少年超越結構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從而有效避免“大腦短路”。
(二)建體系:評估與近親的疏離程度
在社交媒體時代,青少年形成自殺意念之后,往往會經歷一個社交媒體尋伴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他們的自殺實施時間,為挽救他們提供了一定的時間。因此,無論是家長還是學校均需要趕在他們自殺之前進行一定的干預,從而防患于未然。
青少年在網絡尋伴或尋找自殺工具之前,往往經歷了一個典型的疏遠親人的過程,有效地抓取這類信息,將能提前發現青少年自殺苗頭。這一方面需要家長和學校在日常生活中與青少年保持密切交往,另一方面需要他們根據交往頻度、交往內容、交往主動程度來評估青少年的情緒。交往頻度方面主要是日常生活中要保持相對頻繁的交往,無論是有內容的交往還是儀式性交往都需要注意頻度。交往內容主要表現為青少年對自我生活的暴露程度,高暴露表明交往順暢,低暴露表明交往不暢;交往主動程度主要表現為青少年是主動提及還是被動問起。通過對這些相關要素的關注,家長和教師便能實時感知青少年的心理變動。
(三)搭平臺:構建健康的陌生人關系
當青少年處在掙扎階段時,最需要來自外界的幫助。這一段時間青少年會按自己固有的行為模式否定自己,需要長者及時開導,幫助其糾正應對事物的直接想法。更嚴重者會產生自殺想法,表現出不同以往的形象和狀態,傳達出一種非主動的求救信號。
目前國內搭建的相關平臺主要是公益的自殺熱線以及各校設立的心理咨詢中心等,亦有部分人士在網絡上從事心理疏導工作,但是較少。根據已有調研結果,我們發現青少年具有網上尋伴的特點,這一過程既可以看作是表演過程,也可以看作是“求救”過程。但已有的社交媒體多對“自殺意念”起到強化作用,因此有必要構建全國性的公益平臺,讓健康的陌生人關系、健康的思維理念和價值觀及時傳導到具有“自殺意念”的青少年群體中。
(四)釋壓力:探索網絡健康釋壓模式
青少年自殺的誘因在于結構壓迫,壓力無處發泄,生命意義喪失或者說沒有找到生命意義。因此,可以根據青少年社交媒體接觸現狀,探索健康的網絡釋壓模式。
釋壓實際上是一種壓力轉移模式,而并非簡單地將壓力釋放出來。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自殺實際上具有一種典型的“表演性”,由于他們采用的實際的“自殺”模式,從而使得“表演”不具備可逆性,造成悲劇。利用網絡技術或AR(增強現實)技術,探索虛擬表演的可能性,對于自殺的實施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阻止作用。
五、結語
成年人自殺多源于生命意義喪失,而青少年自殺則與生命意義的獲取相關,因為其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本就認知不清,對生命意義的判斷有時也會失之淺薄,從而導致其自殺行為產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研究發現,結構壓迫是青少年自殺的重要誘因,而且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逃出這種結構的壓迫,無論是這種壓力來源于家庭、學校、戀人還是社會,自殺者都有這樣的特征。這實際上表明青少年在解決問題時思維的單一化,社會關系的高度簡單是背后的支撐性原因。
研究發現,由于社交媒體的普及,青少年在遭遇危機時往往求助于社交媒體,這一方面延遲了他們自殺的實施時間,但另一方面由于自殺意念已經形成,他們偏向于尋找與自殺想法類似的信息,從而容易形成意念強化。同時,由于網絡信息紛繁復雜,網絡參與者水平和品行參差不齊,匿名的交往也讓潛在的自殺者強化了他們的自殺意念。因此,如何降低社交媒體對自殺意念的強化影響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