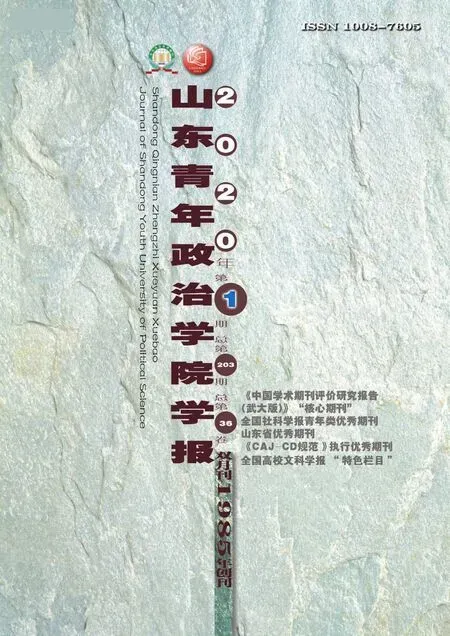“出埃及”主題與中國新世紀文學的超越性面向
于欣琪
(山東大學 文學院,濟南 250100)
《圣經》作為承載基督教宗教歷史和教義的文本,其中蘊含的敘事藝術以及背后反映的基督教神學的價值取向和終極關懷,深刻地作用到西方文學藝術之中。特別是《舊約》中《出埃及記》一卷,其中“關于從壓迫中逃離的記述,成為全世界各民族追求希望的一種偉大敘述”[1],同時也成為了文學作品中一個重要的敘事資源。20世紀前半葉,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的《去吧,摩西》、佐拉·尼爾·赫斯頓的《摩西,山之人》以及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的《野草在歌唱》都借用了《圣經》中“出埃及記”的典故,甚至將小說人物命名為“摩西”以點明文學文本與宗教圣典之間的相關性。這三部作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特征——通過“摩西”帶領以色列民族逃離埃及人奴役的宗教寓言來指涉殖民統治下的種族壓迫。頗有趣味的是,步入新世紀之后,在歷史背景、地域特征、民族文化與西方都不盡相同的當代中國,同樣有一些作家將目光投射到“出埃及”的《圣經》主題上——以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以及莫言的《等待摩西》三個文本為例,它們或是在塑造的小說人物上,或是在顯明的情節構成上,或是在文本無意識的言說上,又或是在更深層次的精神關懷上,都與《圣經》文本中“出埃及”的主題存在密切的對應關系。那么,“出埃及”主題如何從宗教層面作用到文學文本的敘事中?作家們如此關注這一基督教主題,背后的出發點又是什么?此外,這種創作實踐是否能夠為中國新世紀文學的發展提供新思路?對于這幾個問題的探討將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這一文學創作現象,并發掘其背后所蘊含的歷史憂思與價值關懷。
一、“出埃及”的宗教主題與文學文本
德國神學家K·J·庫舍爾在論述“宗教與文學的相互挑戰”之時,曾經拋出一個疑問:“文學和宗教能有什么共同點?是否有一種接近現實的方式上的認識論結構原則?這個原則也許——談話對此有所提示——存在于文學與宗教語言的構想特性中。”[2]文學與宗教的內在思想之所以能夠通過“文本”形式呈現出來,正是基于這種“構想”的可能性。中國新世紀文學與“出埃及記”的宗教主題之間的相關性,首先就體現在文本的言說和構建策略上:一方面,從顯性層面觀察,可以發現二者都采用了一種“離合”型的敘事結構;而另一方面,從隱性層面分析,這些文本將“出走”的文學母題與《圣經》中摩西“走出埃及”的典故相聯結,既能通過宗教隱喻切實地指向人們在經驗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同時也體現了文學所具有的超越性價值。
(一)“離合”型的敘事結構
諾思洛普·弗萊通過對《舊約·士師記》中“以色列反復背叛與回歸的神話情節”的分析,總結出《圣經》所具有的一種典型的敘事結構,他稱其為“U形敘事”——“背叛之后是落入災難與奴役,隨之是悔悟,然后通過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當于上一次開始下降時的高度。”[3]米耶斯將其定義為“離合的修辭手法(inclusio)”[4],認為它普遍地存在于《出埃及記》的敘事中。不難發現,與“出埃及”的宗教主題相互指涉的文學文本總是存在著類似的敘事結構,鮮明體現出這種“在變化中重復”的特征[5]。
在小說《等待摩西》中,“離合”型的敘事結構通過“柳摩西”命名的變化表現出來。小說人物的名字從“柳摩西”到“柳衛東”最后又改回了“柳摩西”,這個過程同時貫穿在他從“在鄉”到“離鄉”再到“還鄉”的生命歷程之中,折射出以柳摩西為代表的一代人,面對時代的巨大轉折,產生的惶惶無依的精神漂泊。與《等待摩西》刊載在同一期期刊上的,還有莫言新作的幾首小詩,詩中寫道——
路高到極點
漸漸折彎
像烤軟的蠟燭
最終成了一個橢圓
法拉利在橢圓內奔馳
像一個著名的幾何命題
除非行星改變軌道
否則我這輩子也到不了巴黎
那遙遠的無法計數的空間
其實只隔著一層膜
穿透就是到達
到達就是出發[6]
幾何圖形“橢圓”的意象既指向哲學意義上循環往復的永恒狀態,同時也指向一種難以逃離的現實的荒誕,正如《等待摩西》中刻畫的那種不確定的無處歸依的生存困境,不僅存在于柳摩西身上,同樣存在于馬秀美的身上、“我”的身上,乃至我們每一個現代人的身上。
而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則更加鮮明地體現出“離合”型的敘事結構,這部長篇小說分為“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上下兩部分,刻畫了楊百順與牛愛國祖孫兩代人面對生活的圍困和精神的困境,試圖不斷尋找、不斷突破的曲折歷程。從整體架構上來看,“出延津”與“回延津”剛好構成了“離合”的敘事形式。“當年曹青娥還叫巧玲的時候,她娘吳香香跟銀匠老高跑了;吳摩西和巧玲去找吳香香和老高,就是假找。沒想到七十年過去,自己也成了吳摩西。兩個出門假找的人,一個是曹青娥的爹,一個是她的兒子。”[7]當年的吳摩西(即楊百順)走出延津“尋找”與人私奔的吳香香與后來的牛愛國“尋找”龐麗娜卻又陰差陽錯地走向延津,共同構成了一個跨越百年的循環,這是一層“離合”型的敘事構造。而在這層結構之下,又隱含著另一層“離合”型的敘事構造——這兩次本應是充滿“怒”與“恨”的“尋找”,為什么皆轉變為無可奈何的“假找”?首先,在作者劉震云的敘事邏輯中,吳香香與龐麗娜的出軌乃至私奔絕不是一種命運般的偶然。表面上看,吳摩西與吳香香,牛愛國與龐麗娜,他們夫妻間婚姻的破裂都是因為產生了“說不上話”的隔膜,但當牛愛國遇到“說得上話”的章楚紅,并糾結是否要與其私奔時,他與朋友崔立凡的對話再次提醒了讀者——“你跟她說得著,是因為她現在由丈夫養著,你就是與她說個話;等你養她,就成了過日子,到時候就該說過日子了。”[8]當情人間的“對話”步入婚姻,面對現實生活的圍困,它的動搖與瓦解似乎成為一種必然的狀態。因此,百年之前的楊百順與百年之后的牛愛國所面臨的是同樣的困境,二者的遭際不是特例,而是一種普遍性的隱喻。其次,“假找”行為的反復發生則是基于人性中的“共感”與人情社會的倫理壓迫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從小說文本中可以看出,迫使婚姻破裂的“說不著”的狀態顯然不是單向存在的,只不過吳香香和龐麗娜以出軌的形式主動破除了膠著的相處狀態。“吳香香走后……吳摩西渾身自在許多”[9],說明吳摩西也早已厭倦了這種家庭生活,所以一開始面對吳香香和老高的逃跑,他基本上是不作為的。而當吳摩西見證了吳香香與老高的幸福生活,牛愛國也通過和章楚紅的相處了解到“說得上話”的魅力時,他們都對妻子的私奔恍然大悟,“共感”的體驗使他們從人性的角度對這種違背社會倫理的行為產生理解和同情,但是卻“不得不為了給鄰里鄉親一個交代而出門假意尋找”[10]。仇恨在爆發之前已經自行消解,那么,破除仇恨的“尋找”行為也就喪失了意義,但人物又迫于人情社會所施加的倫理層面的壓力,無法終止和拒絕“尋找”。于是,“尋找”不得已而成為了“假找”。
米耶斯曾指出作為敘述策略的“‘離合’的修辭手法(inclusio)”與“跨越所有的階級的全體[適用]性(inclusiveness)”之間的關系——“一個涵蓋整個群體在內的節期,具有凝聚群體成員的作用,并賦予人們一個共同的身份,將每一個人同共同慶祝的過去相連接。從跨文化的一般意義而言,這似乎就是以儀式強調與維護‘同感’(communitas)這一觀念的事例。”[11]生存的經驗和生活的邏輯總是相似的,無論是劉震云反復演繹著貌似不合常理的“假找”情節,還是莫言小說中人物在“出走—返鄉”中徘徊的精神困境,其背后都隱藏著必然性的因素,看似生命怪圈一般的輪回,實際上則是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一種寓言。
(二)“出走”的文學母題
《出埃及記》中神呼召摩西,說:“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3:8)摩西秉承神的旨意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這一宗教主題的核心環節,因此,與其相互指涉的文學文本總是不可避免地觸及“出走”的話題。
首先,值得說明的是,有關“出走”的書寫并不為宗教文本所獨有。早在十九世紀,易卜生就在戲劇《玩偶之家》中刻畫了“娜拉出走”的經典情節,其中關于女性獲取獨立的反抗精神,影響了中國“五四”時期的一批啟蒙者,在他們的作品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本雅明也曾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以波德萊爾筆下的“波西米亞流浪漢”為切入點,描繪了“游蕩”主題所具有的現代性表征。隨后,在二十世紀,薩義德更是站在全球化的語境下論述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流亡”狀態——“在當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許多東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鄉其實并非那么遙遠,當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對故鄉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12]這種由“此處”通往“彼處”的“出走”狀態被作家敏銳地感知,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豐富內涵和強大再生性的文學母題,而當它與“出埃及”的宗教主題相互契合,則又為文學作品賦予了一層超越性的價值意義。
從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談起,小說先后以七個人物的第一人稱視角,在交叉重復的十四次敘述中,完成了對沈陽這個城市從文革前后到新世紀頭十年近四十年歷史的重構。故事被套上了懸疑小說的外殼,其中作出“出走”行為的人看似是相繼犯下襲警殺人之罪的李守廉及其女兒李斐,但實際上,正如《出埃及記》中的故事一樣,“出走”并不是某個人的個體行為,小說隱喻著在時代作用力下,一段“被放逐群體”[13]的歷史記憶——小說從1995年這個時間節點展開敘述,這一年里,社會命案的發生、李守廉下崗、莊德增轉業、莊家李家面臨拆遷被迫搬家、蔣不凡等警察迫于社會動亂的壓力和獎金的誘惑展開釣魚執法……都是基于九十年代東北經濟破產和“下崗”熱潮來臨的時代背景。“出走”是每個人不得已的歷史選擇,他們的“出走”是被沉重的時代所放逐,是社會轉型期頹敗現實的產物。與此同時,其背后也負載著人的有限性的一面——
《創世紀》中,神在伊甸園吩咐亞當:“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17)而神對伊甸園中其他生靈則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創3:3)古羅馬哲學家斐洛曾經就這個片段的意喻加以解釋:“當神吩咐可以吃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時,他是對一個人說的;但當它發出禁令不能吃那能知善惡的樹上的果子時,他是對不止一個人說的……神恰當地吩咐一個人在美德中尋找營養,而責令眾人遠離惡行,因為作惡的是眾人。”[14]正如小說中的每個人都是造成時代悲劇的共犯,審判殺人者的人本身也有罪,這正是基督教“原罪”意識的體現。人之所以同神之間有一道永遠無法逾越的鴻溝,就是因為人性的脆弱性以及人的有限性。劉再復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一書中曾對《水滸傳》里“武松殺人復仇”的情節進行了重新思考,“當他用暴力批判社會的時候,自身也在參與制造社會的黑暗并成為黑暗的一部分,他實際是創造整個社會災難的共謀”[15]。《平原上的摩西》其實為讀者展示的是一個又一個新時代的“武松”,無論他們真實地犯罪,還是包庇罪行,都合謀制造了這個黑暗的時代。小說中人物行為上的出走與精神上的放逐是歷史的困境使然,但這困境背后也有著普遍人性的缺陷,“受蒙蔽無罪”的口號不管在哪個年代都是不成立的,人必須正視自己的有限性,才能承擔起自己在“歷史事件中的道德責任”[16]。
雙雪濤小說所具有的超越性在于作者將宗教層面的啟示般的言說與現實的苦難和困境結合在一起,真實地道出了對社會歷史與人性的深刻反思,小說直面黑暗但并不耽溺于對陰暗面的書寫,反而借助宗教的啟示力量,為人指引窮途末路后依舊有路的可能。而在《一句頂一萬句》中,這種超越性表現在伴隨著人物不斷“出走”的過程,作者通過他們所表達的對于“我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終極問題的思考。這三個問題最開始由傳教士老詹拋出,是他勸人信奉上帝的話語策略——“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17]問題的再次出現則是在“出延津記”的結尾處,通過吳摩西在火車上與中年男人的對話又一次拋出。吳摩西的生活史就是一部關于“出走”的流浪史,作者將“出延津記”終止于他最后一次“出走”的過程中。當中年男人詢問吳摩西“從哪兒來”的問題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延津”。但是隨后他又產生了動搖,“回頭一想,又不如實。自己這半年并不在延津。”[18]“從哪兒來”的困惑是在“出走”之后產生的,已經“離鄉”之“鄉”還是來處嗎?這是對生存的本源問題的拷問,同時,也是對自我身份質疑的表現,體現出“我”之為“我”在根基上的不確定性。“到哪兒去”的問題則伴隨著吳摩西“出走”的始終,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就是“出走”的意義之所在。《圣經》中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為了抵達“流奶與蜜”的迦南圣地,而無神指引的吳摩西卻一直不知去向何處,因此,他的“出走”是反反復復、難以終結的。中年男人的最后一個疑問“你是誰”徹底點明了吳摩西的生存困境,從楊百順到楊摩西再到吳摩西,姓名的反復更改貫穿了他整個“出走”過程。海德格爾提出“詞語也即名稱缺失處,無物存在”[19],因此,命名的艱難反映出吳摩西在自我確認時的困惑。直到最后,吳摩西將名字改為兒時的精神偶像“羅長禮”之名,而不再迫于生存不斷被他人命名,他才完成了對自我的指認。
在《等待摩西》之中,“出走”的超越性是模糊的,因為柳摩西“出走”的行為本身就是突兀而無解的。表面上看,《等待摩西》沿用了“出走”的文學母題,并通過小說人物對基督教的信仰將話題引到“出埃及”的宗教隱喻上,但是小說同樣為讀者展現了“出走”的背面——由“出走”而衍生出的“等待”。對于信仰,比柳摩西更為虔誠的是他的妻子馬秀美,自從柳摩西失蹤之后,馬秀美“每次做禮拜,她都熱淚橫流,失聲痛哭。她跪在耶穌基督畫像前,往胸口畫著十字,嘴唇翕動著,嘴里念叨著:主啊,保佑他吧,保佑這個迷途的羔羊吧……”[20]而她三十年間日復一日地張貼尋人啟事更是如同履行宗教儀式一般從不輕慢。在這里,“等待”的神圣置換了“出走”的神圣。德語作家L·林澤爾在探討宗教與文學的關系時,曾經提出:“S·貝克特在他的劇本《等待戈多》中已經開始。在這里可以找到宗教文學的原型,即等待什么。”[21]“等待什么”與《一句頂一萬句》中“到哪兒去”的問題一樣都是對生存意義的質問,都是由“出走”而引發的對現實境遇的思考。正如《等待摩西》初次發表于《十月》上所配的插圖:一個人,向著光明的洞口張望,身后的空白處既像他/她來時開辟的道路,又像靜止時因光線照射所投下的陰影,那么,他/她究竟是要赤腳穿越雜草叢生的荒原,還是要駐足等待誰的歸來?答案我們無從得知,但唯一確指的是這個人的目光所向——一片敞開的光明。
二、“出埃及”背后——歷史謎題與精神困境
雙雪濤在《平原上的摩西》之中借李斐的回憶道出了一句極具《圣經》啟示意義的話語:“誰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遠同在。”[22]這一句話剛好同《出埃及記》中神與摩西的對話形成互文的關系——神對摩西說:“我必與你同在。”然后又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出3:12-14)“我”作為主語只有一個確指,那就是上帝本身,而雙雪濤所說的“誰”卻可以指向所有“人”。從“上帝之口”到“人類之口”,那形而上的啟示轉而作用到“人”的現實生存之中,是對“人”的向導和指引。然而,“人”愈是需要這種向導和指引,愈是說明其已經深陷困境難以自拔,等待著“走出埃及”,等待著“救贖”與“被救贖”。文學作品與宗教精神的相通性在于對“人”的關懷,因此它通過自己的表達來顯露這種困境,并且與宗教話語相結合,共同探尋超越困境的可能。
(一)歷史表述的破碎狀態
這困境在文學作品里呈現為一種歷史表述的破碎狀態。在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中,當隱匿為出租車司機的李守廉載著莊德增來到即將被拆毀的主席像旁時,他曾向莊德增拋出一個問題:“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23]不由得讓人想起郭小川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寫下的長篇敘事詩《一個和八個》,詩中在介紹八個犯人時寫道:“八個都是殺人兇犯,/在這里要把惡行的后果承擔。/有三個是出名的慣匪,……/四個是我軍的逃亡士兵,……/另一個是敵人派遣的奸細……”[24]而李守廉也曾這樣介紹過那“底下”的“三十六個”:“二十八個男的,八個女的,戴袖箍的五個,戴軍帽的九個,戴鋼盔的七個,拎沖鋒槍的三個,背大刀的兩個。”[25]不同的是,這“三十六個”是英勇保衛毛主席的戰士,而那“八個”則是曾經犯下重罪的犯人,然而他們都同樣沒有姓名。倪震將《一個和八個》的主題概括為“冤屈和忠誠”[26],無論在塑造“八個”時,其人物形象多么鮮活,但這主題最為明確的指向卻始終是那“一個”。雙雪濤通過李守廉的質問想揭露的是與之相似的歷史敘事邏輯:“一個”永遠被置于“八個”之前,“八個”被隱沒在“一個”后,就像“個體”淹沒在“群眾”的集合詞里,成為歷史的“底座”。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一語點明了一個歷史謎題——我們如何在歷史統一的敘述語境里呈現自身?《平原上的摩西》從1995年的時間節點出發,卻通過七個人物各自的敘述來完成對歷史的架構與重組。正如學者黃平所言:“小說故事開始啟動的歷史時刻,任何一個人物都無法把握時代的總體性。”[27]一方面,分散的歷史表達代表著難以整合的歷史本身;而另一方面,也在為歷史個體闡明自身作出努力。不過,作為真正的歷史的“受難者”,李守廉始終沒能獲得以自己的視角進行敘述的機會,也許恰恰說明在那個年代承擔歷史苦難的“底座”們喑啞和失聲的真實狀態。
而《等待摩西》與《一句頂一萬句》對歷史宏闊表述的拆解則更為徹底,二者通過將敘事導引至瑣碎的日常生活而強化歷史對個體的關注。小說《等待摩西》中,主人公柳摩西的人生曾經出現過三次巔峰:文革時期,他大義滅親扇了自己爺爺的耳光,被咬斷手指而獲稱“英雄”;改革開放之后,他抓住商機賺取財富,成為人們口中的“柳總”;失蹤三十年,他再度歸來,改回“柳摩西”之名,成為散播教義的“摩西”。其中,第二次短暫的巔峰后繼之而來的就是他的失蹤,時間剛好是八十年代,預示著某種宏大的時代的共同指向即將消弭。那么,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當時代失去了一個共同的精神指向時,與時代緊緊捆綁的柳摩西,他的失蹤成為一種必然,而緊接柳摩西承擔歷史敘事職能的變成了他的兄弟、妻子、女兒以及女兒的家庭等眾多所指,時代不再被表現為一個唯一的巨大的歷史事件,其變化發展通過日常生活的瑣碎敘事表現出來。《一句頂一萬句》也是典型的回歸日常經驗的書寫,但是,它并未體現時間線索和歷史元素。陳曉明提出,《一句頂一萬句》中的“去歷史化”的傾向“或許是回到歷史本身,回到鄉土本身的一種嘗試?在去除經典性的敘事之后,這是一種歷史的剩余,也許是鄉土中國的本真性存在。那是人的歷史,而不是歷史中的人”[28]。歷史的困境與個人的困境息息相關,這三部作品用分散破碎的表達來呈現歷史的曲折以及這曲折處關于個人的悲歡,文學所要承擔的任務就是打破那遮蓋了“底座”的宏偉雕像 ,使下面的“三十六個”一一顯露出來。
(二)現代人的精神孤獨
當文學轉向個人生存經驗時,又將現代人的精神困境顯露出來——一種難以遏制的孤獨之感。《一句頂一萬句》中為我們描繪的是現代社會無法對話的孤獨,達成“對話”在其中無比重要,它是人物情感開始和結束的決定性因素。吳摩西與吳香香夫妻二人“不親”,是因為在瑣碎日子中兩人“說不到一塊去”;而吳香香跟老高私奔,將親生女兒巧玲留給她的后爹吳摩西,是因為“她跟你說得著,跟我說不著”[29];“回延津記”中,牛愛國與龐麗娜婚姻的破裂,與章楚紅感情的開始,龐麗娜與小蔣的偷情和私奔,皆是源于“說話”這件事。作者劉震云曾經提及:“將《論語》和《圣經》對照。第一句話,《圣經》是‘上帝說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說的是人、神、天地、萬物的關系,但《論語》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30]“找到知心朋友”在劉震云這里具有著《創世紀》一般的意義,而“知心”的背后則是“對話”所具有的可能性。“對話”的斷裂導致小說人物精神的“相隔”,從而推動他們不斷“出走”并不斷找尋對話的對象。上帝無處不在,但知心朋友卻不好尋覓,并且,上一秒是朋友,下一秒可能就是敵人,因此,“朋友是危險的,知心話是兇險的”[31]。“說話”既關乎俗世生活的規則;又包含存在本質與存在之思。“上帝說”、“孔子曰”,表達成為玄之又玄的東西,但表達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喪失表達,無異于被生活流放。
尋找一個知心朋友,說一句知心話,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成為人物擺脫孤獨、支撐生活的精神動力。在這里,人生存下去的真實意義被遮蓋,“虛”成了“實”的唯一指向。而《等待摩西》同樣以“等待”的荒誕指向人對“生存意義”的孤獨探索。表面上看,做出“等待”行為的人是馬秀美,她像苦守埃及的以色列人終于盼來摩西帶領他們走出埃及一樣,苦等30年等到柳摩西的歸來,這種“等待”被作家賦予了玄妙的宗教意味。但是,作者在小說的結尾處提示大家“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于是,我轉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門”[32],那么,另一位“等待摩西”的人還有“我”,柳摩西的失蹤構成“我”整整三十年的好奇與想象,甚至力圖把它寫成小說。可直到最后一刻“我”才猛然發現,“我”覺得不正常的事都在按部就班地前進著,看似是迷信的偏執的等待與信仰,卻成為真正支撐人好好活下去的動力。“我”對生活的想象產生偏差了嗎?“我”開始產生動搖,這是“我”的孤獨。
《平原上的摩西》并沒有明確地提到這種精神困境,但是,有一個細節可以證明——當小說描寫到孫天博幫李斐所借的十本書時,作者將書目完完整整地呈獻給讀者,分別是:《摩西五經》《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夜航西飛》《說吧,記憶》《傷心咖啡館之歌》《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哲學問題》《我彌留之際》《長眠不醒》《糾正》[33]。十本書從題目上看就帶有對生命終極問題的思考,而在內容上也與雙雪濤筆下人物的精神困境相互指涉。比如《傷心咖啡館之歌》講述了在美國南方小鎮上,三個現代人從身體到心靈的畸形異化以及他們為了擺脫孤獨的困境所做出的荒誕選擇。小說揭示出人類在現代社會中深陷精神虛無的迷茫狀態,主人公們在掙扎中不斷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也體現出人類擺脫這種狀態的徒勞。《平原上的摩西》中負載著沉痛歷史記憶的人們面臨一種相似的境遇,通過李斐所借閱的書籍,可以窺探此刻她進退兩難的困窘處境和無望的精神孤獨。雙雪濤模仿《圣經》的口吻告訴我們“誰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遠同在”,這句話是對人們面臨時代共同體瓦解時如何自持的寬慰,同時也表達了當“群體”放逐至“個體”時,“同在”之難所造成的精神層面的孤獨感。作者所描繪的東北平原是在那個年代人人都想逃離的埃及地,而在結尾莊樹的口中卻成為穿越紅海所尋找的迦南圣地,因為它承擔著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與歷史想象。小說到最后所要表達的是:我們可以都是罪犯,我們也可以都是摩西,只要我們“同在”,就能穿越紅海抵達迦南,就能把此時此地變成我們共同存在的平原。這是向著時代對“共同體”的瓦解所進行的一次吶喊,“我們”不僅被集體驅逐,更要共同獲得拯救,而拯救我們的人只能是我們自己。
三、在日常中超越日常——中國新世紀文學的新面向
中國新世紀文學創作與“出埃及”宗教主題的相互對應,一方面源于文學作品與宗教精神對于表現人類普遍經驗和終極關懷上的內在契合,另一方面則是作家們的一種有益的嘗試,在不斷嘗試中探索中國新世紀文學“去往何處”的方向性問題。陳曉明先生借用薩義德“晚期風格”的概念,提出新世紀漢語文學已經步入了“晚郁時期”(the belated mellow period),即一個“更具有漢語特性的藝術品格”和“當代漢語文學的氣質格調”[34]的階段。他在論述中引用了肖開愚對于“中年寫作”的看法,藉此表現新世紀文學在“晚郁時期”所具有的成熟風格——“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狀態,文學作品不可能獲得真正的重要性。中年的提法既說明經驗的價值,又說明突破經驗的緊迫性,中年的責任感體現在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上,而非呼聲上。”[35]“及物的狀態”①與“突破經驗的緊迫”在新世紀文學中得到了有效地實踐,這三部有關“出埃及”主題的文學作品就是其中的范例,它們體現了中國新世紀文學創作的一個新的面向——在日常中超越日常。
(一)“向前”的日常生活哲學
中國當代文學對于表現“生活”的重視,最開始深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講話》中強調:“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6]并且,文藝作品對于生活的表現應該具有這樣的特點——“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37]文學被強力地拉回到“及物”的層面上,但是,其中蘊藏著兩個邏輯:一是“生活”是“人民群眾的生活”,二是“文學的生活”要高于“普通的生活”。在這兩個邏輯的統領之下,文學對于“生活”的表現籠統地覆蓋在“階級”與“群眾”上,真正的生活是勞動,是斗爭,是革命,生活的目的是實現共同的崇高理想,而對于個人日常生活的表現則被統一而宏大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所淹沒。此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被囿于“‘階級斗爭’的戰場”[38],而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也始終難以逃離一個宏闊的歷史聲音。直到“新寫實”的興起,文學那種直面個人的瑣碎日常生活的刻畫才達到一個高潮。但是,無論是《煩惱人生》結尾處印家厚以“做夢”的自我暗示來逃避現實,還是《一地雞毛》中小林擱置對老師去世的愧疚與傷感,轉而將生活的重心放在“大白菜”上,“新寫實”展露平庸日常的同時,處處流露著對于無可抵抗的現實的無奈,甚至是逃避。
新世紀文學同樣將目光投射到個人生存和日常生活經驗,但是它以一種“向前”的生活姿態來突破日常,不再是表現生活、暴露生活的展覽,而是對面向終極如何處理現在的思考。在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曹青娥對牛愛國說:“我活了七十歲,明白一個道理,世上別的東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沒法挑。……我還看穿一件事,過日子是過以后,不是過從前。”[39]這句話既是一位七旬老人樸實的人生經驗,同時也在形而上層面提示人們:在面對日常生活的圍困時要以面向未來的維度自持,而不能陷入“往昔之井”的循環里不能自拔。同樣,雙雪濤在小說里引用了《出埃及記》中神的指示:“耶和華指示摩西:哀號有何用?告訴子民,只管前進!然后舉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濤就會分開,為子民空出一條干路。”[40]這“心中的念”成為支撐傅東心和李斐繼續生活的精神信條,憑借信仰沖破現實的圍困,深刻地體現出一種“向前”的日常生活哲學。生活有生活的日常、生活的幸福和生活的苦難,“日常”是一個中性詞,但當“日常”成為重復、瑣屑和虛無時,與苦難無異。中國新世紀文學對“向前”的日常生活哲學的刻畫,表現出現代人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跳出重復的日常,擺脫虛無的困境,這對于文學書寫乃至現實人生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指導意義。
(二)“向下超越”與“向上超越”
王德威在評價《平原上的摩西》時使用了汪暉所提出的“向下超越”②的概念——“‘神性’的期待不必取決于宗教啟悟的有無,或革命幽靈是否復返,但與看待人間境況的意志與方法息息相關。”[41]在蒼涼衰敗的歷史語境與紛擾混亂、暴力橫生的時代背景下,人如何在貧瘠而無常的現實中有所依托,這是雙雪濤所考慮的問題。“向下”表現為一種從既有的歷史想象與被規定的宏闊敘述中回轉到個體生存與現實境況緊密關系之間的維度,而“超越”就是一種近乎“神性”的“意志”,是如何在其中自持、如何不被生活的邏輯所纏繞的“方法”,這也就是新世紀文學面向日常并企圖突破日常的一次勇敢嘗試。
都市作為短暫、瞬間和偶然的現代世俗空間,不能滿足人類的本質需求,它有讓人墮入平庸、相對和虛無的危險,人們一旦認識到了這種危險,便承認自己是需要某種超驗性因素的,是需要從瑣碎和虛無中救拔出來的,以便過上有意義的生活。[42]
不止是“都市”,劉震云告訴我們當“鄉土世界”逐漸進入現代世俗空間的行列,同樣要面對這種陷入“瑣碎”和“虛無”的危險。“喊喪”、“噴空”和“社火”都是對日常生活的暫時擱置,通過孤絕的吶喊、話語的頻繁輸出和“他者”角色的扮演③,來跳出“原來的日子”。2006年,張頤武提出了“新世紀文學如何面對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問題[43]。其實,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就已經表現出“關于日常生活的焦慮”,但是這種焦慮是一種“時代的巨大的集體性焦慮”,并且“必將以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從“60年代下半期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就可窺見一斑[44]。及至新世紀,當時代的集體的焦慮瓦解到每一個孤獨的個體中去的時候,我們難以通過“集體”的相互依托來尋找一個發泄的途徑時,精神的信仰和對生活意義的追尋顯得無比重要。“信仰”可以是宗教,但不等同于宗教,在劉震云那里,“信仰”就是一句話、一個說得上話的知心朋友;在莫言筆下,“信仰”就是馬秀美背后的上帝,是她苦等三十年的柳摩西;在雙雪濤的作品中,“信仰”就是一個共同體的存在,是傅東心的“同在”,是李斐和莊樹的“平原”。“信仰”就是支撐人們在日復一日的平淡日常中生活下去的動力,就是為生活賦予一個意義,推動它不斷地向前。
中國新世紀文學作為漢語文學最年輕的一個階段,實際上越來越具有“晚郁時期”的成熟氣質,它不再追求一致的應和與激昂的反叛,而是扎根于現實的土壤,沉思著生存的問題,并不斷尋求著突破。“出埃及”宗教主題的引入就是一次成功的實踐,對于這些作家來說,宗教不是他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現實才是,但宗教與文學背后的相通,使他們在表達人類普遍經驗和探索深層的終極問題時,能夠產生共鳴。與此同時,就像王德威所言,文學的創作不僅要有“向下超越”的關懷,更要保有“向上超越”的可能,使得我們在文學作品亦或是真實的人生中,能夠直面日常、突破日常,并在日常中實踐“敬畏、慈悲、懺悔、謙卑,以及愛”[45]。
注釋:
①張未民先生認為:“新世紀文學的現代性”表現為一種“生活現代性”。“五四文學的人學主題詞是‘人生’,人生概念、人生問題意味著更多的精神性追問,而生活現代性觀念則是要將這精神性的一面放到實際的世俗的生命、生存、生活中來,讓文學在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建構中重返生活的整體性,補齊其‘體物’的短板。”而這種“重返生活整體性”的“體物”狀態正是新世紀文學在“晚郁時期”走向成熟的表現。詳見張未民《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思潮與文脈— —試論“中國現代文學 3”》,《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4期。
②汪暉評價《阿Q正傳》時提出“向下超越”的概念,用以跳出啟蒙與革命的循環論述。“‘向下超越’——即向著他們的直覺和本能所展示的現實關系超越、向著非歷史的領域超越。”詳見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3期。
③劉震云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描寫了延津縣城“舞社火”的習俗:“平時大家從事五行八作,現在每個人都改做另外一個人;或是百年前千年前的一個人,如共工、勾龍、蚩尤、祝融、文王、紂王、妲己等;或是生活中沒影的人,如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嫦娥、閻王、小鬼等;或是戲里的生、旦、凈、末、丑,只裝扮個大概,不具體要求他是誰。”詳見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