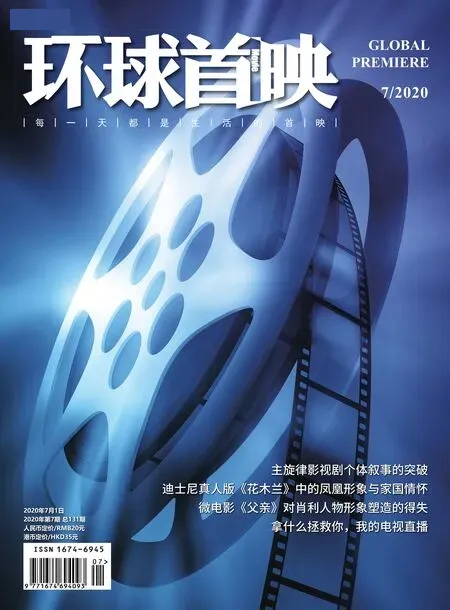盜竊他人占有的本人財物之刑事定性分析
童心怡 華東政法大學
一、所有和占有相分離產生的矛盾
盜竊罪的歷史極其悠久,作為一種自然犯,早在古代社會就已經出現并在審判實踐中加以運用。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權利種類的劃分也更加細致與合理,出現了所有權和占有權分離的現象。此處的占有是指合法占有,包括國家公權力機關對公民財產的合法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也包括基于雙方合意而發生的借用、保管等民事法律關系。確實,在社會結構的完整度和信息化程度遠遠沒有當今水平的時候,很難想象一個人居然要用秘密竊取的方式取走本來就屬于自己所有的東西。但實踐中出現這種現象,卻讓理論界和實務界不得不好好思考其間的個中關系和問題。當財物的所有權人和實際占有人發生分離的時候,哪種權利是應當被優先保護的?
在百家爭鳴的刑法學術觀點中,各不同學派和學者之間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分歧,在盜竊本人財物中最主要的爭議焦點就在于這種行為構不構成盜竊罪、盜竊之后的索賠行為會不會涉及詐騙罪以及犯罪數額究竟該如何認定。
二、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和保護法益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公私財物的行為。理論界和實務界通說觀點認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是他人擁有所有權的公私財物、保護法益是他人公私財物的所有權。而縱觀所有權的內涵和權能,結合民事法律規定以及法學相關理論,所有權其實是一個廣泛意義上的概念,其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這就讓學界走向了通往不同方向的岔路口。有學者認為,盜竊罪保護的所有權是狹義上的所有權,也即該財物歸屬于某人所有,對于自己的財物本就沒有秘密竊取一說,因此不可能構成盜竊罪;有學者認為,盜竊罪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希望獲得對財物的一項或多項所有權能,而本人財物既然是歸屬自己所有,自然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還有的學者則堅持如果有其他合法事由與該財物的所有權相對抗,則考慮該財產所有人構成盜竊罪的可能性。
(一)所有說的局限性
所有說是我國最傳統的刑法理論學生說,也就是將盜竊罪的保護法益理解為對財物的所有權。財產罪的本質是侵犯財產所有權,刑法規定處罰財產罪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護財產所有權。①秘密取回本人所有的他人合法占有財物并未侵犯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且占有的權能與所有相比畢竟無法相抗衡,也就不能用占有去對抗所有人,因此行為人不能構成盜竊罪。而堅持所有說的立場,雖然在標準上比較統一,但會出現許多無法調和的矛盾,在司法實踐中也無法有效保護受害者,會造成財產罪的處罰范圍過小,甚至可能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比如贓款贓物不存在一個合法的所有權前提,對其實施盜竊也不會侵犯持有者的所有權。如果對此不加以規制,顯然是與刑法的保護目的相去甚遠了。
(二)占有說的缺陷
占有說主要是來自日本的刑法理論,該說認為,財產罪的法益是他人對財物事實上的占有。為保護財產所有權,首先必須保護對財產的占有本身。②以合法的占有作為盜竊罪之規制法益雖然能夠解決很多所有說無法解決的難題,但其中的不合理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對占有的保護雖然有必要,但并不具有一般意義,更為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對某些例外情況的規制。盡管所有和占有會出現分離,但這畢竟只是少部分情形,如果用特殊制約一般,顯然有違法理。占有僅僅是一個在理論上構建出來的隱性構成要件要素,將其缺乏根據地提升為法益,并以此判斷盜竊罪成立與否的做法,混淆了構成要件要素與法益,用實質性的法益思考替代了構成要件檢驗。③
(三)折衷說的合理性
折衷說是在吸收了所有說和占有說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其兼具兩者的優勢,同時又避免了更多的理論悖論,因而被大多學者所接受。折衷說承認盜竊罪的保護法益為所有權以及他物權和債權等合法占有財物的權利。就張明楷教授的觀點來說,財產犯的法益首先是財產所有權及其本權,其次是需要通過法定程序改變現狀(恢復應有狀態)的占有;但在非法占有的情況下,相對于本權者恢復權利的行為而言,該占有不是財產犯的法益。④筆者也持折衷說的立場,認為占有應當納入法益保護犯罪進行綜合性考慮,除了合法占有外,非法占有因為涉及社會公共秩序問題,在一定的情形下也應當對其進行刑法保護。
而在折衷說內部,學界又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分歧,其中筆者認為爭議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在同時存在所有和占有的情況下,占有能不能對抗所有”,也就是所有和占有何者為優先。對此得出不同的答案,就會產生完全不一致的刑事定性分析。筆者贊同折衷說內部的一種觀點,即刑法主要保護所有權,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優先保護占有權,至于在何種情況下,則要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分析。
三、秘密取回他人合法占有的本人財物之定性
(一)行為人的主觀要素
盜竊罪作為侵犯財產型的犯罪,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的主觀思想是考據較為困難的無形體,因此必須要借助于客觀事實來具體認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理論界,對非法占有目的之理解主要有三種學說:第一是權利排除說,即行為人的行為只要是排除他人對該財物享有的權能即可,自己后續如何處置并不影響目的實現;第二是權利占有說,即行為人的行為只需要讓自己獲得該財物的一項或多項權能;第三是排除加占有說,認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排除權利者對財物的占有,把他人之物作為自己的所有物,按其經濟的用法利用或處分的意思。⑤
在此,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如果只需要排除他人權利,那么盜竊罪將無法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相區分開來。后者的“毀壞”不僅僅是指物理上的破壞,也包括讓財物喪失使用效能,比如丟棄到一個不可能找的回來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排除了他人權利但是自己并沒有獲得相應權利,定盜竊罪顯然不妥。當然,若是只要求自己獲得權能而并不排除他人權利,就容易過分擴大入罪范圍,比如行為人只是希望短暫使用或者占有一會兒,并沒有排除他人本權的意思,動用刑事法律就顯然過頭了。因此,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不僅表現為行為人對他人財物在物理意義上的實際控制,通常也表現為行為人遵從財物的本來用途進行利用和處分,以實現財物的價值或取得相應的利益。⑥
(二)他人非法占有(無權占有)的情形
行為人的財物雖在他人的占有之下,但這種占有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占有人對該財物的占有沒有合法事由,即無權占有,對此應當具體區分不同情況進行分析討論。
如果財物是行為人合法所有的,但處于占有人非法控制之下,比如占有人使用了盜竊、搶奪等手段,或者是在借用、保管時限到期后拒不返還的,在此種情形下行為人在占有人不知情的時候秘密取回自己的財物屬于一種自救行為,是以合法所有對抗非法占有,因此也就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如果行為人通過非法行為將財物交付給他人,因該行為的不法性,行為人也就失去了對該財物的所有權利,相對的接收人也因沒有合法事由而無權占有該財物。雖然在這種情況下既不存在合法的所有權,也不存在合法的占有權,但作為財產秩序的一部分,刑法應當折衷的保護該非法占有。因此行為人如果在非法交易后將錢款或是違禁品等財物秘密取回的,應當構成盜竊罪。由于司法解釋的規定,賭博后單純盜回所贏或所輸賭資的行為因危害不大不宜認定為盜竊罪。
(三)秘密取回本人財物后未向占有人索賠的情形
如果財物的所有權人在合法占有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財物取回,并且沒有后續的索賠行為,是否能夠認定為是盜竊罪?筆者認為應當區分情況處理。
在占有人占有該財物沒有付出相應對價的情形下,雖然秘密竊取行為發生時財物是處于非所有權人控制之下,其中存在一個合法的占有權能,但至少從刑法意義上來說,這種合法占有并不能對抗所有。行為人將本人財物取回后,看似好像侵害了他人的占有,但因為沒有后續的索賠行為,只是單純將自己所有的東西拿回來,此間并不存在一個新的所有權法益侵害問題。該財物本就是屬于行為人所有,占有人在刑事法律關系上也沒有產生任何損失,因此不能夠定性為構成盜竊罪。如果是基于民事法律關系而被他人合法占有,按照民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理;如果是國家公權力機關查封、扣押、凍結等情形下的財物被秘密取回,也只能被給予行政處罰,至多因情節嚴重可能會觸犯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但在這種情況下侵害的法益已經完全在財產犯罪的規制范疇之外了。
當占有人占有財物付出了相應對價的情形下,所有人將該財物取回實際上是有侵害他人所有的意圖。盡管對該財物只是占有,但占有人基于此占有能夠享受相應的收益,并且為此付出了一定的對價。在付出了對價后,占有人無法繼續行使其應得的權利,實質上就是其財產所有權受到了侵害。對此應按照數額進行認定,如果數額較大達到了刑法規制的范疇,就認定為是盜竊罪,否則就按照一般的合同糾紛處理即可。
(四)秘密取回本人財物后向占有人索賠的情形
當行為人將本人財物秘密取回后,如果并未要求占有人賠償,占有人提出賠償建議后也未被行為人接受的,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會成立犯罪。如果向完全不知情的合法占有人要求賠償,或者接受占有人的賠償的,此時應當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不是單純的為了拿回自己所有的財物,而是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此時,只要數額達到了入罪標準,就應當認定為構成犯罪。但此時應當認定為盜竊罪還是詐騙罪需要分情況討論。
前文中提到,占有人對財物的占有既可以是無償的也可以是有償的。在無償的情形下,行為人秘密取回自己的財物并獲得占有人的賠償(不論是錢還是物),占有人是由于行為人隱瞞了真實情況而產生錯誤認識,因而“自愿”將賠償交付給財物所有人,自己則白白蒙受了財產損失(因為占有人并不是由于自身過錯而導致財物滅失),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成立詐騙罪。在占有人支付對價后合法占有該財物的情況下,所有人將財物竊回的時候,如果達到數額較大標準就已經構成了盜竊罪,事后再向占有人索賠或者接受賠償的,又屬于隱瞞真相詐騙的情形。對此應分別處理:若所有人一開始就是為了索取賠償而竊回本人財物的,前一秘密竊取行為只是詐騙行為的手段,詐騙才是最終目的,按照吸收犯的原則定詐騙罪;若所有人只是單純竊回財物后又接受賠償,或者突發奇想索賠的,就是兩個彼此之間獨立的犯罪,以盜竊罪和詐騙罪數罪并罰即可。
注釋
① 劉明祥:《財產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② 沈志民:《對盜竊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財物行為的刑法評價》,載《北方法學》2012年第2期,第39頁。
③ 車浩:《占有不是財產犯罪的法益》,載《法律科學》2015年第3期,第122頁。
④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頁
⑤ [日]曾根威彥著:《刑法的重要問題》(各論),成文堂 1996年補訂版,第130頁。
⑥ 陳興良:《故意毀壞財物行為之定性研究——以朱建勇案和孫靜案為線索的分析》,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第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