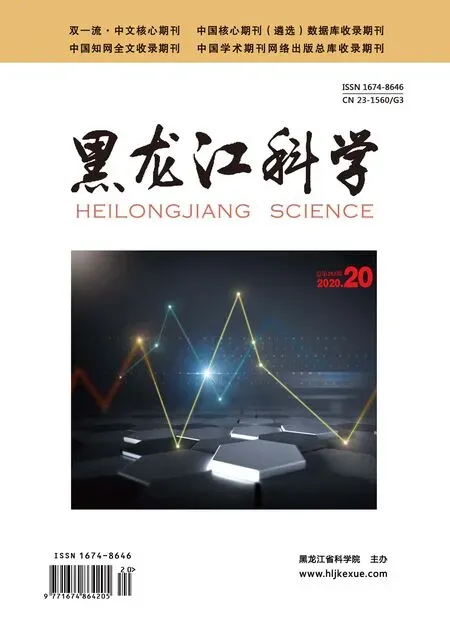新冠肺炎患者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沖突的社會心理分析與建議
李卓析,趙浩然
(1.哈爾濱醫科大學 第五臨床醫學院,哈爾濱 150081;2.吉林大學 法學院法律碩士教育中心,長春 130012)
新冠肺炎對于民眾是一個嚴重危害健康的疾病,對于國家是一場嚴峻的公眾衛生安全保衛戰,其對于軀體的傷害遠遠低于精神上的損傷,侵犯與保護成為疫情防護的重要課題,這需要法學與社會心理學的共同努力。
1 隱私權讓度給公眾知情權的必要性
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自己的個人隱私進行支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人格權,《民法總則》第110條明確規定了隱私權這一人格權。但行使隱私權也不得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也就是不能濫用隱私權。雖然公眾知情權在我國法律中還沒有被明確提出,但顧名思義,它是賦予公眾的一種集體性權利,是指社會大眾有權知曉、了解個人或組織信息的權利。然而,這些信息是指國家社會中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信息,就是在與自身無關時,不能打著公眾知情權的旗號去侵犯他人隱私,其權利行使同樣不能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二者似乎存在著權利沖突,而其權利界限目前學術界仍有諸多討論,但筆者認為,雖然兩種權利沒有權利位階的差別,可在某些特殊的社會階段,隱私權讓渡給公眾知情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根據公共利益原則,隱私權和公眾知情權的行使都不允許破壞社會公共利益,可見當二者發生權利沖突時,應該優先考慮公共利益。恩格斯曾指出:“當個人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發生聯系的時候,其性質就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權的保護,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因此,某些公眾人物的私人信息、政府依法應當對外公開的信息以及涉及公共安全的私人信息,應該為公眾所了解。根據比例原則,在權衡這兩項權利時需要考慮二者背后的利益。而不同的社會時期,利益衡量也有所不同。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確診患者途經公共場所接觸其他人可能會加重疫情的傳染,此時對大眾公開這些患者與疫情及社會公共利益有關的信息就是適當的,既符合公共利益原則,同時也是比例原則的體現。當然,絕不認同肆意公開個人隱私,將私人信息完全暴露給社會大眾,這也絕不是法律賦予并保護公眾知情權的本意。只有當二者在實踐中確實發生了權利沖突時,才應當考慮是否存在隱私權讓渡給公眾知情權的必要。而只有當需要以公眾利益為優先時,才能根據比例原則權衡,適當地將隱私權讓渡給公眾知情權。
2 信息模糊是社會公共事件中謠言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顯示,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眾批判能力。公式說明,謠言產生與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正比,公眾批判能力在謠言傳播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2011年日本發生的由地震引發的海嘯和核泄漏公共事件中,因為事件發生突然而重大,信息公開滯后,“吃碘鹽可以防輻射”的謠言在我國沿海地區迅速擴散,民眾恐慌情緒相互感染,上演瘋狂搶購食鹽的社會行為。又如 2020年1月末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官方突然發布武漢封城信息后,信息模糊疊加事件重大性質,上演了1月31日晚的“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謠言傳播,大量民眾相互感染恐慌情緒,進而聚集搶購。
3 謠言傳播的公眾心理分析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謠言傳播現象。將搶購商品簡稱為“行為A”。在突然降臨的災難事件中,民眾產生恐慌情緒,忽略消息來源的真實可靠性(理性思維),在“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感性心理作用下加入“行為A”的從眾行為當中。由于市場儲備量不足,部分民眾未能成功實施“行為A”,新一輪的緊張再起,強化了焦慮與恐慌。由于人的社會屬性,所以無論是在個人意志(是否實施“行為A”)還是價值判斷(“行為A”的真實性)上都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干擾。而人們往往為了保證自己與周圍環境(社會狀態)的一致性而選擇“去個性化”,將自己的“個人思維”轉化為社會環境下的“群體思維”,進而去實施“行為A”。
4 過度侵犯隱私權帶來污名化的心理學分析
疫情防控之初,一位被冠名“讓胡路溜達雞”的感染者信息在網絡上傳播,不僅有人連夜制作其詳細行動軌跡圖表,還在說明處加以冠名“讓胡路溜達雞”。雖后經證實該患者是一名在職采購員,但也依舊無法挽回其聲譽,在病痛之上再次被輿論“污名化”傷害。人們近乎“急迫”地過度攝取他人的隱私,已屬于一種侵犯行為,然而繼續污名化一個人,更加屬于一種侵犯。侵犯行為的產生與發展,可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侵犯行為是指有意傷害他人的行為,或者是以傷害他人為目的的行為,即侵犯行為必須有侵犯意圖和侵犯動機,是有意使他人受到傷害的行為。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曾經提出,侵犯行為是避免痛苦或尋求快樂的行為受到挫折時的“本能反應”。
通俗地講,當疫情迅速蔓延,人們為了避免受到疫情波及帶來痛苦,試圖了解實情卻沒有正式渠道(例如官方通報信息的不及時等),使得保護自己的行為受到了挫折,而“本能”地自己拿起“武器”,“保護”自己,最終演變成了一種侵犯。
5 隱私權讓度的目的
隱私權讓度的目的是降低謠言,減少侵犯。筆者總結出了如下幾條減少侵犯行為的方法:
宣泄負性情緒:當發現自己處于負面情緒當中,要盡可能地去尋找適當途徑來宣泄不良情緒。例如進行輕微的體育鍛煉,撥打心理援助熱線等。
培養移情能力:大量的研究證明,移情能力與侵犯行為之間呈現負相關,移情能力越高,越不容易對別人采取侵犯行為。所以,當自己面對一些情緒上的陰暗面時,可以試圖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往往會令自己茅塞頓開。
規范社會活動: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越積極正面,對待侵犯行為的懲罰越詳細規整,越益于侵犯行為的降低。作為行為人主體也不要將責任完全歸因于社會,要積極主動地攝取正面信息,管理自己。
抵制不良消息的傳播:在攝取到一些“不實報道”“陰謀論”時,要不信謠、不傳謠,主動屏蔽掉不良信息源。因為社會活動多在于模仿學習,只有規避不良榜樣,才能減少不良模仿。
6 法律對讓渡隱私權可能帶來的心理傷害的保護
《侵權責任法》第2條明確規定保護隱私權這一類民事權益,第3條規定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可見,如果侵害自然人的隱私權,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如果侵害了自然人隱私權,那么由此產生的對其的心理傷害,相關法律也會通過責任承擔的方式,對其救濟。此種心理傷害,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是精神損害。《侵權責任法》第22條明確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最高院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1條也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可見,在法律規范這一層面,對侵害隱私權的精神損害救濟已較為完善,雖然實踐仍有困難,因為如果侵害的是自然人的隱私權,需要明確對于被侵權人是否帶來了重大影響,如果沒有造成影響,則通常不能認為有精神損害。但筆者相信,隨著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伴隨著我國民法典的頒布施行以及學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因侵害自然人隱私權而給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一定會得到愈來愈完善的保護。
7 結語
當遭遇類似上述“污名化”的侵害時,可以從精神司法鑒定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面對侵害之初,當事人的心理由起初對疾病的緊張逐步轉化為對社會的自責,在此心態的催化下,很容易進入到焦慮與抑郁的惡性循環當中。此時,當事人應主動到當地具有精神司法鑒定職能的部門去做相關的心理測評與調節,通過專業的指導減少事件對自己的傷害及對相關侵害的行為人進行精神損害的追責與賠償,通過訴訟判決等合法途徑對其進行法律約束。而相關的精神司法鑒定部門也要積極地推進精神損害賠償的判定等級規劃,讓遭受到精神損害的人能夠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流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