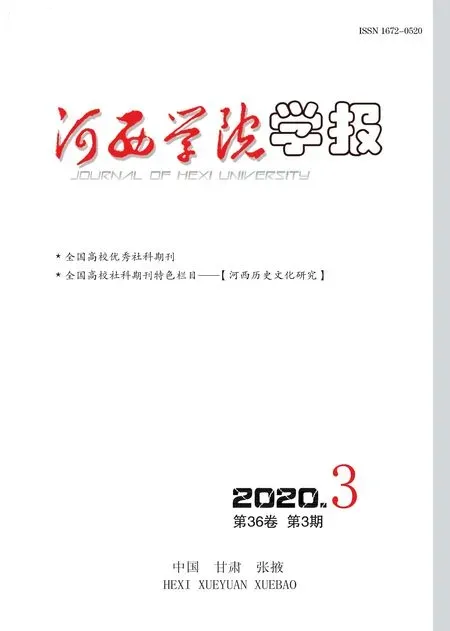明清時期河西水稻種植考略
閆廷亮
(河西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河西走廊地處我國西北內陸,屬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干旱和半干旱氣候。降水稀少,無霜期短,水稻種植的自然條件先天不足。自漢代大規模開發以來,農業生產一直以旱作農業為主。但由于河西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歷史時期在本區某些地方已有水稻種植的零散記載。對此,學界相關領域的研究中雖多有提及,然由于史料所限,均未展開深入的研究①。近年來,隨著敦煌學研究的深入,有關敦煌農業史研究也進一步深化,郝二旭依據敦煌資料對唐五代敦煌地區的水稻種植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但未涉及整個河西地區[1]。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地方史資料對歷史時期特別是明清時期河西水稻種植作以全面探討。
一、漢唐時期河西水稻種植的相關信息
西漢武帝時期,隨著對匈奴戰爭的勝利,河西正式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西漢王朝通過設郡置縣、移民實邊、修筑長城、駐軍屯墾等一系列措施,開啟了大規模開發經營河西的序幕。經過近百年的屯墾經營,河西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過去單一的畜牧業區逐步成為農牧并舉而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史稱河西“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2]1645據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記載,這一時期河西境內種植的糧食作物主要有粟、大麥、小麥、穬麥、青稞、黍、糜、??、豆等[3],均為北方典型旱作品種。漢簡中雖然也有部分官吏和戍卒食用“米”的記錄,但由于缺乏任何水稻種植的相關信息,其性質和來源尚無法判定。實事上,從河西早期農業開發的情況看,無論是生產要素還是生產技術,都還不具備水稻種植的客觀條件,因此,漢簡中的“米”很大程度上應是從內地轉輸而來。
西漢末到魏晉時期,河西經濟經歷了一個從停滯到逐步恢復發展的時期。針對河西自然環境別是農業生產發展的特點,不論是統一王朝或割據政權,都將水利事業作為地方農業發展的先決條件而不遺余力的推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4]“水田”的數量不斷擴大,為河西灌溉農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關于河西的“水田”最早出現在東漢初,史載:馬援為隴西太守時上奏朝廷在金城破羌之西“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使各返舊邑。”并“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5]835-835三國曹魏時期,徐邈為涼州刺史,鑒于“河右少雨,常苦乏谷”,乃“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谷,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6]739-740又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詔六鎮、云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7]164一個時期以來,部分學者將水田與水稻混為一談,在研究中國歷史上水稻分布時,把文獻中記載的水田作為稻田的證據,認為在這一時期河西地區已有水稻種植。其實,這一時期文獻中的北方水田主要是指可以引水灌溉的水澆田,即有水源保證和灌溉設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澆灌,種植旱生農作物的耕地,并不與特定的農作物種植相聯系。直到唐以后,受南方稻作文化的影響,水田才與稻田等同起來。[8]仔細分析史料,不難看出,這些鼓勵地方“開水田”興耕作的舉措都是糧食短缺的背景下提出的為保障民生的應急之策,種植傳統的北方旱作農作物當是首選。若是種植水稻,一是北方水稻生長周期長,二是產量低,短期內難以滿足當地對糧食的迫切需求。
此外,在發掘的河西魏晉十六國壁畫墓中,有大量反映當地民眾農耕生活的壁畫磚,生動展現了農夫犁地、播種、耱地、耙地、揚場、晾曬、堆糧、撮糧等農作場景,涉及的生產工具主要有犁、耱、耙、耰、鐮刀、連枷、叉、磙、簸箕等。[9]從這些畫面所呈現的內容看,顯然都是河西典型的旱作農業勞作程序和工具,從中難以看出有關水稻生產的信息。
隋唐以降,河西農業開發又迎來了一個新高潮。尤其是唐代前期,政府十分重視對河西的經略,水利建設方興未艾,耕地面積日益擴大,生產技術不斷改進,糧食產量大幅提高,作物品種種類增多,農業生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水平,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基地之一。糧食生產不僅滿足境內軍民所需,而且可支數十年,甚至還源源調撥東運,以實皇廩。[10]在這樣生產條件和背景下,加之南北農業生產交流互動日益密切,為滿足部分上層階層和特殊群體的需要,在走廊個別生產條件較好的地方,開始小規模種植水稻。郝二旭依據敦煌文書P.3841號背《唐開元廿三年沙州會計牒》沙洲居民向官府繳納的糧食中“米”的記載,以及P.2942號《唐永泰年代河西巡撫使判集》河西士卒要求增加稻米供應的信息,考證文書中的稻米不是外地轉輸而來,應是本地所產,據此認為在八世紀前期敦煌地區已經有水稻種植。至吐蕃占領時期,敦煌文書中已有土地被用于種稻以及寺院役使寺戶割稻舂稻的記載,進一步證實敦煌地區確有水稻種植,并一直延續到歸義軍時期。[1]
這一時期既然敦煌能種植水稻,那么處于同一地區自然和生產條件要好于敦煌的河西其他地方也應該也有水稻的種植。史載,早在武則天時期郭元振任涼州都督時,“遣甘州刺史李漢通辟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11]4362甘州地處黑河中游,地勢平坦,水資源豐富,土壤肥沃,具有種植水稻的優勢和條件。“稻收豐衍”雖是虛夸之詞,但此時在甘州種植水稻應是不爭的事實。只是由于種植規模小,在糧食生產中占比很小,未能留下更加詳細的記載。
唐中葉到元末,河西先后被吐蕃、回鶻、黨項、蒙古所統治達六百余年,經濟發展也經歷了諸多波折,許多地方雖“俱不能如曩時”,“無復昔日殷富繁華。”但在某些時期,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漢唐以來傳統的農業生產得以延續。敦煌的水稻種植在歸義軍時期依然小規模存在,西夏時期包括河西諸州在內“其地饒五谷,尤宜稻麥。”[12]14028說明河西地區的水稻種植并未停頓。
二、明清時期河西的水稻種植
明清時期,河西作為西北邊鎮和經略新疆的戰略基地,農業開發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伴隨持續不斷的移民以及人口的不斷增殖,農業耕地面積迅猛擴大,水利工程遍及綠洲,生產技術和生產理念得以提高和改造。僅耕地面積到清代初年已達450萬畝,其中水澆地占80%以上,達350萬畝。[13]除種植傳統的麥、粟、谷等農作物之外,玉米、棉花等外來作物也得到引進和推廣。同時隨著南稻北栽技術的推廣,河西的水稻種植也得到了進一步擴大和發展。
明正統年間,江南下邳人鄒和任鎮夷守御千戶所(治所在高臺縣羅城鎮天城村)指揮,在其任上“教民樹藝,稻田自和始。”[14]250這是明清時期河西水稻種植的最早記載。此外,在河西各地均有水稻種植的記錄。史載,肅州雖“土瘠風寒,物產不多,”但稻“宜種,人鮮知法,間有種者,獨鎮夷多種。”[14]100稻的品種有“紅、白二種,亦分粳、糯,糯可釀酒。”[15]115高臺“稻有糯、粳二種。粘者為糯,俗稱江米。可釀酒,并制糕糖。不粘者為粳,俗稱白米,為食糧佳品。”[16]190甘州“土腴氣正,麥稻兼宜。”[17]74有“秔、糯二種出張掖西北及撫彝。”[18]227“稻,蘭、鞏、秦、階、肅、寧皆有之,惟甘州所產最佳。”涼州“稻有紅白兩種,惟高臺、鎮番有之。”②這些信息大致反映了這一時期河西地區從東到西水稻種植的分布情況。
由于河西地區自然環境及農業生產發展的差異,這一時期,水稻種植主要集中甘州、臨澤、高臺等地的黑河沿岸地帶。《新纂高臺縣志·物產》記載“《肅鎮》謂‘種不甚廣’,今黑河沿岸普植之。”[16]190《重修肅州新志·高臺·物產》記載了具體種植的地方,“甘州城北門外烏江窯子延黑河北、柳樹堡、板橋、平川、三、四、五壩,以及張掖縣屬河南、撫夷、新添、三工、雙泉等堡,俱廣種稻。”[15]58這里旁依黑河,地勢低平,土地肥沃、水利渠系完善、灌溉便利,歷史上就是灌溉農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具有種植水稻的優勢。經過一個時期的試種和推廣,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呈現出一派“塞上江南”的田園風光。自明代弘治年間至清末許多到過河西或在此地任職的官宦文人,都用其筆墨真實描繪和贊美了黑河沿岸稻花飄香的南國景致。如明代曾任甘肅行太仆寺卿的郭紳作《觀刈稻詩》云:“邊方渾似江南景,每至深秋一望黃。穗老連疇從秀色,稻繁隔隴有余香。”[15]58明代詩人石玠詩《高臺》云:“重重云樹隱高臺,幽景能冷郁抱開。秋水入田應熟稻,晚煙著地欲成苔。”[15]123清雍正年間駐肅州西安糧監道軍需庫務沈青崖詩《過高臺縣》云:“榆木山前古建康,南都風景繪屯莊。兩行高柳沙汀暗,一派平湖水稻香。”[15]123清末甘涼道道臺廷棟《過高臺水鄉紀實》云:“秋水稻粱鴻鵠滿,春渠楊柳鱖魚肥。”“此鄉魚米堪招隱,到處鶯花淡俗家。”[16]471“稻香綠野”的景致被舊志列為明清時高臺“十景”之一。《新纂高臺縣志·形勝》“高臺十景”之“稻香綠野”云:“郭外西郊,平疇萬頃,悉種粳稻。清肅州道沈公青崖過高臺,留有‘一派平湖水稻香’之句,即指此也。春夏之交,碧毯線頭,秧針掩映,頗有佳致。”[16]152清人袁泰、徐家瑞、錢昌緒、薛樹勛等地方官員和文人等都有詩文抒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地一個時期水稻種植的興盛。
隨著水稻種植規模的擴大,生產技術的相對成熟,水稻產量也逐年增加,在一些地方稻米亦成為繼糧(麥)、粟之外“農產品之大宗也。”甚至“邑商運銷于酒泉、安西、敦煌、哈密等處,獲利甚豐。”[16]190自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甘州府還將稻米列入國家賦役征收名例,每年按畝征收。史載:“甘州賦役,屯科殊致,芻粟并征,更有非田而賦以粟,等田而獨賦米。”規定雜田“稻米地原額米六升七合五勺八抄,折征正糧二斗二合七勺四抄。”乾隆七年(1742年)又“減征一斗二升。”[18]207-208除此之外,由于“高邑素產大米”,高臺縣甚至按渠攤派稻米以供衙署消費,規定“每年由各渠供支署內大米二十六石八斗九升,糯米二石六斗九升。”[16]457高臺如此,鄰近生產稻米的張掖、撫彝其情形應大體相同。直至民國,水稻仍是這些地區重要的農產品,據民國三十六年(1947)編《高臺縣要覽》記載:“本縣耕地面積,約十六萬三千五百二十七畝,可耕荒地面積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畝。年產稻米二千九百余石,小麥九萬八千四百余石。”[16]535無論是種植面積還是產量仍相當可觀。
宋元時代,我國水稻栽培技術已相當成熟,尤其是育苗插秧已成為提高水稻產量的重要技術環節。但明清時期的河西地區,許多地方水稻種植依然采用古老的撒播方法,如鎮夷“人鮮知法,間有種者,……亦不栽苗,但亂種耳。”[14]100高臺“惟土人不諳置畦、插秧之法,只散播種籽于田間,聽其自生,故收入不及南方優勝。”[16]190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水稻產量的提高。直到1954年,素有“水稻之鄉”甘州烏江地區,才開始推行插秧技術,水稻產量提高了近三分之一。[19]其余地方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總體而言,由于河西境內水稻種植規模小、技術落后,水稻產量低,故市場價格很高,“菽麥賤值,秔稻貴值。秔米常日視粟米等價皆倍之。”[18]226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50年代。
三、水稻種植對河西經濟社會的影響
水稻原作為南方的主要糧食作物,隨著南稻北植技術的逐漸成熟,自唐代中葉在河西部分地方種植,到明清時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廣和發展。這一過程,一方面是河西作為歷代重要的軍事屯墾和移民區,來自全國不同地域的戍卒移民將南北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這里,促動了水稻的種植和推廣;另一方面也是河西特殊的自然環境,尤其是漢唐以來發達的農業生產條件為水稻的生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縱觀其生產發展的歷史,雖然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而時斷時續,在分布上也處于零散狀態,規模小、產量低,亦未引起政府和地方的高度青睞而予以大力扶持,與整個北方種植的情形一樣,“五谷則麻菽麥稷黍,獨遺稻者。”稻被排斥在傳統的糧食作物之外。但無論怎樣,作為一種新的農作物品種,在引進和種植后,其對河西經濟社會仍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水稻的種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河西傳統的旱作農業種植結構,水稻成為一些地方繼黍、稷、麥之外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如明清以來河西地方志所記地方物產“谷”類中,“稻”都被列在靠前的位置。甘州、高臺等地把稻米作為國家和地方田糧征收的重要品種。由于水稻種植特殊的生產條件以及技術要求,也進一步推動了地方水利設施建設,對土地的改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水稻生產在一定范圍內改變了河西民眾傳統的飲食結構。歷史時期,受自然、地理條件限制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與中原及其他經濟發達地區相比,河西物產不論是經濟作物還是畜牧產品都十分有限。史書所謂“河西殷富”,“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等說,不過一時一地一物之美譽。在地處“南山之麓,地高多寒,雨澤稀少”[16]189的大環境中,“茲土山田賦輕,然地少獲寡。”[20]27“地寒產少,然物之因寒而產,轉以御寒為土宜。”[20]30“土瘠風寒,物多不產,惟麥豆之需,不過數種,及果實蔬菜之類,視中土不及二三,且交夏甫有,春色生長,俱在一時。”[14]100生之有限,取之不易,食物來源單一。“北人饔餮,多屑麥、稷、蕎為□饦及粟飯。”[21]是人們的日常飲食的一般寫照。但明清時期水稻種植引入后,稻米成為河西地區一些地方的重要糧食之一。在飲食習俗上人們“食重羔、豚、雞、鴨。谷、麥、稻、糯,性溫味甘,積數年不爛。”[18]158“食主麥、粟,間以稻,貧者飯粟。中產家款客或奉尊長,則以肉菜與稻、麥,余皆食粟,間以麥。”[16]184稻成為一般傳統食物之外的重要補充。同時,稻還被用來釀酒,“以糯、稻和曲,內入汾酒釀成者即紹興、玉蘭、金盤、三白諸色酒。”[18]158高臺所產糯米,“俗稱江米,可釀酒,并制糕糖。”[16]190每年端午河西民眾“戶插楊柳,家食角黍”[18]159的傳統也增添了新的內容,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團粽”、[21]“糕糖”等。所有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河西民眾的飲食生活。不過,在我國古代北方,稻米是帶有濃厚階級性的食物,主要是為了滿足少數“肉食者”即上層社會的消費,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還難以進入他們的日常飲食。[8]河西的情形更是如此。
第三,水稻生產也帶動了河西糧食的商品化程度。長期以來,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條件下,河西傳統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極低,嚴重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稻米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糧食產品,得到了周邊地區上層消費者的青睞。張掖的“白麥青稞,蠶豆胡麻,香粳玉粒”成為米糧市場交易的主要商品。由于稻米產量少屬希有產品,“秔米常日視粟米等價皆倍之。”“遠銷于酒泉、安西、敦煌、哈密等處,獲利甚豐。”[16]190特別是烏江所產黑米,品味香淳、品質上好,元代被列為貢品,民間俗稱“貢米”、“藥米”、“長壽米”,具有特殊的營養價值和藥用價值,一度曾是市場上的緊俏產品。因此,稻米生產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河西商品經濟的發展。
注釋:
①參見張澤咸《試論漢唐間的水稻生產》,《文史》第18輯,第33-68頁;鄒逸麟《歷史時期黃河流域水稻生產的地域分布和環境制約》,《復旦學報》1985 年第3 期;張芳《夏商至唐代北方的農田水利和水稻種植》,《中國農史》1991 年第3期;華林甫《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中國農史》1992年第2期等。
②張澍輯著:《涼州府志備考·物產》,武威市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校印,1986年,第75頁。按:此處“鎮番”當為“鎮夷”,文引《甘鎮舊志》。但張澍先生備考云:“今鎮番不種稻,想自國初兵燹后廢之,留心民生者尚其復諸。”亦說明清初民勤一帶有小規模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