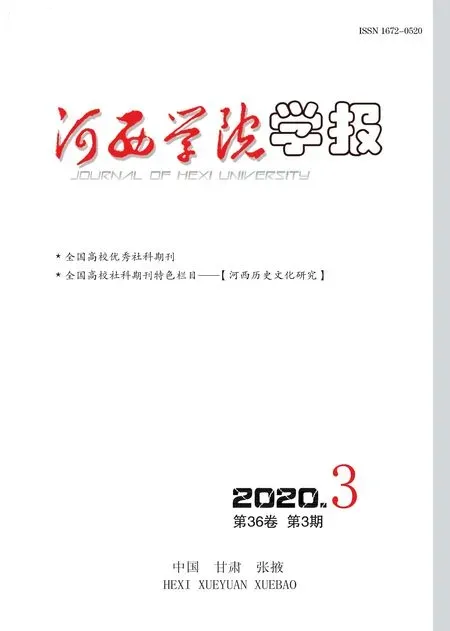論馮驥才非虛構新作《漩渦里》的寫作特色
畢莉莉
(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引言
近年來,對于非虛構的討論越來越激烈,對非虛構的起源、特點、意義與價值的研究也越來越豐富,馮驥才是我國文學界做口述史最早且最負盛名的作家,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在新時期文學的浪潮中,他便采用口述實錄的方式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非虛構文學作品《一百個人的十年》。《漩渦里》是馮驥才的非虛構新作,是他深切關注社會問題后的思想結晶,作為他自傳體、非虛構系列寫作的最后一本,傳達了他更全面、更新穎的思考內容。口述實錄史與傳承人口述史有所不同,《漩渦里》采用自我口述史的方式,在回答他兩次重要“轉型”問題的同時,向讀者展示了豐富多彩且寶貴的文化發現,傳達了他文化保護與文學思考的最新動向,不僅具有社會研究價值,同時也具有很深的文化研究意義。
一、敘述者的四重身份
在《漩渦里》中,馮驥才將其作為作家、畫家、學者、文化遺產保護人這四重身份歸結為“四駕馬車”。在馮驥才一步步深入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里,文學、繪畫、教育“三駕馬車”無一不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保駕護航。
(一)作家馮驥才
作家是馮驥才永不會褪色的身份印記,寫作是他永不會停止的事業。對他來說做文化保護的最初動力來自于一種情懷,一種作家的情懷,他說:“在作家眼里,民間文化不是一種學問,不是學術中的他者,而是人民的美好的精神生活及其情感方式”[1]143,“文化遺產”這個概念正是他在九十年代初,基于作家身份,站在時代轉型的立場上,關注民間文化時提出的。1994年,馮驥才以作家身份應邀為維也納作一本文化游記,這次出行,馮驥才感受到歐洲人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保護中國民間文化的緊迫感增強了他投入“漩渦”的決心,他開始利用寫作這一方式,在呼吁文化遺產保護時,創作演講稿,進行演講,希望通過文字傳達內心的聲音,用其作家的力量,喚醒大眾去堅守民族的精粹。
社會的瞬息萬變、經費的空缺、專家的極度缺少、社會支援的無力,都為文化的搶救工作增加難度,這使得馮驥才不得不為搶救工作四處奔走,既使如此他仍然沒有完全放下文學創作,但創作只能在旅途中進行,奇妙的細節與情節也總是在:“馮老師,我們快到了”的聲音中被忘的一干二凈,也正因在這樣的環境中,馮驥才有機會創作出大量文化思辨與文化批評的文章,如《作家的責任》《文化怎么自覺》《弱勢文化怎么辦》等,均引領當代文藝理論趨向。
(二)畫家馮驥才
正如馮驥才自己所說,寫完此書才發現他人生中的兩次“重要”轉型——從繪畫到文學,再從文學到文化遺產保護。他最初有志于丹青,曾畫了十五年的畫,高中畢業報考中央美術學院,但因出生不好未被錄取,后加入天津國畫研究會,但在他拿起筆寫作之后,用馮驥才自己的話來說“文學改變了我”,文學的創作改變了他繪畫時的思考方式、心境與心緒,使他更習慣于追求事物的本質。繪畫對于他是一種自我的藝術,為文是對于社會人生的一種負責任方式,作畫則更多是一種深刻的生命方式。
因為繪畫,因為走南闖北辦畫展,馮驥才目睹了九十年代中國第二次革命浪潮,了解到這股浪潮正以雷霆萬鈞之勢沖擊著民間文化,如上海郊外周莊的柳亞子迷樓,寧波慈城鎮上的賀秘監祠,因經濟發展需要,遭到拆毀。在上海,馮驥才以賣畫的行動促成了迷樓的保護,在慈城,他用賣畫所得切實保護住了賀秘祠,這可能便是馮驥才下意識地走入漩渦的第一步。同時,受邀到海外舉辦畫展,使得更多的外國民族文化展現在馮驥才眼前,使他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勢在必行,文化比較與自我反思兩種思維,隨著世界各地舉辦畫展,深深地烙在馮驥才的腦中。
在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里,寫作與繪畫不僅是馮驥才的私有武器更是公器,寫作用來做文化批評,或用來寫田野歸檔;繪畫用來賣錢,資助文化。通過文化批評,引起社會關注,引發大眾的文化自覺性;通過繪畫,資助沒有經費資助的志愿團體,使他們能夠在艱難的歷程中繼續前行。
(三)學者馮驥才
馮驥才一向十分關注教育,二十世紀80 年代初,他的散文《挑山工》便被選入小學語文教材,據調查,至少有兩億中國人在課堂上讀過這篇文章,影響深遠。《漩渦里》回憶了馮驥才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碰上的一件大事——天津大學要建立一所以馮驥才為名的學院,并聘請他為終身教授,這無疑為他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打開了又一扇大門。
從文聯到天大,馮驥才開始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教育事業當中,10余年來,他在教學科研方面也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培養了一批視野開闊、有思辨力、操作能力與社會責任的青年學者,這為他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造就了一批有力的后備軍,可以說大學教育是他以文化遺產為中心展開的新事業。此時,馮驥才左手的文化搶救與右手的教育也漸漸合二為一,學院成為組織與推動文化搶救的工作室,師生成為他的助手,如在全國木版年畫搶救專項活動中,他帶著學生深入田野,一邊做調查一邊培訓,在行動中思考。
與此同時,天津大學也為馮驥才提供了一個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向大眾發生的最佳“高地”。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成立引起了全社會的好奇與關注,由他本人所形成的社會熱點大大提升了人們對民間文化的關注。在這樣的機遇下,他一個人帶動了一個領域、一個專業、一個文化樣式由社會的邊緣進入時代與社會的中心。
(四)文化遺產保護人馮驥才
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漩渦里》的主線,是馮驥才二十余年來工作的核心。1993年至1994年,此前的“新文化時期文學”是他盡文學責任的十余年,此后的“文化遺產搶救”是其盡文化責任的二十余年。馮驥才曾說:“一旦你丟掉了自己的文化,那這個民族就會面臨很大的精神危機,這比物質貧困還要可怕。”[2]更重要的是,民間文化是活著的文化,民間文化遺產是過往的歷史所創造的,必須保存的文化精華,是一種歷史財富。
《漩渦里》記錄到,在一次文化普查中,由于設備的缺乏,沒能及時錄制一位老太太的民歌《花兒》,從此這種民歌便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在經濟快速發展面前,文化丟失的速度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可以說每一分鐘我們都在丟失,文化遺產的搶救刻不容緩。馮驥才為保護老街連夜制定保護計劃;為及時記錄散落年畫、木版畫,深入田野進行調研,曾與同事在狂風大雨中推熄火的車;為進行古村落的保護工作,穿越太行山,只為感受最本真的山村。作為文化遺產保護者與倡導者,馮驥才以六七十歲的高齡深入田野,在風里、雨里、雪地里進行文化普查,并四處宣講、呼吁,致力喚醒國人的文化自省與文化自尊,二十年如一日,在文化遺產保護中,“只有逗號,沒有逗號”已然成為他的口頭禪。
馮驥才的“四駕馬車”在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中并駕齊驅,為馮驥才文化五十年歷程注入血脈與精魄,在文學和文化保護兩個領域齊頭并進的人,可謂少見,在當代中國文學中,文化保護方面,馮驥才必將占據一個重要位置。
二、馮驥才的創作意圖
馮驥才在以作家、畫家、學者、文化遺產保護人四重身份記錄文化遺產保護歷程時,透露出的是其作為知識分子與文化遺產保護人的立場,傳達出作為一位知識分子應有的文化反思與文化自覺。
(一)現實關懷
馮驥才作為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領頭人,曾說他的口述史是對他二十年進行城市文化搶救、民間文化搶救與古村落搶救過程的文學式記錄,《漩渦里》以紀實的文學風格展示了馮驥才“以第一視角對非遺保護曲折歷程的見證”。
九十年代中期,馮驥才開始投身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中,成為文化遺產保護先覺者、先行者與先倡者,繪畫為其打開了第一扇窗戶,第一次保護行動,他將目光鎖定在農民印刻的粗礪而又質樸的木版年畫上,歷時十年,普查了全國數十個年畫產地,最終形成22卷《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和數十部《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天津老城保護是馮驥才兼顧木版年畫保護的第二個重點項目,面對響徹全國的舊城改造口號,建成六百年的天津老城岌岌可危,馮驥才為了與拆除搶時間,緊急組織志愿者與學生拍照、攝像、調查訪談原住民、搜集相關文物,整理出版,建檔建立博物館等,在老城保護活動之后,接踵而來的是搶救老街,馮驥才為引起相關部門注意,寫了長文《老街的意義》發表在《今日報》上,同時為了增加保護估衣街的社會輿論,制作估衣街明信片并在估衣街簽售。天津古城與老街的保護行動幾乎就是后來全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的一個縮影。此后,民協與政協給了他更高的平臺與機會,使其有決心與信心更深一步進入龐大而復雜的古村落保護計劃當中,深入的田野調查,國家社會的支持,使得馮驥才有機會在后溝村親眼見到原生態的各式洞窯,寺廟,同時,馮驥才深切地體會到一種無能為力的悲傷,這種原生態的美,在日益突飛猛進的工業化進程中,傷痕累累,直至最后無跡可尋。
木版年畫、老城老街、古村落,構成馮驥才文化遺產保護之旅的核心,而四重身份豐富了馮驥才的觀察視角,在國家層面,馮驥才推動了民間文化遺產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面搶救與保護,在文化層面,他以一己之力掀起了民間文化熱潮,改變了民間文化邊緣性的狀態。
(二)文化反思
歷史中的個體對于自身生命的理解,沉思性的文字表達,不僅能夠向我們真實地展示豐富的個體記憶,而且有利于我們理解把握整體的歷史脈絡,馮驥才在《漩渦里》中選擇采用自我口述的方式記錄保護歷程,正是為了更真實、更自由地傳達自己在這段歷程中的所思所得。
繪畫與寫作給予馮驥才更多出國的機會,文化遺產保護人的身份使其比一般作家多了遺產保護視角、大的文化情節與國家意識。在國外,馮驥才感受到奧地利人民談到本國民間文化現狀的自豪,他思考文化遺產在中國普通民眾心中分量到底有幾許?“如今除去少數精英還在堅守自己民族的精粹,大眾卻已經無視甚至輕視自己的文明了,這種悲哀在我后來進行文化遺產保護中感受得愈加深切”。[1]147法國人當代的遺產觀、保護理念、方法、知識分子和政府的分工合作,促使馮驥才不得不思考中國文化遺產面對重重困境的出路。在國內,面對天津老城的改造,估衣街的拆遷,古村落的無跡可尋,馮驥才思考國人的精神面臨怎樣的困境,而歷史文明在當代生活中又應該處于怎樣的地位?現實給了馮驥才眾多反思的機會。
馮驥才在《漩渦里》下篇中記錄到,在一次政協會議上講到的一個話題——文化怎樣自覺,他堅決表示,在當代社會中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文化自覺的責任“當社會迷茫的時候,知識分子應當先清醒;當社會過于功利的時候,知識分子應給生活一些夢想”知識分子是做文化的,必須要先覺。當一位老朋友對馮驥才說:“如果現在你撂下挑子沒人指責你。因為你已經年過七十。”[1]188馮驥才只是回答說:“我做的事與年齡無關”,從進入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馮驥才從未想過退卻,在這時代轉型的重要關頭需要的正是這樣一份真摯的文化人的情懷。
無論是不斷觸發的對我國民間文化現狀的反思,還是對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文化責任的先覺性呼吁,馮驥才不惜解剖自我的生命歷程,用非虛構真實地袒露自己的生命軌跡、思維軌跡與思想軌跡。[3]
三、《漩渦里》的價值表征
(一)文化發現
藝術來源于生活,對于馮驥才來說,眾多的文化發現是其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最大的收獲,從《漩渦里》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切實的保護行動,為我們保留住了多么珍貴的一筆民間文化遺產。
與馮驥才每個階段的核心保護對象一致,我們首先了解到“年畫重鎮”楊柳青鎮,馮驥才在此期間發現并記錄了《雙槍陸文龍》《農家忙》《五大仙》等大幅年畫,在深入田野的文化普查中,及時保護住了藏于河北農民房頂上的一批珍貴古版畫,更在賈氏農人家中發掘出《三月爭魚》《合家出行圖》孤品。在天津老街保護行動中,馮驥才發現了帶年號的老城磚、明代木門與古井、馬順清與劉鳳鳴的磚雕、劉杏林的木雕等等,最終經過努力,將鐘鼓樓中心城區與東區內大街原生態保留地保留下來。在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古村落保護面臨最嚴峻的考驗,也是馮驥才最為關注的對象之一。羌族文化在汶川地震后近乎絕跡,經過馮驥才及時發文呼吁,得以在北川地震遺址建立博物館。絕大多數的古村落都沒能抵擋住工業化大潮的沖擊,但至少馮驥才等人在后溝村發現的明代風格的彩繪畫梁,明代天啟六年的嵌墻碑《重修觀音堂碑》等均被及時記錄在冊,浙江西塘更是在古村落保護聲中,將生態的,活態的,以人為本的生態理念貫徹至今,成為古村落保護的典范。除此之外,在馮驥才10 年地毯式民間文化普查活動中收獲了184 萬篇民間故事,302 萬首民間歌謠,748萬條民間諺語,為后人留下了可供參閱的寶貴資料。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珍貴的民間文化遺產最終會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馮驥才運用獨到審美觀,通過文化發現,及時保護、記錄、整理民間文化遺產,具有無法忽視的社會現實價值與意義,同時他弘揚民間藝術,以先覺者的眼光,先行者的行動切實的為當代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保護貢獻力量,將民間文化氣息注入《漩渦里》。
(二)檔案留存
在《漩渦里》中,馮驥才在記錄各個階段文化遺產保護歷程時,將其在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民間文化遺產搶救過程中,創作的一系列具有創新性、創意性思想的文字摘錄在自我口述史中,這些文字見證了馮驥才二十年來,對于民間文化遺產思考的變化軌跡,具有史料性的意義[4],總體來講,實現了檔案留存的重要作用。
這些具有文化思考性意義的文字摘錄可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一是每次文化行動后的反思,如第一次文化行動天津老城保護后,為老城編輯的圖冊——《舊城遺韻》;為引起社會與國家更多關注木版年畫保護行動,寫的長篇序文《中國木版年畫的價值及普查的意義》;在看到一批批民間文化遺產猶如落葉殘花飛去后所寫《從潘家園看民間文化的流失》一文;《羌去何處》是為遭受汶川地震幾乎消失的羌族文化發聲。二是具有重要啟示性意義的講演稿摘錄,如楊柳青石家大院元宵晚會上的發言《津門文化盛會考紀》,為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得到更多支持而發表的《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在政協上表達對文化命運深切思考的《莊嚴地宣布》,為古村落發聲的《古村落是我們最大的文化遺產》。三是以民協代表身份提出的建設性意見,馮驥才代表民協先后提出《關于緊急搶救民間文化遺產的提案》《建議國家確立文化建設主體的戰略結構》《為傳承人口述史立論》與《關于中國古村落保護的幾點建議》,在傳達其對民間文化深切的關懷同時,也切實的影響到國家文化戰略和政策。
《漩渦里》馮驥才對這些體現其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文字性史料地摘錄,完成了對其二十年來文化思考進程的整理與留檔,不僅對現代知識分子文化遺產保護觀念具有啟示性的價值與意義,同時具有研究馮驥才文化思想走向的史料性參考價值。
(三)自我心靈口述史
口述史作為人類記錄歷史的最早形式,在中國有著較為悠久的傳統,馮驥才也采用口述實錄的方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一百個人的十年》,從八十年代中期的口述實錄文學,到開創傳承人口述史,呈現出馮驥才在口述史方法上的共性、發展與變化[5],而《漩渦里》中,馮驥才在口述史中加入自傳成分,強調非虛構創作中對文學性的關注,凸顯出其作為文化學者與人民之間真誠的心靈交流。
馮驥才的口述實錄文學注重用真實的材料塑造獨特的人,傳承人口述史成為以人為核心的文化檔案,《漩渦里》采用的自我口述史則在這兩者基礎之上追求對人心靈的叩問,使用第一人稱敘事,注意運用小說與散文化的語言,貼合他所強調的非虛構創作的“優化提升原則”,描寫和講述的是故事,表達的卻是歷史個體在此背景下的心靈成長史。《漩渦里》中,馮驥才進行對自己的訪談,實現了訪談人與口述者的零距離互動,將自傳體文學具有的個體記憶的豐富與口述史的真實相融合,雖然這樣的記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以歷史性的眼光審視與關注的社會現實,以個人的命運轉折,表現激蕩巨變的時代,使得口述史充滿力量與意義,以我手寫我心的態度,[6]賦予了文字前所未有的表現力,使得描寫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細節都更加充滿意味。
馮驥才口述史實踐經驗是其豐富的文學、文化學、遺產學思想的綜合體現,他的口述史實踐是我國口述史研究的范例,《漩渦里》中他更是將這一方法從實踐上升到學科方法論地位,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書寫范式,記錄他的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事業,使其非虛構文學更具打動人心的感染力。
結語
非虛構寫作是馮驥才在小說與散文之外的另一只筆,文章合為時而著,《漩渦里》中,馮驥才以知識分子、文化遺產保護人的視角,傳達的是民間傳統文化的魅力,具有遺產保護與文化社會研究價值。因《漩渦里》是馮驥才自傳口述史系列中的一本,講述的僅僅是其1990 至2013 年的歷程,具有時間的限制,同時因是作者自我的口述,在內容上可能只局限于個人的記憶,因此不僅有待于對其同系列的自傳口述史進行進一步研究,也還需要對其口述實錄文學作品以及傳承人口述史作品進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