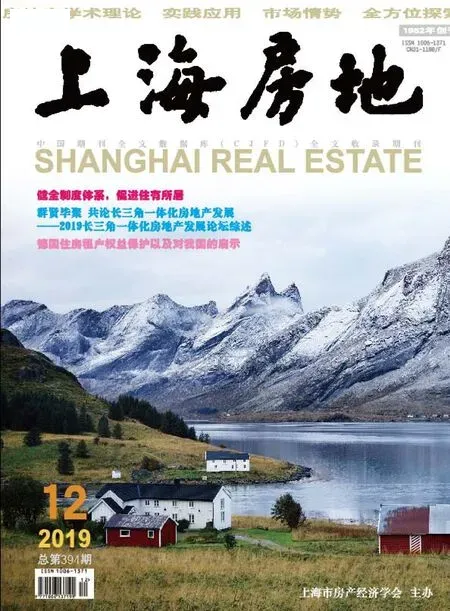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問題探析
文/馬帥帥
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規定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指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進入土地交易市場,即將符合法律規定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使用權通過有償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出讓、互換、轉讓、抵押)在土地市場上進行交易與流轉,其實質是通過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市場化配置,盤活存量土地,充分利用土地資產價值,實現土地增值的過程。
2019年8 月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以下簡稱“新法”)頒布,在涉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制度中,刪除了原《土地管理法》中規定的用于任何建設的土地性質必須為國有土地的條款,并且在本次修訂后的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分別規定了入市的決策主體、入市交易的集體土地范圍、入市交易的方式和途徑、入市后的土地用途等。這些規定從根本上掃除了原有集體建設用地需依法轉為國有土地后才可作為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出讓的法律障礙。

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面臨的法律問題
新法從法律層面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消除了法律桎梏和制度阻尼,將各試點的入市改革納入了法治化軌道,然而,仍需研究新法修訂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面臨的法律問題,從而保證制度的有效實施。
(一)入市主體問題導致的交易風險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有三類主體,即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所有、村農民集體所有、鄉(鎮)農民集體所有,與之對應的入市所有權主體是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村農民集體、鄉(鎮)農民集體,也即集體經濟組織。
各試點地區均明確:土地屬于鄉(鎮)農民所有,由鄉鎮農民作為入市主體;土地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民集體作為入市主體;土地屬于村民小組,由村民小組作為入市主體。在入市模式中逐漸探索出以農村股份制經濟合作社、農村土地資產管理公司等作為入市主體的代表或代理,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進行具體的入市操作。
然而,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性質不明確,內部成員的法治意識、權利觀念薄弱以及權利行使機制不順暢,因而仍存在部分問題。

1.入市主體因內部成員的復合性而增加入市協商成本。較之于國有土地單一的所有權主體,用于入市的農村集體土地涉及上述三類主體所有的土地,此種土地按照由大到小的范圍所產生的多層次所有權關系架構會導致入市所有權主體成員的復雜性,即大多數成員同時滿足鄉(鎮)農民集體成員的身份、村集體成員身份以及村內小組成員身份。在這樣的架構體態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重復,作出某種有利于集體的決策時,決策機制的運行不存在問題,但若是某種不利于此類群體的決策需要表決時,這類具有復合型身份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往往會阻礙甚至排斥決策的生成、運行與實施。簡言之,若是入市決策不能滿足具有復合型身份的成員利益訴求時,則形成入市決策意見存在一定的困難,也會增加相應的協商成本。同時,新法未規定該如何保障入市決策形成的過程中所涉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知情權、表決權以及救濟權。因此,即使入市交易達成,也可能因成員的不同意見而影響合同的履行,從而產生權屬糾紛。
2.入市主體在交易活動中衍生的土地所有權人代表或代理會對入市交易產生影響。合作社、經營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作為所有權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是否具備法定資格,是否依合法的表決程序而產生,目前并未有相關法律規定。且在這種入市交易的民事合同中,受讓方需要甄別此類人員或組織所產生的代理風險,如是否存在無權代理、超越代理權、代理權終止的情形,這在無形之中增加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中交易對方的識別成本。
(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法律定性不明
《物權法》中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客體是國有土地。新法第六十三條與第六十六條均提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但援引法理學中的擴大解釋與體系解釋,并不能將《物權法》中有關“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涵義應用于新法中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有學者認為,“農村集體土地中的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既沒有被明確規定為獨立的用益物權,也沒有涵蓋在現有的建設用地使用權規范中”。即使在中央關于“三塊地”改革的一系列文件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用語屢見不鮮,但也未有現行法對其進行法律定性。
《土地管理法》作為管控法,其立法目的是國家在城鄉二元制體系下對土地的規劃、利用進行有效的規制。事實上,新法在修訂后進一步規范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主體內涵以及權利義務,并且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使用權的具體權能(轉讓、互換、贈與、抵押)作出了具體規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具有“私權”的性質,但其仍未獲得《物權法》的正名。若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發生爭議,尤其是將此土地的使用權用于項目融資、基建項目時,法院在判決中援引相應法律依據,究竟是引用《物權法》中關于“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定,還是承認新法中有關“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定,不同法院可能會有不同的判例。當然,這種情況會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處于不確定的狀態。
(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的法定收益分配不明
新法并未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的收益分配方案進行規定。入市后的收益分配主要涉及三方主體,即政府、集體經濟組織以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集體經濟組織為媒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的收益分配主要分為外部分配(政府與集體經濟組織)和內部分配(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
1.對于外部分配,無法律規定。各試點地區主要根據《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征收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已于2017年底失效)由政府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其中存在的問題有:其一,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征收比例不明晰。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只規定按照入市收益的相關比例征收,但這種規定下的征收比例并不易操作。其二,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會阻礙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使用權市場的構造。為逐步實現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土地市場中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交易的改革目的,有序建立起統一的稅收制度與服務監管制度,逐步賦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相同權利義務,最終達成二者之間的權責一致,就應確保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所應繳納的稅金不應囿于土地調節金,理應通過契稅、增值稅等方式進行征收,從而與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規則保持一致。
2.對于內部分配,亦無法律規定。《辦法》第十六條表明,集體經濟組織以現金形式取得土地增值收益,按照壯大集體經濟組織原則留足集體后,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公平分配。然而,這也存在一定問題:一是僅以現金形式在內部進行分配是片面的。若是將入市交易的土地使用權進行價值評估繼而資產證券化后在資本市場進行交易,或將使用權作價入股,則不一定會及時產生現金流,那么面對此階段現金流的斷裂,應如何應對?二是收益的分配對象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成員資格的確認存在問題。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制度加劇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不穩定性與流動性,收益分配應如何在新舊成員的遷入遷出中抉擇亦存在困難。三是對于留存于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缺乏監管機制。壯大集體經濟組織會涉及該部分收益用在哪兒以及怎么用的問題,但目前并無相關法律規定。
三、解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法律問題的建議
新法為了兼顧改革的穩定性,并未將本文中所提及的法律問題進行詳細規定。因此,本文將就其存在的法律問題提出針對性建議。
(一)確定入市所有權主體的成員資格,保障合法權益
入市實施主體在形式上存在多元化的情況,但入市的決策與表決仍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執行。鑒于目前新法中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制度的加持,組織成員遷入與遷出的流動性強,故成員資格的認定是確定入市實施主體的關鍵。《土地承包法》以戶籍為標準認定成員資格,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如:組織內成員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應盡的義務與責任;除集體土地外是否還有其他生活保障來源;因出生收養、結婚離婚、外出務工和進城落戶帶來的成員身份的流動性和入市決策人數的不確定性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法和公序良俗等。在明確成員資格的確定規則后,方可從實質上確定入市主體,保障復合型成員的權利,從根源上弱化土地入市交易協商成本和存在的風險。若是考慮到日后成員的流動性,在成員已登記在冊的集體經濟組織,可仿照公司法人的組織形式進行落實,將其內在成員資格與入市決策的表決形式予以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比例化,并增設入市決策的公開聽證制度,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知情權與參與權,同時引入入市決策異議的司法救濟制度,明確規定與入市利益相關的利害關系人對入市決策的表決程序和擬定收益持有異議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訴訟期間,停止入市交易進行,但這些必須在相應的法律制度下運行。

(二)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進行法律定性
新法雖然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進行了細致的規定,但其缺乏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屬性進行法律定性的法理。2019年4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草案二次審議稿)》中也未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進行法律制度上的回應。這表明在《物權法》與《土地管理法》之間沒有形成規則明晰、公私兼備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民法典物權編》理應在后續編撰中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法律地位作出具體規定,即:建設用地使用權是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與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上位概念;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是宅基地使用權、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使用權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上位概念,并且用于入市的集體建設用地僅限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基于以上規定,才可使物權法意義上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與新法中的相關規定趨于一致,使其得到物權法的支撐,從而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具備法定權利的完整性。

(三)明確集體性經營建設用地入市后的收益分配機制
在入市收益的外部分配上,由于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的征收比例不明晰,有必要構建城鄉統一的土地價格管制制度與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城鄉統一的土地價格管制制度應包含對不同區位地塊的差異化評價制度、地價公開公示制度、地價申報制度、地價宏觀調控制度以及地價監管制度。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合法入市后,必然會擴大增值收益調節金的資金池,政府理應對建設用地地價進行統一的行政管理,使其在法律確認的基礎上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價格管控制度。此外,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的征收并非長久之計,應以稅收的方式調整入市收益,從而有利于實現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同時,這樣的方式也使入市收益在政府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逐步實現公開化、透明化,從而極大地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整體利益,進而惠及組織內部的成員。在2019年7月財政部公布的《土地增值稅法(征求意見稿)》中,擬將出讓、轉讓集體土地使用權、地上的建筑物以及附著物納入征稅范圍。若是后續《土地增值稅法》的修訂過程中能吸收此建議,則將進一步規范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增值收益征收方式,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這也有利于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建立。
在入市收益的內部上,在已經確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前提下,收益應落實到每一位內部成員。對歸于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可納入專戶管理,并在組織內部設立監督小組,使監督小組對全體內部成員負責。在因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抵押和融資而活躍在金融市場的情形下,應將其收益的分配方式突破現金的給付。集體經濟組織可在其內部組建或者委托保理公司,將土地入市收益所產生的應付賬款債權進行資產證券化交易,從而使其轉變為現金流,分配給組織內成員。當然,這將進一步考驗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能力。
(四)制定《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管理法》以及相關細則
制定《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管理法》以及相關細則也較為重要。可以參照與新法同期修訂的用于規范城市房地產管理與保障國有土地利益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在后續立法及其相關細則中,規定入市確權登記管理、入市分配、入市期限、入市監管、入市中介機構、非法入市的法律責任等內容,并進一步授權各地區政府在不與上位法相抵觸的原則下,制定與入市相關的行政法規、規章以及規范性文件,切實解決本文中提及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所面臨的法律問題。只有建立起規范的入市交易系統,才能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形成有效的規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