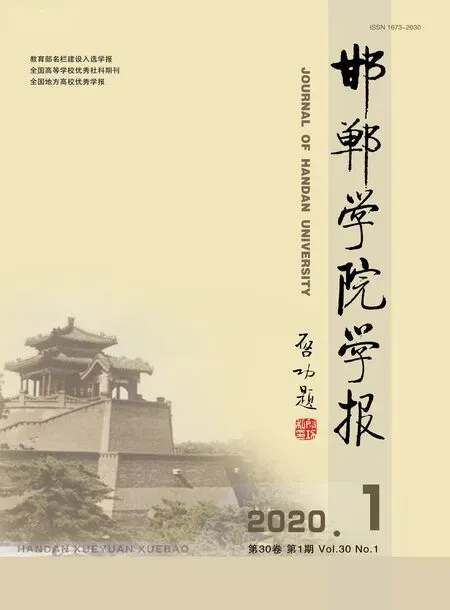蒼頡、沮頌造字作書真實性的文化人類學考察
付希亮
(內蒙古師范大學 文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先秦兩漢時期,蒼頡造字傳說盛極一時。《荀子·解蔽》記載:“好書者眾矣,而蒼頡獨傳者,壹也。”[1]401《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記載:“蒼頡作書。”[2]1061《韓非子·五蠹》記載:“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謂之私,背私謂之公。”[3]450《鹖冠子·近迭》記載:“蒼頡作法,書從甲子。”[4]130-13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容成氏》記載:“盧氏、赫胥氏、喬結氏、蒼頡氏、軒轅氏、神農氏、椲乙氏、壚蹕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其德酋清,而上愛下,而一其志,而寢其兵,而官其才。”[5]250-251除了蒼頡外,沮頌也是黃帝時代的史官,參與了作書造字工作。《世本八種》記載:“沮頌、蒼頡作書,并黃帝時史官。”[6]356
漢代關于蒼頡造字傳說的記載更多。甘肅玉門花海農場漢代邊塞遺址發現的《蒼頡篇》殘簡記載:“蒼頡作書,以教后嗣。”[7]29《淮南子·本經訓》記載:“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8]571《論衡·感虛篇》記載:“傳書言:‘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9]249《論衡·譏日篇》記載:“又學書(者)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9]995-996《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并明。”[10]314這些記載說明蒼頡造字之說由來已久。蒼頡造字之事是真有其事,還是出于古人的虛構,就成了我們進行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不可回避的的問題。
進入20世紀之后,中國學界對蒼頡造字傳說提出了質疑。高明先生《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中說:“蒼頡造字更是一種傳說,無任何科學根據。”[11]26呂思勉先生《中國文字變遷考》中說:“伏羲造字之說,鑿空附會如此,故后人多不之信,而信文字始于黃帝時,蒼頡為黃帝史之說。然夷考其實,則鑿空附會,亦與伏羲造字之說同。”[12]67郭沫若先生《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中說:“文字是語言的表像。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稱,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它決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13]59
蒼頡造字傳說在先秦那么流行,必有其真實的成份。姜亮夫先生在《古文字學》中對此傳說提出了解釋:“漢文字源始不可知。想來最早時期,必定或體很多,字形很亂。到了某個時代,有一人(應當是某一族的人)來統一它,這一統一使天下大便。這個族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蒼頡族。這應該是漢字流傳的一段史影。從理論上講,也應有這么一回事。”[14]15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中說:“原始漢字在原始社會開始出現的時候,是勞動人民的創造……進入階級社會之后,在漢字由原始文字發展成為完整體系的過程里,起主要作用的大概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巫史一類人了……歷史悠久的蒼頡造字的傳說,也許并沒有真實的歷史根據。但是相傳是黃帝的史官,把史官跟造字聯系在一起,還是有一些道理的。”[15]27-28
姜、裘二先生的解釋很合理,但要證明蒼頡造字之事的真實性,光有理論上的合理性和傳世文獻的記載還不夠,還需要借助新材料予以印證。就像居里夫人從瀝青中發現鈾元素一樣,筆者幸運的是從以往常被人忽略的傳世文獻《山海經》中發現了其對蒼頡的記載。《山海經》就成了可以證明其它傳世文獻可信性和蒼頡、沮頌造字作書事件真實性的新材料。
一、《山海經》記載,蒼頡、沮頌兩族商初居住在河洛地區
本文所用史料,主要是《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典籍,這些典籍中國傳統史學稱之為小說。清代紀昀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將《山海經》歸入小說家類。其斷語曰:“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玄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并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16]727
中國傳統史學上所說的“小說”,是稗官及閭里平民所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之言,與來自西方文學上重敘事、重虛構的“小說”截然有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類一》談到了“小說”的類別和價值:“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16]714可見,中國傳統史學把“小說”當作“廣見聞、資考證”的“雜史”。《山海經》《穆天子傳》是寶貴的先秦文獻,絕非西方文學意義上的小說,應該成為歷史研究材料。20世紀歷史研究者多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把《山海經》《穆天子傳》歸于西方文學意義上的小說并把它們排除在史料之外,從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被前人遺棄的材料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用文化人類學的圖騰理論進行解讀,分析蒼頡沮頌二族的圖騰、婚姻和血緣關系,從而弄清他們在中國上古歷史上的貢獻。
《山海經》的前身《山海圖》完成于商初,[17]當時中國的文字系統還不成熟,文字少而生活中詞匯多,故《山海圖》上所標注的文字多用“同音假借”字代替。秦代巫祝歷史知識不夠豐富,他們在將《山海圖》“翻譯”成《山海經》時,多誤譯《山海圖》上的文字信息。如《山海圖》上有熊山、熊穴、熊神,圖上標著“夏”“啟”二字,秦朝巫祝就把它翻譯成“熊穴夏天開啟,冬天關閉”。[17]類似的情況有很多。筆者解讀《山海經》,有時需要求助于唐作藩先生的《古音手冊》,以尋找《山海經》中的文字與歷史人名在讀音上的聯系。下面開始從《山海經》中尋找蒼頡、沮頌二族存在的歷史信息。
《山海經·中次四經》的記載,顯露出蒼頡族存在的跡象。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其名曰?。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瓀石。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厘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蒐。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獸焉,名曰,其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鬛。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谷,多涂石,其上多?琈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羬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可以毒魚。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苧,可以毒魚。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其獸多?牛、羬羊,鳥多赤鷩。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歡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間也。[18]56-58
蒼頡氏族居住在厘山。其根據是:
第二,此列山在伊水、洛水之間,并有玄扈之水,正與蒼頡在玄扈水相符合。《水經注》記載:“《河圖玉版》曰:蒼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19]363《中次四經》中的歡舉山之“歡舉”,讀音為“元曉平”和“魚見上”,玄扈水之“玄扈”讀音為“真匣平”和“魚匣上”,“蒼頡”讀音為“陽清平”和“質匣入”,三詞讀音相近。[20]歡舉山與玄扈水是蒼頡活動之地。《春秋元命苞》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蒼頡之姓“侯岡”逆讀為“岡侯”,其讀音為“陽見平”和“侯匣平”,與其名字“蒼頡”讀音相近。“岡侯”“歡舉”“玄扈”不過都是“蒼頡”之名近讀而已。
第三,此列山還有柄山,其山名正與《論衡·譏日篇》所記蒼頡“諱丙”相合。
第四,發源于柄山的河流名叫“滔雕水”,“滔雕”二字的讀音“幽透平”和“幽端平”與蒼頡的外貌“龍顏侈哆”之“侈哆”讀音“歌昌上”和“歌端平”相近。
第五,《孝經援神契》言“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21]506,奎星為大豬之神。[22]1305《春秋孔演圖》言“蒼頡四目,是謂并明”[10]314,此處之“并明”當是“并封”之誤。明、封二字讀音相近。并封是豬。《山海經·海外西經》載:“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厘山之獸“其毛如彘鬛”,帶有豬的特征。
第六,蒼頡“四目靈光”顯示其與大儺儀式中的方相氏的聯系。蒼頡“四目靈光”即方相氏的“黃金四目”。《周禮·夏官司馬》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中次四經》扶豬山、厘山所出現的“瓀石”“獳犬”,其字讀音為“侯日平”,與“儺”讀音“歌泥平”相近,也顯示出蒼頡部落與大儺的聯系。
總之,古代文獻所記載的蒼頡的諸多文化特征都可以與《中次四經》的記載相印證,可見《中次四經》所記載蒼獸就是蒼頡部落的圖騰。
厘山記載證明蒼頡族的圖騰是青色兕牛。武王伐紂時,蒼兕部落站在周武王一方,姜太公渡黃河時曾向蒼兕族發號施令。《史記·齊世家》記載:“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遂至盟津。”[22]1479《論衡·是應篇》載:“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蒼兕!蒼兕!’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則復觟?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夫觟?之觸罪人,猶蒼兕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9]762-763《淮南子·覽冥訓》載:“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于是風濟而波罷。”[8]445-446武王從孟津渡過黃河,孟津之北有陽樊,陽人所居,故有陽侯之波。周人的聯盟中有以蒼兕為圖騰的蒼頡族,故姜太公渡河以蒼兕為前鋒。周人勝利后,將蒼頡族分封在陽樊,其地在今河南濟源市一帶。
春秋時代,陽樊還有蒼頡族的后代居住的跡象。《國語·晉語四》記載:“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23]375可見,陽樊是陽人居住之地。倉葛之“葛”讀音為“月見入”,蒼頡之“頡”為“質匣入”,二字讀音相近。倉葛所用的名字沿自祖先蒼頡。①在氏族制度還有一定殘余的社會中,每個氏族都有一套個人的名字,并世代沿襲。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易洛魁人的氏族》中說:“印第安人的個人名字通常卻能表示出個人所屬之氏族,以別于同部落中屬其他氏族的個人。一般習慣,每一個氏族都有一套個人名字,這是該氏族的特殊財產,因此,同一部落內的其他氏族不得使用這些名字……當一個人被選舉為首領或酋帥時,就要廢掉原有的名字,在就職時另外授以新名……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現在所使用的名字大多是很古老的名字,它們在各氏族中由遠古流傳下來,沿用至今。”《古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76-77頁。宋代鄭樵《通志·氏族略第四》記載:“倉氏,黃帝史官倉頡之后。或言古有世掌倉庾者,各以為氏。春秋時周有倉葛。”他們被分封在洛陽附近,與周王室通婚,并世代保存夏商之嗣典,這正與蒼頡為史造字的身份相符合。
可見,從商初到春秋,蒼頡族居住在河洛一帶。河洛一帶,《山海經·中次二經》還居住著與蒼頡齊名的沮頌族。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輝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鹖。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蠪蚔,食之不瞇。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18]54-55
《中次二經》之山位于今伊水與洛水之間。《水經注》記載:“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酈道元注:“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19]373-374這里說的蔓渠山、陽山、鮮山、伊水、陽水、鮮水正與《中次二經》記載相符合,說明《中次二經》之山在伊洛兩河之間。
與蒼頡齊名的沮頌族居住在陽山和鮮山一帶。沮頌是火神祝融的異稱。“沮頌”讀音為“魚從上”和“東邪平”,“祝融”讀音為“覺章入”和“冬喻平”,二詞讀音相近。沮頌也以造書造字著稱。《世本八種》記載:“沮頌蒼頡作書,并黃帝時史官。”[6]35620世紀50年代在沂南城西北寨村發現的漢代畫像石墓中南壁東段畫像石畫的就是相對而坐的蒼頡與沮頌。①曾昭燏等:《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第22-23頁,圖版52。作者解說詞是:“上格是蒼頡造字的故事。左一人四目,披發,長須,衣獸皮,坐在一塊獸皮上,此獸皮鋪在一株開著花朵的大樹下,下面有榜,題曰‘蒼頡’。蒼頡右手持著有柄的、末端帶柔軟物的東西(大致表示筆),左手張開五指,正與對面一人交談。對面的人也披發,衣著和坐著的獸皮同蒼頡的一樣,也坐在一株開花的樹下,右手持著一棵小樹,作聽蒼頡說話的姿勢。這人眉骨突起,令人聯想到‘中國猿人’的樣子。下有榜,未刻字。這人大概是沮誦。”
陽山之化蛇包含蛇、豺、鳥三個圖騰,相鄰鮮山之鳴蛇包含蛇和鳥兩個圖騰,也就是說,此二山有三個氏族,其圖騰是蛇、豺、鳥。可能因為蛇圖騰氏族名聲大、政治地位高,所以二山居住氏族都以蛇為總名。此蛇為祝融族的圖騰。根據是:
第一,祝融為火神,此山為陽山,且鮮山之鳴鳥現則“其邑大旱”,都與太陽有關,火神與太陽正相適應。
第二,祝融之父耆童的形象為蛇,且“聲如鐘磬”,與鮮山鳴蛇“其音如磬”相合。祝融黎之父為耆童。《史記·楚世家》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后,復居火正,為祝融。”[22]1689此處“卷章”為“耆童”之訛誤,為祝融黎的祖先。黎因為辦事不力,被高辛氏帝嚳誅殺,帝嚳命黎之弟吳回為祝融。《山海經·西山經》載:“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其下多積蛇。”[18]30
第三,祝融黎之弟吳回又名康回,本是共工。堯評價共工“靜言庸違”,[24]40“庸違”即“庸回”“康回”,暗含了吳回的名字。共工長于治水,“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25]1361,故被視為水神。吳回為水神,正與化蛇現則“其邑大水”相符合。由此可知,此列山居住的是祝融之族,也就是沮頌之族。
《中次二經》之山所出之水注于伊水,《中次四經》之山所出之水注于洛水,說明這兩列山都在伊水和洛水之間。《中次二經》居住著祝融族,《中次四經》居住著蒼頡族,正與中國造字造書祖師為蒼頡沮頌相符合,這說明我國古代蒼頡沮頌造字的傳說絕非空穴來風。
二、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證明,五帝和夏代中國存在漢字文獻
考察蒼頡、沮頌的貢獻,不能不先考察中國漢字起源問題。中國漢字起源的時間,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仰韶和大汶口時代遺址出土的陶文、刻劃符號都是文字,中國文字起源距今至少五六千年。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漢字究竟起源于何時呢?我認為,這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遺址距今的年代為指標。……要之,半坡遺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認為,這是就是漢字發展的歷史。”(《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10卷,第60-61頁。)隨著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發展,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帶有刻劃符號的器物也越來越多,歷史越來越悠久,中國文字的源頭會越追越遠。但這種脫離社會發展階段的問題思考方式是錯誤的。
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說:“關于漢字的起源應該這樣提問題: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于何時?結束于何時?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原始漢字的出現大概不會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隨著夏王朝的建立,我國正式進入階級社會。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即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漢字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夏商之際(約公元前十七世紀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15]22-27人類在山巖、器物上刻劃某些符號或圖畫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及新石器初期,但那些符號和圖畫還不屬于記錄語言的成體系的文字,人類能記錄語言的成體系的文字只能形成于社會組織較為發達、矛盾較為復雜階段,即人類社會由原始時代發展到文明時代的關節點上。當中國社會出現超越于部落聯盟之上的更高級的政治組織以后,該組織就會安排專門人員對各部落自然產生的原始刻劃符號進行統一搜集、整理,形成一套較為完備的文字系統,以表達其語言。此時的系統的刻劃符號才算是成熟文字。
中國成熟文字系統創立于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時期,歷史學上的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說的五帝時代。黃帝委派沮頌、蒼頡兩族專門負責刻劃符號的統一工作。他們整理出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之后,其后嗣不斷地補充增添新的漢字,大約到商代中期才發展成為足以完全表達口語的的文字體系。由此反推,龍山時期和夏代存在的文字,應該有與殷墟文字屬于同一體系者。①中國最初的文明是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載的文明。據《史記》記載,黃帝在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中戰勝了蚩尤和炎帝,分食蚩尤之醢。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正亂》(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第67頁,從而建立其一個龐大的、暴力政權,這標志著中國由此進入此文明時代。這一組織成立之后,日益繁多的部落之間的糾紛、政權與外部其他部落的沖突必然要求該政權制作一套較為完備的文字符號系統。此體系經歷了從黃帝到舜、從夏啟到桀、從成湯到盤庚,最后發展成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殷墟文字體系。從龍山文化晚期的黃帝到成湯代夏桀為天子大約經歷了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中國的文明沒有中斷,文字體系的發展自然也不會中斷。在這過程中漢字逐漸增多,圖畫性逐漸削弱,用法逐漸復雜。由此推知,龍山時代、夏代文字與殷墟文字應該屬于同一體系,我們可以用殷墟文字體系來解讀龍山文化晚期、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部分文字材料。
陶寺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扁壺上所描畫的兩個文字,與后來的殷墟文字屬于同一體系。200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訊》一期刊發了李健民先生的文章《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將扁壺上的一個字釋為“文”。2003年11月28日《中國文物報》上刊登何駑先生的文章《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將扁壺背面原來被看作兩個符號的朱書視為一個字“堯”。葛英會先生在《破譯帝堯名號,推進文明探源》一文中,對何駑先生的觀點進行補充論證。[26]141-146由此看來,龍山文化時期,在堯舜禹時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與商代甲骨文系統相一致的漢字。
清華簡《保訓篇》記載了文王臨終的談話,其中提到了“舜求中”“得中”和商部落首領上甲微“假中于河”“歸中于河”之事:“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遠邇,乃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授厥緒。嗚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乃歸中于河。微志弗忘,傳貽子孫,至于成湯,祗服不懈,用受大命。”[27]143
關于“中”是什么,學術界有爭論。黃懷信先生認為它是法規和前代流傳下來的法律案例。《逸周書匯校集注·嘗麥解》記載:“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策執策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黃先生注釋說:
此云“宰承王中”,又云“執策從中,宰坐尊中”,又云“大正坐,舉書及中降中并謂獄訟成要之簿籍也”,《周禮·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鄭注云:“罪中所定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鄭注云“士師受獄訟之成,此中即彼獄訟之中,登于天府者也。”……刑書如今之律刑,中如今之成。案二者蓋同,藏于太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并受而藏之。)此篇所記即前年登于天府之中,出而陳之,以與刑書相鉤考也。[28]769-777
可見,“中”是先王禮法之典和法律案例。舜所求所得、上甲微向河伯所借、所還之“中”,指的是五帝時代所制定的法律文書。舜按照先王之典來處理部落中的事務,部眾心悅誠服。上甲微得到了先王之典,他拿著“中”去跟有易氏綿臣打官司,綿臣認罪受誅。清華簡《保訓篇》的記載證明,五帝時代中國已有較為完備的文字體系和文獻記錄。
《穆天子傳》顯示出黃帝時期的文獻用彩色顏料書寫于玉石之上,保存在名山的洞穴中,由專門的部落負責看管。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旹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之珤,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珤,賜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周觀天子之寶器,曰:天子之寶,玉果、璇珠、燭銀、黃金之膏……柏夭既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土。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現在很多人把《穆天子傳》當作小說來讀,認為此書出自戰國人虛構,這是對《穆天子傳》的誤解。《穆天子傳》記載了周穆王與西方各部落交往之事,并沒有什么神話成分。這本書對周穆王的行程、日期記載那么詳細,說明它屬于帝王起居注,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①關于《穆天子傳》的性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三》說:“《穆天子傳》雖編次年月,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為信史。”(第1285頁)《小說家類三》載:“此書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為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為近實。”其按語又曰:“《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徒以編年紀月,敘述西游之事,體近乎起居注耳,實則恍惚無征,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為古書而存之可也,以為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說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為嫌也。”(第3625頁)四庫館臣對《穆天子傳》的看法有三點:第一,此書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為近實,并沒有什么奇幻變怪的記載;第二,此書恍惚無征,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為信史;第三,前人都把此書歸入“起居注類”,從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也就是說,四庫館臣之所以將它歸入小說(雜史)類,是因為其體裁歸類困難的緣故。因為此書是敘事體,有頭有尾,不像皇帝近臣每天所記的短小瑣碎的起居注。可見,他們將此書歸于小說(雜史)主要并不是因為它“恍惚無征”。當然考察穆天子的行程是一門難度很高的學問,當時還沒有研究人研究穆天子的行程路線。四庫館臣所說的“恍惚無征”大概就是指這個。事實上,《穆天子傳》沒有神怪成分,因為連西王母都沒有一點神仙色彩。因此四庫館臣對此書的看法值得重新思考。穆天子巡行天下,《左傳》中也提到此事,說明并非虛言。穆天子西行,歷時一年多,史官有必要、有可能把此事詳細記錄下來。我們不能把它看作是魏國史官給死去的魏襄王寫的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娛樂小說。隋唐以來的史官把此書歸為“帝王起居注”,比四庫館臣歸為小說(雜史)要合理得多。
從《穆天子傳》的記載可以看出,舂山有黃帝留下來的寶物,這些寶物的詳細情況都記載在河伯族所繪圖上。昆侖山有黃帝之宮,舂山有專門看守寶物的部落。群玉山是容成氏負責看守之山,是先王策府之所在。先王的策府是保存先王典冊的庫府。郭璞注釋:“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河宗部落有記錄黃帝寶物的圖冊,不經河伯族的祈求,不經黃帝之神的同意,連周穆王也不能觀看。這也是上甲微要向河伯借“中”的原因。
由此可知,在夏代之前的五帝時期,華夏族已經發明了文字,并且有了典冊文獻。這些文獻,大概是史官用朱、碧、黑等顏色的礦石磨粉書寫在美玉之上。周穆王“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當是為書寫而取。春秋時代各國還保存著將文字書寫在玉石上以祭告神靈的習慣。例如侯馬盟書,就是春秋末年趙氏用墨或朱砂書寫在玉版上,在昭告天地神祇帝之后,把玉版埋到地下。這種書寫方式帶有神圣的性質,與遠古文獻記載形式有關。我國古代文獻中所說的“河圖洛書”當也是這類性質的文獻。
孫作云先生曾談到“河圖”“洛書”:“那時候的圖書當然不是竹簡木板的圖書,也不會是甲骨上所刻的圖書(如殷墟甲骨之所見者),并且在那時候也決不會有字的。但我想這圖是可能有的,這圖就是研究圖騰藝術史的人所說的‘圖騰圖畫’。圖畫的東西可能是石板,或木片。澳洲阿龍泰(Alunta)人有用木片或磨石制成卵形或橢圓形物,小者長約一英尺,大者五六尺不等,其上概作動物及代表其神話傳說的紋樣。這種神物叫做Churinga 或Tiurunga。阿龍泰人相信此物是他們圖騰祖先的寄托之所,故常將其放置秘密的地方,除長老外,部族成員絕對不知其所在。婦女及未入社的青年,也不許接觸。埋藏這種東西的地方,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地,稱之為Ertnatulunga。我想原始的河圖洛書一定是這一類關于圖騰信仰的神秘的玩藝兒。[29]58孫作云先生的判斷正與《穆天子傳》記載相合。群玉山的策府,大約類似于阿龍泰人的Ertnatulunga,是一個神圣的用來收藏黃帝族圖騰和文獻的地方。策府的典策,應該是玉石,不會是木片,因為木片不能長期保存。《尚書·顧命》中提到了河圖:“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24]502-503這些都是遠古留下來的寶玉,陳寶是一塊肝臟形的玉,弘璧是直徑較大的玉璧,琬琰是與女和月母族和岷山氏女琬琰有關的寶玉,大訓是記載著先王訓言的寶玉,天球可能是畫著天文圖的球形玉,而河圖當是河伯部落所制作的繪有黃帝族圖騰、神圣之言、黃河流域地圖的寶玉。由此可見,在夏代之前,中國已有原始文字系統和文獻。
雖然現在二里頭文化遺址還沒有發掘出一定數量的可以與甲骨文和金文相聯系的符號,但不能證明夏代還沒有文字系統和文獻。《墨子·非樂上》記載:“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30]383武觀是夏啟之子,《武觀之書》記載的武觀部落對夏啟罪惡的聲討,證明夏朝初年已有文獻流傳下來。這些材料說明,夏代的確有文獻記載,并且“武觀之書”還流傳到了戰國時代。
西晉時期出土于魏襄王墳墓中的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對中國歷史的記載從夏朝初年開始。《晉書·束皙列傳》記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31]1432《國語》記載:“陽人有夏、商之嗣典。”[23]375這些材料說明,夏代是有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和較為豐富的文獻典籍存在的。
結 語
較為規范的文字系統的出現是文明產生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們要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就不能不先研究先秦文獻中所記載的蒼頡、沮頌造字作書問題。由于史料不足,當前要解決這一問題非常困難。20世紀以來所發現的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竹簡帛書等文字材料雖多,但還沒有發現關于蒼頡、沮頌造字的記錄,可以直接為蒼頡、沮頌造字作證的考古材料還不知何時面世。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另辟蹊徑。
本文從文化人類學圖騰理論出發,對《山海經·中山經》中的圖騰進行分析,發現蒼頡、沮頌氏族有在河洛地區居住的歷史痕跡。《山海經》的前身《山海圖》完成于商朝初年。《山海經》的記載證明蒼頡、沮頌氏族在商初還居住在河洛地區,傳世文獻對二族造字的記載并非出自幻想。
從陶寺文化遺址出土的扁壺上的文字,清華簡《保訓篇》所記載的舜求“中”和上甲微借“中”的記載看,從《墨子》上所記載的“武觀之書”、《穆天子傳》所記載的黃帝“策府”、西晉時期所出土于魏襄王墳墓的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看,五帝時代和夏代,中國是有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和較為豐富的文獻典籍的。這說明五帝時代歷史上發生過蒼頡、沮頌二族從各部落搜集、整理、規范刻劃符號以記錄語言之事,先秦文獻中說記載的蒼頡、沮頌造字、作書的記載是有其歷史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