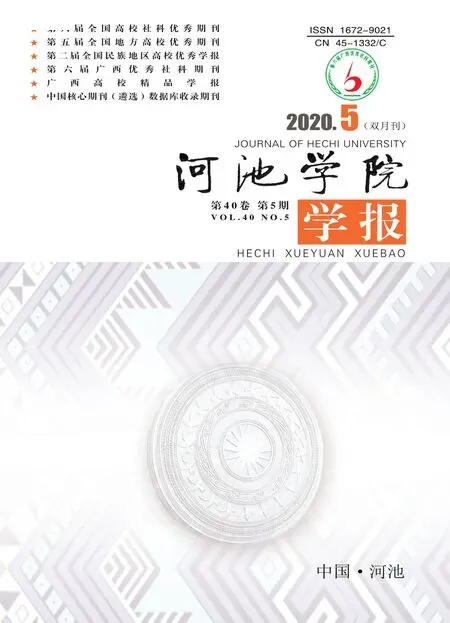傳統節日再造視角下民族體育的現代傳承與價值創新
——以廣西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仫佬族依飯節為例
梁日忠
(河池學院 體育學院,廣西 河池 546300)
民族傳統節日體現著一個族群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其形成過程是一個族群傳統文化的積淀過程,在族群構建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中西文化的交融以及工業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人們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也逐漸改變,在這一現代化過程中,人的傳統意識日漸淡化,民族傳統節日傳承式微。為了繁榮優秀傳統文化,推動我國節日文化建設,國家提出《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1],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全面評價和高度贊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因此,在社會轉型及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怎樣保護傳統節日文化并充分發揮節日文化在現代社會建設中的作用已成為政府和學界面臨的重要的現實問題和迫切的理論議題。仫佬族依飯節是世代傳承的以多神崇拜為特征的宗族祭祀儀式,當依飯節“傳統”遭遇“現代”,文化變遷與儀式重構成為必然。地方政府介入依飯節始于20世紀80年代,自此依飯節被注入新的時代內涵,開啟了從傳統村寨宗族祭祀活動到仫佬族民族節日盛典的再造。從單純描述民俗事項轉到闡析民俗的“國家在場”,可以為文化傳承研究提供新的解釋框架。有基于此,筆者多次對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羅城”)仫佬族依飯節進行田野考察,描述依飯節在政府主導下所開展的文化實踐,挖掘依飯節這一傳統節日文化實踐在當代民族傳統體育傳承乃至文化生產及其價值構建中的意義,以為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和復興工程提供借鑒。
一、 仫佬族傳統節日再造與仫佬族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承與創新
(一)從民間敘事的“依飯節”到國家在場的“依飯文化節”
“傳統是可以被發明的,而非流傳不變”[2]1-2,傳統的創新就是促使傳統走向現代或更加現代的新現代的變遷過程,“傳統”也因為“現代”產生意義”[3]。仫佬族是嶺南土著民族,依飯節是民族特色濃郁的仫佬族傳統節日,作為仫佬族傳統民間儀式,已約有 500 多年的歷史[4]22-23。依飯節原為地方漢族因崇拜“依飯公爺”而舉行的宗族還愿儀式,其在羅城境內傳承過程中受民間宗教影響,逐漸演變為以多神崇拜為特征的仫佬族祭祀習俗。進入20世紀80年代,依飯節“傳統”遭遇“現代”,儀式重構與文化變遷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
改革開放后地方政府介入傳統節日的文化重建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2年,羅城東門鎮中石村大銀屯在村委組織下舉辦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依飯節,作為節日重要場所的“祠堂”得以重建。在政府力量的持續推動下, 依飯節在1998年、2003年得以重辦,由此推動了具有家族特征的“依飯節”在更多村落的復興。2006年,仫佬族依飯節成功進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依飯節至此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名正言順”地成為地方政府可資利用的傳統文化符號和資源,用以推進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此后,羅城制定詳細的依飯節保護方案,并對“依飯節”的價值重新定位,提出了做強依飯文化,弘揚傳統文化、打造依飯文化品牌,將依飯節打造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級民俗文化旅游品牌的思路。2009年11月28,“中國羅城首屆仫佬族依飯文化節”舉辦,依飯節在內容和形式上有所改進。2013年的“中國羅城第二屆依飯文化節”以弘揚仫佬族民族文化藝術為主題,在整合多種民間文化、摒棄部分封建迷信色彩濃厚的內容的基礎上,簡化了祭神的儀式過程。2017年舉辦的“第三屆依飯文化節”,結合仫佬族旅游發展與脫貧,以“依飯文化旅游節暨扶貧產業招商活動”為主題,通過民俗展演和民俗巡游展示仫佬族依飯文化場景,并與廣西電視臺“開心擂臺·走進羅城”節目組合作開展活動。至此,從傳統的“依飯節”到“依飯文化節”,從傳統村寨宗族祭祀活動到包括仫佬族、漢族等在內的各民族共享的現代民族節日,依飯節實現了從民間敘事到國家在場的文化節日盛典的轉變。依飯節儀式場域的改變,新內涵與意義的賦予,彰顯了政府主導下“依飯節——依飯文化節”文化實踐的當下意義。傳統節日文化在新的文化實踐中迸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成為仫佬族人表達時代情感、傳承和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新舞臺。
依飯文化節日的確立過程,是“國家在場”情境下仫佬族傳統文化的現代重構過程,是政府、民間利益共謀下傳統節日文化創新性發展的社會實踐。除了表達民眾感恩還愿、保壽積福及人丁安泰、五谷豐登的傳統心理訴求,依飯節也成為民族團結和國家認同的文化表征。
(二)仫佬族傳統節日重構拓寬民族體育傳承的文化空間
傳統仫佬族“依飯節”是通過各種身體活動達到與“神靈”交流的敬神、娛神祭祀儀式。在演化進程中,傳統的依飯節儀式逐漸演變為人神共歡的大型群體娛樂性活動,現代節日文化的創新更使其成以娛人為主的文化展演活動。依附于民族節日傳統中的各種民族傳統文化在節日的演變中煥發生機,傳統節日的重構推動了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民族傳統文化則成為節日慶典文化主題從而促進節日的創新再造,這種文化傳承路徑是時代背景下仫佬族對其文化進行調試以適應社會文化變遷的選擇。
仫佬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創造了豐富的民族文化,傳統體育是其中典型的文化形式之一。據不完全統計,羅城自1983年以來挖掘和整理的民族傳統體育就有40多項。總體上看,仫佬族多數傳統體育活動游離于節日之外,雖然得到挖掘和整理但未能如愿開展和傳承,只有舞草龍、搶粽粑、仫佬竹球等少數一直依附于節日的項目在節日復興中得到重視與開展。2007年,在《關于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意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條例》等文件要求下,羅城有關部門根據本縣實際制定民族文化傳承保護工作的實施方案,開始反思仫佬族傳統文化的發展困境,提出以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文化重建思路——由政府統一組織并劃撥專項活動經費,挖掘整理傳統民俗文化,將零散的民俗文化活動融合于節日活動中,使節日文化和民俗文化兩者一體相聯、互為表達、彼此推進。至此,作為仫佬族重要文化樣式的傳統體育文化得以整合到節日活動中。2009年的首屆仫佬族依飯文化節,民族傳統體育成為核心的文化主題,民族特色濃郁的舞草龍、貓獅表演、仫佬族竹球、搶粽粑成為開幕式的表演節目。此后的第二、第三屆“依飯文化節”,民族傳統體育與節日文化進一步整合,兩者相得益彰,形成了民族體育文化與節日文化融合發展的互贏局面。傳承空間的拓寬,使民族傳統體育進入更廣闊的民眾日常生活領域,促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發展多元路徑的形成。
二、節日慶典再造與仫佬族傳統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一)依附節日展演的民族傳統體育傳承發展路徑
現代社會文化大變遷背景下,民族傳統節日傳承的式微屢見不鮮,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國家在場”為顯在特征的傳統文化復興運動,則使仫佬族依飯節以及依附于依飯節而展演的民俗活動煥發生機,仫佬族民族傳統體育即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一者地方政府的介入使依飯文化節的定期舉辦成為慣制,并推動了民間依飯節的勃興,民族傳統體育因節日的定期舉辦提升了展演時間和空間;二者地方政府的介入拓寬了依飯節活動籌資渠道。1982年以前,民間依飯節的舉辦經費一直由村民自籌,其后民間自籌、企業贊助、政府出資等多渠道并舉,保證并增加活動經費,維持了節日活動正常舉辦,參演的單位和觀眾人數大為提高。由于經費來源穩定,依飯文化節規模增大、舉辦數次增加,不少民族體育項目得到了更多的展演機會,在依飯文化節中民族體育與節日相互促進,融合發展,拓寬了文化傳承空間,有力推動了民族體育的傳承與發展。
(二)依附于競賽活動的民族傳統體育傳承與發展路徑
依飯文化節的成功舉辦和確立,使更多的民族體育被整合其中,成為節日慶典中的主要文化表現形式,激發了民眾的民族體育熱情,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民族體育競賽活動。如羅城 “文明杯”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民族特色村寨傳統體育比賽、仫佬族舞草龍大賽等,在首屆依飯文化節后相繼舉辦。比賽涉及全縣各鄉鎮,范圍之廣,參與人數之多前所未有,成為推廣、推動仫佬族傳統體育傳承發展和全民健身運動的重要活動。2015年第二屆仫佬族“文明杯”傳統體育運動會,共有100個隊伍和近1 000位運動員參與氣排球、仫佬竹球、兵乓球、抱球接力、投繡球等競賽項目和表演項目。2017年仫佬族舞草龍大賽, 11個鄉鎮共計32條草龍和300多位運動員參加比賽。值得一提的是,仫佬竹球、搶粽粑、奪龍珠等項目屢次在全國各級各類民族運動會中展演并獲獎,基層民族體育活動的蓬勃開展正推動著個別民族體育項目走向更廣闊的表現舞臺。
(三)依附于學校教育的民族傳統體育傳承與發展路徑
國家大力提倡民族文化進校園,以豐富學校教學內容和促進民族文化傳承,學校體育正成為民族傳統體育傳承的重要途徑,依飯文化節的成功舉辦,激發了仫佬族民眾的民族文化熱情,在羅城出現了民眾積極參與民族文化發展的盛況。在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引導下,民族體育開始進入中小學校園,優秀的仫佬族傳統體育項目被引入學校教育中。在筆者調研的羅城高中、羅城中學和羅城二小等學校,已經結合課外活動和課堂教學推進民族體育進校園,一些仫佬族特色鮮明的體育項目成為學校體育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學校的主要做法:一是讓民族體育融入教學活動,讓竹梆謠、搶粽粑、背簍拋繡球等項目進入課堂教學活動和課間活動;二是讓民族體育融入競技訓練,將具有競技特色的仫佬竹球、奪龍珠等納入學校民族競技項目后備人才培養和輸送基地的訓練項目;三是讓民族體育融入學生課外健身活動,使民族體育成為中小學課程興趣班、課間活動或校運動會項目,成為學生教學、健身活動的重要內容。
三、仫佬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與發展中的現代價值轉換
(一)塑造仫佬族傳統體育文化新內涵,弘揚仫佬族民族精神
在特定的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創造的民族傳統文化,內含著人文思想與道德規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財富。深入挖掘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基本要求。“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5]164。依飯文化慶典的再造,是政府和民間利益共謀下構建仫佬族文化認同和對外宣傳民族文化的標志性事件。節日慶典的再造,有利于傳統文化的本土化傳承,也體現了地方政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挖掘傳統文化當代價值的自覺追求。在此過程中,民族傳統文化與傳統節日緊密聯系、互為表達、彼此推進,在動態的文化變遷過程中創新內涵,在調適中創新和重構價值追求。
舞草龍、搶粽粑、仫佬竹球是典型的仫佬族傳統體育樣式,它們借助依飯節的慶典再造得到創新性傳承并塑造著新的價值范式。在“宣揚依飯文化,打造依飯文化品牌,尋求新時代價值”的發展思路下依飯文化節得以復興,也促進了舞草龍創新性發展。在依飯文化節中,舞草龍在展現龍文化的底蘊的基礎上,宣揚團結協作、勇敢拼搏的仫佬族精神。從承載祈福消災的原始寓意到展現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成為政府借以重建地方精神的重要文化載體。搶粽粑活動則與仫佬族“走坡”民俗結合,在表現豐收之情和祈盼來年風調雨順寓意的同時傳達對甜美愛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既創新了搶粽粑的文化內涵,又強化了活動樂趣,得到民眾普遍認同。仫佬竹球原是依飯節中為推選下一屆主持和操辦人而舉辦的活動,在依飯文化節中已演變為強調勇氣和體現民族團結意識的競賽項目,這使其成為仫佬族民族精神重要的表達方式。節日重構促進了民族體育的傳承創新,重塑了仫佬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價值追求,樹立了仫佬族的文化自信,使民族體育成為弘揚民族精神的文化載體。
(二)創新仫佬族傳統體育價值范式,調適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
在多民族國家,由于族群成員身份的雙重性,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必然產生關聯。族群認同屬于文化性認同,而國家認同除了文化性認同外,還包括政治性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具有差異性并表現出一定的張力。當前學者關于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探討主要圍繞兩者的“矛盾性和同一性”來說明兩者的關系體現為此消彼長的矛盾性與和諧可調適的同一性。看待兩者關系需要辯證的分析,既要正視其矛盾的一面,也不能否認其同一性,不能只強化族群認同或國家認同,要在尊重民族“異質性”的前提通過調適使兩者走向“一體化”[6]。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關系的協調統一是促進中華民族團結的重要途徑。全球化導致文化根性焦慮,傳統文化符號表征建構國家認同便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景觀[7]。民族傳統文化承載了民族發展過程中的全部歷史記憶,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記憶來進行表達并發揮族群凝聚作用,成為族群認同的心理指向。而傳統文化的創新又使傳統文化成為調適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關系的媒介,成為建構國家認同的文化資源。
一方面,節日慶典儀式的再造,強化了仫佬族族群認同。依飯節的儀式再造過程推動了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使歷史記憶有了具體的承載者。使傳統文化在新時期適應新的要求,為文化自信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這種制度化操作的文化建設,使族群的歷史記憶能夠通過儀式中的身體儀式而在族群構建中“通過儀式中的物和行為實現儀式表征”[8]。傳統的仫佬族依飯節是崇拜多神的祭祀儀式,而在復興依飯節即政府主辦的依飯文化節中,多神白馬娘娘成為唯一受到祭拜的主神突顯出來。主辦方有意傳達“依飯文化節是祭祀白馬娘娘的節日”這一觀念,白馬娘娘被表征為依飯節祭祀的共同祖先得到崇拜[9],依飯節中的民族體育活動成為祭拜白馬娘娘的主要文化形式。民族體育獨特的身體儀式與節日儀式的融合,使仫佬族共同祖先記憶不斷被喚起,達成族群成員共祖的族緣感情共識,形成族群集體表象,在非正式制度下作用于族群認同構建,民族體育成為可利用的傳統文化符號用以強化族群認同。
另一方面,仫佬族民族體育的傳承發展成為調適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并使其和諧共存的文化紐帶。節日慶典儀式再造下的傳統體育的繁榮發展,是少數民族文化在“國家在場”情境下的重塑過程,體現了官方對少數民族傳統的尊重和認同,既促進了族群認同,也強化了國家認同意識。2006年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仫佬族依飯節榜上有名,搶粽粑和仫佬竹球2009年被列入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舞草龍2015年進入廣西第三批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標志著這些民族文化及其價值得到了國家層面認可。此外,仫佬族體育文化還積極“走出去”,與其他民族體育文化一道在全國各級各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賽場開展交流、競技,通過民族文化交流形成國家認同符號”[10]。
仫佬族傳統體育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進入國家賽場并與經濟活動有效結合,使民族傳統體育有了實實在在的傳承載體,族群歷史記憶由此得以存續并強化。節日慶典再造——傳統的“復興”是建構現代國家認同的需要,傳統體育成為建構國家認同的重要的文化資源。在節日慶典再造中,民族傳統體育成為政府進行文化建設而征用傳統文化符號,民族傳統體育在新時代產生新的內涵,成為調適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關系的文化紐帶。
三、結語
作為仫佬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依飯節的傳承與發展,在改革開放后民族節日文化日漸式微的大潮中一度舉步維艱。由于政府的介入,使其完成了節日活動內容拓展、儀式過程優化的再造,成為傳統體育與節日文化融合,被賦予新時代文化內涵的現代民族節日。依飯文化節的推出是政府主導下民族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過程,是新舊文化融合實踐典范。這種傳統的“再造”對民族文化傳承、民族文化認同,民族地區民族文化建設的推動乃至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實踐與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