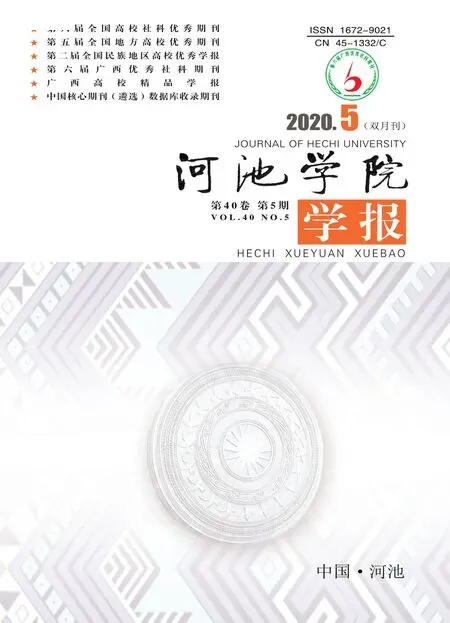用戶思維語境下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平臺功能
安 嵐
(貴州工程應(yīng)用技術(shù)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貴州 畢節(jié) 551700)
縣級融媒體中心經(jīng)過幾年的建設(shè)與發(fā)展已經(jīng)在全國范圍內(nèi)鋪開,并積累了一定的經(jīng)驗,也出現(xiàn)了一些“爆款”。然而,在具體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從業(yè)者還是從傳播者到受眾的傳統(tǒng)線性思維,缺少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和用戶思維。縣級融媒體中心應(yīng)該如何建設(shè)?如何走進(jìn)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提升影響力、傳播力、引導(dǎo)力和公信力?如何更好地服務(wù)群眾?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如此發(fā)達(dá)的今天,以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作為邏輯起點,在用戶思維、平臺思維和大融合思維框架下,發(fā)揮好主流信息傳播、用戶參與內(nèi)容生產(chǎn)、服務(wù)廣大用戶三大平臺功能是解決縣級融媒體中心“最后一公里”不通的有效路徑。
一、主流信息傳播
媒介融合常常被理解為傳統(tǒng)媒介與新媒介的融合,然而,媒介融合今后的一個發(fā)展趨勢是媒介發(fā)揮基礎(chǔ)的連接功能,更有效的連接更多的社會資源,人們所需的資源,成為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基礎(chǔ)工具。這種連接說到底還是在用戶思維指引下創(chuàng)建的平臺功能。更高級別的媒介融合其實是“萬物互聯(lián)”,超越簡單內(nèi)容傳播成為一個社交化的平臺型媒介,媒介與各種資源相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后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就不只是一個信息發(fā)布與傳播的機構(gòu)或媒介,而是一個社交平臺與服務(wù)平臺,是人們生活中的一個日常工具。“融媒三大路徑是重建用戶關(guān)系,響應(yīng)用戶需求,增強用戶粘性。”[1]用戶思維說起來簡單,但要做到其實很難,需要來一次“哥白尼式的思維革命”。傳統(tǒng)媒介時代,或者今天很多縣級融媒體中心是從“我”出發(fā),而用戶思維則是要從用戶角度出發(fā)。什么內(nèi)容?什么服務(wù)是和用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是用戶真正需要的和離不開的。從用戶出發(fā)反推回來,應(yīng)該構(gòu)建一個什么樣的平臺,提供什么樣的服務(wù)?傳播什么樣的內(nèi)容?
主流信息的傳播具體要如何去做呢?從受眾的角度考慮傳播的內(nèi)容和提供服務(wù),用用戶的思維來建設(shè)縣級融媒體中心主流信息傳播平臺。王曉偉在談到縣級融媒體建設(shè)的長興經(jīng)驗時認(rèn)為“不管傳播載體形態(tài)如何演變、如何多元,媒體融合堅持黨媒性質(zhì)不會改變”[2]。長興傳媒集團的全媒體融合發(fā)展無疑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實現(xiàn)了主流信息傳播和商業(yè)盈利的雙豐收。作為新型主流媒體,主流信息、正能量傳播、政治傳播是縣級融媒體中心的首要任務(wù)和初心。那么,縣級融媒體中心如何獲取更多的信息資源,達(dá)到主流信息的最佳傳播效果呢?首先,共享大平臺資源。喻國明教授認(rèn)為“在平臺戰(zhàn)略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主流發(fā)展模式以后,大平臺嵌套小平臺的模式正在成為主流。”[3]作為一個縣級媒體,從資金、技術(shù)到人才各方面都是相對薄弱的,所擁有的資源也很有限,所以長興傳媒集團的經(jīng)驗在多數(shù)縣是難以復(fù)制的。要構(gòu)建一個縣級新型主流媒體還得依靠更大平臺的資源助力,例如湖北廣電的“長江云”就是典型的“大平臺嵌套小平臺”的模式。“長江云”實施“新聞+政務(wù)”將輿論引導(dǎo)和社會治理及新聞信息傳播融為一體,走出了一條縣級融媒體中心依靠大平臺提供政務(wù)服務(wù)的成功之路。其次,信息的本土化。信息的本土化指縣級融媒體傳播的信息以本地為主,這符合新聞價值的“接近性”原理。當(dāng)?shù)匕l(fā)生的事、身邊的人、當(dāng)?shù)爻擎?zhèn)建設(shè)、當(dāng)?shù)卣恼摺?dāng)?shù)厣鐣陌l(fā)展變化等等這些往往會引起用戶的接受欲望和興趣。例如,當(dāng)?shù)卦谛藿ㄒ粭l高鐵,那么從開工的那天開始一直到順利通車,差不多用五六年的時間,對于這條鐵路修建的進(jìn)展?fàn)顩r都會是民眾非常想要關(guān)注和了解的信息。縣級融媒體很好地抓住這些新聞點進(jìn)行實時的報道,就會得到民眾關(guān)注,培養(yǎng)潛在用戶。“成貴高鐵”修建過程中沿線各區(qū)縣融媒體中心對工程進(jìn)展的實時追蹤報道就達(dá)到了這樣的效果。當(dāng)然,本土信息不一定都具有接近性,有時可能是情感的接近性,體驗的接近性等,所以也不能局限于本土化信息的傳播。最后,信息的民生化。縣級融媒體要做到服務(wù)群眾、引導(dǎo)群眾,首先得走進(jìn)群眾,去關(guān)注他們的日常生活,家長里短、衣食住行。老百姓生活當(dāng)中遇到的困難是什么?融媒體要擔(dān)負(fù)起當(dāng)?shù)厣鐣摹安t望哨”的功能,如去關(guān)注低保人員、因病致貧人員等邊緣群體的生活狀況,體現(xiàn)媒體的溫度。
按照拉斯韋爾提出的媒介“環(huán)境監(jiān)測”功能去履行媒介的職能,在縣域范圍內(nèi)融媒體中心一定能發(fā)揮重要作用。融媒體平臺在其中起到一個下情上達(dá)的作用,同時通過政務(wù)服務(wù)平臺,還可以為民眾帶去方便,溝通信息,達(dá)到上情下達(dá)的功能。當(dāng)然,主流信息的傳播不只是媒介傳播者,還包括了用戶參與的內(nèi)容生產(chǎn)與傳播。在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shè)和發(fā)展過程中也會出現(xiàn)一些主流信息傳播弱化,過于商業(yè)化、娛樂化等現(xiàn)象,這些苗頭是應(yīng)重點防范和糾正的。
二、用戶參與內(nèi)容生產(chǎn)
在傳統(tǒng)媒介時代,傳播通常是從傳播者到受眾的線性傳播方式,很少考慮受眾的能動性。按照拉斯韋爾提出的“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說,對誰說?效果怎么樣?”的線性方式思考,常常會過多地考慮傳播者的選擇和偏好,進(jìn)入“我”想怎么做,“我”希望怎么做的固定思維邏輯中去,而忽略了受眾作為服務(wù)對象的用戶體驗和需求。這在今天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逐步走向個性化信息推送的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下,肯定是行不通的。“用戶端,而非傳者端,應(yīng)該成為融合發(fā)展的邏輯起點。”[4]按照卡茨的“使用與滿足”理論,受眾使用媒介不單純是獲取信息,在他們對媒介有需求和興趣的基礎(chǔ)上,要讓他們?nèi)缤褂萌粘5纳罟ぞ咭话闳ナ褂妹浇椋屆浇槌蔀樯a(chǎn)生活、學(xué)習(xí)工作的必需,媒介推送的信息才有被接受的可能。正如許多電視觀眾為了看綜藝節(jié)目、電視劇而同時也接受了電視臺推送的廣告一樣。反觀QQ、微信等社交媒體,當(dāng)初研發(fā)這些產(chǎn)品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做用戶,用戶達(dá)到一定的量了,再慢慢考慮如何盈利的問題。
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人人都是傳播者,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的界限在不斷模糊。在這個語境下,縣級融媒體中心如果單靠那幾十號人來鼓搗,無論在那里如何吶喊“內(nèi)容為王”,還是很難盤活整個縣級融媒體,用戶參與生產(chǎn)內(nèi)容無疑能大大提升傳播內(nèi)容創(chuàng)新和增強融媒體平臺的傳播力。反觀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會發(fā)現(xiàn),上面的大量內(nèi)容其實就是用戶自己在生產(chǎn)。生產(chǎn)者是用戶,消費者還是用戶,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界限也模糊了。在這里,傳統(tǒng)意義上的“傳播者”干什么呢?他們生產(chǎn)和傳播廣告。用戶在打開微信朋友圈的時候,常常會看到一些廣告,那就是他們的“內(nèi)容生產(chǎn)”。縣級融媒體中心如果做到了用戶既是內(nèi)容的生產(chǎn)者也是消費者,那傳統(tǒng)意義上的傳播者干什么呢?也是生產(chǎn)和傳播“廣告”。微博、微信傳播的廣告是為了經(jīng)濟效益,縣級融媒體中心傳播的這種“廣告”其實就是主流信息傳播,縣級融媒體中心的黨媒性質(zhì)決定了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用戶參與內(nèi)容生產(chǎn)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式服務(wù),讓用戶“上癮”而欲罷不能。例如用戶可以自己拍攝制作一些短視頻,或者將自己的所思所感進(jìn)行傳播,很好地滿足他們的表達(dá)欲。用戶參與的內(nèi)容生產(chǎn)和傳播總體來看,分為信息流和意見流兩類。
這里指的信息流就是消息類的信息,在縣級融媒體平臺上開通一個版塊,比如“身邊的新聞”,類似于微信的朋友圈,只是這個朋友圈覆蓋的范圍更廣。如今,很多影響很廣而且充滿正能量的新聞就來自微信朋友圈。貴州省畢節(jié)市七星關(guān)區(qū)融媒體中心就曾經(jīng)發(fā)過這樣一條“老人跌倒了,你扶不扶?看看小學(xué)生怎么做”的新聞,該新聞講述在某城區(qū),一位老人摔倒了,路過的一名小學(xué)生很快過去攙扶,后面再來一名小學(xué)生一起把老人扶起來的事情。這段視頻就是一位商店的店員用自己的手機拍下來發(fā)到微信朋友圈,后來被融媒體中心當(dāng)成新聞進(jìn)行了報道。如今的許多網(wǎng)絡(luò)新聞常常會有微博、微信朋友圈或聊天記錄的截圖,它們其實早已成為新聞傳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
不久的將來,5G技術(shù)商用化的進(jìn)一步推廣,其“兩高兩低”的技術(shù)特征,高速率、高容量、低時延、低能耗,必然帶來一場信息傳播的革命。早期的傳統(tǒng)媒介主要靠書寫進(jìn)行信息傳播,后來有了電視,進(jìn)行視頻的傳播。但是,作為視頻傳播的電視,進(jìn)入門檻是很高的,所以,這時的傳播者其實還是一種精英化的邏輯。直到出現(xiàn)了4G技術(shù),使得視頻的移動傳播成為了可能。于是各種短視頻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微信朋友圈融視、聽、讀為一體的社交媒介傳播也成為了可能。更重要的是,許多不會用電腦的人,甚至識字不多的人,都開始用自己拍的視頻來進(jìn)行表達(dá)和交流。這時,“人人都是傳播者”,“個人生產(chǎn)內(nèi)容”才得以真正實現(xiàn)。到了5G時代,人們交流的主要手段將更進(jìn)一步從書寫轉(zhuǎn)向視頻表達(dá)。喻國明教授認(rèn)為:“中長視頻必然成為5G 時代最主要的社會表達(dá)方式,對傳播領(lǐng)域的影響以及新聞傳播學(xué)的學(xué)科構(gòu)造也會帶來革命性改變。”[5]當(dāng)5G技術(shù)日趨商用化之后,用戶參與生產(chǎn)內(nèi)容必將越來越成為內(nèi)容生產(chǎ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意見流即是用戶表達(dá)意見觀點的內(nèi)容。在縣級融媒體平臺上開辟一個類似論壇的版塊,用戶可以在論壇里就某一話題展開討論,形成一個網(wǎng)絡(luò)虛擬社區(qū)。管理員可以對論壇進(jìn)行管理,比如,推出一些時政方面的熱點話題,以引導(dǎo)大家進(jìn)行討論。這里的意見流還包括對新聞信息的留言評價。通過用戶對信息的評價反饋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是提升縣級融媒體傳播力的最有效途徑。
草根民眾的意見有時更具說服力,在許多輿情發(fā)生時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2014年清華大學(xué)化工系學(xué)生PX詞條保衛(wèi)戰(zhàn)事件,“西藏3·14打砸搶事件”中,中國學(xué)生自己創(chuàng)建的反CNN網(wǎng)站等。縣級融媒體中心通過用戶對一些焦點問題的意見也能很好地起到輿論引導(dǎo)的作用。隨著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一些社會矛盾凸顯,縣域范圍內(nèi)出現(xiàn)輿情的風(fēng)險大大增加。這時,縣級融媒體平臺除了及時推送官方的真相消息,用“議程設(shè)置”策略回應(yīng)公眾訴求,還應(yīng)樹培草根用戶“意見領(lǐng)袖”以引導(dǎo)社會輿論向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因為如今許多網(wǎng)民只信“壞消息”而不信真相,網(wǎng)民的媒介素養(yǎng)也是參差不齊,因此,草根意見領(lǐng)袖有時會起到關(guān)鍵作用。早些年的“甕安事件”,還有近些年的“甘肅永昌女中學(xué)生墜樓事件”以及“獲嘉縣兩幼童墜樓事件”,都起因于未成年人的意外死亡而引發(fā)關(guān)注,謠言不斷。對類似輿情的處理,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及時推送官方發(fā)布的真相的同時,如果有草根意見領(lǐng)袖的參與,輿論的引導(dǎo)將更有效果。
“縣級融媒體中心不再僅僅是縣域的新聞發(fā)布工具,更需要在縣域社會治理與溝通中扮演關(guān)鍵性角色。”[6]草根的民眾作為縣級融媒體中心的用戶是有傳播信息、發(fā)表意見的需求的。同時,他們在發(fā)生輿情時可以幫助引導(dǎo)、撫慰民眾,最終達(dá)到較好的引導(dǎo)輿論的效果。例如,可以在年終,在用戶發(fā)表的好新聞中評選出一些優(yōu)秀作品進(jìn)行獎勵等。也肯定會有少數(shù)用戶發(fā)出的消息和意見是有悖于新聞道德,有悖于主流價值觀傳播的,這時,就需要融媒體中心有專人進(jìn)行監(jiān)管和處理,發(fā)揮好媒介把關(guān)人的作用。
三、服務(wù)廣大用戶
縣級融媒體中心的用戶思維,就是要把融媒體中心建設(shè)成為一個為用戶服務(wù)的平臺型媒介,為用戶服務(wù)就是平臺的宗旨。比如生產(chǎn)手機、汽車要考慮用戶的使用體驗,它們的功能能否滿足使用者的需要一樣。手機、汽車生產(chǎn)隨著社會發(fā)展、用戶需求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和完善,新老更替。縣級融媒體中心也一樣,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的大框架下,如果還用以前傳統(tǒng)媒體的思維方式和表達(dá)、傳播方式去面對受眾,那就只有傳播者們的自娛自樂,而“最后一公里”將成為最遙遠(yuǎn)的距離。縣級融媒體中心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換了馬甲”的傳統(tǒng)媒體,思維方式和運營方式不從根本上改變就還會回到老路上去。
縣級融媒體中心不再只是一個生產(chǎn)和傳播信息的機構(gòu),而是作為連接和整合社會資源、政務(wù)資源和商務(wù)資源的一個平臺型媒介。使其成為一個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便民服務(wù)平臺,以提升平臺的使用率和影響力,客觀上也達(dá)到了由服務(wù)群眾到引導(dǎo)群眾的目的。“新聞+政務(wù)+服務(wù)+電商”的“鄭州模式”,并不一定適用于其他各縣的具體情況,但是這種模式的思路和思維方式是對的。一般說來,縣級融媒體中心服務(wù)用戶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政務(wù)服務(wù)。在縣級政務(wù)中心能辦理的業(yè)務(wù)盡可能地通過縣級融媒體中心進(jìn)行網(wǎng)上辦理,把政務(wù)中心整合進(jìn)縣級融媒體中心來,比如:預(yù)約辦理、政策咨詢、聲明發(fā)布等等。還可以包括投訴報警、車票購買、醫(yī)保繳費、水電費、煤氣費繳費;縣域各醫(yī)院的預(yù)約掛號等業(yè)務(wù)。縣級融媒體中心的政務(wù)服務(wù)這一塊如果做好了,可以達(dá)到行政部門“簡政放權(quán)”的實際效果,減輕了政務(wù)工作的繁重勞動和復(fù)雜程序,也方便了市民,同時還可以成為智慧城市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起的“社區(qū)通”就是提供社區(qū)政務(wù)服務(wù)的一種很好的嘗試。其次,民生服務(wù)。例如:失物招領(lǐng)。常常有許多市民的東西會丟失到出租車上、公交車上,或者公共場所,然后又被其他人撿到,丟東西的人急著想找到東西,撿到東西的人又不知到哪里尋找失主。正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可以建立這么一個平臺,做一個撿到東西和丟東西的人的橋梁和紐帶。每天在融媒體中心平臺上公布有人丟失的物件,切實地為老百姓服務(wù)。其它的民生服務(wù)還有交通信息、天氣預(yù)報等。最后,電商服務(wù)平臺。利用“媒體+電商”服務(wù)平臺幫助老百姓直播帶貨等方式提升融媒體中心的平臺服務(wù)功能,凝聚人氣,增加平臺影響力。例如,重慶市潼南區(qū)融媒體中心在新冠疫情后,依托“潼掌柜”消費扶貧電商平臺直播帶貨的方式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潼掌柜”抖音號和新潼南APP平臺聯(lián)合開展“我來帶貨助您脫貧”電商直播,解決農(nóng)戶銷售難問題。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在2020年3月27日首場‘小龍蝦專場’直播當(dāng)天,潼掌柜平臺共接到350多個訂單,累計賣出1 600多斤,銷售額2萬多元”[7]。同時,“買對不買貴,看我‘潼掌柜’”的直播宣傳語也被當(dāng)?shù)匕傩账熘F渌虡I(yè)類的服務(wù)平臺也可以根據(jù)各縣的實際進(jìn)行開發(fā)創(chuàng)建。如房屋租賃、二手市場、就業(yè)招聘等。
綜上所述, 縣級融媒體中心不能再按照內(nèi)容生產(chǎn)或傳播中心的方向來建設(shè),這不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思維方式。應(yīng)該用一種大融合的思維方式,把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shè)為一個平臺型的媒介。這個媒介兼具主流信息傳播、用戶參與生產(chǎn)內(nèi)容和服務(wù)廣大用戶等綜合功能。這三大功能交叉影響和提升了媒介的影響力、傳播力、引導(dǎo)力和公信力。受眾不但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媒介的長期用戶,還是媒介內(nèi)容的生產(chǎn)者和傳播者。在這個平臺型媒介上形成一個信息傳播到意見反饋的閉環(huán),信息的傳播者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縣級融媒體中心如何從傳統(tǒng)主流媒體那里接過接力棒,成為新型主流媒體并解決好“最后一公里”不通的問題?很重要的一種解決方案就是從用戶出發(fā),積極發(fā)揮其平臺的“三大功能”,把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shè)成為主流輿論陣地、綜合服務(wù)平臺和社區(qū)服務(wù)的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