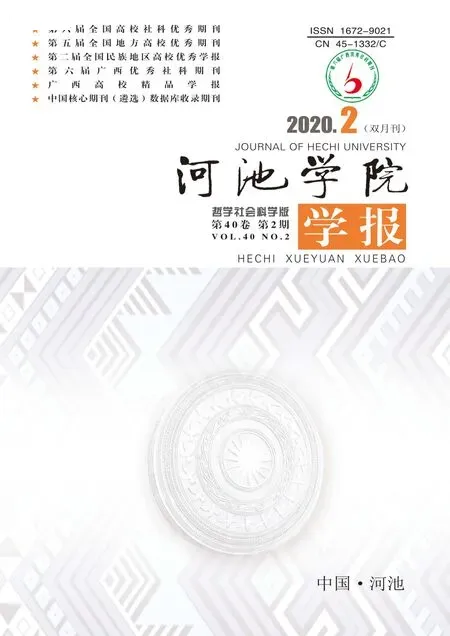文化人類學視域下大涼山彝族漢語詩歌研究
張兵兵
(信陽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
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 Mark Bender) 曾談到,“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詩人的漢語寫作是一種‘民族志詩歌’”[1]。得天獨厚的彝族母語文化熏陶和當代漢語教育背景,使得彝族詩人既能以“在場”的方式,對民族文化有著深層的理解與體驗,又能夠跳出傳統的藩籬,獲得外延性的現代詩歌觀念。詩人們“以對彝族當代文化命運和族群生存現實的深切關注和自覺擔當為使命,以彝族審美傳統與現代漢語新詩語言藝術探索的美學實踐為精神內涵。”[2]深深扎根在大涼山這片時空中,進行著民族傳統文化和詩歌語言秩序的重構。
從文化人類學視域探究大涼山彝族漢語詩歌,是在文本內部研究的基礎上,深入解讀詩歌文本背后傳達的族群文化信息、心理特征和審美內涵。通過對這一詩群的漢語詩歌創作解讀,可以看出詩人們以彝族自然環境和普遍化的生活場景為對象,關照本族歷史、文化、服飾、風俗習慣等的發生,同時對民族性格、生命觀給予詩意闡釋,在精彩多樣的彝族文化原型意象書寫中,領會山地族群元文化的本質和魅力。
一、宗教與原型
恩格斯認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3]250擁有著千年歷史的涼山古老彝族,因其自成一體的特殊邊緣地域環境,使得這里保留著古樸完整的原始宗教觀念。例如,流淌于彝人血脈中的祖先崇拜、“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等,體現著彝族先民早期的生產生活中對未知世界的認知,歷經時間的積淀,成為彝族社會基本的道德習俗、民族心理、精神信仰和生死觀,這些都為大涼山彝族詩人詩歌寫作提供了豐厚的原型意象和文化資源。
詩人阿庫烏霧在《巫光》中這樣寫道:“白天 我凝視每一片木葉/在太陽下幽幽地反光/確信那是先祖的神跡/通過木葉微顫/昭示生命內蘊。”[4]13彝族有著根深蒂固的祖靈崇拜,認為父母無論生前還是死后都護佑著子孫后代,死后自己的靈魂回到袓地和袓靈們在一起才是彝人的最終歸宿,更深層次地表現出彝族對生命起源的探索和對生命力量的崇敬。可以說,鬼魂世界和現實世界共同支撐了彝族人的精神世界。詩人們的使命就是將蘊含著民族強大的文化心理進行關照書寫。祖靈崇拜更深層地反映了彝族靈魂不滅的生死觀,這種永生觀念也內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潛藏在彝族詩人的大腦。吉狄馬加的《畢摩的聲音——獻給彝人的祭司之二》:“當它呼喊太陽、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召喚神靈與超現實的力量/死去的生命開始復活!”[4]119詩人在文本中頌揚靈魂的復活,生命的永存通過彝族的神職人員——畢摩的誦經招魂中實現復活的形式來詮釋,帶給彝人新的希望。實際上,他用詩歌傳遞了一種民族自信心,喚起彝人在新的時代捍衛自己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
“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是大涼山彝族宗教文化的另一重要觀念。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曾說:“自然崇拜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對象。”[5]2這句話折射出人和自然的密切關系,也反映了原始人思維活動的性能。封閉阻塞的地域環境使得彝人依靠自然的贈予,早期生產力水平和知識結構的匱乏,彝人在生產勞作中對自然衍生出崇拜感,這種崇拜感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一種文化心理,并獲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狀態與文化背景。彝人認為每個物種都有神,自然和人都感性地存在,人要敬畏自然。大涼山詩人繼承了從遠古傳下來的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態觀和文化精神,這片地域空間的山、水、黑土地、森林、索瑪花、巖石等自然物都成為詩人書寫的對象。如倮伍拉且在《山的懷抱》里寫道:“滋養血液的泉水/夜夜拍打/我們睡眠/天亮后睜開眼睛/我們要穿越房前那片樹林/去收獲或播種/玉米和蕎子、洋芋/大涼山溫暖的懷抱里/身軀般挺拔的樹木/棵棵樹木/伸出枝椏/與我們的手掌相握/相互致以早安/并祝愿好運。”[6]70自然的山、水、樹被詩人注入情感的力量,能夠與人類意志相通,大自然不僅是詩人情感的歸屬,更是彝人世代生存的家園。“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念被詩人繼承,通過詩意寫作,表現出強烈的生態美學觀和生命意識,對于后工業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命題指出了方向。
圖騰崇拜可以說是自然崇拜的延伸,以文化人類學視域而言,圖騰代表了人類早期的審美文化,以及對于外在世界的認知,蘊含著強烈的原型色彩。大涼山彝族主要的圖騰崇拜對象有龍、鷹、虎等。彝族對龍的崇拜集中在對神話英雄——支格阿龍的情愫中。吉狄馬加曾寫道:“我不知道,在遠古/霜和雪是否在東方/老天的胡須蒼蒼/老天的眼睛泱泱/但我卻知道/確有一個彝族的祖先/確有一個古老的民族/于是英雄的支呷阿魯/便在龍年龍月龍日龍時誕生/留下龍之圖騰 。”[7]201詩中寫出了神話英雄支格阿龍的誕生,族群對于龍圖騰崇拜的開始,彝人自稱是支格阿龍的后代,詩人以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跨越了時空局限,以一種開放的人類文明視野關照傳統,讓傳統記憶在詩歌藝術的張力中得到完美詮釋。
另一位詩人阿蘇越爾在《花朵》中寫道:“源遠流長的詩歌的河流日漸明朗/在每一個映出傳說的光芒的山岡上/被著意描繪的情景紛紛披上夢幻的色彩/這時,所有的英雄都被稱作支格阿龍/心中的美女都喚作呷嫫阿妞。”[8]7支格阿龍、呷嫫阿妞早已內化為彝族文化符號,代表著英勇無畏和美麗善良的族群品質,詩人將神話傳統中的圖騰原型與普通人的關系拉得更近,毫不吝惜對族人的贊美與崇敬。
此外,彝人以“鷹的后代”自居。瑪查德清在《鷹魂紅黑黃》寫道:“在黑色的山里/神鷹的后代們在追尋陽光的熱點/一雙不屈的眼睛/發射出驍勇的火焰/屬于彝人的道路/充滿鮮紅的鷹血。”[6]289詩中將鷹的神勇無畏品質聯系到彝人身上,展示出了神秘多彩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特征。諸如在《看不見的波動》《鷹圖騰》《鷹爪杯》《雛鷹》等詩歌中都有著對“鷹”原型的詩意描述,表現出一種集體性的對彝族氏族社會流傳至今圖騰崇拜的深切眷戀。
彝族有“虎化萬物”的說法,對于“虎”原型意象的書寫也有很多,如俄尼·牧莎斯在《虎的圖騰》中寫道:“就是那一只潔白如雪的虎/昨夜暮色降臨時分/才告訴過我/上有蒼天/下有大地/生命的精靈就在天地間舞蹈。”[4]92詩人筆下的“虎”擁有著智慧,向彝人傳達著民族的歷史與知識,拓展了對虎的認識,使得圖騰文化內涵得到延伸。
二、畢摩與儀式
從文化人類學而言,詩歌與儀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儀式作為人類文化具體行為表現形式之一,是一種能夠傳遞信息和表達觀念的象征體系。”[9]在彝族社會生活中,有著豐富的民族儀式,而畢摩是彝族社會知識的掌握者和傳播者,也是各類宗教活動儀式的主持者,從事著主持祭祀,排解災禍,占驗兇吉,溝通著人、神、鬼等職責。在彝族社會中畢摩與儀式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獨特的畢摩文化。大涼山彝族詩人們對古老的畢摩文化進行多角度書寫。
阿蘇越爾在《聽畢摩誦經》中寫道“神靈啊,在整個的羅母里空/你以這樣漫長的經書見長/洞悉家族的歷史和恩怨/尾隨松油燈的明滅/卷卷經書漫起塵土飛揚/在崎嶇的羊腸小道,辨認/我們靈魂的氣息/這樣被釋放的夜晚/神的羊群布滿了天空/在通往閃光的路上相遇/面對高埂和蕁麻的只有我們。”[10]87“聽畢摩誦經”是每個自小在“羅母里空”(彝區)長大的彝人難忘的記憶。詩人由畢摩誦經,聯想到民族的歷史。作為彝族文化的維護者和傳播者,畢摩在各類儀式中以經書為載體,通過念經或口誦,向人們輸送著知識、撫慰彝人心靈的同時,也以古老神秘的語言帶領彝人進入神靈的世界。可以說,正是在畢摩和彝族社會的集體共識所形成的畢摩文化,才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得以世代相傳。
在儀式中構筑著彝人的生死觀。在濃厚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在喪葬儀禮上由畢摩唱誦彝文經典《指路經》《送魂經》,將死者之魂送往祖界,才算完成整個人生的程序。吉狄馬加在《白色的世界》中寫道:“我知道,我知道/死亡的夢想/只有一個色調/白色的牛羊/白色的房屋和白色的山崗/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就是/迷幻中的苦蕎/也像白雪一樣。”[11]127面對死亡,彝人并未感到恐慌,而是在儀式中實現了進入祖先世界的夢想。正是憑借強大的畢摩文化支撐,在喪葬儀式中安撫著參加葬禮的人們失去親人的悲傷,不斷構筑著彝人的豁達樂觀的生死觀,顯示出深層次的儀式文化功能。
此外,在彝族重大儀式場合,“火”必不可少。彝人自古崇尚火,彝人出生在火塘邊,彝族有著盛大的節日儀式——火把節,彝人實行火葬的傳統。在火葬儀式中,靈魂才得以超脫。吉狄馬加曾在《彝人談火》中寫道:“給我們血液,給我們土地/你比人類古老的歷史還要漫長/給我們啟示,給我們慰藉/讓子孫在冥冥中,看見祖先的模樣/你施以溫情,你撫愛生命/讓我們感受仁慈,理解善良/你保護著我們的自尊/免遭他人的傷害。”[4]109詩人以極大的熱忱謳歌火,并將火與對祖先的懷念緊緊聯系在一起,肩負著為彝人祈福攘災的功能。而倮伍拉且在《永不熄滅的紅紅的火》中寫道:“永不熄滅的火塘里的紅紅的火/染紅了我的血液我的心肝脾臟/照亮我的眼睛/照亮我的黑暗……有了永不熄滅的紅紅的火/就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4]207詩中的“火”早已不是普通實體性事物,詩人采用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貫穿了歷史與現實,表現出具有神秘魔力的“火”意象和精神象征意義。
皮爾斯曾指出,“符號是這樣一種東西,對于某種心靈來說,它可以代替另一種東西。”[12]35大涼山彝族詩人充分發掘文化符號元素,將古老文明進行現代言說。巴莫曲布嫫在組詩《圖案的原始》中,以女性的細膩、敏感的心靈感悟古老民族的魅力,如“你可記得支格阿魯/七天喊日,晝夜混沌”,“黑虎肢解化為天地萬物/左眼作太陽/右眼作月亮……”(《日紋》),“先祖阿卜篤慕,率族人/幾路分進/向寒冷/向蒼茫/向貧瘠的安全帶/跋涉,遷徙”,“我們共舉作齋大典/分為六支”(《武土上的雞冠紋》),對彝族社會生活中的日紋、雞冠紋、蕨子紋、水紋、羽紋給予了現代性關注和重新闡釋。我們從其詩歌創作中看到了詩人運用民族文化符號和元素,不斷拓寬表述空間,摘取彝族生活中常見的意象符號,運用諸如想象、暗喻、擬人等藝術技巧,構建著詩人的詩意世界與審美世界。
三、民族“活化石”
彝族的民族服飾是大涼山的另一種文化符號。彝族又稱為“諾蘇”,意為尚黑的族群。大涼山彝族的服飾主色調自然是他們所喜歡的黑色系列,并搭配紅、藍色。獨具特色的彝族傳統服飾表現出鮮明的生活方式、家支等級觀念和審美心理。
彝族社會的“百褶裙”“察爾瓦”“英雄結”等服飾元素也成為彝族漢語詩歌表現的對象。霽虹在《我披著的察爾瓦》中寫道:“我披著的察爾瓦/是一千只羊的毛紡成的/散發出百里高原的草香/幻化著太陽的光彩/我披著的察爾瓦/是女人從歌聲中織出來的/藏著千百條小路的影子/那種心事那種思念/爬滿我的一身/我披著的察爾瓦/是一方土地一座房屋/而站在門前的母親/在等著我回去。”[13]26詩中的“察爾瓦”作為情感媒介物,以遞進方式表現了多層的含義,先是作為普通服飾的材質描寫,進而以“女人從歌聲中織出”“思念爬滿一身”蘊含著愛情的甜蜜,最后從“站在門前的母親”傳遞出母愛與親情。而阿庫烏霧在《百褶裙》中則寫道:“豎起成瀑布誰能看透/橫陳為山路走不盡/彝人之妻再用我/終將不腐的靈魂/作源頭讓生命/在百褶千回里/摘到人間/最后一枚生澀的果子/在祖靈面前默默/呈現不會發芽的/果核。”[6]262詩人將“百褶裙”這一代表女性美的傳統服飾與民族歷史和審美相聯系,極大延展了這一服飾的文化內涵,表現出對于生命的熱切推崇。瑪查德清在《藍色的情緣》中則把“百褶裙”指向了年輕彝族女子在盛大的火把節中的裝扮,表現出對愛情的悸動與期待。
大涼山彝族的服飾以其豐富的文化所指和社會情感價值符號展現出彝族社會的多彩性,在服飾中鑲嵌著色彩文化,不斷構建著彝人夢幻般的審美世界和對生命的獨特感受。而大涼山彝族詩人自覺以民族文化“守護者”的身份,用漢語詩歌將具有民俗風情的“活化石”——傳統服飾給予創造性的書寫,散發出濃郁的邊疆地域文化特色和鄉土氣息,顯示出與異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詩歌氣質。
四、結語
大涼山彝族漢語詩歌是一種地域性文學創作,有著極大的文化人類學價值,這一群體透過文學寫作“表達著主體對其文化及其價值意義的體認與經驗,在表達真實的個體經驗并揭示經驗背后深邃的文化意義。”[14]他們以文學的民族志書寫為范本,努力探討著民族傳統文化的“突圍”與“混血”。可以看到,以大涼山彝族為代表的西南少數民族詩歌,堅守古老原味的本民族精神和物質世界的文化命脈,以現代意識和開放的視野,嘗試民族傳統的創造性解構,在當前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與弘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語境下愈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