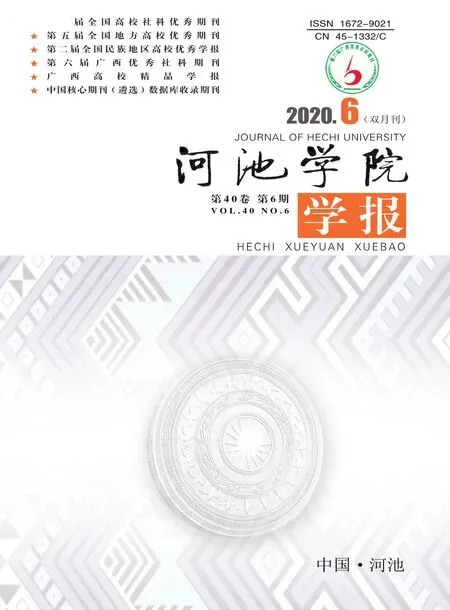“圣境”“神境”“化境”
——金圣嘆小說敘事理論關鍵概念命題研究之三
周淑婷
(河池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廣西 河池 546300)
對文藝作品進行藝術品級評判從鐘嶸《詩品》就開始了,此后幾乎歷代都有人熱衷于此事。分級評定既是文藝批評的方式,也是文藝理論建構的方式。在金圣嘆之前,大部分評判標準針對詩歌、史傳、散文、書法、繪畫、音樂等,還沒有針對小說提出一個評判標準。金圣嘆在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評點中,以“圣境” “神境” “化境”之三境說,作為評判小說藝術境界的級次標準:
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1]5。
由這段文字可以判定“三境”說評判對象“文章”中應該包括小說。鐘嶸《詩品》以“品”論詩的價值,宋代黃修復在《益州名畫錄》中以“格”論畫的價值,金圣嘆則用“境”論小說價值。據《說文解字》,“境”本義指地域,“境,疆也”[2]290,本是一個空間實存性與限定性概念,不同的空間構成不同的“境”域狀況。“境”由此衍化出狀況、地步、境界等義,是事物所達到的程度或表現的情況。“境”可借“竟”以代,比如《禮記·曲禮上》有言“入竟而問禁”[3]14。“竟”在《說文解字》中訓為“樂曲盡為竟”,段玉裁注曰“曲之所止也,引申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4]102。“樂曲盡為竟”是指樂曲存在的時間,可見“境”也是一個時間限定性概念,此時它既是實存的,也是心理想象的。所以后世美學意義上的“境”具有時空雙重意義,也具有主觀和客觀,心理想象和客觀實存兩方面的含義,“境”的這種時空、主客觀雙重性為后世“境”在不同文藝文體中的廣泛運用提供了基礎。比如它運用于詩歌、繪畫、書法等,強調的是“境”所具有的空間層面,也可運用于音樂、小說等,強調的是“境”所具有的時間性層面。丁福保認為 “心之所游履攀援者,謂之境”[5]1247,梁啟超說“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6]45,丁福寶和梁啟超在此都強調“境”的主觀性和心理想象性層面。“境”在文學上最重要的運用之一是“意境”。“意境”概念最早出現于王昌齡的“詩有三境”說中, “意境”“物境”“情境”,意為言志詩,其中的“意境”非后來作為美學范疇的“意境”。美學范疇的“意境”經過歷代理論家的不斷完善,有一個逐漸建構的過程,至王國維始集其大成。在王國維的“意境”理論中,“意境”由“意”和“境”兩方面構成,或者說由“情”與“景”兩部分構成,“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7]682。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說:“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后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的態度也。故前者客觀的,后者主觀的也;前者知識的,后者感情的也。”[8]17王國維在同一書中又說:“上之所論,皆就抒情的文學言之(《離騷》、詩詞皆是)。至敘事的文學(謂敘事詩、詩史、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格為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有人格矣,然他戲曲則殊不稱是。要之,不過稍有系統之詞,而并失詞之性質者也,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此則后此文學家之責矣”[8]18。王國維所言“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包含在“以上所論”中。王國維以為意境論總結的是我國抒情文學的文學本體,并不包括敘事文學,敘事文學有其獨特性。王國維后于金圣嘆,但他忽略了金圣嘆把意境論用于敘事文學的嘗試,金圣嘆的“三境論”觸及的正是這個問題。“三境論”是金圣嘆試圖用傳統的意境論來解釋小說這種敘事類文體的理論嘗試。從實踐上看,把意境論用于敘事類的小說有一定的困難,其困難之處源于小說的時間性質和詩歌空間性質這種本質的區別。抒情文學立足于空間的抒情方式,即情感的表達是通過空間化實“景”、實“象”的建構而完成,借助空間化的意象而達成。小說的時間性意味著小說文本的創作和閱讀都是在時間中建構起來的,它不能像抒情文學中那樣實“景”、實“象”作為一個空間整體呈現,而只能夠一點一點地在時間中建構,這是小說獨特的存在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金圣嘆實際上已經抓住了這種區別的本質,這主要體現在他對化境的設置和界定上。把意境論直接應用于小說批評則主要體現在他對神境的設置上,二者均將在下文進一步討論。
“三境”說中“圣”“神”“化”分別代表小說藝術所達到不同水平、程度、境界,其間的區別在于“心”“手”關系不同。以“心”“手”關系來區分“三境”,實際上是以“意”和“言”之間的關系來區分三種不同境界。莊子最早提到以“意”和“言”為內核的“心”“手”“口”關系問題:“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9]166。輪扁的這段話是為了論證莊子提出的一個論點:“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9]165-166莊子用輪扁斫輪故事中的“心”“口”關系說明“言”、“意”關系,證明其“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言”“意”關系就如同輪扁斫輪時“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言不達意,二者之間為矛盾關系。則所謂“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所談則為言、意的和諧、矛盾諸關系。一般而言,“意”可有作者立意、文字傳達意、讀者閱讀中建構意三者。這三者中除了語言文字意因凝聚在文字上而得以實體化之外,作者意和讀者建構意都具有某些不確定性。因此,言意矛盾的說法是模糊的,表面化的,實質上是意和意之間的矛盾。讀者建構意只能無限靠近而不能最終抵達、還原作品意,二者之間始終有間距。作者在創作中努力用文字表達出自己所想表達的意,但實際上作者意和作品意之間也有間距。讀者建構意和作者建構意之間隔著作品意,距離更遙遠。可見以文學作品為交流場的系統具有開放性,三意彼此追逐又彼此齟齬,各自追求自己的主體性,所以追逐意和意的一致幾乎毫無意義,亦即追逐言(作品意的載體)、意一致毫無意義。對于文學語言而言,更是基于語言“陌生化”與修辭性拉開言與意的距離,由此拓展文學想象,創造詩性空間,并在兩者之間介入“象”,形成言-意-象結構關系。因此董仲舒提出“詩無達詁”說明作者、讀者和作品三者之意永遠在相互齟齬抵牾,在這種齟齬、間距、矛盾中,文學的審美意義得以產生,也就是說文學作品本來就追求言、意之間的間距和張力關系。這其間唯一穩定不變的是作為語言符號的言,語言本身就是意,除了語言,沒有其他的意。據此也可以說文學之間的差異不在意,而在于言,語言就是文學的家和本體。基于這樣的觀念來考察所謂三境論的“心至”“手至”,或“心不至”“手不至”說,其實就是作者之意、作品之意和讀者之意的關系問題。“心至”是作者意,“心不至”是作者意中無有。“手至”是作者意轉化成文字,在語言文字上得到落實,構成作品意,作者意和作品意間距較小。“手不至”是作者意沒有落實在文字上,作品意和作者意之間距離較遠。“心手皆至”說的是作品意和作者意的一致性,這強調的是語言文字所具有的傳達信息的實用功能。“心不至手至”是作者意中無,而作品意中有,形象大于思維。“心手皆不至”“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談的是作者意中無,作品意中亦無,讀者卻能夠根據作品意在閱讀作品中完形建構起來的讀者意。這段文字所談論的表面上是言、意關系問題,實則是一個意和意之間的關系問題,強調的是意與意之間的張力、間距以及在實用層面上的一致性。所以金圣嘆所談論的言意矛盾關系歸根結底談的是作者意、作品意、讀者建構意之間因齟齬、矛盾、間離、實用層面有限度的一致性而造成的審美張力關系,這就是金圣嘆“三境論”中言、意關系之意義所在,迥異于傳統文論視此為語言的遺憾之處。
一、“圣境”:“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
“圣境”是小說所應該達到的最低要求,只有達成了這個最低要求,才能夠追求“神境”“化境”等其它的境界。小說達成的“圣境”是實境,是作者建構整個作品的基礎。
(一)“圣”:真善之境
從金圣嘆談論“圣境”的語境看,“圣境”之“圣”是指那些著述六經,有“圣人之位”又有“圣人之德”從而有著述權的人,這樣的人達成了“內圣外王”,被儒家稱為“圣人”。金圣嘆曰: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結繩,而其盛崤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圣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1]1。
可見金圣嘆言“圣境”之“圣”是指儒家之“圣”,而非道、佛等別家之圣。儒家之“圣人”是達成了“內圣”心性修養境界并具有“外王”的事功的人,即金圣嘆所謂“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內圣”是人內心達到一個仁、圣的境界,達成這一境界的即可被稱為“圣人”。“圣人”是儒家道德人格追求中最高境界的一類人,區別于君子、鄉愿和狂狷者。中國歷代被尊為“圣人”的都是在“內圣”“外王”或其中一方面達到最高境界的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征圣》中說“夫作者曰‘圣’”[10]9,“圣”是指儒家經典的作者,“圣境”是圣人因有其位其德其權而創作儒家經典從而達成的境界。“若圣與仁,吾則豈敢。”[11]175“圣人”是人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人,其標志即在于他的道德水平達到了“仁”的境界,“圣境”的實質是仁境。“圣經燒,而民不興于善”[1]3,“圣境”也是善境。“圣境”為小說寫作和評論樹立了一個最基本的內容方面的標準“仁”“善”,要求小說內容對人類具有正價值正能量。金圣嘆反復提到的“勸懲”“教化”“自娛”“冤苦”“發憤”“寫出自家錦心繡口”“娛人”等分別就文學作品對社會、對個人、對他人的價值而言,都是小說具有正價值正能量的表現。
(二)“心手皆至”:言意一致之境
小說求仁求善,亦求真。小說達成基本的內容仁、善后,當追求“心手皆至”的求真標準。只有達成了這一標準,小說作品才真正進入第一層境界的“圣境”。在劉勰的眼中,儒家經典“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10]13,后學應該據此“稟經以制式”來創作。金圣嘆對儒家六經評價很冷靜,認為它們達成的境界僅僅是“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言意達成一致,言很好地表達了意,即作者之意和作品之意基本吻合,作品意略等于作者意,如此而已。“心之所至手亦至焉”意味著言、意之間無張力,語言忠實地傳達了作者之意,強調的是語言傳達信息的實用性功能,要求語言具備基本的交流信息的功能,但不關注言辭的審美功能。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辭,達而已矣”[11]418。言辭,足以表達意思便罷了。
金圣嘆所謂“心手皆至”之“圣境”樹立了一個求真、求善的寫作標準。“圣境”中追求的言意一致是一部小說中所具有的實體性的成分,類似于抒情性作品中的實“象”、實“景”,是讀者閱讀填空想象完形的基礎。沒有“圣境”達成的實體性成分作支撐,“神境”和“化境”將因無所附麗而不能夠存在。
二、“神境”:“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
“圣境”求真、求善,“神境”和更高一級的“化境”則求美。同為求美,“神境”達成的層次低于作為審美理想存在的最高層次的“化境”。“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神境也”,“神境”內涵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下文詳論。
(一)“手至”:有法之境
《周易·系辭上》云:“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12]561-562,“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12]588,《周易·系辭下》也有言:“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12]648-649。此時“神”還不是文藝批評概念。《淮南子》對“神”的意義作了新的闡發,使其接近于美學概念:“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13]82,“神”與“形”“氣”相對,是人的精神,為“生之制”,即生命的統帥。淮南子還把“形”、“神”構成一對概念,為后世形神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13]87,“神貴于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13]1042。此論奠定了歷代強調神似輕視形似的基本觀念。最早把“神”這一概念用做文藝批評概念的是顧愷之的“以形寫神”說,“神”與形體、形態、物質形式相對,指的是對象的精神。在此基礎上,唐人張懷瓘在評定書法等級時提到神、妙、能三品,惜乎未對三品作詳細解說,但從其列入各品的畫家看,張懷瓘最重“神品”。“神”由此變成了一個標示作品等級的概念。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于張懷瓘三品之外另加“逸品”,但最看重的仍舊是“神品”,“神品”上等僅列吳道子一人,逸品則在三品之外,為“格外不守常法”[14]1者。宋代黃修復在《益州名畫錄》中對朱景玄提出的畫之逸、神、妙、能四格進行了詳細解釋,其中逸格和神格這樣解釋:
逸格
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矩于方圓,鄙精研于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
神格
大凡畫藝,應物象形,其天機迥高,思與神合。創意立體,妙合化權,非謂開廚已走,拔壁而飛,故目之曰神格爾[15]1。
《益州名畫錄》列逸格一人、神格二人,妙格上中下共二十八人,能格上中下共二十七人,可見逸格和神格都是很高的境界。逸格強調自然、簡、不見規矩,鄙視彩繪。神格最重要的特征是“應物象形”,可見神格以追求形似,以生動形象為能。在黃修復的解釋中,對比張懷瓘的神、妙、能三品論,“神格”地位下降,以“逸格”為最高。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列“自然”“神”“妙”“精”“謹細”五等,“神”品地位次于“自然”品,“自然”品與黃修復的“逸格”相當,二者在基本內涵上都類似于金圣嘆的“化境”:
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16]38。
王世貞對此批評道:“畫至于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發不自然,則非神矣。”[17]7071陳望衡認為王世貞的批評有道理,但又為張彥遠辯解道:
張彥遠也并非不明白“神”亦可理解為“自然”,他力主區別這兩個概念,是想將天工與人工區別開來,“自然”是天工,“神”是人工。當然,人工如能達到天工之巧,那也就是自然了[18]140。
王世貞說的“能事”是人所作為之事,可見他也同意“神”具有人工所為性,“神”品是人工達成的自然,“自然”品是天工之自然,這是二者最本質的區別。金圣嘆提出的“圣境”“神境”“化境”之“三境”中,“化境”即相當于張彥遠之“自然”、黃修復之“逸格”,其實也就是“道”的境界。“神境”與它們所說的“神”品相當。“神境”與“化境”之間的本質區別也就是人工與天工的區別。
“神境”的人工性質體現在何處?“神”在中國文化中有人格化的神靈、得道之人的聰明才智、神圣的、宇宙萬物變化莫測的規律等義。金圣嘆“神境”之所謂“神”是“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12]561-562之“神”,是“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12]588之“神”,是宇宙萬物變化莫測的規律。陰陽關系變化無窮,這種無窮難測的變化被稱為“神”。《周易》曰:
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12]599-600。
陳望衡解釋說:“乾辟坤闔,乾剛坤柔,乾進坤退。就在這辟闔、剛柔、進退之中產生了變,這種變,往來不窮,上通下達。其可見之處叫做‘象’;其成形之處叫做‘器’;掌握它、利用它就叫做‘法’。如果能夠把‘法’運用得十分純熟、靈活,富有創造性,那就叫‘神’了。”[19]259因為“神境”是通過處理好作品的對立關系這種形而下的方法來達成,所以其成就的層次還在“有法”之境界。“神境”作為人工之自然就意味著小說要想達到“神”這一境界就要很好地處理藝術創作中各種對立的陰陽關系,如形神、冷熱、動靜、高低、大小、明暗、虛實、遠近、雅俗等諸關系。能夠很好地處理這些關系的作品就可以說達到“神境”了。金圣嘆所提出三境論的這段文字中表明:作者比較好地處理了構思、布局、琢句、安字即構思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前后、左右、正反諸對立關系,就達到了小說藝術所追求的“神境”。
從上可知,“神境”之“神”有兩方面的內涵值得注意:其一,“神”可以用于標示作品成就的等級;其二,“神”的地位在下降,由一開始的最高等級下降為“自然”品,是“逸格”之后的一個等級,為人工境界而直逼自然者。
(二)“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虛實相生之境
“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意為作者意中無,作品意中有,類似于形象大于思維說,也與中國傳統詩歌言有盡而意無窮、象外之象說類似。在此金圣嘆把詩學中“景生于象外”的意境理論直接運用于敘事文學,追求“有生于無”“虛實相生”“有無相生”而強調了“無”“虛”。作品意大于作者意,其大于的部分要由讀者在閱讀中根據“圣境”達成的“實有”部分而建構起來。須注意,此處讀者的建構純粹是審美建構,無關乎信息的傳達,是讀者據以聯想和想象的部分,正所謂“文到入妙處,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聯綰激射,正復不定,斷非一語所得盡贊耳”[1]417。
三、“化境”:“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
“神境”雖然已經是很高的境界了,但畢竟還沒有達到藝術的極致,達到藝術極致的是“化境”。“化”是造化。“造化”與“道”“自然”“天”等都是表征宇宙本體的概念,“化境”即是與道合一的境界,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特征。
(一)“手不至”:無法之境
中國文論認定無法勝有法,老子講“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20]139,所以石濤說“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穿眾法也”,“無法之法,乃為至法”[21]3,一旦達到“無法”之境界,這樣的藝術極致就被稱為“化境”。“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強調“無”字。與金圣嘆的“化境”同出而異名的是李贄提出的“化工”論: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圣,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22]108-109。
李贄視“化工”為藝術的最高境界,“化工”之美,美在自然、和諧、本真,流暢,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化工”是最高的藝術境界,其特性就在于雖說是人創造但宛如造化,人工所為而不見工,有法而宛如無法。“畫工”雖窮極工巧,但留有人工的痕跡。所以“化境”比“神境”更高一層,它就幾乎等同于造化本身,是完美、自然、至善的境界,對比那些法度森嚴的作品,“化境”“化工”之作看不見形而下的法。所謂“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并非真的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而是有宛如無,強調的是作品的自然美。
(二)“心手皆不至”:空白可達意之境
“心手皆不至”亦即作者意中無,語言表達中亦沒有,意味著作品意與作者意都等于零,而意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的空白部分。小說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著空白的構架,這些空白與“神境”中的空白將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由讀者的完形心理來填充。其區別在于“神境”的空白建構不關乎信息傳遞,是審美性空白。“化境”中的空白則不僅是審美的建構,更是信息建構,是結構性空白,即只有在閱讀中把空白部分完形,讀者才能夠構筑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及其人物。只有把那些人物、情節、環境空白建構完形,小說作品才能夠完整。所以化境強調的是讀者之意,所謂“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是也。作家之意中沒有,作品之意中也無,即所謂“心手皆不至”,但讀者可以通過“心手皆至”部分即上下文在心中完形填空,構筑出整個作品。“神境”是以最少的文字,留下最大的藝術空白供讀者想象,追求的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造成“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是審美化建構;而“化境”雖然有審美化建構的成分,但更強調讀者的信息建構,這是二者區別的實質。下面兩例是信息化建構的代表。
第一例是《水滸傳》第十四回吳用說三阮撞籌一節,書中寫道:“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什么來!’”金圣嘆批曰:
“罷罷”只二字,忽插人“叫道”,二字作敘事,然后又說出九個字來,卻無一字是實,而能令讀者心前眼前,若有無數事情、無數說話、靈心妙筆,一至于此![1]233
第二例是《西廂記》一本二折張生向法聰借房,上場后劈頭唱了一句:“不做周方,埋怨殺你個法聰和尚!”對此行文,金圣嘆云:
張生因未嘗先云借房,則聰殊不知其“不做周方”之為何語也。張生未嘗先云借房而便發極云“不做周方”者,此其一夜心問口、口問心,既經百千萬遍,則更不計他人之知與不知也。只此起頭一筆二句十三字,便將張生一夜無眠,盡根極底,生描活現。所謂用筆在未用筆前,其妙則至于此……試思“不做周方”二句,十三字耳,其前乃有如許一篇大文,豈不奇絕![23]35-36
以上第一例中金圣嘆指出了讀者可在心中建構出阮小五、阮小七兄弟平日的言語,第二例中金圣嘆指出讀者可在心中建構出昨晚張生情境,這些都是信息的建構補充。這種結構性空白李漁在《閑情偶寄》中也描述過:
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發沖冠,能使人驚魂欲絕,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絕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贊嘆為戰爭,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為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于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于雅中之俗乎哉?[24]43
李漁所言“觀者叫絕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讀者處理好冷熱和雅俗這兩組對立關系之后,根據上文內容,在“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這樣結構性的空白中達成的效果。
“圣境”是圣人境界,圣人只是凡人中杰出者,但仍舊是凡人;“神境”是神人的境界,神人比之于凡人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化境”是與道合一的境界,是形上觀念的體現。三境之間具有等級性關系,用于表征不同的作品藝術價值的程度大小。同時,達成“化境”的作品一定三境具備,達成“神境”的作品一定同時達成了“圣境”。三境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完善小說的審美要求,在優秀小說作品中三足鼎立而又三位一體,形成構成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