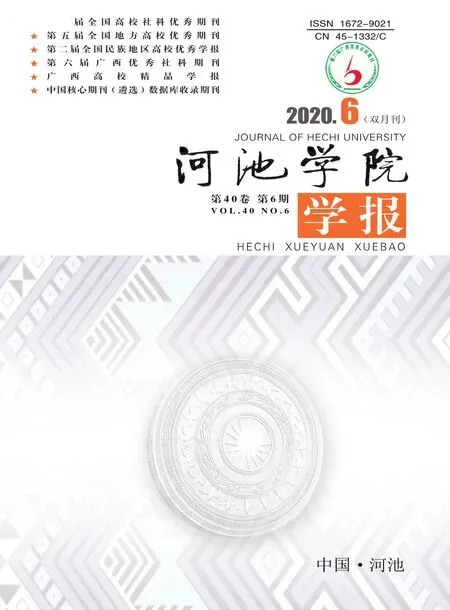《守羊人》中的“無(wú)思觀看”
王 婭
(廣西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廣西 桂林 541006)
費(fèi)爾南多·安東尼奧·諾格拉·佩索阿(Fernando António Nogueira Pessoa ,1888-1935)生于里斯本,是20世紀(jì)著名的葡萄牙語(yǔ)詩(shī)人、作家、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哲學(xué)家。與眾不同的異名寫作風(fēng)格使他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贏得了廣泛的聲譽(yù)。詩(shī)集《守羊人》的作者就是佩索阿創(chuàng)造的主要異名之一阿爾伯特·卡埃羅,這位以“導(dǎo)師”身份存在的牧羊人在詩(shī)歌中始終呼吁簡(jiǎn)樸和自然,并且不斷強(qiáng)調(diào)“無(wú)思觀看”這一觀念,反對(duì)一切哲學(xué)和宗教,不過(guò)他卻于反對(duì)之中發(fā)展了自己的形而上學(xué),正如其在詩(shī)中所言——“不思考任何事物之中,有著很多形而上學(xué)。”[1]15從而讓這簡(jiǎn)樸與自然的背后透露出復(fù)雜、機(jī)巧與闡釋的多種可能性。
一、直觀領(lǐng)悟世界的本質(zhì)
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借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在詩(shī)集《守羊人》中表達(dá)無(wú)思地觀看才能達(dá)到真正的客觀狀態(tài)與內(nèi)心自由之思想。在這一過(guò)程中,觀審者處于一種非常單純而平靜的狀態(tài),沒(méi)有任何思考和憂慮,也沒(méi)有任何情緒的起伏和波動(dòng)。在詩(shī)人看來(lái),正是這樣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才能夠讓我們領(lǐng)悟到世界永恒的本質(zhì),通達(dá)內(nèi)心的愉悅和暢達(dá)。
這一觀點(diǎn)在《守羊人》的許多篇章中都有所體現(xiàn),比如第二首:“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雛菊,/因?yàn)槲铱吹搅怂5也蝗ニ伎妓?因?yàn)樗伎际遣焕斫狻?創(chuàng)造世界不是為了讓我們思考它,/(思考是眼睛害了病)/而是讓我們注視它,然后認(rèn)同”[1]7。從這一詩(shī)節(jié)中,阿爾伯特·卡埃羅否定思考的任何實(shí)質(zhì)性意義,因?yàn)樵谒磥?lái)思考意味著不理解,創(chuàng)造世界僅僅是為了讓我們注視它、觀看它,最后直接認(rèn)同它,因?yàn)橛^看即已經(jīng)領(lǐng)悟,不需思考;又如第二十三首“即便草場(chǎng)上生長(zhǎng)出新的花朵,/即便太陽(yáng)也變得更美,/我卻覺(jué)得草場(chǎng)的花兒更少了,/我卻認(rèn)為太陽(yáng)更丑了……/因?yàn)橐磺腥绯#褪沁@般/我接受,我也不會(huì)去感謝,/為了看起來(lái)沒(méi)有思考這些……”[1]55從這首詩(shī)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草場(chǎng)上生長(zhǎng)出新的花朵,即便是每天東升西落的太陽(yáng)變得比從前更美,但詩(shī)人始終認(rèn)為它們和往常一樣并沒(méi)有多大的不同,而他這種一切如舊的感覺(jué)不過(guò)是為了說(shuō)明在觀看過(guò)程中自己并沒(méi)有思考這些事物的變化,因?yàn)橐坏┻M(jìn)行思考,就會(huì)進(jìn)入思考本身,而不是進(jìn)入事物本身,這樣一來(lái),關(guān)注和理解的就是思考而不是事物,這正如詩(shī)人所說(shuō)的,“如果我思考這些事情,/我便不再看樹(shù)木與植物,/不再看大地,/而只去看我的思想……”這樣一來(lái),“我會(huì)悲傷,在黑暗中掣足。/因此,不去思考,我會(huì)擁有大地與天空。”[1]74可見(jiàn),在詩(shī)人看來(lái),思考使人失去所擁有的事物,只有拋棄思考,人才擁有該擁有的。在第二十四首中,詩(shī)人說(shuō)道:“最重要的是知道去看,/知道去看而不去思考,/當(dāng)觀看的時(shí)候知道觀看,/當(dāng)觀看的時(shí)候不去思考,/當(dāng)思考的時(shí)候不去觀看”[1]56。在此,佩索阿的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首先將“觀看”和“思考”的重要性進(jìn)行鮮明的對(duì)比,以此突出“觀看”遠(yuǎn)遠(yuǎn)高于“思考”的觀念,進(jìn)而直截了當(dāng)?shù)乇砻髯约旱膽B(tài)度:當(dāng)觀看的時(shí)候只需做到全神貫注地觀看,不必?fù)诫s多余的形而上學(xué)的思考,因?yàn)檫@樣的思考純屬多余,就像此前他明確表達(dá)過(guò)的,“思考事物的內(nèi)在意義,/是多此一舉,好像去思索健康,/或把杯子拿到泉水旁。”[1]17在第三十九首中,詩(shī)人借助異名直言:“事物的神秘,存在于哪里?/至少要向我們顯示它是神秘的,/它既不出現(xiàn),那又存在于何處?/河流知道什么?樹(shù)木知道什么?/而我,并不比它們高尚,又知道什么?/每當(dāng)我注視事物,想起思考它們的人/便笑了,仿佛小溪撞上石頭清脆地響。”[1]81在這些詩(shī)句中,我們可以看到,阿爾伯特·卡埃羅將自己和河流、樹(shù)木做類比以此說(shuō)明他的普通與平凡,更重要的是,在詩(shī)人看來(lái),世界就是由平凡構(gòu)成的,其中并沒(méi)有什么內(nèi)在神秘性,所以每當(dāng)詩(shī)人無(wú)思觀看事物而想起那些思考它們的人時(shí),便覺(jué)得他們的行為著實(shí)荒唐,因此便無(wú)所顧忌地笑出聲來(lái),“仿佛小溪撞上石頭清脆地響”。由以上所有舉例與分析來(lái)看,佩索阿借用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表述了“無(wú)思觀看”的“觀看”即“理解”的思想,主張摒棄所有的知識(shí)和任何理性思考,直接地觀看和感受世界、事物本身[2],從而通達(dá)對(duì)自然、世界本質(zhì)的真正認(rèn)識(shí)。
佩索阿在其文論中也表達(dá)出“無(wú)思觀看”所達(dá)到的對(duì)事物本質(zhì)的直觀理解,如在《卡埃羅談?wù)鎸?shí)》一文中,詩(shī)人有如此表述:“看,椅子是椅子,椅子是木頭,椅子是形成木頭的物質(zhì)……如果我觀看它,它基本上是個(gè)椅子……它就像事物的前后左右各方面。每個(gè)方面都是真實(shí)的。”[3]357在其他作品中,肯定觀看輕視或否定思考的觀點(diǎn)也時(shí)有出現(xiàn)。例如,在異名阿爾瓦羅·德·岡波斯的《牛津郡》一詩(shī)中,詩(shī)人寫道:“曾有一次,在牛津的鄉(xiāng)下步行/……/直到今天才明白它的意義……/那條路,讓我從尖頂看到/古老的精神性,辛勞的美德。/當(dāng)我進(jìn)了村,尖頂不過(guò)一個(gè)尖頂,更重要的是,它在那兒。”[4]131在異名特夫男爵唯一的手稿《禁欲主義者的教育》中,《在愛(ài)比克泰德的花園里》一文有如此闡述:“和我安靜地坐在這些綠樹(shù)的涼蔭里,當(dāng)秋天來(lái)到,它們的思想比枯萎的葉子還輕……和我安靜地坐下來(lái),沉思努力多么無(wú)益,意志多么陌生,而我們的沉思像努力一樣無(wú)用……”[5]275在異名伯納多·索阿雷斯的《萬(wàn)物無(wú)靈》這篇文章中,作者寫道:“對(duì)于那些強(qiáng)大得足以從中得出結(jié)論的人來(lái)說(shuō),這些思考含有一整套哲學(xué)的種子。而我不是這樣的人。關(guān)于邏輯的哲學(xué)專深而朦朧的想法,于我飄忽而過(guò),消失于一道金色陽(yáng)光的景象之中”[6]291。從以上所寫的內(nèi)容中,我們可知除了詩(shī)集《守羊人》外,佩索阿以其他異名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也直接或間接地表達(dá)了“無(wú)思觀看”觀念并肯定直觀的“觀看”優(yōu)于“思考”。
二、直觀的藝術(shù)觀審內(nèi)涵
《守羊人》中詩(shī)人阿爾伯特·卡埃羅“所見(jiàn)即所是”的無(wú)思觀看方式其實(shí)是一種藝術(shù)觀審,其本質(zhì)上屬于一種非理性的直覺(jué)認(rèn)識(shí),這與叔本華的 “審美直觀”理論和莊子的“審美虛靜觀”思想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契合。
(一)契合叔本華的“審美直觀”理論
叔本華曾從意志本體論出發(fā),在認(rèn)識(shí)論方面提出了直觀認(rèn)識(shí)的觀念。所謂直觀認(rèn)識(shí)是指與運(yùn)用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形式的理性認(rèn)知相對(duì)立的一類認(rèn)識(shí),它具有非功利、非理性的特點(diǎn)。具體地說(shuō)就是認(rèn)識(shí)主體把對(duì)象從時(shí)空、因果等一切關(guān)系和根據(jù)律的束縛中抽拔出來(lái),最后只剩下“本質(zhì)”而被加以直觀。這種純粹的觀審方式切斷了個(gè)別事物與現(xiàn)實(shí)的一切關(guān)系,要求審美主體掙脫一切生命欲求,進(jìn)而能看到意志的直接客體性——理念,最終達(dá)到物我兩忘的審美境界和靜謐喜悅的內(nèi)心和諧。在《守羊人》中,卡埃羅否定觀看過(guò)程中思考所具備的任何實(shí)質(zhì)性意義,否定所有的形而上學(xué),“沒(méi)有思考,也沒(méi)有遲疑,/我猜想這才是真實(shí)”[1]95,進(jìn)而運(yùn)用藝術(shù)的“審美直觀”方式來(lái)達(dá)到對(duì)世界本質(zhì)意志的認(rèn)識(shí)。在這種狀態(tài)下,由于精神力量的提高,詩(shī)人放棄了對(duì)事物的習(xí)慣性看法,不再按照根據(jù)律的線索去追究事物的相互聯(lián)系,也不讓抽象的思維、理性的概念盤踞著意識(shí),而是把人的全部精神力量獻(xiàn)給直觀,沉浸于直觀[7]222。這時(shí),詩(shī)人不再是一個(gè)認(rèn)識(shí)個(gè)體,而是暫時(shí)擺脫了意志束縛的純粹認(rèn)識(shí)主體,他“自失”于作為審美對(duì)象的整個(gè)世界中,看到了它而不去思考它,只注視它而后認(rèn)同它,以此做到無(wú)關(guān)利害地、客觀地直接觀察事物本身,進(jìn)而達(dá)到對(duì)理念的絕對(duì)把握和心靈的絕對(duì)寧?kù)o。因此,可以說(shuō),在《守羊人》這部詩(shī)集中,卡埃羅這種只想觀看仿佛沒(méi)有靈魂,只想觀看仿佛沒(méi)有眼睛的超功利的、高于一切科學(xué)和理性認(rèn)識(shí)的藝術(shù)觀審和叔本華的美學(xué)思想形成契合,體現(xiàn)為一種棲息于、沉浸于眼前對(duì)象的親近觀審。在這一過(guò)程中,詩(shī)人聚精會(huì)神地專注于當(dāng)下的觀看,早已忘記了審美對(duì)象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同時(shí)也忘記了自己作為個(gè)體時(shí)的生命意志,努力踐行“審美直觀”的他,將自己與直觀融為一體,而他和所要認(rèn)識(shí)的這個(gè)世界也在瞬間消失,兩者合二為一,即整個(gè)意識(shí)完全為一個(gè)單一的直觀景象所充滿,所占據(jù)[8]250。
(二)契合莊子的“審美虛靜觀”思想
詩(shī)人卡埃羅的“無(wú)思觀看”與莊子美學(xué)中的“審美虛靜觀”也有某種程度上的契合。眾所周知,莊子從生命意識(shí)的體驗(yàn)出發(fā),在《天道》中提出“虛則靜,靜則動(dòng),動(dòng)則得矣”[9]206,即要求審美主體在面對(duì)審美對(duì)象時(shí),內(nèi)心應(yīng)該達(dá)到一種超越一切利害關(guān)系的虛靜自由狀態(tài),這樣便能擺脫身心受到的羈絆,從而保持精神上的逍遙。那么,如何才能擁有這種空靈明澈的心境呢?莊子給出了自己所認(rèn)可的答案:忘。“忘”是一種人生態(tài)度,從忘物、忘欲到忘智,最終達(dá)到物我兩忘,忘卻一切[10]。可以說(shuō),卡埃羅的“無(wú)思”和莊子的“忘”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兩者都著意說(shuō)明在審美觀照中,只有做到排除任何雜念和思慮的干擾,超越一切功利世故,忘掉外物和自我的存在,才能進(jìn)入一種“物我界限之消解,萬(wàn)物融化為一”的“物化”境界。在《守羊人》中,卡埃羅認(rèn)為事物唯一的意義在于根本沒(méi)有任何內(nèi)在意義,因而在觀看的過(guò)程中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觀看的時(shí)候知道觀看,當(dāng)觀看的時(shí)候不去思考”。在“無(wú)思”的狀態(tài)下,人就可以不計(jì)利害、得失、是非、功過(guò),忘乎物我、主客、人己,從而讓自我與整個(gè)宇宙合為一體[11]211。由此看來(lái),此時(shí)作為審美主體的詩(shī)人內(nèi)心純凈如鏡,虛靜清明,從而在心理上達(dá)到一種理想人格的狀態(tài),而沒(méi)有正式教育的人生經(jīng)歷更不會(huì)使詩(shī)人被其他的學(xué)說(shuō)、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等雜亂的思想所充塞,也不會(huì)利用概念對(duì)審美對(duì)象進(jìn)行分析、批判、肯定或否定,他只是專注于眼前當(dāng)下所看的事物,通過(guò)最簡(jiǎn)單、最直接的體驗(yàn)逐漸進(jìn)入到一個(gè)主客體之間完全融合無(wú)間的心靈自由狀態(tài),從而在交感互蕩的審美境界中獲得一種美的愉悅感。應(yīng)該說(shuō),卡埃羅的這種藝術(shù)觀審方式在本質(zhì)上也是莊子美學(xué)思想的一種具體顯現(xiàn),因?yàn)樵?shī)人在觀看過(guò)程中對(duì)一切認(rèn)識(shí)、思慮、分析的否定和莊子所追求的“無(wú)不忘也,無(wú)不有也,澹澹無(wú)極而眾美從之”[9]247的至善至美境界顯然有異曲同工之處。
三、審美直觀的超越
阿爾伯特·卡埃羅這一異名給讀者留下了性情質(zhì)樸、飄逸灑脫的深刻印象。他既沒(méi)有職業(yè),也沒(méi)有豐富的教育經(jīng)歷,只是以無(wú)思觀看的“牧羊人”身份出現(xiàn)在世人眼中。而這一異名形象實(shí)際上是佩索阿的一個(gè)側(cè)面。透過(guò)歷史背景和《守羊人》中的描寫情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佩索阿不僅在其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悲觀主義傾向,而且他也有著對(duì)于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悲劇意識(shí)審美超越的強(qiáng)烈渴望。
從審美超越途徑來(lái)看,佩索阿通過(guò)塑造無(wú)思觀看的阿爾伯特·卡埃羅形象,反映出他想要對(duì)紛紛擾擾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和世俗社會(huì)的痛苦的一種超越,而這種超越實(shí)際上是他建立在對(duì)國(guó)家、人民艱難生存困境的清晰認(rèn)知之上的。不言而喻,阿爾伯特·卡埃羅是一個(gè)田園牧羊人,這樣的身份設(shè)置蘊(yùn)含著一種更為深刻的涵義。“牧羊人”最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的是靜謐安逸的田園生活,然而從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初期,現(xiàn)實(shí)中的葡萄牙農(nóng)村生活和作者呈現(xiàn)給我們的“桃花源”意境相距甚遠(yuǎn)。首先,資產(chǎn)階級(jí)君主立憲制度下的葡萄牙發(fā)生了1890年大危機(jī),雖然其他產(chǎn)業(yè)對(duì)國(guó)家財(cái)政收入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遠(yuǎn)不及占主導(dǎo)地位的葡萄酒行業(yè)。然而,更為糟糕的是,這一時(shí)期的國(guó)際葡萄酒貿(mào)易趨于停滯,而此時(shí)的葡萄牙農(nóng)民沒(méi)有得到應(yīng)有的技能培訓(xùn)、引進(jìn)新技術(shù)以改善葡萄生產(chǎn),也沒(méi)有合格的管理者來(lái)改善營(yíng)銷以改變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落后的狀況。可以說(shuō),當(dāng)時(shí)葡萄牙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失敗迫使人們逃離了土地,有些經(jīng)濟(jì)難民甚至以偷渡的方式離開(kāi)祖國(guó)前往巴西,這也導(dǎo)致了國(guó)家勞動(dòng)力的海外流失;其次,在葡萄牙共和國(guó)時(shí)期,人口的增長(zhǎng)使得小麥問(wèn)題繼續(xù)成為國(guó)家的一大困擾。當(dāng)政治家們爭(zhēng)論為城市無(wú)產(chǎn)階級(jí)購(gòu)買國(guó)外廉價(jià)小麥的好處時(shí),卻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戰(zhàn)爭(zhēng)破壞了航運(yùn)并帶來(lái)了痛苦的面包騷亂。而戰(zhàn)后,政治家們雖然希望通過(guò)補(bǔ)貼面粉廠以使社會(huì)平靜,但小麥的產(chǎn)量依然未能增加,因此糧食短缺的情況未能消除[12]139。這樣的環(huán)境讓佩索阿感到國(guó)家和人民處在一種水深火熱的極端生存境遇中,因農(nóng)業(yè)發(fā)展滯后而帶來(lái)的嚴(yán)重社會(huì)問(wèn)題使人與人之間互相攻訐以致于國(guó)家頻頻出現(xiàn)暴亂。每個(gè)人為了保證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斷被物質(zhì)所奴役甚至異化,而物質(zhì)上的極度匱乏更不可能使人們?nèi)ふ异`魂的真正歸依之處。此時(shí)的佩索阿對(duì)久未走出經(jīng)濟(jì)危機(jī)的葡萄牙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迷茫,對(duì)深處生存困境的人們感到痛苦和無(wú)奈。于是,在《守羊人》中,詩(shī)人借助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之口,說(shuō)出了這樣的話:“昨天下午,一個(gè)城里的男人/……/談到受苦的工人,/談到長(zhǎng)久的工作,談到挨餓的人,/談到富人,說(shuō)他們對(duì)此漠然無(wú)視。”“然后,他注視著我,看到我眼中的淚水,”[1]69“那男人沉默了,他看著落日。”[1]71在面臨痛苦與無(wú)奈中,他想極力擺脫一切束縛,渴望回到那種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中,這里沒(méi)有因食物緊缺而導(dǎo)致的廝殺爭(zhēng)搶,只有遠(yuǎn)離塵世喧囂、靜謐恬淡的自然風(fēng)光,而無(wú)思觀看的牧羊人也便暗示了佩索阿想要通過(guò)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方式讓自己超脫現(xiàn)實(shí)中的一切苦楚,從而達(dá)到一種最本真、最本己的絕對(duì)自由狀態(tài)。因此,可以這樣認(rèn)為,佩索阿對(duì)這一異名的塑造一方面體現(xiàn)出他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悲觀主義傾向,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出他對(duì)靈魂安頓之鄉(xiāng)的呼喚和向往之情,“愿我的生命變成一架牛車,/一大清早,在大路上吱嘎吱嘎的駛來(lái),/從哪里來(lái),再回哪里去,/夜色深沉,行在同一條大路。”[1]44“我不必?fù)碛邢M抑槐仨殦碛熊囕啞盵1]45同時(shí)也是他對(duì)現(xiàn)實(shí)苦難和生命悲劇意識(shí)的一種勇敢超越。
然而,佩索阿的這種審美超越途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yàn)樗囆g(shù)的觀審方式只能給生存本質(zhì)的痛苦提供暫時(shí)性的避難場(chǎng)所,并不能達(dá)到徹底擺脫意志的目的。現(xiàn)實(shí)世界盡是充滿了太多的心酸和悲劇,所以在異名阿爾伯特·卡埃羅的筆下,出現(xiàn)了“穿著如乞丐的圣母”和“被虐待的兒童”[1]49等,雖然這是佩索阿為爭(zhēng)取幸福不斷抗?fàn)幍姆绞剑⒉荒鼙3忠环N持久永恒的快樂(lè),更不能使世間的人們真正意義上地?fù)碛凶约合胍耐昝郎睿皇菚簳r(shí)地舍棄和懸擱了厚重深沉、無(wú)法改變的生命悲劇性存在。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佩索阿的審美直觀雖然能使人暫時(shí)獲得心理上的絕對(duì)自由和享受,給焦慮不安的靈魂片刻喘息的機(jī)會(huì),但這終究還是否定了人的社會(huì)性和歷史性,嚴(yán)重脫離了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實(shí)際狀況,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xiàn)出佩索阿的逃避心理。這種逃避卻是不切實(shí)際的,所以才有這樣的感嘆——“做自己,只看能看到的一切,真是一件難事!”[1]61因此,這種審美直觀超越方式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然而,這并不影響佩索阿的偉大,因?yàn)樗撊松纯嗟膹?qiáng)烈渴求體現(xiàn)出他對(duì)國(guó)家、人民生存困境的深切觀照和對(duì)人類生命本質(zhì)悲劇性的關(guān)懷,盡管這種方式顯得那么虛幻和不切實(shí)際,而正是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讓我們感受到了佩索阿的一種崇高美和悲壯美。
《守羊人》中的“無(wú)思觀看”實(shí)際上是一種藝術(shù)的審美直觀方式,它向讀者展示出佩索阿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悲觀主義傾向,同時(shí)也顯現(xiàn)出他對(duì)人的極端生存境遇和生命本質(zhì)痛苦超脫的熱切追求。雖然這種超脫方式只是一種暫時(shí)性的安慰,但佩索阿對(duì)于祖國(guó)和人民艱難處境的真切關(guān)懷深深打動(dòng)了無(wú)數(shù)讀者的心。與以往研究成果相比較而言,本文嘗試在審美直觀方面結(jié)合叔本華的理論和莊子的思想進(jìn)行探討,同時(shí)結(jié)合了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具體的生活時(shí)代背景對(duì)其作品中的思想進(jìn)行分析,希望有利于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國(guó)內(nèi)翻譯文學(xué)中的這位邊緣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