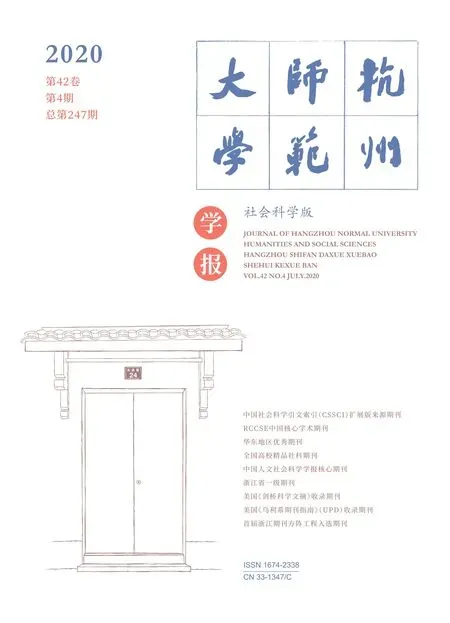葉公超的比較文學(xué)思想研究
凌淑珍
(1.清華大學(xué) 外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系,北京 100084 ;2.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 外語(yǔ)系,陜西 咸陽(yáng) 712100)
近年來(lái),國(guó)內(nèi)對(duì)葉公超的研究逐漸呈現(xiàn)遞增態(tài)勢(shì),這些研究集中在他的教學(xué)思想、詩(shī)學(xué)和對(duì)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介紹等方面。然而少有的幾篇介紹葉公超比較文學(xué)思想的論文尚未秉承葉公超對(duì)文本的細(xì)讀宗旨,缺乏從作品出發(fā)去深度探究葉公超的比較文學(xué)思想。葉公超秉承以作品為中心的理念與他所接受的人文教育以及劍橋?qū)W術(shù)傳統(tǒng)密不可分。1924-1926年葉公超求學(xué)于劍橋大學(xué),并獲得文藝心理學(xué)的碩士學(xué)位。在劍橋期間,他深受當(dāng)時(shí)學(xué)術(shù)多產(chǎn)的李維斯、瑞恰慈、燕卜遜、艾略特的影響,反對(duì)印象式批評(píng),排斥空洞的概念和理論,主張作品的細(xì)讀和批評(píng)的準(zhǔn)確性等。受葉公超細(xì)讀作品的啟發(fā),本文采用歷史分期的思路,嘗試細(xì)察葉公超的作品,分析他的比較文學(xué)思想。
一、比較文學(xué)意識(shí)的覺(jué)醒
自成立起,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就一直具有濃厚的比較文學(xué)氛圍。1925年9月,清華大學(xué)增辦大學(xué)部。1926年,西洋文學(xué)系成立,王文顯任系主任,設(shè)有英文門、德文門和法文門。1926年吳宓代系主任,仿照美國(guó)芝加哥大學(xué)和哈佛大學(xué)比較文學(xué)系的培養(yǎng)方案和課程設(shè)置,擬定了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的辦系方針和課程計(jì)劃。在《外國(guó)語(yǔ)文學(xué)系學(xué)程一覽》開(kāi)篇的課程總則中,吳宓提出了清華外文系5個(gè)培養(yǎng)目標(biāo):本系課程編制之目的為:“使學(xué)生將能 (甲) 成為博雅之士; (乙) 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 (丙) 熟讀西方文學(xué)之名著,諳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國(guó)內(nèi)教授英、德、法各國(guó)語(yǔ)言文字及文學(xué),足以勝任愉快; (丁)創(chuàng)造今日之中國(guó)文學(xué); (戊) 匯通東西之精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布”[1](P.315)。這個(gè)培養(yǎng)目標(biāo)下的課程設(shè)置展現(xiàn)了“博雅”與“專精”兩個(gè)原則。課程設(shè)置要求本系學(xué)生第一年起就研修法、德第二外國(guó)語(yǔ),故本系學(xué)生法、德兩種第二外國(guó)語(yǔ)必須研修4年(1935年開(kāi)始規(guī)定第二年研修第二外國(guó)語(yǔ))。另外,大一課程以中西文史為核心,兼顧數(shù)理化生,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國(guó)文的學(xué)習(xí),使學(xué)生熟悉西洋文學(xué)和中國(guó)文學(xué),從而匯通中西。就此而言,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的課程設(shè)置可謂中西合璧、文理兼修、專精結(jié)合。這種辦學(xué)理念和實(shí)踐成為清華大學(xué)“中西融匯、古今貫通、文理滲透”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華大學(xué)這種博雅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有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比較意識(shí),形成對(duì)中西語(yǔ)言文學(xué)的整體認(rèn)識(shí),從而最終促成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在清華大學(xué)最早萌芽。在第一代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學(xué)人中,出身于華僑家庭的王文顯基于他的多種語(yǔ)言文化背景,用英語(yǔ)編寫(xiě)戲劇,向西方傳播正面的中國(guó)形象和中國(guó)風(fēng)情,為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做出了貢獻(xiàn)。王文顯師從耶魯大學(xué)戲劇大師喬治·皮亞斯·貝克(George Pierce Baker)教授。1927年,他用英語(yǔ)創(chuàng)作了《北京政變》。該劇在美國(guó)成功上演,獲得貝克教授的盛贊:“自從西方接觸中國(guó)以來(lái),外人曾經(jīng)努力表達(dá)各方面的中國(guó)生活,傳教士、官員、游歷者和小說(shuō)家,在文學(xué)上和舞臺(tái)上,出奇制勝,刻畫(huà)中國(guó),因?yàn)椴⒉还Y(jié)局大多數(shù)人對(duì)于中國(guó)人形成一種定型的看法:刺激、邪惡、古怪,但《北京政變》努力表現(xiàn)中國(guó)人民的生動(dòng)的風(fēng)俗人情,可能盡一份力克服西方人士的誤解。”[2](P.172)1929年,王文顯的英文三幕劇《委曲求全》(SheStoopstoCompromise)在耶魯大學(xué)戲劇學(xué)院再次成功上演。除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王文顯給學(xué)生講授莫里哀的《吝嗇鬼》、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等現(xiàn)代戲劇。與王文顯不同,在哈佛大學(xué)獲得比較文學(xué)碩士的吳宓掌握多種語(yǔ)言,教授《柏拉圖》《文學(xué)與人生》等古典文學(xué)課程和《中西詩(shī)之比較》《世界文學(xué)史》等比較文學(xué)以及中西方哲學(xué)比較課程。他反對(duì)某一國(guó)別研究,主張打通外語(yǔ)專業(yè)和中文學(xué)科界限,用比較方法審視中西方文化。他不僅比較了中西方有關(guān)音樂(lè)的詩(shī)歌,華茲華斯與陶淵明的相似性,而且他采用比較的方法得出結(jié)論:《紅樓夢(mèng)》勝過(guò)任何一部西方小說(shuō)。
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的比較研究氛圍離不開(kāi)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科的研究經(jīng)驗(yàn)。眾所周知,清華大學(xué)的人文學(xué)科一直以比較傳統(tǒng)和跨學(xué)科研究著稱。陳寅恪和馮友蘭等人在歷史和哲學(xué)等方面進(jìn)行了卓有成效的比較研究。陳寅恪和吳宓雖然治學(xué)方向相異,但關(guān)系甚好。陳寅恪的《與劉叔雅論國(guó)文試題書(shū)》發(fā)表在吳宓創(chuàng)辦的 《大公報(bào)·文學(xué)副刊》上,繼而又刊登在吳宓主辦的《學(xué)衡》雜志上。和老師吳宓一樣,浦江清雖然大學(xué)期間主攻西方文學(xué),但是由于畢業(yè)后他做了陳寅恪助手,也一樣受到陳寅恪影響,極重中國(guó)舊學(xué)。此外,時(shí)任清華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在增加古典文學(xué)課程的同時(shí),并沒(méi)有減少比較文學(xué)課程。[3](P.193)
葉公超受益于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科的比較傳統(tǒng),比較成功地從前期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和文化的淺薄認(rèn)知轉(zhuǎn)變?yōu)橐晃槐容^文學(xué)學(xué)者。葉公超吸納王文顯和吳宓等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老一輩學(xué)者的比較意識(shí),發(fā)揮他在歐美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優(yōu)勢(shì),推動(dòng)中國(guó)文學(xué)的新舊傳承、中西方文學(xué)互鑒,有效解決新時(shí)期中國(guó)新文學(xué)發(fā)展中的諸多問(wèn)題,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的“清華學(xué)派”。葉公超9歲起就留學(xué)美國(guó),除了中途短期回國(guó)之外,他先后在英美國(guó)家的中學(xué)、大學(xué)接受了10年西學(xué)教育。這樣的學(xué)習(xí)經(jīng)歷不免使他和中國(guó)傳統(tǒng)產(chǎn)生隔閡。1926年他從劍橋大學(xué)獲得文學(xué)碩士學(xué)位,回國(guó)在東南大學(xué)任教時(shí),校長(zhǎng)鄭洪年曾稱他為“外國(guó)名士派”。此話不虛。1929年,葉公超正式任職清華。據(jù)梁實(shí)秋回憶:“本來(lái)他(葉公超)不擅中文,而且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的認(rèn)識(shí)也不夠深。聞一多先生常戲謔的呼他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的精通洋文不懂國(guó)故。”[4](P.11)顯然,葉公超受了刺激,開(kāi)始惡補(bǔ)中國(guó)文學(xué),通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研習(xí),不久他就成了“十足的中國(guó)文人”。同時(shí),葉公超開(kāi)始對(duì)比較文學(xué)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1929年夏至1934年夏,他任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教授,開(kāi)設(shè)一、二、三年級(jí)的英文課、英國(guó)散文、現(xiàn)代英美詩(shī)、18世紀(jì)文學(xué)、文學(xué)批評(píng)和翻譯等課程之外,還開(kāi)設(shè)中國(guó)新詩(shī)中的西洋背景等比較文學(xué)課程。
1929年任職清華大學(xué)之后,葉公超開(kāi)始和清華大學(xué)人文學(xué)科具有比較意識(shí)的學(xué)者朝夕相處,深受清華大學(xué)自由開(kāi)放和充滿人文主義的學(xué)術(shù)氛圍的熏染。1931年自徐志摩逝世后,葉公超承擔(dān)了《新月》最后6期的編輯工作,1934年又與聞一多等合作創(chuàng)辦《學(xué)文》,推介清華大學(xué)師生的作品,刊登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錢鐘書(shū)的《論不隔》(《談藝錄》的先聲)等。他與《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主編沈從文、《文學(xué)雜志》主編朱光潛過(guò)從甚密,積極參加朱光潛等組織的讀詩(shī)會(huì)。在清華大學(xué),吳宓是公認(rèn)的“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之父”。自1926年回國(guó),葉公超就與他相識(shí)。葉公超和吳宓在清華大學(xué)是同事,葉公超受到吳宓的比較文學(xué)意識(shí)的影響自不待言。據(jù)梁實(shí)秋記載:“(葉公超)住藤荷西館,與吳雨僧(吳宓)為比鄰。一浪漫,一古典,而頗為相得。”[4](P.11)據(jù)吳宓日記記載,葉公超和吳宓兩人共同承擔(dān)一些課程,而且經(jīng)常串門,吳宓甚至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在葉公超家搭伙吃飯。1929年之后,葉公超投入到比較文學(xué)研究上,同時(shí)倡導(dǎo)將外國(guó)文學(xué)人才的培養(yǎng)定位在為中國(guó)語(yǔ)言和文學(xué)服務(wù)。根據(jù)葉公超的學(xué)生常風(fēng)回憶,有一次葉公超教導(dǎo)他說(shuō),咱們學(xué)外語(yǔ)的人總須另找個(gè)安身立命之處。只教外文,講外國(guó)文學(xué),不過(guò)是做介紹,傳播外國(guó)文化的工作。這固然重要,可是應(yīng)該利用從外國(guó)學(xué)來(lái)的知識(shí)在中國(guó)語(yǔ)言和文學(xué)方面多鉆研。[5](P.58)這可以視為葉公超比較文學(xué)思想的自覺(jué)表現(xiàn)。
二、從比附西學(xué)到中西比較
任教清華大學(xué)之前,葉公超著力歐美文學(xué)評(píng)論,先后發(fā)表以下文章:1926年6月在《晨報(bào)副鐫·戲刊》上發(fā)表《辛額》(JohnM.Singe)、1928年3月在《新月》上發(fā)表《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的命運(yùn)》、1928年9月在《新月》上發(fā)表《牛津字典的貢獻(xiàn)》。在《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的命運(yùn)》中,他將福樓拜等法國(guó)小說(shuō)和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英美現(xiàn)代小說(shuō)進(jìn)行比較,從而辨識(shí)出這些現(xiàn)代小說(shuō)呈現(xiàn)的冷靜的客觀主義和對(duì)全人類的普遍同情的特征。在這段時(shí)間,他局限于英、美、法等歐美文學(xué)之間的比較,這和常年在清華大學(xué)外文系講授“比較文學(xué)”的溫德教授類似。在《牛津字典的貢獻(xiàn)》一文中,葉公超詳細(xì)介紹了《牛津字典》的編撰過(guò)程和特點(diǎn),同時(shí)指出《說(shuō)文解字》《康熙字典》《辭源》等中國(guó)辭典在體制和細(xì)節(jié)等方面都遠(yuǎn)不及《牛津字典》。同樣,《辛額》這篇評(píng)論再次展現(xiàn)了他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和文化的淺薄以及對(duì)西方文學(xué)的盛贊。他詳盡介紹了辛額這位愛(ài)爾蘭作家的作品和性情,但在文章末尾,他只是用寥寥數(shù)語(yǔ)呼吁中國(guó)作家需要多“注意于方言和村民的各種信仰與傳說(shuō),用同情的態(tài)度和他們一同度生活,方可以得著民族的自然精神”[6](P.110)。雖然此時(shí),胡適已經(jīng)在北京大學(xué)等地展開(kāi)收集民謠等工作,但是葉公超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如火如荼的文化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卻一無(wú)所知,更談不上像胡適、朱自清等學(xué)人那樣借鑒西方詩(shī)歌來(lái)發(fā)展中國(guó)文學(xué)。由于缺乏國(guó)學(xué)背景和比較文學(xué)意識(shí),僅僅有西學(xué)背景的葉公超無(wú)力化解中西文學(xué)、新舊文學(xué)溝通互鑒的難題,而只能參照、比附西學(xué)。
1929年之后,葉公超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展現(xiàn)了他開(kāi)始摒棄此前所懷有的比附西學(xué)心態(tài)。在《文學(xué)的雅俗觀》一文中,他大量引證了古人品藻詩(shī)文的標(biāo)準(zhǔn):姚惜抱與陳碩士、歸震川與沈敬夫的書(shū)信,《論語(yǔ)》《周禮》《孟子》中的諸多論述以及劉海峰的《論文偶記》等。他指出這些文學(xué)體現(xiàn)了恰當(dāng)?shù)难潘子^。他揭示出諸多西方著名批評(píng)家所使用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名詞并非我們想象的具體和切實(shí)。在文尾,他強(qiáng)調(diào)王爾德、蕭伯納和韋爾士的文學(xué)作品中存在的“俗”在于“過(guò)分表露情感”。在1933年3月發(fā)表于《新月》第4卷第6期上的《論翻譯與文字的改造——答梁實(shí)秋》中,葉公超認(rèn)為翻譯的問(wèn)題不在于直譯、曲譯和硬譯,而在于沒(méi)有絕對(duì)正確的翻譯。“世界各國(guó)的語(yǔ)言文字,沒(méi)有任何一種能單獨(dú)的代表整個(gè)人類的思想的。任一種文字比之他種都有缺點(diǎn),也都有優(yōu)點(diǎn),這是很顯明的。從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譯到中文都可以使我們感覺(jué)中文的貧乏,同時(shí)從中文譯到任何西洋文字又何嘗不使譯者感覺(jué)到西洋文字之不如中國(guó)文字呢?就是西洋文字彼此之間只怕也有同病相憐之感吧!”[6](PP.152-153)在葉公超看來(lái),由于不同的文明發(fā)展有差異,所以文字并無(wú)優(yōu)劣之分。
葉公超憑借他對(duì)英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造詣和掌握英法兩種語(yǔ)言的優(yōu)勢(shì),不僅醉心于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和英美新批評(píng)的研究,更是將中國(guó)文學(xué)作品與抽象的西方文學(xué)理論結(jié)合,將中西方文學(xué)比較,從而將西方理論本土化。在《談讀者的反應(yīng)》中,他舉證中國(guó)宣紙來(lái)解釋莫泊桑所持的“不受任何成見(jiàn)的心靈”的觀念。“當(dāng)然,最理想的是我們的心靈(mind)在閱讀的時(shí)候能像一張舊宣紙一般地靈敏。最好的舊宣紙必是礬棉生熟的成分最相稱的,所以才能顯出筆墨間種種細(xì)微的差別。它不只能吸收墨色,而且能忠實(shí)地透出各種運(yùn)筆的方法(即董其昌所謂劣紙有墨無(wú)筆之意),使善書(shū)者全分的精力與技能都現(xiàn)身于紙面。” [6](P.39)從跨學(xué)科視野出發(fā),在贊揚(yáng)宣紙和國(guó)畫(huà)的單純的同時(shí),葉公超采用比較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了文學(xué)作品會(huì)受到讀者反應(yīng)的影響,以及讀者和作者的情感經(jīng)驗(yàn)難于同一的現(xiàn)實(shí)復(fù)雜性。為了揭示源于西方的讀者反應(yīng)理論,他首先列舉了讀者對(duì)柳宗元《江雪》這首五言絕句可能會(huì)產(chǎn)生的三種直覺(jué):人道、美觀和訓(xùn)世;然后懇請(qǐng)讀者縱觀柳宗元的年譜和作者的生活情況,以此考證這首詩(shī)的整體意義和柳宗元對(duì)世態(tài)凄涼的感慨。總之,通過(guò)把西方理論放置在中國(guó)古詩(shī)的大語(yǔ)境中去審視,葉公超有效地傳達(dá)了來(lái)自西方的讀者反應(yīng)理論的復(fù)雜之處。
葉公超不滿足于使用中國(guó)文學(xué)來(lái)印證西方理論。他還從比較出發(fā),立足于中國(guó)文學(xué)的博大精深,用我國(guó)悠久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以獨(dú)特的見(jiàn)解和洞察力來(lái)豐富、補(bǔ)充、重估西方文學(xué)研究的成果。雖然他對(duì)瑞恰慈的理論極為推崇,但是在1934年7月發(fā)表于《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的《現(xiàn)實(shí)世界與藝術(shù)世界》一文中,他指出:“英國(guó)批評(píng)家瑞恰慈在他的《科學(xué)與詩(shī)》里說(shuō)文學(xué)是人對(duì)于外界一種情感的滿足。這話說(shuō)得未免太不著邊際一點(diǎn)。”[6](P.33)葉公超并不滿足于用瑞恰慈的西方觀念來(lái)分析和解釋中國(guó)文學(xué)。他認(rèn)為文學(xué)的價(jià)值不僅在于它可以滿足讀者的情感訴求,而且可以滿足他們的理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來(lái)理解他的觀點(diǎn)。首先,他指出,當(dāng)我們閱讀《水滸傳》時(shí),“我們讀著只感覺(jué)自己深入了另一個(gè)世界,而這里的一切恰都合于我們的理智與情感條件” [6](P.34)。對(duì)葉公超而言,雖然施耐庵創(chuàng)作《水滸傳》是主觀的,但又是合乎作家的理智與情感條件的。他認(rèn)為,一個(gè)有判斷力和有情感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一部分動(dòng)機(jī)是由于他們想充分認(rèn)識(shí)復(fù)雜的現(xiàn)實(shí)世界。當(dāng)現(xiàn)實(shí)無(wú)法滿足作家的理智和情感時(shí),他們就會(huì)根據(jù)所接觸的生活,通過(guò)創(chuàng)作來(lái)創(chuàng)造、翻造一個(gè)符合他們的理智與意愿的藝術(shù)世界來(lái)替代現(xiàn)實(shí)。同時(shí),他指出藝術(shù)世界的真實(shí)性和生命力不僅是由于藝術(shù)家主觀地創(chuàng)造一個(gè)符合他自身的理智與情感的藝術(shù)世界,而且藝術(shù)還要符合廣大讀者、一般人的理智與情感世界。他贊譽(yù)施耐庵的作品不僅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符合作家本人的主觀世界,而且這些作品符合廣大讀者的理智和情感。他不僅關(guān)注藝術(shù)的自足性,而且主張藝術(shù)與時(shí)代、大眾的生活體驗(yàn)、廣大讀者的情感以及理智密不可分。他辯證地看待藝術(shù)的主觀性和客觀性、感性和理性之間的關(guān)系。為此,他教導(dǎo)學(xué)生在創(chuàng)作時(shí),一定要擴(kuò)大生活經(jīng)驗(yàn),這樣讀者才能從理智和情感上去理解和感應(yīng)。在他指導(dǎo)和修改季羨林書(shū)寫(xiě)的《年》這篇散文時(shí),他建議作品要超出個(gè)人狹隘世界,要有“擴(kuò)大意識(shí)”。要將作家個(gè)人觀念和情感擴(kuò)大到一般人的世界。他認(rèn)為藝術(shù)作品影響到廣大讀者之后,藝術(shù)才會(huì)有真實(shí)性和生命力。
三、葉公超與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píng)
葉公超用比較方法研究中國(guó)文學(xué),使他能夠超越胡適和梁實(shí)秋等人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作家做出更為完整和公正的評(píng)價(jià)。在19世紀(jì)30年代吳宓和許多文人交惡之時(shí),1931年吳宓創(chuàng)辦的《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刊登了葉公超的《志摩的興趣》。他認(rèn)為徐志摩的詩(shī)也許不及他崇拜的雪萊,但是其幽默卻遠(yuǎn)在雪萊之上。在葉公超看來(lái),雪萊時(shí)時(shí)刻刻不忘是是非非的爭(zhēng)斗,理想和現(xiàn)實(shí)的沖突,不免缺乏相當(dāng)?shù)挠哪O喾矗熘灸Ρ拘缘募冋妫瑢?duì)一切生活的熱愛(ài)和毫無(wú)怨恨之性情,使他超越平凡、追求遠(yuǎn)大理想的同時(shí),還能夠領(lǐng)略人生的趣味。這種平行研究促使人們超越浪漫主義概念的束縛,從文本出發(fā)去深入了解徐志摩。葉公超不僅用比較的方法客觀評(píng)價(jià)了他的好友徐志摩,而且也用比較思維公正評(píng)價(jià)了和他政治思想相異的魯迅,他指出:“五四之后,國(guó)內(nèi)最受歡迎的作者無(wú)疑的是魯迅。”[6](P.97)梁實(shí)秋以及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倡導(dǎo)者胡適雖是葉公超的好友,但對(duì)葉公超的上述評(píng)價(jià)甚為不滿。他們都從歐美留學(xué)回國(guó),并均從事平行比較實(shí)踐,他們卻對(duì)魯迅的評(píng)價(jià)殊異。他們對(duì)魯迅評(píng)價(jià)的差異與他們的比較文學(xué)觀的不同大體一致。在《文學(xué)改良芻議》(1917)、《我們對(duì)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1926)、《試評(píng)所謂中國(guó)本位的文化建設(shè)》(1935)等文章中,胡適呼吁國(guó)人承認(rèn)中國(guó)物質(zhì)文明不及西方的事實(shí),并且虛心接受西方及它背后的精神文明,從而更新中華文明。胡適的《論新詩(shī)》(1919)更是多次援引西方例證來(lái)佐證中國(guó)新詩(shī)的合法性。在此意義上,胡適主張采用比較的方法來(lái)吸取他者的長(zhǎng)處,從而推動(dòng)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無(wú)獨(dú)有偶,梁實(shí)秋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之浪漫的趨勢(shì)》中用西方文學(xué)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的框架,反思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浪漫和任性,批評(píng)其缺乏建構(gòu)文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魯迅和左翼作家對(duì)梁實(shí)秋有關(guān)文學(xué)與抗戰(zhàn)以及文學(xué)與人性方面的見(jiàn)解曾發(fā)表過(guò)尖銳的批評(píng)。與胡適、梁實(shí)秋不同,葉公超用比較方法來(lái)研究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問(wèn)題,對(duì)于魯迅的評(píng)價(jià)卻更為公正和客觀。他認(rèn)為一方面,由于魯迅的易怒性格容易使他摒棄初始的冷靜諷刺,而走向謾罵境界,所以他不及斯威夫特顯示的理智和冷靜;另一方面,受制于18世紀(jì)英國(guó)禮貌風(fēng)氣的斯威夫特講究禮貌,壓制個(gè)性,缺乏魯迅特有的抒情。“這種‘沉靜下去了’的感傷情調(diào)是魯迅的一種特色。斯偉(威)夫特則不但沒(méi)有這種的表現(xiàn),而且在《論優(yōu)良禮貌與修養(yǎng)》里曾表示對(duì)于描寫(xiě)自己的悲哀的輕視。”[6](P.100)雖然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葉公超弱化了魯迅的反抗姿態(tài),對(duì)魯迅作品進(jìn)行了誤判,但是葉公超超越時(shí)空的平行研究,以外來(lái)資料來(lái)填充本土框架,增加了我們對(duì)魯迅的了解。魯迅與斯威夫特的比較研究展現(xiàn)了葉公超對(duì)比較對(duì)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認(rèn)識(shí),避免主觀任意和似是而非之嫌。他深諳斯威夫特書(shū)寫(xiě)《一個(gè)小小的建議》(AModestProposal)時(shí)展現(xiàn)的冷靜諷刺的原因在于,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模仿法國(guó)要求在生活和寫(xiě)作中講究禮貌。由于他搜集到充分的史料和證據(jù),并且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斷能力和綜合貫通的眼界,葉公超將看似沒(méi)有接觸和相互影響的不同時(shí)代和國(guó)家的人物進(jìn)行比較,避免了一般平行比較和簡(jiǎn)單類比的牽強(qiáng)附會(huì)、隔靴撓癢之嫌,更使得他對(duì)魯迅為代表的白話散文和徐志摩為代表的中國(guó)新詩(shī)等中國(guó)文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絲毫不遜色于他早期對(duì)外國(guó)文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
葉公超利用學(xué)到的西方現(xiàn)代文學(xué)知識(shí)來(lái)補(bǔ)充和豐富中國(guó)新文學(xué)研究。20世紀(jì)30年代,以艾略特和伍爾芙(Virginia Woolf)為代表的英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在西方受到排斥。《細(xì)察》(Scrutiny)雜志的評(píng)論家布雷德·布魯克(M.C.Bradbrook)批評(píng)伍爾芙僅僅給予主要的情境一些反思性的、間接的呈現(xiàn)(reflected,indirect presentation)[7](P.344),但是此時(shí)英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卻意外地在中國(guó)受到歡迎。葉公超被公認(rèn)為是中國(guó)第一個(gè)向國(guó)人介紹艾略特等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學(xué)者。在劍橋大學(xué)讀書(shū)期間,葉公超曾得到過(guò)艾略特的賞識(shí)。作為艾略特的信徒,他不僅寫(xiě)過(guò)《艾略特的詩(shī)》《再論艾略特的詩(shī)》,還指導(dǎo)卞之琳翻譯了艾略特重要的論文《傳統(tǒng)與個(gè)人的才能》,為趙蘿蕤翻譯的《荒原》作序。除此之外,他還書(shū)寫(xiě)《墻上一點(diǎn)痕跡譯者識(shí)》介紹伍爾芙,發(fā)表《曼殊菲爾的信札》介紹曼斯菲爾德。“葉公超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應(yīng)當(dāng)引起我們更多思考的, 是在中國(guó)的語(yǔ)境中如何闡釋和研究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xué)與批評(píng),并轉(zhuǎn)換應(yīng)用于中國(guó)文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建構(gòu)上。”[8](P.191)葉公超等學(xué)人在20世紀(jì)30年代借鑒歐美現(xiàn)代文學(xué),尤其是艾略特的古今錯(cuò)綜意識(shí)為中國(guó)文學(xué)的古今彌合問(wèn)題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他借助艾略特的比較方法,推動(dòng)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北伐運(yùn)動(dòng)后,中國(guó)文學(xué)尤其是古典文學(xué)傳統(tǒng)無(wú)法和新文學(xué)匯通。此時(shí)中國(guó)的外文系肩負(fù)時(shí)代使命,思考由中心走向邊緣的中國(guó)該如何在新的世界文學(xué)和世界體系中求生存,他針砭中國(guó)新文學(xué)沉溺于抒發(fā)個(gè)人情緒的“西化”之濫觴,喚醒中國(guó)新文學(xué)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自知。
我們可以從新詩(shī)和白話散文兩個(gè)方面來(lái)具體考察葉公超對(duì)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貢獻(xiàn)。在《論新詩(shī)》中,葉公超反對(duì)當(dāng)時(shí)興盛的“新詩(shī)是從舊詩(shī)的鐐銬里解放出來(lái)的”之說(shuō),也質(zhì)疑聞一多對(duì)嚴(yán)格格律的堅(jiān)信。他指出“我們新詩(shī)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據(jù)我們說(shuō)話的節(jié)奏,一方面要切近我們的情緒的性質(zhì)。西洋的格律決不是我們的‘傳統(tǒng)的拍子’,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詩(shī)詞又是建筑在另一種文字的節(jié)奏上的,所以我們現(xiàn)在的詩(shī)人都負(fù)著特別重要的責(zé)任:他們要為將來(lái)的詩(shī)人創(chuàng)設(shè)一種格律的傳統(tǒng),不要一味羨慕人家的新花樣”[6](P.51)。葉公超主張中國(guó)新詩(shī)要借鑒中國(guó)古代詩(shī)歌的格律形式,認(rèn)為格律是變化的起點(diǎn)和歸宿,是組織我們情緒的根據(jù)和增加我們內(nèi)在形式的力量。在新詩(shī)的形式方面,他不僅強(qiáng)調(diào)格律,而且注重詩(shī)歌的節(jié)奏和音步。
葉公超借助比較的方法,為中國(guó)新詩(shī)提出建設(shè)性的主張,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古詩(shī)里有許多新詩(shī)可以借鑒的材料,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人要擴(kuò)大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意識(shí),要大膽地閱讀古詩(shī),覺(jué)悟“他本國(guó)的心靈”[6](P.63)。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國(guó)人羨慕西方詩(shī)歌的流弊,葉公超強(qiáng)調(diào)西洋詩(shī)的所有技巧都可以在中國(guó)詩(shī)歌里找到。他察覺(jué)到,中國(guó)新詩(shī)多半受英國(guó)19世紀(jì)浪漫情緒影響,但是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文字的特殊性。“以運(yùn)用文字的技巧而論,中國(guó)詩(shī)詞至少是不低于任何西洋詩(shī)。”[6](P.53)他以杜甫的《月夜》為例,指出中國(guó)古詩(shī)里最有詩(shī)意的特殊隱喻在任何西洋文字和中國(guó)白話里都不易有同樣的辦法。他引用《文心雕龍》來(lái)說(shuō)明中國(guó)古詩(shī)講究字音彼此的合作。他揭示出追求音樂(lè)性的中國(guó)文字和西洋文字之間的差異,在《音節(jié)與意義》文中,葉公超認(rèn)為丁尼生(Tennyson)詩(shī)歌中的音樂(lè)性太濃厚,破壞了意義的表達(dá),贊揚(yáng)徐志摩的《火車禽住軌》詩(shī)中節(jié)奏與火車奔馳呼應(yīng)的情景,指出卞之琳及其何其芳常用的平淡、從容的節(jié)奏和所表達(dá)的思想極為和諧。在比較研究中,葉公超建議“詩(shī)人的情緒與經(jīng)驗(yàn)上確應(yīng)當(dāng)多多的增加本色或土色的表現(xiàn)。我感覺(jué),新詩(shī)人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設(shè)法移種外來(lái)的影響,不是采花而是移種,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多接觸中國(guó)的東西,多認(rèn)識(shí)中國(guó)的事情”[6](P.72)。葉公超辯證地指出,脫胎于西方的中國(guó)新詩(shī)需要借鑒西方資源的同時(shí),還要借鑒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特有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葉公超對(duì)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貢獻(xiàn)還在于他對(duì)魯迅為代表的中國(guó)白話散文的客觀評(píng)價(jià)上。魯迅去世后。葉公超發(fā)表《談白話散文》(1939)一文,基于比較中文和西洋文字之間的殊異,他揭示出魯迅散文的特色。他認(rèn)為中國(guó)文字的力量在語(yǔ)詞上,而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在句子或段落的結(jié)構(gòu)上。他還特意指出魯迅的文字特色正是在于語(yǔ)詞的力量。葉公超和朱光潛屬于當(dāng)時(shí)少有的從中西方語(yǔ)言的比較出發(fā)去評(píng)析中國(guó)文學(xué)的語(yǔ)言問(wèn)題的學(xué)者。雖然葉公超未曾提及魯迅以及中國(guó)歷來(lái)在句法上的造詣,但是“這在‘五四’以后受歐化影響而依賴日趨僵硬單一的語(yǔ)法構(gòu)造的白話文世界,還是具有糾偏作用的,尤其是可以彌補(bǔ)片面追求句法效果而不知練字的不足”[9](P.50)。
葉公超從艾略特為代表的歐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中吸取一種比較意識(shí),并自覺(jué)地運(yùn)用這種比較觀念和外國(guó)知識(shí)來(lái)鉆研中國(guó)文學(xué),來(lái)重新審視唐宋文學(xué)為代表的中國(guó)文學(xué)和文化。在《艾略特的詩(shī)》和《再論艾略特的詩(shī)》中,葉公超發(fā)現(xiàn)艾略特將英國(guó)17世紀(jì)玄理派與法國(guó)19世紀(jì)象征派進(jìn)行比較,“就是用兩種性質(zhì)極端相反的東西或印象來(lái)對(duì)較,使它們相形之下益加明顯……這種對(duì)較的功用是要產(chǎn)生一種驚奇的反應(yīng),打破我們習(xí)慣上的知覺(jué),使我們從驚奇而轉(zhuǎn)移到新的覺(jué)悟上”[6](P.122)。他探究到艾略特將兩個(gè)毫不相干的東西進(jìn)行比較,從而使讀者產(chǎn)生異樣的聯(lián)想。受艾略特的比較思想啟發(fā),葉公超遂將艾略特的用典技巧和宋代的奪胎換骨之說(shuō)進(jìn)行比較,使我們頓悟中國(guó)古代高超的智慧所在。在他看來(lái),艾略特主張利用古代現(xiàn)成的典故來(lái)補(bǔ)充我們個(gè)人才能的不足,形成一種古今錯(cuò)綜感和擴(kuò)大的意識(shí),而唐宋詩(shī)詞借用古人句律卻略去原句的意義,這些真正高明的中國(guó)古代詩(shī)人借用他人的東西“熔化于一種單獨(dú)的感覺(jué)中”,創(chuàng)造一種與脫胎的原物完全不同的東西。在為趙蘿蕤翻譯的《荒原》作序中,他指出“艾略特可以說(shuō)是主張文以載道者,他的‘道’就是他在《奇異神明的追求》里所提出的tradition和orthodoxy的兩種觀念。假使他是中國(guó)人的話,我想他必定是個(gè)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者”[10](P.225)。葉公超將艾略特放置于中國(guó)文化語(yǔ)境中進(jìn)行闡釋,幫助讀者形成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覺(jué)悟。他主張中國(guó)新文學(xué)必須更多地借鑒中國(guó)古典語(yǔ)言、文化和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才能使其有所發(fā)展和突破。他將民族文學(xué)的特色、特性的保留作為比較的基礎(chǔ)。在他看來(lái),有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學(xué)這個(gè)媒介,不同民族文學(xué)之間的交流才能深入持久。概而言之,比較文學(xué)既彰顯民族文學(xué)特色又存在跨界聯(lián)絡(luò)。
四、結(jié)語(yǔ):比較文學(xué)走向人類共同命運(yùn)
葉公超的比較文學(xué)思維聚焦于他對(duì)整個(gè)人類共同命運(yùn)的體察。在葉公超看來(lái),艾略特的價(jià)值和重要性不僅在于他的古今錯(cuò)綜意識(shí),而且在于艾略特對(duì)人類共同命運(yùn)和整個(gè)人類文明前途的思量。在1934年發(fā)表的《艾略特的詩(shī)》一文中,葉公超批評(píng)馬克格里非片面推崇艾略特的天主教信仰,抹殺了艾略特在詩(shī)歌技術(shù)上的創(chuàng)新,他主張將艾略特詩(shī)歌的技術(shù)和宗教信仰分而論之。他指出:“總之,艾略特的詩(shī)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進(jìn)一步的深刻表現(xiàn)法,有擴(kuò)大錯(cuò)綜的意識(shí),有為整個(gè)人類文明前途設(shè)想的情緒,其余的一切都得從別的立場(chǎng)上去討論了。”[6](P.117)艾略特對(duì)于歐洲文明深有反思,憂心于人類發(fā)展的前途。一戰(zhàn)后,諸多英法人士對(duì)德國(guó)予以責(zé)難并肆意瓜分德國(guó)利益,這成為導(dǎo)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僅僅休戰(zhàn)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爆發(fā)的重要原因。其實(shí)艾略特早已感嘆道:“如果我們思考的只限于反對(duì)德國(guó),那么我們不會(huì)走得比1918年更遠(yuǎn)。為了超越1918年,我們必須盡力對(duì)我們自己和德國(guó)持同樣批評(píng)的態(tài)度。”[11](P.291)就此而言,鑒于對(duì)人類發(fā)展的關(guān)照,艾略特主張英法等歐洲國(guó)家要反思自身。雖然葉公超并沒(méi)有具體甄別和詳細(xì)考證艾略特作品中的世界主義元素,但是他體察到艾略特對(duì)于人類整體的憂慮和設(shè)想。今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葉公超的這一評(píng)價(jià)是公正的,具有前瞻性的。就此而言,葉公超對(duì)比較文學(xué)持有濃厚的興趣并非僅僅局限于西學(xué)中用,對(duì)于他來(lái)說(shuō),比較意識(shí)可以給學(xué)者提供一種借鑒,一種整體視野。這一見(jiàn)解在1934年發(fā)表的《從印象到評(píng)價(jià)》一文中有集中體現(xiàn)。他認(rèn)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范圍自然就變成整個(gè)人類,或整個(gè)文明的批評(píng)了。因?yàn)槲┯袕恼麄€(gè)文明的前途的眺望上,我們才可以了解生活中種種狀況的意義。” [6](P.20)他主張文學(xué)批評(píng)涉及整個(gè)人類文明,堅(jiān)信比較視野可以關(guān)注人類的整體。葉公超主張文學(xué)批評(píng)要超越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和意識(shí),將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范圍擴(kuò)展到整個(gè)人類的批評(píng),將文學(xué)批評(píng)定位在肩負(fù)整個(gè)人類文明的前途上。“批評(píng)家先要了解他自己的經(jīng)驗(yàn)的意義,……當(dāng)然,已往的經(jīng)驗(yàn)是最主要的,不過(guò)已往的經(jīng)驗(yàn)很容易給我們一種錯(cuò)覺(jué),一種個(gè)人的色彩,或自身階級(jí)的意識(shí)。這時(shí)候,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范圍自然就變成整個(gè)人類,或整個(gè)文明的批評(píng)了。因?yàn)槲┯袕恼麄€(gè)文明的前途的眺望上,我們才可以了解生活中種種狀況的意義。所以歷史上的大批評(píng)家大半都不免帶著幾分道德與訓(xùn)世的色彩。”[6](P.20)葉公超主張超越自我為中心,把“人類全體的文化”[12](P.90)看作一個(gè)整體,將本民族文化看作是人類全體文化中的一個(gè)元素而已。
葉公超對(duì)人類共同經(jīng)驗(yàn)的注重還可以追溯到瑞恰慈、燕卜遜等劍橋?qū)W派。1924-1926年求學(xué)于劍橋的葉公超與他們的交往至深。1929-1930年瑞恰慈離開(kāi)劍橋大學(xué)的教職,來(lái)到清華大學(xué)任教,與葉公超共事。在清華任教期間,瑞恰慈講授《文學(xué)批評(píng)》課程,推動(dòng)實(shí)用批評(píng)。他深感中國(guó)學(xué)生對(duì)西方文學(xué)的誤讀并非種族和智力所致,而是語(yǔ)言和傳達(dá)的問(wèn)題。這種見(jiàn)解超越了諸多西方人所持的東方主義偏見(jiàn)。正因?yàn)榇耍源嘶ㄙM(fèi)畢生精力致力于建立和普及基本英語(yǔ)(basic English),以促進(jìn)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葉公超準(zhǔn)確把握瑞恰慈的思想。在為曹葆華翻譯的《科學(xué)與詩(shī)》寫(xiě)就的序言中,葉公超指出:“ 瑞恰慈的目的,一方面是分析讀者的反應(yīng),一方面是研究這些反應(yīng)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價(jià)值……他的抱負(fù)也是要用文學(xué),尤其是詩(shī),來(lái)保障人類的將來(lái),因?yàn)樗嘈盼┯泻玫乃囆g(shù)與文學(xué)作品才能給我們最豐富、最敏銳、最活潑、最美滿的生活。我們的經(jīng)驗(yàn),不論是生活中的還是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都應(yīng)當(dāng)受同樣標(biāo)準(zhǔn)的評(píng)衡。”[6](P.147)在瑞恰慈的影響下,葉公超不僅在文學(xué)批評(píng)上致力于促進(jìn)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還在實(shí)踐中積極推動(dòng)跨文化的雙向傳播。葉公超非常賞識(shí)高徒卞之琳。詩(shī)人卞之琳的小說(shuō)《紅褲子》記載了山西八路軍游擊隊(duì)抗擊日寇的故事。葉公超將《紅褲子》翻譯成英文,轉(zhuǎn)發(fā)給燕卜遜,發(fā)表在英國(guó)雜志《人生與文章》上。就此而言,葉公超向世界傳達(dá)了勇敢頑強(qiáng)的中國(guó)形象。1937-1939年燕卜遜和葉公超一起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葉公超曾無(wú)微不至照顧燕卜遜。在任國(guó)民政府中央宣傳部國(guó)際宣傳處駐倫敦辦事處處長(zhǎng)期間,葉公超經(jīng)燕卜遜引介,認(rèn)識(shí)奧威爾。1943年9月20日應(yīng)奧威爾邀請(qǐng),給BBC錄制了英語(yǔ)講座“我希望的世界”(The World I hoped For)。
1929年葉公超任職清華大學(xué),涵養(yǎng)于清華大學(xué)比較文學(xué)氛圍。為此,他逐漸摒棄了早期對(duì)中國(guó)文化及文學(xué)的隔膜,從比較文學(xué)視角關(guān)照和反思中國(guó)新詩(shī)、小說(shuō)等的發(fā)展,用比較文學(xué)的成果推動(dòng)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葉公超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熟練運(yùn)用西方文學(xué)理論和方法來(lái)豐富、補(bǔ)充、重估西方的英美文學(xué)研究成果。他以超越時(shí)空的平行研究,用外來(lái)資料來(lái)填充本土框架,增進(jìn)我們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了解。他堅(jiān)持中國(guó)架構(gòu),保留中國(guó)傳統(tǒng),同時(shí)極力在中西文學(xué)比較中保持公正態(tài)度。他將民族文學(xué)作為比較的基礎(chǔ),認(rèn)為中國(guó)新詩(shī)和白話散文更多地受到中國(guó)古典文化的影響,主張中國(guó)新文學(xué)除了借鑒西方文學(xué)技巧之外,更多地還需要借鑒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在他看來(lái),只有通過(guò)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學(xué)這個(gè)媒介,不同民族文學(xué)之間的交流才能更深入持久。比較文學(xué)是既保持民族文學(xué)特色又存在國(guó)際聯(lián)絡(luò)的文學(xué)批評(pí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