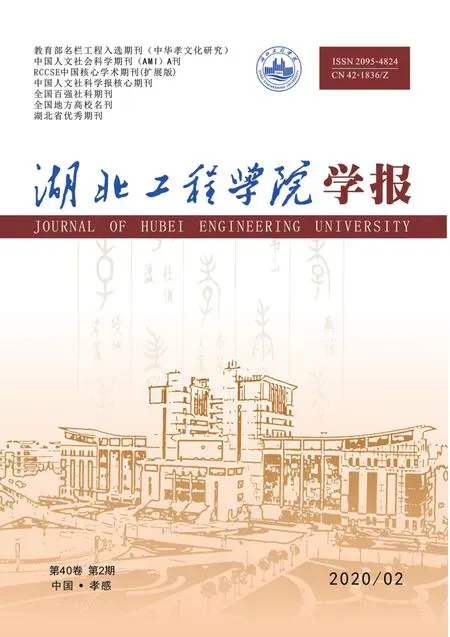“東學西漸”之蘇軾禪趣詩的美國傳播研究
黃力平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東學西漸指的是一個和西學東漸互相補充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東學西漸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對世界文化的發展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如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等。中國禪趣詩作為“東學西漸”的一項重要內容,自唐宋以降逐漸成熟并開始向國外傳播,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在研究中國禪 趣詩之前,先來看中國“禪”。“禪”是梵文“禪那”(Dhyāna)的音譯,本是古代印度宗教普遍采用的修行方法,而“中國古代那些佛教大德和好佛的知識精英們賦予了外來佛教的禪以豐富的思想內容,與本土的儒家、道家的某些內容進行結合,形成了以‘見性’、‘頓悟’為綱領的中國禪宗”[1]。可見,印度佛教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本土化”的過程,是中國人在傳統的思想文化土壤中消化吸收外來佛教的禪觀、禪法再加以發揮、創造的成果。因此,中國禪宗不同于單純的佛教佛法,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三根支柱之一(儒、道、釋),彰顯了中國人的智慧。
一、禪趣詩的介紹
禪趣詩是中國禪宗佛禪詩的一個重要分支,深圳大學錢學烈教授將“佛禪詩分為佛教勸戒詩和禪悅詩兩類。禪悅詩細分又可分為禪語禪典詩、禪理詩、禪悟詩、禪境詩和禪趣詩五種”[2]100。 華南師范大學崔大江教授認為:“禪趣詩本可歸理趣詩一類, 是理趣詩中最高境界者。”[3]28既然禪趣詩在中國禪宗詩歌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又頗能得到文人墨客們的青睞,那么何為禪趣詩呢?
錢學烈教授在她的文章中接著指出:“禪趣詩是指詩人用真性情去細心體察萬象的幽微奧妙,去分辨山水人物一切聲色的虛實真偽,并與萬物混然冥合,涵泳相忘,締造出詩作玲瓏微妙的境界。”[2]100詩心禪心乃為一心,表達的近乎是一個意思,無論是徜徉在山水間或是對事物發展的管窺,都需用心來“悟”,去體會其中的無窮奧妙。崔大江教授也指出:“禪趣詩往往表現詩人從大自然的陶冶欣賞中獲得的超悟,在對宇宙、自然的靜觀中,領略到的人生哲理、生命的真諦。”[3]28因此,禪趣詩的重點在“趣”,需要讀者浸潤到詩人的思蘊之中,慢慢忖度、細細品味方能悟出其中之禪道。正如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在其著作《禪與文化》中一語道破的“一言以蔽之,詩與禪的共同點就在于‘悟’或‘妙悟’上”[4]。因此,禪趣詩并非完全是對佛教佛理佛經的披露,而是妙在一個“悟”字之上,它既讀之妙趣橫生又能道出自然萬物之奧秘,還能將所感所悟寓于文字之中。
二、蘇軾禪趣詩在美國的傳播
唐宋文人王維、蘇軾好用佛經典故,尤其是王維的詩中多具有禪境中的“空靈”之感,被后人稱為“詩佛”。王維的禪詩在國內外受到熱捧,以其禪理詩研究居多,而東坡先生則以禪趣詩見長。清代文學家劉熙載在其名作《藝概》第2卷中指出:“太白長于風,少陵長于骨,昌黎長于質,東坡長于趣。”[5]蘇軾雖以詞聞名,但他在禪趣詩的書寫和表達方面也是較為熟練和高深的。事實上,美國學界吸收中國的禪文學主要是以禪趣詩為主(因其他禪詩較為深奧難懂),下文就重點探討蘇軾的禪趣詩是如何在美國進行傳播的。
1.傳播過程介紹。要研究蘇軾禪趣詩的傳播,先要了解傳播的過程是如何進行的。事實上,傳播既可以看作一個運動變化發展的過程,也可以看作一個由諸多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組合起來實現特定功能的系統。“1948年,拉斯韋爾在題為《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的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結構順序將它們排列,形成了后來人們稱之為‘5W模式’或‘拉斯韋爾程式’的過程模式(見圖1)。”[6]48
后來此模式遭到了學界的質疑和批評,認為其太過于簡單和武斷,不過“賴利夫婦(J.W. and M.W.Riley)認為,這個簡單的模式有多種用途,其中特別有助于來組織和規范關于傳播問題的討論”[6]48。確如賴利夫婦所述那樣,“5W”模式雖簡單,卻能很直觀簡潔地說明傳播的過程。而且,此模式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也較多地被應用,“周逢年的《朱舜水思想在日傳播研究》也是應用此簡潔模式作跨學科學術研究的著作”[7]。為此,本文也借助此傳播模式來討論蘇軾的禪趣詩在美國的傳播過程。此傳播模式中的傳播主體和傳播信息,即蘇軾的禪趣詩,將放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與美國英譯版蘇軾的禪趣詩進行對比分析來較為直觀地表現傳播效果中的文化差異和文化誤讀,在此重點討論蘇軾的禪趣詩在美國傳播過程中的兩個要素,即傳播的媒介和接受者。
2.蘇軾禪趣詩在美國的傳播媒介。蘇軾在中國是位家喻戶曉的大文豪,但大多數人比較熟悉他的詞而經常忽略他的詩歌。依據上述“禪趣詩”的含義,事實上,蘇軾的禪趣詩在其詩中所占比例最大也最好,表現出他在面對人生患難態度上的感悟和超脫。他將自己這種豁達的人生妙悟寄寓到自己的詩作中而又不直接表露出來,需要讀者含英咀華,仔細玩味,才能回味無窮。他的這種創作方式深深吸引了很多美國的文學家和翻譯家。
那么蘇軾的禪趣詩是何時以何種方式傳入美國的呢?這涉及到傳播學領域中一個較為重要的概念,媒介。通俗來說,媒介就是傳播的中介,在跨文化傳播領域里,媒介是傳播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媒介雖然被定義為‘擴大人類信息交流能力的傳播中介物’,但是,在傳播研究領域,媒介卻處在突出的位置(中心)。”[8]由此,仔細地梳理蘇軾的禪趣詩是經由何種媒介傳入到美國不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先來看中國禪趣詩是如何傳到美國的?中國禪趣詩并非是直接傳播的,大多以間接傳播為主,即通過英文譯文傳入(因只有極少數美國人能直接閱讀中文原典)。依據香港浸會大學鐘玲教授的考證,“日本人鈴木大拙是中國禪宗傳入美國的最重要的媒介,因中國禪宗先傳日本(大約十二、十三世紀傳入日本),再傳美國”[9]。
20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禪宗文化在美國的愈加流行,少數學習研究東亞文化的美國學者和相關的研究人員開始自主地翻譯原文,出身于英國中產階級的艾倫·瓦茲(Alan Watts, 1915—1973)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外祖父是傳教士,去過中國,因此瓦茲母親手中保留了一些家傳的中國山水畫、詩及中國刺繡。他從小就廣泛閱讀有關東方歷史及哲學的書籍,他在五六十年代用英文翻譯了大量禪詩,對美國影響深遠。這些禪詩引起了美國更多的漢學者和禪修人員直接前往中國的一些寺院修禪,并帶回來了大量的與禪有關的書籍,進行自主英譯。然而,這幾乎不涉及宋詩詞(英語中不區分詩詞,都是poem),主要以唐詩為主,此時禪詩的英譯以史耐德(Snyder)的二十四首《寒山詩》(1958)最為著名。
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才有翻譯家注意到宋代詩詞,這時蘇軾的禪趣詩才被介紹到美國。1994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東亞系任教的J. P.西頓(Seaton, 中國古典詩英譯家)和丹尼斯·馬龍尼(Dennis Maloney,美國著名詩人及中國詩、日本詩和韓國詩的譯者和編者)共同編譯的《泛舟:中國禪詩集》(ADriftingBoat:AnAnthologyofChineseZenPoetry)[10]出版,共收集了70多位中國詩人的詩作(也有宋詞),其中就第一次收錄有蘇軾的7首禪詩詞,其中禪趣詩詞占6首,僅有一首《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DrinkingwithLiuTzu-yuatGoldMountainTemple)與佛理有關。此后,陸續出版的英譯禪詩集中,如:1998年拉里·史密斯(Larry Smith)所譯的《中國禪詩》(ChineseZenPoems)[11]、1999年彼得·哈理斯(Peter Harris)所編的《禪詩》(ZenPoems)[12]以及2004年西頓再編禪詩集(ThePoetryofZen)[13],都有蘇軾的禪詩詞收錄在其中。由此,蘇軾的禪趣詩詞開啟了它的“美國之旅”。
3.蘇軾禪趣詩在美國的傳播受眾分析。從傳播學之父美國威爾伯·施拉姆的傳播途徑來看,“社會上流通傳播的型式至少有兩種:一種是為了維持社會機體一般水平的功能所需的型式,另一種是為了應付對社會機體提出的挑戰和嚴重問題所需的型式”[14]。簡單來說,一種文化得以在他國傳播與他國社會的需要(無論是維持社會的需要,還是反叛社會的需要)有直接相聯的關系。因此,蘇軾的禪趣詩傳到美國與其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環境有關,這些因素共同影響和決定著人們對信息的篩選和接受。
蘇軾的禪趣詩流行于美國,主要得益于中國禪宗對印度佛教中紛繁復雜的戒律進行了舍棄,重視其中對于生活的感受和覺悟。這與從19世紀30年代美國本土開始興起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運動有關,該運動相信人的內心有神性,可以用直覺感受到,與禪趣詩對日常生活經驗細節的注重有相似之處,比如,美國作家梭羅在瓦爾頓湖(Walden)上通過觀察日月星辰,體會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來進行感悟。此外,20世紀50年代后,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大發橫財的美國,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提高,一些成功人士或其子女發現物質上的富足已經不能滿足他們,或者即使得到了自己追求的財富地位,內心仍有不安。因此,他們渴望反叛,通過離家、逃學或吸食毒品等手段來對抗美國主流文化,被稱為“垮掉的一代”。到20世紀70年代后,前期的青年已經步入中年,長期的吸毒和酗酒將他們的身體透支,他們已經無力再用以前的“狂歡”形式來反傳統,于是開始重新思考這種“垮掉的行為”的反叛意義,追尋本地文化系統之外的信念成了他們的新目標,來自神秘東方的禪文化正是他們要努力尋找的。
從20世紀中葉禪宗修行流傳于美國民間開始,到蘇軾的禪趣詩傳入的90年代時,禪宗在美國已經流行近40年,各地禪修中心林立,信仰禪宗及對禪修有興趣的美國人逐漸增加,因此對蘇軾禪趣詩的接受主要有兩類人群。第一類是美國的東亞文化的研究學者和文學家,他們可以被稱為直接受眾,因他們是少數可以直接閱讀蘇軾中文禪趣詩的接受者,在他們自己學習研究接受的過程中,他們還為了保持原詩的原貌進行了直譯(也有少數創造性變異),供第二類人群學習和禪修用,如上文提到的西頓、史密斯等。第二類人群,可被稱為間接受眾,這類人群占較大比重,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家庭較為富裕,對禪理要求不高,只求學習鑒賞的美國中產階級。
三、蘇軾禪趣詩在美國的傳播效果及文化誤讀
在蘇軾禪趣詩傳播過后的20世紀末,美國禪修者已有一二百萬人,為廣大的受眾群體。雖然禪趣詩在美國的傳播受眾群體較多,有一定的影響,但這并不能說明美國的讀者就能完全參透其中的“禪趣”。詩是濃縮的語言,翻譯起來難度較大。禪趣詩有豐富的文化和宗教內涵,翻譯起來難度更大,再加上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誤讀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下文就以蘇軾禪趣詩的中英文比對,一方面說明“禪趣詩”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文化誤讀,一方面彰顯中國語言文化的博大精深。
1.《題西林壁》中的文化空缺和創造性變異。任何一種文化的出現都是有一定淵源的,不是隨意產生的,而是與一定的地域、習俗、歷史、價值觀有著緊密的聯系,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的變遷,中西各個民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在對英漢語言進行翻譯時,會發現源語與目標語在翻譯中出現不對等的情況,也就是在目標語中沒有適當的詞語與源語的文化相對應,造成詞匯上的空缺。《題西林壁》是蘇軾于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與友人在游觀廬山后所作。詩中的禪趣在于最后一句“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廬山的遮蔽,高瞻遠矚,才能把握住廬山的全貌。此詩在美國有相對應的英文版本,分別是拉里·史密斯所譯《題西林寺壁詩》(AnInscriptionPoemfromtheWallofHis-linTemple)和彼得·哈理斯編的《禪詩》(ZenPoems)里由碧塔·格蘭所譯《寫于西林寺壁》(WrittenontheWallatXilinTemple)。詩文如下: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格蘭所譯的詩文:
Regarded from one side, an entire range;
from another, a single peak.
Far, near, high, low, all its part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If the true face of Mount Lu
cannot be known,
It is because the one looking at it
Is standing in its midst.
史密斯譯文:
At the horizon the mountain seems huge;
up close it’s towering peak.
From far, near, high, or low, it’s not the same.
What is the true face of Mount Lu?
If the true face of Mount Lu
On a mountain, one cannot see the mountain.
原詩中的“橫看”和“側看”是非常傳神的描寫,這兩個版本的英譯都沒有將其翻譯出來。格蘭只是將其簡單處理成“from one side(從一邊看)”“from another(從另一邊看)”,略顯呆板,少了很多的想象空間。同樣的,在史密斯版本的譯文中也沒有翻出“橫看”和“側看”二詞,而是直接將其去掉,換成at the horizon(在地面上)看。“橫看”和“側看”屬于英語“空缺”詞匯,并無具體的詞匯與之對應,所以在翻譯的時候無法準確匹配原詩中作者“絞盡腦汁”的“橫看”“側看”的思考過程,少了很多的“靈動”。
另外,史密斯將原詩第三句的陳述句變為了疑問句以及形容山的高度用“towering”都屬于“創造性變異”。“創造性變異”是譯者有意而為之,為了達到填補文化差異的溝壑,適應本國審美特征的目的,有意識地利用目的語優勢和特點,對原文實施的增補、減損、更換、替換等變動。[15]史密斯對句式的轉換無疑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思考,或者至少是引起讀者重視最后一句的“禪味”。名詞tower加后綴-ing,變成了形容詞towering表示“高聳的”意思,但是其詞根依然是“tower”,這種高聳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呈現的是像“尖塔”一般,而不是中國人腦海中的高山的“巍峨屹立”。這是源于西方大多信奉基督教,而遍布于各地的基督教教堂的建筑風格(哥特式或巴洛克式)都以高聳的塔尖為主,這也是史密斯為了能夠幫助目標語國家的讀者消化吸收所挑選的“變異”詞匯。
2.《贈劉景文》與《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二》中的文化內涵誤讀。語言與文化之間有密切的聯系,語言是文化的反映,語言中包含著一定的文化信息,字面意義相同的語言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文化聯想意義。英漢文化中都有獨特的文化意象,因此在翻譯過程中,由于譯者缺乏對該文化意象的理解,將會造成翻譯中出現誤讀的現象。《贈劉景文》是蘇軾在元佑五年 (1090)任杭州知州時所作,送給好友劉景文的一首勉勵詩,勉勵朋友困難只是一時,要樂觀向上,切莫意志消沉。詩文和譯文如下: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
正是橙黃橘綠時。
西頓版譯文:
Presented to Liu Ching-wen
Lotus withered, no more umbrellas to the rain
A single branch, chrysanthemum stands against the frost
The good sights of the year : remember those
and now too: citrons yellow, tangerines still green.
這首詩的題目雖為贈劉景文而作,卻全在描寫詠物看景,無一字涉及對朋友的褒貶之義。這似乎不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實際上,作者的高明之處正在于將劉氏品格和節操的稱頌不著痕跡地糅合在對深秋景物的描寫之中,這就是這首詩的“禪趣”所在。西頓版譯文中只是將詩中的字詞進行了直譯而沒有譯出詩人所要傳達的對朋友的勉勵之情。譯文第二句中少了原文中的“傲霜”,只翻譯成了“a single branch”(一根樹枝),將“殘菊”那種傲霜凌寒的意象抹掉了。菊花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是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的,與“梅”“蘭”“竹”并稱為“四君子”,歷來象征著孤傲高潔和頑強不屈。最后一句的橙黃橘綠一方面道出的是時間,深秋時節金黃色的橙子與青綠的橘子,另一方面也是對劉氏的贊揚,橘樹和松柏一樣,在中國人的意象中是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堅貞節操的。屈原就有《橘頌》一詩,稱其“深固難徙,廓其無求”,贊美其堅貞不移的品格。譯文中只簡單地翻譯出“citrons yellow(黃柚)”和“tangerines green(綠橘)”,不加解釋的話,對于不了解這些“文化負載詞”的美國讀者來說,這首內涵豐富的詩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二》作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結束了貶謫嶺南七年的生活,在北歸途中經虔州時寫下的。
《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二》
鐘鼓江南岸,
歸來夢自驚。
浮云時事改,
孤月此心明。
雨已傾盆落,
詩仍翻水成。
二江爭送客,
木杪看橋橫。
西頓版譯文:
A Harmony to Ching Hui-shu’s Rhymes
Bells and drums from the south bank of the river.
Home? Startled, I wake from the dream.
Clouds drift : so also this world.
One moon: this is my mind’s light.
Rain comes as if from an overturned tub.
Poems too, like water spilling.
The two rivers compete to see me off;
In the treetops the slanting line of a bridge.
英文版中在“Home”后加“?”是創造性變異,將原句中的陳述句變為疑問句,能夠傳達出原詩作者在“驚醒”后,睡意朦朧中對自己是否身在故鄉狀態的一種質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二句是此詩中的佳句,深受文人喜愛。此二句表達的意思是,“世間事像浮云一般變幻不定,我這顆心卻像孤月高懸般潔凈明亮”,寫出了在世事多變或歷盡滄桑后,內心的堅守和孤高情懷,頗有一種寧靜、恬淡之美,正是禪趣之所在。英文中相對應的翻譯用了兩個句號,說明譯者并沒有弄清這兩句話的獨特內涵,因這兩個單句只有合在一起時,才形成一個意群表達出詩人的原意,若拆分開來,則兩單句意蘊全無。此外,譯文將“浮云(偏正結構)”譯為了“云在漂clouds drift(主謂結構)”,明顯傳達出譯者對“浮云”意象的不解。“浮云”不可拆分,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在古詩詞中多為“貶義”的意象,如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中:“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同理,將“孤月”譯成了“一個月亮 one moon”,也是對“孤月”文化內涵的一種割裂。
3.《南歌子·帶酒沖山雨》中的文體風格誤讀。蘇軾的詞中也有“禪趣”,由于英譯中詩詞不分,會造成文體誤讀。蘇軾的《南歌子·帶酒沖山雨》上片寫作者悠游自在的心境“一身輕”,下片明寫“愛沙路”“免泥行”,實際上是暗指拋棄官場宦途和世俗功利之心,表現了作者歸隱田園的志向。“泥”與“沙”之別在于沙上雖然走不快,但仍可順利前行,但在泥路上卻會陷而不以自拔,且腳上會沾泥,這為禪趣所在。因此,美國翻譯家西頓也將這首詞進行了英譯并收錄在他的那本《禪詩集》中,但采用的翻譯文體與詩歌并無兩樣。
詩文如下:
帶酒沖山雨,和衣睡晚睛。不知鐘鼓報天明。夢里栩然蝴蝶、一身輕。
老去才都盡,歸來計未成。求田問舍笑豪英。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
西頓版譯文:
Song to the tune nan ho tzu
rapt in wine against the mountain rains
dressed I dozed in evening brightness
and woke to hear the watch drum striking dawn
in dreams I was a butterfly
my joyful body light
I grow old, my talents are used up
but still I plot toward the return
to find a field and take a cottage
where I can laugh at heroes
and pick my way among the muddy puddles
on a lake side path
英漢文化翻譯中,文體風格方面的誤讀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源語與目標語之間的表達方式方面的差異所引起的,漢語中的詩詞是有著嚴格區分的。首先,漢語中詩詞最明顯的區別在標題上,詩只有題目, 而詞的標題卻有兩部分,前一部分叫詞牌,后一部分才是標題,而且標題可以就是詞的第一句,西頓版的英文中只有一個標題“Song to the tune nan ho tzu”與詩并無區別。其次,在句式上也有所不同,詩有律詩和絕句,有七言和五言之分,格律詩句式整齊劃一。詞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90字)和長調(91字以上,最長的詞達240字),西頓版的這首英譯在字數上也看不出與詩歌的區別。最后,詩詞在押韻方面有區別,格律詩隔句壓韻,詞卻較為靈活。仔細觀看西頓的英譯,發現他為了保持詩歌原貌并沒有注重押韻規律(英文詩中也注重押韻和行數,有押頭韻有押尾韻,詩行有九行有十四行等)。
綜上,蘇軾的“禪趣詩”追求的是從詩歌的語言中激發出對詩歌所描述的情、景、物的意境與韻味,著力于言有盡而意無窮。然而,英語是一門結構嚴謹、邏輯性強的語言,因此對“禪趣詩”進行翻譯時,為了能清楚、準確地傳達出詩中的內涵,不得不逐字逐句地對其翻譯。雖然這樣的翻譯可以譯出詩中的字面意思,卻無法令讀者體會古詩中所呈現的意境,喪失了禪趣詩中語言美和意境美。
四、結 語
美國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后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然而,工業文明的高度發達使人產生了異化的危機感,敏感的知識階層思索著拯救沉淪、救贖自我的可能方式。這時,美國學者將目光轉向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去尋找力量和可以借鑒的東西,中國的古典詩歌和古典哲學時常成為美國作家的精神寄托、心理慰藉和思想歸宿。反觀當下,作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的繼承人,我們更要傳承和發揚這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堅定信心。當然,我們也不可盲目自信,自我文化封閉,只有吸收各種對我們有利的文化精華,才能創造出更加光輝燦爛的文化,要知道即使美國文學吸收了中國的古典詩歌和古典哲學思想,美國文學仍然是美國文學,仍具有美利堅民族特色。所以,各國在文化交流和融合時,都要兼容并蓄、博采眾長,才能有所發展、有所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