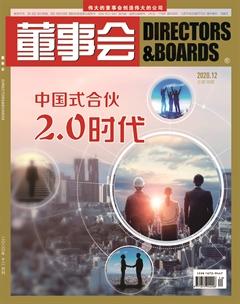公司治理亂局倒逼“揭開公司面紗”
趙佳
“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又稱“公司人格否認”、“公司法人資格否認”等,是英美國家在司法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判例規則,指控制股東為逃避自己的義務或責任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濫用公司法人資格或有限責任,致使債權人利益嚴重受損時,法院或仲裁機構對公司債權人及控制股東法律責任、義務的執行機制。當前,疫情之下的企業發展困局,面紗之下的公司治理亂局,使我們不得不反思如何在中國現有司法及商業環境下“揭開公司面紗”,還公司治理原貌。
典型判例
由于“揭開公司面紗”制度是在判例規則的應用中得到闡釋的,所以,在國內公司治理案例的導入并不具有普遍性,如公司股東濫用權利、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行為,股東與公司之間人格高度混同等,都是在個案中進行判定和引用的。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發布的指導案例15號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訴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打破了僅就股東與公司之間混同適用的情形,將關聯公司納入了承擔債務連帶責任的范疇。另在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沈陽辦事處與新東北電氣(沈陽)高壓隔離開關有限公司等金融不良債權追償糾紛案中,由于債務連帶責任的承擔、股東出資義務的履行及濫用公司獨立法人地位、人格混同等主張均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高院不予支持“揭開公司面紗”,此案雖冗長而繁復,但從判例角度,充分闡釋了“揭開公司面紗”制度的涵蓋情形及法院判定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目前,《公司法》及高院的司法解釋都過于寬泛,適用的情形及范圍尚有留白之處,而法院在個案中行使的裁量權則存在不同尺度問題,所以,尚須從立法高度、公司治理角度去重新審視如何“揭開公司面紗”。
他山之石
“揭開公司面紗”在國內并不是一個制度,也不是某項法令,是在大量的判例實踐中積累、總結出來的,因此目前并無具體條文規定其適用于何種領域及適用的主體,而是通過有關要件進行認定。經過多年發展,“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已在不同國家得到延伸,認定范圍及內涵也在不斷擴展。
在馬來西亞公布的高等法院個案判決中,依據該國《商標法》法令考慮了注冊商標的所有人是否實際上錯誤地聲稱擁有該商標的所有權的問題而“揭開公司面紗”。原告是一家在印度注冊成立的公司,從事制造和經銷牙膏業務,第一被告為從事快速消費品貿易公司業務所有人,第二被告在馬來西亞從事草藥和保健產品貿易,第三被告是第二被告的前董事。原告授權第二被告在馬來西亞分銷牙膏,2014年第二被告在馬來西亞成功申請注冊了該商標,第一被告隨后制造并銷售了該牙膏產品。2015年,原告終止協議,隨后分別對三名被告提起法律訴訟,以確定被告是否合法注冊該商標。此案中,馬來西亞聯邦法院認定原告是馬來西亞該商標的普通法所有人,且有證據表明,自2001年以來,原告通過在馬來西亞分銷該牙膏產品而使用了該商標,即確定為商標在該國的普通法所有人后,法院繼續考慮第二被告及第三被告是否欺詐地注冊了商標。在此案中,馬來西亞聯邦法院裁定依據是在知道另一人的在先權利的情況下提出所有權主張的行為構成欺詐,即出于“公議”對此案中被告在商標注冊所有權事先認識的情況下揭開公司面紗。盡管此判例本身并不新穎,但表明了其廣泛的適用性及一般滿足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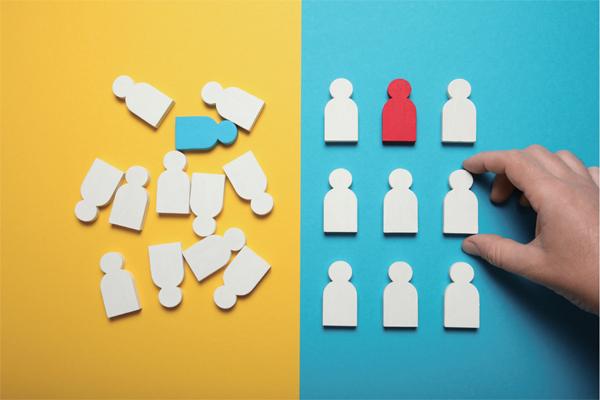
在英美法系國家,“揭開公司面紗”判定往往出于幾個依據,包括欺詐及非法行為、虛假陳述及公平正義等,而判例覆蓋領域也不僅僅局限在維護債權人利益、人格混同、股東權責逃避等,在具體實踐中,我們可不斷借鑒國外成熟的判例經驗,結合我國《公司法》實施情況,積極進行應用探索。
現實意義
當前,不可否認的是國內公司治理的整體水平還不高,特別是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及公司股東與公司(包括子公司)之間人格混同的行為普遍存在,如公司控股股東對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操控,公司與子公司及關聯公司業務、財務、人員、機構高度混同等情況,特別是國有企業“一套班子、幾塊牌子”的情況經常出現,子公司層級較多,企業決策機構形同虛設,往往無法通過投資鏈及股權鏈刺穿實際控制人的面紗。另外,不管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還是有限責任公司、一人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說,“面紗”覆蓋了《公司法》所包含的所有治理領域、組織形式及范疇,所以,各層面應予以重視。
一是制度層面的建構。目前,國內雖已進行了相應的探索及實踐,但《公司法》目前針對此制度只是原則上的規定,并無延展,而司法程序及解釋也不夠全面,更多是個案的事后處置,尚無法形成制度層面的聚焦及共識,更無法約束企業在內部控制中加以糾正、完善,所以,應有必要對個別法案及實施條例進行細化,固化為可遵循、可約束的制度架構。
二是立法層面的聚焦。或可在立法層面借鑒、部分引入“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國內雖然已在公司個案中加以應用,但總體來說,應用的廣度及深度還遠遠不夠,特別是適用條件、原則及要件須有本土化的一套規則,基于此,更應從立法層面對不同類型個案中的舉證、判定程序進行歸納總結,對如何刺破“面紗”、為何刺破“面紗”等問題進行頂層設計,并頒布實施。
三是政府層面的監管。目前,國內雖針對企業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印發了相應的規范及指引,但始終不成體系,缺乏有效監管,更難變成企業的自覺行為。出于現代企業投資人對利益的普遍追求,漠視公司法人人格有其強大的商業動因,須考慮從政府層面制訂企業治理準則,在公司治理層面加以控制、防范,揭開公司治理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