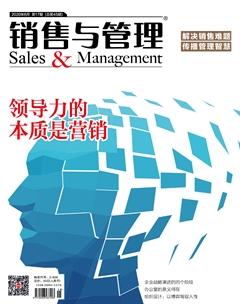道德型領導的新模式
馬克斯·巴澤曼

未來,自動駕駛汽車可能會接管道路。這種新技術會通過減少駕駛員失誤來救人一命,然而,事故仍然會發生。這種汽車的電腦將被迫做出艱難的抉擇:當撞車不可避免時,汽車是該救車上唯一的乘員還是五位行人?汽車應該優先保護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的性命?孕婦該怎么辦——她應該算作兩人嗎?汽車制造商應該提前考慮這些難題,并為他們的汽車設計應對程序。
在我看來,回答這些倫理道德問題的領導者們,應該以為社會創造最大價值這一目標為指導思想。這種觀點源于哲學家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著作,突破了一套簡單的道德準則(“不要撒謊”“不要欺騙”),提供了做出各種重要管理決策所需的清晰思路。
數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們對于什么是道德行為爭論不休,對于人們應該做的事進行了理論建構。最近,社會科學中的倫理學家提出了基于研究的解釋,對人們面對倫理困境時的實際行為進行了說明。這些科學家已經證明,環境和心理過程可能會致使我們做出存在道德問題的行為,即使這有違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如果我們出于私利而行為不軌,我們通常都意識不到自己在這樣做——這是一種動機性失明現象。比如,我們可能會聲稱自己對團隊的貢獻比實際做的更多。我和我的同事已經證明,如果對他們或公司有利,高管們會無意識地忽略他們公司中嚴重的不道德行為。
實現價值最大化
我改進道德決策的方法是將哲學思想與商學院的實用主義結合起來。我總體上贊同功利主義的原則,這是邊沁最初提出的哲學,認為道德的行為就是在世上實現“功利”最大化的行為——我在此稱之為價值。這包括最大限度地提升總體幸福,最大限度地減少總體痛苦,通過追求決策效率來幫助實現目標,不計私利地實現道德決策以及避免部落行為(比如民族主義或群體偏好)。我推測,即使你奉行的哲學注重個人權利、自由和自主,你也會在很大程度上贊同這些目標。即使你信奉另一種哲學觀點,也請在那種觀點的范圍內試圖理解盡可能創造最大價值這一目標。
一般說來,功利主義支持的決策在多數時候與其他大多數哲學并無二致,因而為檢驗領導道德倫理觀提供了有用的依據。可是與其他哲學一樣,嚴格的功利主義并不總是會給出輕松的答案。比如,它的邏輯與局限性在那些自動駕駛汽車制造商面臨的選擇中一覽無余。如果目標僅僅是實現價值最大化,那么汽車的程序設計就應該是限制集體的損失和痛苦,車內的人就不應該被給予特殊地位。照此算法,如果汽車必須在救車上一人之命與救道上五人之命之間進行選擇,它應該犧牲乘客。
顯然,這會帶來一大堆問題——如果乘客是孕婦怎么辦?如果她比行人年輕怎么辦?——對于如何最好地為汽車設計程序問題,沒有簡單的功利主義答案。
此外,制造商可能會合理地辯稱,人們不太可能買一輛不把自己生命放在首位的汽車。因此,不優先考慮乘客的企業競爭地位會低于優先考慮乘客的企業——而購車者很有可能選擇由人駕駛的安全性較低的人類駕駛汽車。然而,功利主義價值觀可以有效地用來考慮什么樣的監管會有助于為所有人創造最大的利益。
雖然自動駕駛汽車的案例所代表的道德決策比多數管理者會面臨的道德決策更難,但是它卻凸顯出全盤考慮的重要性——你的大小決策以及你管理的那些人的決策將如何為社會創造最大的價值。人們通常認為道德型領導就是那些堅持我所提及的簡單準則的人。可是當領導者做出公平的人事決定、在談判中策劃出惠及雙方的權衡方案,或者明智地分配自己及他人時間的時候,他們就是在實現“功利”最大化——在世上創造價值,從而以道德的方式行事,讓他們的企業整體上更道德。
克服障礙
看看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及其同事提出的兩個問題:
1.為了不讓2000只遷徙的候鳥溺死于敞露的油池,你愿意出多少錢?
2.為了不讓20萬只遷徙的候鳥溺死于敞露的油池,你愿意出多少錢?
他們的研究顯示,被問及第一個問題的人提供的資金數量與被問及第二個問題的人幾乎相同。當然,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創造盡可能多的價值,鳥的數量差異應該會影響到我們選擇出資的數量。這說明了我們道德思維的局限性,而且,改進道德決策需要有意識地做出理性決定,實現價值最大化而不是跟著感覺走。
有限理性的概念是行為經濟學領域的核心,它認為管理者希望具有理性,但卻受到偏見和其他妨礙性認知局限的影響。研究決策的學者們并不指望人們完全理性,可是他們認為,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追求,以便更好地讓我們的行為與目標保持一致。在倫理道德領域,我們與有限道德性作斗爭——妨礙我們如自己希望的那樣有道德的系統性認知障礙——抗爭。通過調整我們的個人目標,從實現我們自己(和我們企業)利益最大化調整為在行為上盡可能合乎道德,我們就可能建立起一種可以指引我們的北極星。我們永遠不能到達那里,但它能夠激勵我們為每一個人創造更多的美好,增加幸福感。目標瞄準這個方向可以讓我們的行動邁向我稱之為最可持續的善德:我們可以真正實現的價值創造水平。
欲創造更多的價值,我們必須正視自己的認知局限性。正如卡內曼《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的讀者所知的,我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模式。比如系統1是我們的直覺系統,這個系統速度快、無意識、不費力、情緒化。我們的多數決定是用系統1做出的。系統2是我們更慎重的思維,更慢、有意識、費力氣、合邏輯。我們在使用系統2時更接近理性。哲學家、心理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對道德決策提出了一種平行的雙系統觀點:一個直覺系統和一個更慎思的系統。慎思系統導致更具道德的行為。以下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兩個策略實例:
首先,通過比較選擇而非單獨評估的方式來做出更多的決定。直覺和情感通常會支配決策的一個原因是,我們通常一次只考慮一個選項。當我們評估一個選項的時候(比如,單獨一份工作邀請或單獨一次潛在的慈善捐贈),我們依靠系統1來處理。可是當我們比較多個選項時,我們的決定會得到更仔細的考慮,偏見更少,他們就會創造更多的價值。當我們孤立地考慮各慈善機構時,我們的捐贈是基于情感拉鋸;可是當我們對慈善機構進行橫向比較時,我們通常會更多地考慮我們的捐贈在哪里才能發揮最大用處。同樣,在與經濟學家艾里斯·博內特(Iris Bohnet)和亞歷山德拉·范吉恩(Alexandra van Geen)的研究中,我發現,當人們一次評估一名求職者時,系統1的思維就開始發揮作用,而且他們通常會仰賴性別偏見。比如,他們更有可能雇用男性來完成數學任務。可是當他們同時比較兩個或多個求職者時,他們會更關注與工作相關的標準,更符合道德規范(不那么像性別歧視主義者),錄用更優秀的應聘者,為企業獲得更好的結果。
第二種策略涉及運用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所稱的無知之幕。羅爾斯認為,如果你在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地位(富人還是窮人、男人還是女人、黑人還是白人)的情況下思考社會應該如何構建——即,在無知之幕后面——你會做出更公平、更合乎道德的決定。事實上,我最近與凱倫·黃(Karen Huang)和喬舒亞·格林的實證研究表明,那些在無知之幕背后做出合乎道德決定的人的確創造了更多價值。比如,他們更有可能用稀缺的資源(比如,醫用品)拯救更多的性命,因為他們分配資源的方式不那么自私自利。我們研究的參與者被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了能夠給9名送到醫院來的地震受害者實施手術,取走一名住院患者的氧氣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當“幕”遮掩了他們可能是這10人中的哪一位時,他們更傾向可以接受。不知道我們會從一個決定中如何受益(或受害),可以讓我們不會因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產生偏見。
一個相關的策略是隱去被評判人的社會身份。如今,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招聘初審中刪除了求職申請中的姓名和照片,來減少帶偏見的決定,增加錄用最具資質人選的幾率。
通過權衡創造價值
下面哪個對你更重要:你的薪水還是你的工作性質?晚餐時的葡萄酒還是食物?你家的地理位置還是房子大小?奇怪的是,即使不知道自己需要放棄多少薪水才能得到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不知如果住的地方離單位或學校再遠五英里,他們擁有的空間會有多大變化,人們也愿意回答這些問題。決策分析界認為,我們需要知道一種屬性在多大程度上與另一種屬性進行權衡才能做出明智的決定。選擇合適的工作、住房、假期或公司政策需要思路清晰地權衡得失。
最容易分析的得失取舍包括我們自己的決策。一旦兩個或更多的人參與一項決策,而他們的喜好各不相同,這就成了談判。通常,談判分析重點關注的是對特定談判者最有利的方面。而就你關心的他人及全社會而言,你在談判中的決定應該傾向于努力為各方創造價值。
這一點很容易在普通的家庭協商中看到——我已經參與了數百次這樣的協商。設想一下,你和你的伴侶某晚決定外出就餐,然后看一場電影。你的伴侶建議去一家最近重新開張的北意大利高檔餐廳,而你反過來提議去你最喜歡的比薩快餐店。你們倆達成妥協,去了第三家店,這家店有好吃的意大利食物和比薩,比你最愛的那家比薩店供應的食品更高檔一些。就餐期間,你的伴侶提議你們看一部紀錄片,你卻提出看喜劇電影,你們達成的妥協是看戲劇。在度過了一個美好(但并非妙不可言)的夜晚之后,你們倆都意識到,由于你的伴侶更在意晚餐,而你更在意電影,選擇北意大利高檔餐廳和喜劇電影本會讓你們過一個更美好的夜晚。
這個相對微不足道的例子表明了如何通過尋求權衡取舍來創造價值。研究談判的學者對于尋找更多價值源泉的途徑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這些策略包括建立信任、共享信息、提出問題、透露價值創造信息、同時就多個問題進行談判以及同時做出多個提議。
如果你熟悉談判策略,你就會明白,最重要的談判涉及為自己(或你的公司)爭取價值與為雙方創造價值——做大蛋糕——之間的矛盾。即使在知道蛋糕的大小并不固定時,許多談判者還是擔心,如果共享了為所有人創造價值所需的信息,對方也許就主張獲得更多創造出來的價值——而他們可不希望上當受騙。所有關于管理談判的主要書籍都強調,在管理失敗風險的同時創造價值的必要性。
雖然許多專家會從不欺騙或不撒謊的角度來定義談判道德,但是我對它的定義是將關注重點放在創造最大價值上(誠實當然有助于此)。你非但不會忽視價值主張,反而會有意識地防止它阻礙你做出最大的蛋糕。即使對方會因此而要求獲得一點額外價值,從長遠來看,對價值創造的重視仍然有可能會給予你回饋。作為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有道德的談判者,你所建立的所有優質關系會大大彌補你在機會主義對手面前的損失。
利用時間創造價值
人們通常不把時間分配當成道德選擇,但是他們應該這樣做。時間是稀缺資源,浪費你自己或他人時間只會損害價值創造。反之,明智地利用時間來增加集體價值或效用才是道德行為的真正定義。
看看我朋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琳達·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的經歷。她收到很多帶著任務的電子郵件,這些任務有助于他人,但并不會給她帶來直接好處。她很樂意做一名好公民,執行了部分任務,但她沒有時間承擔所有任務。琳達懷疑女性被要求執行這種任務的頻率比男性高,于是邀請四位女性同事與她會面,討論她的推測。就在那次聚會上“我就是無法拒絕”(I Just Cant Say No)俱樂部誕生了。這些女教授舉行社交聚會,發表研究,幫助彼此更仔細地思考她們的時間在什么地方可以創造最大的價值。
她們的理念對所有聲稱自己時間緊迫的人都有啟示:你可以把對時間的需求看作一種對有限資源的需求。你可以分析你的以及他人的時間如何在世上創造最大的價值,而不是憑做個好人的直覺愿望做出決定。這可以讓你獲得說不自由,不是出于懶惰,而是出于通過不同要求來創造更大價值的信念。
在員工之間分配任務為管理者創造價值提供了更多機會。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戴維·里卡多(David Ricardo)1871年提出的比較優勢是一個實用概念。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經濟理念,我則把它當成道德行為指南。評估比較優勢包括讓每個人或每家企業衡量如何把時間用在創造最大價值的地方。當企業能夠以比競爭對手更低的成本生產和銷售產品與服務時,他們就具備了比較優勢。當個人能夠比他人以更低的機會成本來執行任務時,他們就具備了比較優勢。每一個人都有比較優勢的來源,相應地分配時間可以創造最大的價值。
里卡多的概念在許多企業中都可以看到。在這些企業中,一個個體在很多事情上極其出色。想象一下,一家科技初創企業的創始人擁有最優秀的技術能力,不過只比第二有才華的技術人員略勝一籌。然而,這位創始人在向投資者宣傳公司方面遠比其他所有員工更有成效。她在技術問題上具有絕對優勢,但她的比較優勢在于其與外部支持者打交道,當她將注意力集中在這方面時,就會創造更多的價值。許多管理者本能地利用自己和員工的絕對優勢,而不是倚重他們的比較優勢。結果可能是資源配置不佳,價值創造較少。
整合道德自我

不管你的企業是何性質,我猜他在某些方面很有社會責任感,但在其他方面社會責任感不足,而你可能對后者感到不快。多數企業在某些方面的道德評分高于其他方面。我知道有些企業的產品讓世界變得更糟,可是他們卻擁有很好的多元化與包容性政策。我也知道其他一些企業的產品讓世界變得更好,可是他們卻致力于不公平競爭,破壞了他們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我們多數人在道德上也不是從一而終,否則誠實的人在與客戶或同事談判時可能認為欺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們可能在某些領域是道德的,而在其他領域則不道德,如果我們在意我們創造的價值或制造的傷害,記住這一點則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在哪些方面進行變革最有用。
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將他90%的財富——約3.5億美元——捐贈給了包括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卡內基基金會(the Carnegie Foundation)在內的一系列機構和2500多家圖書館。可是作為企業領導人,他也從事過吝嗇、無效甚至可能是犯罪的行為,比如,他破壞了賓夕法尼亞州霍姆斯特德他自己鋼鐵廠的工會。最近,這種善惡之分在薩克勒(Sackler)家族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明顯。薩克勒家族向美術館、研究機構和包括哈佛在內的大學捐贈了大筆資金,這些資金是通過其家族企業普渡制藥(Purdue Pharma)賺取的。普渡制藥通過營銷——多數專家認為是過度營銷——處方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tin)賺得了數十億美元。截至2018年,奧施康定和其他阿片類藥物每天導致了100多名美國人死亡。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想想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可能創造或破壞價值,在我們做得很好時,應該獲得嘉獎,但也要注意改進的機會。我們通常在后一項任務上花的時間太少。當我在評估我人生的各個方面時,我能夠發現自己為世界創造價值的許多方式。然而,我也能夠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本可以做得更好。我的計劃是明年比過去的一年做得更好。我希望你會在自己的生活中發現同樣的機會。
提升身為領導者的影響力
領導者能做的遠不止讓自己的行為更合乎道德。由于他們既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也要為他人的決定負責,所以通過鼓勵他人變得更好,他們可以大大增加自己行為帶來的好處。作為領導者,想想你如何才能利用你制定的規范以及你創造的決策環境來影響你的同事。
人們會效法他人的行為,尤其是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企業的領導有道德,員工自己才有望表現出合乎道德的行為。我的一個客戶因在社會責任方面的努力而受到盛贊,該公司制作了一段四位高管為主角的內部視頻,每位高管都講述了在老板未能遵守公司所信奉的道德標準的時候越過老板行事的故事。這段視頻表明,當權威摧毀社會價值的時候,質疑權威是正確的做法。通過建立道德行為規范——并明確授權員工幫助執行規范——領導者可以影響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人,激勵并促使他們行事更合乎道德。
領導者還可以通過塑造他人的決策環境來創造更大的價值。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們的《激勵》(Nudge)一書中描述了人們如何能夠圍繞各種選擇設計“架構”,以促使大家做出創造價值的決策。也許最常見的激勵形式包括改變決策者面臨的默認選擇。在一些歐洲國家,一項鼓勵器官捐獻的著名激勵措施是系統幫公民自動登記注冊,如果他們愿意也允許他們選擇退出。這項計劃將同意捐獻器官的人數比例從不到30%提高到80%以上。
領導者可以通過開發、推動可贏利的新產品,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比如,我在發表了一篇關于道德行為的論文之后收到了一封來自初創保險公司高管斯圖爾特·巴澤爾曼(Stuart Baserman)的郵件。他所在的Slice公司向經營家庭企業的人出售短期保險。他在尋找讓投保人在索賠過程中更加誠實的方法,我們一起合作制定了一些激勵措施。
我們創建了一個流程,索賠人使用手機拍攝的短視頻來描述索賠。這一激勵措施行之有效,因為相較于書面形式,多數人在視頻中說謊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索賠人還會被問及有關損失的可核實的問題,比如“你買這件物品花了多少錢?”或者“在亞馬遜網站上重新購買要花多少錢?”——而不是問“這東西值多少錢?”具體的問題比模棱兩可的問題更能讓人誠實。而且索賠人會被問及還有誰對損失情況知情,因為當他人可能知道他們的貪腐行為時,人們就不太可能騙人。這些激勵措施不僅減少了欺詐行為、提高了保險業務的效率,還讓Slice公司通過幫助人們遵守道德而獲益。
我們每天都面臨新的道德挑戰,從為自動駕駛汽車創建何種算法到如何在疫情期間分配稀缺的醫用物資。隨著科技創造出驚人的方式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環境足跡成為了更讓人關注的問題。許多國家都在為如何采取行動而痛苦掙扎,在太多國家,尋找集體價值不再是國家目標。我希望我所描述的理念能影響身為領導的你。攜手共進,我們可以盡力做得更好。
本文作者系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Jesse Isidor Straus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