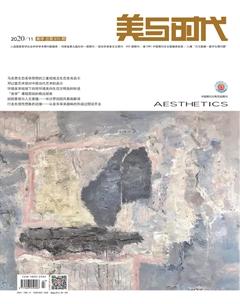田園景觀與人文意蘊
摘? 要:印象主義畫家畢沙羅,以寫生方式回歸客觀世界本源,描繪了一幅幅鄉村田園風景畫,形成了獨具風格的地域田園歷史的碎片。這些田園風景畫呈現出了他關注自然,關心社會的人文視角,也反映出地域自然資源特征、經濟狀況、農耕生活情景等,具有豐富多彩的人文意蘊。
關鍵詞:田園景觀;人文意蘊;畢沙羅;田園風景畫;解讀
大自然是人類生命孕育及賴以生存的搖籃。人們在生存發展中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與土地、山川、草木為伴,形成天人合一,和諧共存的景象,從而產生了農耕文明。這是千百年來文人墨客謳歌的題材內容,詮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與價值,折射出豐富的感情色彩和文化思想的內涵。畢沙羅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居住鄉村,以寫生方式表現了一批印象主義風格的田園風景畫作品,呈現他“關注自然,關心社會”[1]32的人文視角。
一、田園寫生再現自然資源特征
風景畫初期,圖式語言傳承了古典格律體形式,營造畫面的神圣宏偉與寂寞的氣氛,使故土的一草一木、道路、海灣、風車等景物的描繪都充滿畫家的崇敬與虔誠之情。“因為他們喜歡將云彩、大海、山丘只是看做諸神的呈現形態,從而抽掉了自然本身的豐富意味。”[2]畢沙羅突破風景畫初期古典格律體的僵化圖式語言,追求客觀自然的現實主義。他曾說:“只要我眼晴一睜開,我的意識就開始得到自由了。”[1]15這與中國唐代張彥遠所認為:“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客觀物質世界,折射出現實社會文化的印跡,具有地域、時代、社會的歷史屬性與審美價值。在他們看來,古典格律體繪畫那些想象、理想化修飾的自然是一種概念化、假大空及矯揉造作的自然,是一種“水不流,花不開”的境象表現,都缺乏時代生活氣息,他們認為只有客觀現實才是自然生活的美。畢沙羅崇尚以寫生方式回歸客觀世界本源,“強調自然狀態下產生的創作沖動”[3]。面對伸手可及的現實生活,聆聽大自然的呼吸,近距離觀察、感知歲月痕跡及勞動的果實,忠實記錄鮮活和生動的具體細節。“他要求在創作時不能設置構圖,甚至不允許自己隨意改變自然中物象的位置,追求畫面自然的和諧”,[1]32在特定視角狀態下取景,因勢利導,呈現自然而然的視覺圖像。
他的一些畫作,登高遠眺寫生再現田園結構的特征,即產生廣角俯視現象,視點較高,盡顯層出不窮的視野。如《龐圖瓦茲的風景》(1868年)描繪的是龐圖瓦茲丘陵地帶的特征。拓展了縱深的地域面貌,減少了景物隱匿和遮擋,趨于平面圖式的展示效果,使田園結構和植被特征盡收眼底。山丘、平地、田埂、堤堰、河塘溪流、開墾的紅土地、綠油油的菜園、金黃色的麥田、高低錯落的紅瓦白墻的農舍、田園曲徑上形態各異的人物……世態人情盡在畫面之中,淋漓盡致地描繪出這片沃土上農作物品種繁多,物阜民豐的景象。
而他的另一類畫作,則近距離寫生再現景物細節的特征,即形成小景現象,充分展示和塑造具體、翔實、清晰的物象形態、色彩和質感等內容。如在他眾多的作品中是透過樹叢空隙看到農舍、山丘及天際的,樹木便成為前景或中景部分重點塑造的對象。因此我們可以清晰地從《龐圖瓦茲的水堰》(1862年)、《龐圖瓦茲之景》(1872年)等,看到參天聳立,上接霄漢的楊樹;從《龐圖瓦茲的蘋果樹》(1876年)等,看到虬枝屈曲,盤繞多姿的果樹;從《紅色屋頂》(1877年)、《透過樹林看龐圖瓦茲》(1879年)等,看到裊娜體態,綽約風姿的新苗;從《龐圖瓦茲的春天》(1877年)等,看到銅皮鐵桿、毛辣蒼勁的古樹;從《林中大道》(1871年)、《龐圖瓦茲的路》(1872年)等,看到葉張翠蓋,綠樹成蔭的叢樹;從《村莊入口》(1872年)等,看到葉落凋零,風骨傲然的枯樹。這些近距離寫生也為觀眾提供了翔實的自然信息。
色彩寫生再現四季農作物生長的特色。印象主義追求光色變化的自然科學原理,畢沙羅通過寫生觀察,準確捕捉光色瞬息的變化,客觀再現即時的光色視覺現象。如1872年所作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系列等,可以從畫面光源、環境色彩關系與色調中感知到不同季節、氣候、時間所形成的田園農作物生長的特色,認識到農事耕作的變化規律。
二、田園景象再現地域經濟狀況
“畢沙羅在印象派畫家中獨樹一幟,就在于他力求光色表現出對象的實體感及全部結構的力量。”[4]在他的作品中景物形態、質地、色彩的特征更自然生動、更典型和充實完整,由此感知歲月歷史的痕跡及生存的經濟環境狀況。
反映出新興菜農經濟狀況。“整個19世紀,農村和農業人口是法國的主體人口,菜園構成了鄉村農業的主要部分。”[5]198畢沙羅主要熱衷于反映地域農作物與蔬菜種植的資源狀況及經濟價值。特別是龐圖瓦茲的菜園系列的表現,既是風景畫題材內容的創新,又是他“表現了被開墾的自然,即自然變成了產品進入到經濟領域中。”[5]198也反映了巴黎周邊主體農業的經濟狀況,一種新型消費商品經濟的縮影。如《赫米達奇菜園》(1879年)、《龐圖瓦茲鋤地的農民》(1881年)等作品,從中可清晰地看到家前屋后、山坡平地種植的一茬茬的卷心菜、一片片的大白菜、一行行的大頭菜、蘿卜、土豆等生長在黃色的沃土之中,在收獲之后供應當地居民、周邊城市和出口。
反映出民居與環境狀況。《龐圖瓦茲的房屋》(1872年)、《龐圖瓦茲一角》(1874年)、《鴨池》(1874年)等眾多作品,從不同視角描繪了民居建筑與環境狀況。形態妙肖地再現了壘砌的石頭墻、斑駁的白石灰墻壁、橙與藍色尖頂的農舍。在家前屋后,或有時令蔬菜和特產品種的菜田;或有山丘上開墾得井然有序的、五顏六色的農田;或有果樹下、草地上的牧牛羊群;或有明鏡般的池塘里群鴨嬉戲,泛起微波漣漪和晃動的倒影;或有石頭路徑上騎著騾子歸家的漢子和過往的村婦等。一種生機盎然的鄉村景象躍然于眼簾。
反映出家畜與家禽養殖狀況。在畢沙羅對先后居住過的龐圖瓦茲、盧孚西安、埃拉尼村鎮的景象描繪中,都有不相同家畜和家禽放養場景。如《池塘里的鴨子》(1871年)、《蒙特福構的牧鵝女孩》(1876年)、《盧孚西安的景色》(1879年)、《農舍前的女人和羊》(1879年)等作品,都有表現農婦或少女放牧的畫面;描繪草地、林間、池邊吃草喝水的牛羊,以及池中游動的白鵝或鴨子。家庭養殖并非農民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而是通過鄉村街頭地攤集市將剩余家禽等銷售出去,這也是最古老的的商品交易平臺。為此畢沙羅還表現了家禽等銷售市場的景象。如《龐圖瓦茲的家禽市場》(1882年)、《吉索的家禽市場》(1885年)等。在這類集市主題的作品中以表現禽類買賣的內容比較多。畫面的主角賣主婦女,是作為勞動者形象去表現的。她們把家中飼養的活禽放置于身邊的地面,蛋類盛在籃子里。背景則是擁擠不堪的逛街消費者。以此可以判斷家庭養殖業市場需求量及經濟價值較大,一是供給當地居民,二是供外地和周邊城市商販的采購。但從攤主的貯存和裝運貨物的容器來看,都是較小的簍筐和籃子,還未形成家庭養殖規模化和專業化,僅作為一種副業收入。
反映出交通運輸狀況。畫中常見的交通工具是村道馬車、水路船舶、鐵路火車等。當時馬車有載客和載貨兩種類型,如《運干草的馬車》(1879年)表現了三位農夫用馬車裝載干草的場景。這種兩輪平板式馬車,沒有車箱和頂篷,可以最大限度地裝載干草等農作物;在《獨輪車》(1879年)中表現田間搬運的小型運輸車。農民們在田間將收割的麥桿穗子捆扎成把,堆放在獨輪車上,便于在狹窄田埂小道和泥濘崎嶇田間手推行駛運輸,這是當時農村特有的田間運輸工具。船舶水運的作品有《塞納河》(1871年)、《龐圖瓦茲的木筏》(1872年)等,既有古老的木筏、木船、駁船,也有近代的蒸汽機船,再現了塞納河和瓦茲河水運的繁忙景象。特別是蒸汽機船的出現,極大提高了運輸效率。火車是當時現代化的標志,在他的田園風景畫中有著濃重的渲染。其中有全景式表現山丘之間一列行駛的火車經過村鎮的作品,如《龐圖瓦茲的夏天》(1877年)等;有小景式聚焦于火車軌道經過村落各個地點的作品,如《龐圖瓦茲的鐵路道口》(1873—1874年)、《龐圖瓦茲的鐵路橋》(1873年)等。這些景觀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龐圖瓦茲的交通運輸狀況在當時是較為先進和便捷的,這也為當地農工商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反映出鄉鎮工業狀況。在畢沙羅的一些田園畫面的遠景部分,能看到現代工廠高聳的煙囪形象,這也是最早不經意間表現現代工業文明內容衍生痕跡的啟蒙畫作。如《龐圖瓦茲的風景》(1867年)、《河岸上的景色》(1873年)等。隨后這類圖景在其作品中直接從背景內容改變為中景的主體內容。作為田園風光的一個主題,如《岸邊的工廠》(1872年)等,這類作品直接反映了龐圖瓦茲村鎮工業化的痕跡和經濟發展的潛力。
三、田園人物再現農耕生活情景
從田園景物聚焦人的活動,表現了藝術家對自然與社會生活關系的態度。通常風景畫是通過自然景色間接地表達人物思想感情。但在畫面中添加人物的活動,使人與景有機關聯與結合,則可直接揭示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生活的狀況及作者的態度。西方繪畫歷史中田園人物的表現有不同的思想表達和情感表達方式。早期法國現實主義畫家米勒作品更多的是再現勞動者的艱辛、凄涼、惆悵的生活狀態,反映創作者對農民勞動者的同情與崇敬,這類作品往往象征神圣與安貧樂道的思想內涵;柯羅的鄉村風景類似理想中的伊甸園,充滿詩意盎然的浪漫色彩,他將巴比松村表現為人間世外桃源的田園風光;馬奈是在郊區風景中描繪城市中產階層度假、游樂、閑逸的生活;畢沙羅的特點“不像米勒,也不像同時代的沙龍藝術家去表現理想化的農民或為農民的工作添上一層宗教、民族的情感,而是將農民的勞動表現為現代生活與經濟現實的一部分。”[5]204
畢沙羅長期生活在龐圖瓦茲和歐維鎮等地,因此他“得以更仔細、更專注地觀察一個區域的人情風貌”[1]55,“他畫自然而然的見聞,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畫面,真實地再現寧靜、安詳的鄉村生活場景。”[1]32另一方面,畢沙羅表現田園題材的作品,顯然也反映了當時法國商業中身無分文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現象。畫中菜園農場主將收割后的新鮮蔬菜運往巴黎農貿市場和鄉村集市,這也令觀賞者聯想到畢沙羅賣畫為生的經歷。他創作的油畫作品也同樣依賴城市市場銷售,家庭經常處于經濟危機之中,他不得不往返于城市與鄉村之間,所以將自己描繪成中產階級,這或許也是畢沙羅描繪農村場景的興趣因素。
菜園風景是農業現實狀況的一個縮影。從菜園的人物動態及勞動的環境中反映出當時農業人口結構狀況和勞動者的身份。有有土地的農民,也有流動打工的農民。如《龐圖瓦茲的菜園》(1879年)描繪了二位農民在簡樸農舍前的菜園中忙綠的身影。其中一位戴著紅頭巾的農婦低頭俯視菜苗;另一位男子膝蓋跪在泥土上面收割成熟的蔬菜。這勞作的男女看似是一家人,或是土地的主人。再看《收割》(1889年)描繪了一群青壯年婦女們聚集在一塊麥田里收割、捆扎、拾穗的場景。可以看出她們年齡相仿,不像是一家人,更像是在莊園間流動打散工的農民。
集市場景反映村民的社交活動。《九月的龐圖瓦茲》(1872年)、《吉索的家禽市場》(1885年)等,描繪的都是每周的市集日街頭路邊地攤式的市場景象。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扶老攜幼,人群簇擁,人聲鼎沸,熱鬧非凡。有推銷的叫買者;有詢價、討價還價者;有逛街的觀望者;有相互交流并指手劃腳,評頭論足一番的消費者。集市日是鄉村人口聚集最多的場合,在這里被畢沙羅表現為“農村分散的農民社交與交際生活的場所”[5]194,村民光臨集市“更多的是為了交流信息而不是貨物”[5]194,相對于貧乏單調的鄉村生活,集市就是物質與精神生活中的一頓大餐。
鄉村道路演釋鄉村人物角色的特征。《龐圖瓦茲的風景》(1874年)是一個橫幅畫面,景致寬廣,較為全面地反映田園日常生活的場景。畫面主體部分是橫穿綠色田園的村鎮艾尼麗路,畢沙羅把它處理成曲折蜿蜒的之字形狀,由此分割出遠、中、近的層次空間,并圍繞這條村道塑造出具有典型角色特征的村民形象。中遠景是田園司空見慣的場景,在路的盡頭有牽牛耕地的人影,草叢里有星星點點的白色的羊群。近景則是重點刻劃的人物角色,在道路最右邊是兩個并排緩慢地行走的中年村婦,兩人邊走邊聊,婦人的肘部挎著籃子,似乎是從早市購物回家;路中間位置是一輛行駛的馬車,載著兩位男士,一位是直視前方,專注地趕著馬車的車夫,另一位男士則側身瞭望田間地頭勞作的鄰里親朋好友及種植的莊稼狀況,好像是游走于周邊城市的收購商;最左邊是一位駝背的老人,肩背面袋,右手拄著拐杖,小心翼翼地前行,或許是從集市購物歸來,又或是做點小買賣的生意補貼家用,從中可以感受到老農的樸實勤勞的高尚品格。同時也引發觀者對社會保障問題的思考。
反映村民交往鄰里和睦的關系。世代生活在鄉村的一條河畔,一座山坡,共走一條道,擁有同一口鄉音,過著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里生活。在田間小憩、歸家途中、門前屋后、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聚集閑聊,有事一起做,有忙一起幫的淳樸民風,在他眾多作品中都有如此精彩的抒發。代表性作品《龐圖瓦茲隱秘居所小山》(1867年)描繪了正午時分陽光明媚的春景:山坡上一片翠綠色的樹叢與草地,其間有高低聚散、錯落有致的橙色屋頂民居;一條明亮的山間小路由近及遠,向山上迂回延伸,時隱時現地在農舍與樹林之間穿插;近處小路有位打著遮陽傘的婦人帶著她的幼童,正和一位迎面走來的農婦聚集在一起悠然地聊著天,路邊草地上席坐著幾個大男孩在嬉戲玩耍;遠處山坡小路上有一個農夫向遠方的人打著招呼,遠方農夫駐足回望并等候著路人一同回家,由此表現了祥和、溫馨的鄉情。畫中的人物活動是主題意境的點晴之筆,點撥出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的主題。
四、結語
畢沙羅地域田園風景畫似歷史的碎片,傳達出生活中真實自然的信息。展現出地域自然資源、經濟環境、農耕生活等多方面的內容,反映出地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狀況及發展演變的端倪,詮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并完美地再現了自然美與生活美。因此對當今風景畫寫生取景及題材內容的人文、生活化表現有著重要的啟示。
參考文獻:
[1]黃苗子主編.世界藝術大師·畢沙羅[M].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8.
[2]丁寧.歐洲風景畫漫議[M]//上海市博物館編.摹造自然:西方風景畫藝術.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39.
[3]楊新林.從山水畫中折射倪瓚平淡美的意蘊[J].藝術百家,2008(2):99.
[4]陸琦.風景畫的高度:西方名家作品精選[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24.
[5]愛斯金.印象派繪畫中的時尚女性與巴黎消費文化[M].孟春艷,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王展,淮陰師范學院美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繪畫美學,美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