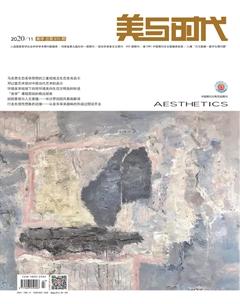論白居易詩(shī)中的教坊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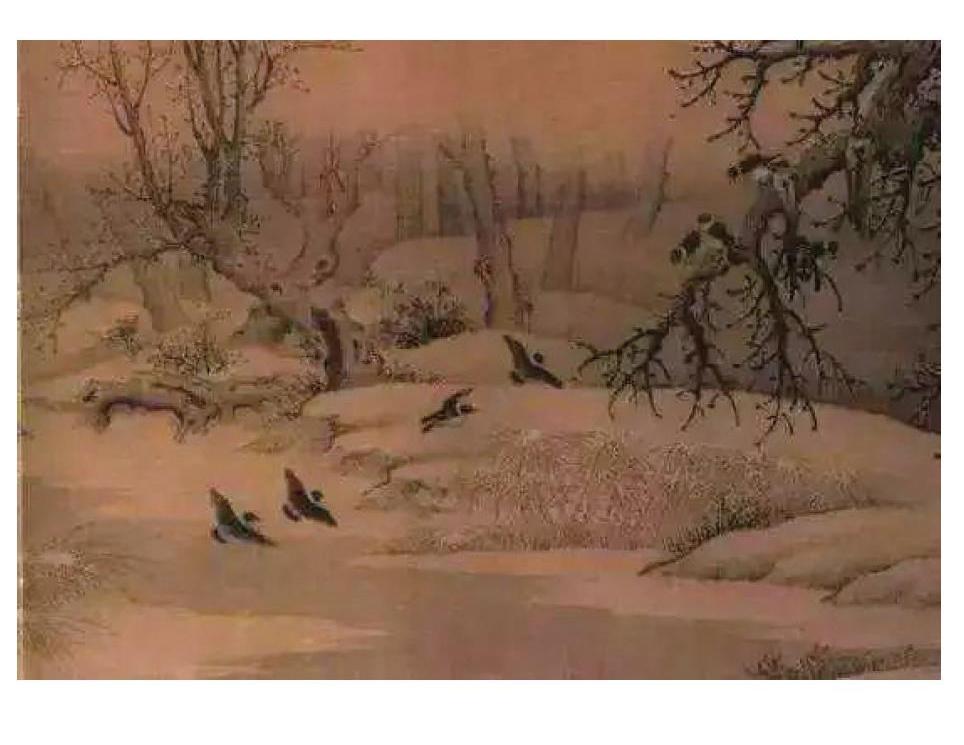
摘? 要:白居易是中晚唐時(shí)期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音樂詩(shī)人,他一生創(chuàng)作了兩千多首詩(shī)歌,其中以唐代教坊曲名為題的創(chuàng)作共有八首,包括《楊柳枝》《想夫憐》《烏夜啼》《長(zhǎng)相思》《山鷓鴣》《何滿子》《伊州》和《離別難》。這八個(gè)教坊曲名分三個(gè)部分論述:第一部分通過分類的方式分析每個(gè)曲名的本事、源流以及相關(guān)情感;第二部分著重分析白居易的詩(shī)歌如何體現(xiàn)應(yīng)用這些曲名;第三部分側(cè)重探討白詩(shī)創(chuàng)作的原因。
關(guān)鍵詞:白居易;白詩(shī);教坊曲名
唐代教坊分為內(nèi)教坊和外教坊。唐高祖武德年間創(chuàng)立的內(nèi)教坊主要負(fù)責(zé)演奏宮廷雅樂;玄宗時(shí)期,唐明皇設(shè)立了包括左右教坊在內(nèi)的外教坊。外教坊多演奏俗樂,樂曲題材來源廣而雜,不僅可以為宮廷服務(wù),也可以面向普通百姓。本文論述的白詩(shī)教坊曲名屬于后者,以《教坊記》中出現(xiàn)的教坊曲名為參考,集中論述白詩(shī)中出現(xiàn)的八個(gè)曲名,包括《楊柳枝》《想夫憐》《烏夜啼》《長(zhǎng)相思》《山鷓鴣》《何滿子》《伊州》和《離別難》。
一、教坊曲名事類
曲名事類,就是指按照曲名之含義,將曲名分類排列,“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實(shí)而號(hào)之,非有深遠(yuǎn)難知之義也。故仰以取諸天……俯以取諸地……中以取諸人”[1]255。由此可知,教坊曲名的命名或是含義最初都是來源于生活中的萬(wàn)事萬(wàn)物,而且蘊(yùn)含的意思也多通俗易懂。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歷史的變遷以及人為情感的加入,教坊曲名才產(chǎn)生了多樣的內(nèi)涵。白詩(shī)中的八個(gè)曲名可以按照這種方法分為三類。
(一)“自然”類屬
《伊州》是“自然”類屬中“地”的一種。作為教坊曲名它最早出現(xiàn)在《教坊記》中,而關(guān)于其本事最早見述于《樂府詩(shī)集》:“《樂苑》曰:‘《伊州》,商調(diào)曲,西京節(jié)度蓋嘉運(yùn)所進(jìn)也。”[2]843源自龜茲樂的《伊州》,由于節(jié)度使蓋嘉運(yùn)的進(jìn)獻(xiàn)來到宮廷,最終成為唐玄宗時(shí)著名的教坊大曲。《新唐書·五行志》又云:“天寶后,詩(shī)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3]由此可知,歷史的變遷導(dǎo)致詩(shī)人的心理發(fā)生了變化,因此,《伊州》就由最初為宮廷演奏的大曲演變?yōu)樵?shī)人寄托流寓思想的載體。
(二)“人事”類屬
“人事”就是包括人生存、發(fā)展在內(nèi)的各項(xiàng)事宜。其中第一類《離別難》屬于“旅情”,簡(jiǎn)單來說就是人的羈旅、思友或是思鄉(xiāng)這些情感的綜合。《樂府詩(shī)集》記載:“《樂府雜錄》云:‘《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篳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終號(hào)《怨回鶻》云。”[2]852可知《離別難》創(chuàng)立最初是表達(dá)妻子對(duì)丈夫的思念哀傷之情,同時(shí)也贊美了良人的優(yōu)秀品行。
第二類《想夫憐》與《長(zhǎng)相思》均屬于“戀情”一列,即男女之情。《想夫憐》據(jù)《樂府詩(shī)集》八中引《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為南齊相,一時(shí)所辟,皆才名之士,時(shí)人以入儉府為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hào)蓮幕者自儉始。其后語(yǔ)訛為‘想夫憐,亦名之丑爾。又《樂苑》:‘《想夫憐》,羽調(diào)曲也。”[2]852其實(shí),《想夫憐》是由《相府蓮》衍生而來的,但《相府蓮》屬于祝賀曲,用于宴會(huì)上,而《想夫憐》則用在青樓閨房,多為相思曲。
《長(zhǎng)相思》一曲的來源可以在《樂府詩(shī)集》中《長(zhǎng)相思》的“小序”得知:
古詩(shī)曰:“客從遠(yuǎn)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zhǎng)相思,下言久離別。”李陵詩(shī)曰:“行人難久留,各言長(zhǎng)相思。”蘇武詩(shī)曰:“生當(dāng)復(fù)來歸,死當(dāng)長(zhǎng)相思。”長(zhǎng)者久遠(yuǎn)之辭,言行人久戍,寄書以遺所思也。古詩(shī)又曰:“客從遠(yuǎn)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zhǎng)相思,緣以結(jié)不解。”謂被中著綿以致相思綿綿之意,故曰長(zhǎng)相思也。又有《千里思》,與此相類。[2]750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郭茂倩為我們提供了四種《長(zhǎng)相思》曲名的來源,分別出自漢末的《古詩(shī)十九首》以及相傳為李陵、蘇武二人的詩(shī)作當(dāng)中,但是其所表達(dá)的主題不外乎兩種——男女之情和朋友之誼,因此也決定了之后的詩(shī)人在創(chuàng)作詩(shī)歌時(shí)的主體情感風(fēng)向標(biāo)。
最后一類《何滿子》是“士女”行列的一種。查閱《教坊記箋訂》附錄三,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士女”類的曲名大都以“娘”“子”“女”結(jié)尾,這也就說明這一類的曲名多表達(dá)的是女性的情感事態(tài)。《何滿子》歷來有“何”與“河”兩字差異之爭(zhēng),宋郭茂倩《樂府詩(shī)集》曰:“開元中,滄州有歌者何滿子,臨刑時(shí)進(jìn)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杜陽(yáng)雜編》曰:“文宗時(shí),宮人沈阿翹為帝舞《何滿子》,調(diào)辭鳳態(tài),率皆宛暢。然則亦舞曲也。”[2]854由此可知,《何滿子》既是曲名又是舞曲。
(三)“物情”類屬
《楊柳枝》是“物情”類屬中“木”的一種。據(jù)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記載《楊柳枝》:“白傅閑居洛邑時(shí)作,后入教坊。”[4]《折楊柳》屬于橫吹古曲,起初是以楊柳喻送別之意,中唐以后,經(jīng)樂童改編,始為新聲,即白樂天創(chuàng)詞之《楊柳枝》。又據(jù)《碧雞漫志》卷五:“《鑒戒錄》載:‘《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shī)云‘萬(wàn)里長(zhǎng)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又云‘樂苑隋堤事己空,萬(wàn)條猶舞舊春風(fēng)。皆指汴梁事。”[5]
“禽”列的曲名包括《烏夜啼》和《山鷓鴣》兩種。關(guān)于《烏夜啼》,《教坊記》云:“宋彭城王義康,衡陽(yáng)王羲季弟,囚之潯陽(yáng),后宥之,使未達(dá),衡陽(yáng)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dāng)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1]6其實(shí),六朝樂府詩(shī)歌中早有此曲,《樂府詩(shī)集》將其歸為清商曲辭中吳聲歌曲之西曲歌,則此曲應(yīng)為清樂。據(jù)近人任半塘《唐聲詩(shī)》:“教坊廣羅里巷之樂曲,且及邊塞之聲。”[6]由此知《烏夜啼》一方面預(yù)示吉兆,引申為慈孝之鳥,另一方面又與邊塞之事相聯(lián)系。
《山鷓鴣》是來自民間的樂曲,經(jīng)過整理改編才成為教坊曲的經(jīng)典,它是《教坊記》中的第一百八十三個(gè)曲子,主要在宮廷宴饗時(shí)演奏。《歷代歌辭》曰“《山鷓鴣》,羽調(diào)曲也”[2]853。《唐音癸》記載:“《韻語(yǔ)陽(yáng)秋》:李白有聽此曲詩(shī):‘清風(fēng)動(dòng)竹,越鳥起相呼蓋其曲效鷓鴣之聲為之。”[7]
總之,教坊曲名都不是古者憑空臆造的,它們都有屬于自己的獨(dú)特內(nèi)涵,當(dāng)然教坊曲名的分類也是多樣的,但是不論是哪種方式,它的本事以及表達(dá)的情感意趣都是有共同點(diǎn)的。
二、白詩(shī)中的教坊曲詩(shī)
教坊曲和唐代詩(shī)歌是互相影響的,一方面詩(shī)歌創(chuàng)作提高了教坊樂曲的表現(xiàn)能力與價(jià)值,另一方面詩(shī)人根據(jù)教坊曲創(chuàng)作歌辭,也有利于表達(dá)自己豐富情感,促進(jìn)詩(shī)歌風(fēng)格的多樣化。
從教坊曲的曲名看,教坊樂曲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正如任半塘所云:“則因取材真切,而覺含意生動(dòng),分明。由此可見唐代樂曲富有生命,多為時(shí)代與社會(huì)反映逼真之物……余名或表宗教信仰,或寄才人幽憂,或抒宮閨怨思,或彰“蠻夷”響慕……顯然范圍廣闊,而情志真純。”使用教坊樂曲所作之歌都是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表達(dá)著詩(shī)人的真切感情。
(一)白居易所作的題為《楊柳枝》的詩(shī)共有十首,包括《楊柳枝八首》和《楊柳枝》兩首,均屬于晚年詩(shī)作。
1.《楊柳枝八首》作于大和年間,當(dāng)時(shí)白居易任秘書監(jiān)及刑部侍郎,但是由于朝廷日益激烈的朋黨之爭(zhēng)再加上好友的不斷被排擠,白居易選擇退居洛陽(yáng),以太子賓客的身份分司東都洛陽(yáng)。
六幺水調(diào)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yíng)里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yáng)橋。
依依裊裊復(fù)青青,勾引清風(fēng)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shí)。可憐雨歇東風(fēng)定,萬(wàn)樹千條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夸,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fēng)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huán)樣,卷葉吹為玉笛聲。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裊輕風(fēng)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yīng)無續(xù)得期。
這組詩(shī)是作者為當(dāng)時(shí)流行曲調(diào)寫的歌詞,根據(jù)其所寫內(nèi)容,第二、三、七、八首都是以歌詠楊柳為貫聯(lián)線索,描寫了各種相思離別的場(chǎng)面。第一首點(diǎn)明詩(shī)人翻新曲調(diào)的原因,認(rèn)為詩(shī)歌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反映時(shí)代的聲音、時(shí)代的脈搏,這樣的詩(shī)歌才有生命力。第二首屬于懷古詩(shī),其中借用與“柳”有關(guān)的兩個(gè)歷史人物典故,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思緒萬(wàn)千的感慨之情。第五、六首巧妙描寫南朝名妓蘇小小,實(shí)際上暗指詩(shī)人家妓樊素,借著懷念前朝名妓而表達(dá)自己對(duì)家妓的思念與不舍。
2.《楊柳枝》二首:
其一:
一樹春風(fēng)萬(wàn)萬(wàn)枝,嫩于金色軟于絲。
永豐西角荒園里,盡日無人屬阿誰(shuí)?
其二: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
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兩星。
其一是一首詠物言志詩(shī),通過寫柳枝的婀娜多姿及其荒涼的生長(zhǎng)環(huán)境,詩(shī)人表現(xiàn)出對(duì)永豐柳的痛惜之情,實(shí)際上抒發(fā)了自己對(duì)當(dāng)時(shí)政治腐敗、人才埋沒的感慨。其二是繼其一所作的,我們可以將其看做是詩(shī)人當(dāng)時(shí)的一種愿望,寄希望于柳枝,幻想得到重用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
縱觀白居易新翻的《楊柳枝》,我們可以看出,詩(shī)人舊瓶裝新酒,雖然重復(fù)著相似的題材賦詩(shī),但卻極大地豐富了詩(shī)歌的內(nèi)容,因此也為我們展示了詩(shī)人更多樣的情感。
(二)《聽歌六絕句·想夫憐》中寫道:“玉管朱弦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杯。長(zhǎng)愛夫憐第二句,請(qǐng)君重唱夕陽(yáng)開。”這首詩(shī)作于開成至武宗會(huì)昌年間,這里的“夕陽(yáng)開”指的是王維的詩(shī)句“秦川一半夕陽(yáng)開”,原題為《和太常韋主薄溫陽(yáng)寓目》,后因歌者選詞以配樂的需要而改為《想夫憐》。古人常有“男子做閨音”的現(xiàn)象,“想夫憐”即為思念丈夫而顧影自憐之意,加上古詩(shī)常以男女之情喻君臣關(guān)系,因此這首詩(shī)在一定程度表達(dá)的是詩(shī)人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和處境的不如意之情。
(三)《烏夜啼》詩(shī)云:“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jīng)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wù)邽檎唇蟆B曋腥绺嬖V,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dú)哀怨深。應(yīng)是母慈重,使?fàn)柋蝗巍N粲袇瞧鹫撸笟{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fù)慈烏,鳥中之曾參。”此詩(shī)作于元和六年退居下邽之際,時(shí)白母逝世,詩(shī)人對(duì)母親感情深厚。這首詩(shī)采用寓言體,借詠慈烏表達(dá)了對(duì)母親的深情。
(四)《伊州》詩(shī)云:“老去將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應(yīng)不得多年聽,未教成時(shí)已白頭。”這首詩(shī)作于大和二年,當(dāng)時(shí)白居易居于洛陽(yáng),仕途受挫,積極進(jìn)取的人生理想也隨之破滅。詩(shī)中的作者懷著一種愁緒教琴,但最終的結(jié)果卻是“未教成時(shí)已白頭”,詩(shī)人并沒有在教琴的過程中感受到排遣掉自己的憂愁,反而增添了教琴不成的煩惱,其實(shí)根本原因是詩(shī)人當(dāng)時(shí)的心情是憂愁的。
(五)《聽歌六絕句·離別難》詩(shī)云:“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回一望塵。不覺別時(shí)紅淚盡,歸來無淚可沾巾。”這是一首送別詩(shī),據(jù)白居易的生平情感記錄,可推測(cè)分別的兩人是白居易和他的初戀湘靈,詩(shī)人在詩(shī)中表達(dá)了自己強(qiáng)烈的不舍和依依惜別之情。
(六)白居易的《長(zhǎng)相思》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diǎn)點(diǎn)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shí)方始休。月明人倚樓。”這是一首懷人念遠(yuǎn)的抒情詩(shī),有人認(rèn)為送別思念之人是初戀,有人認(rèn)為是家妓樊素。在這里,據(jù)謝思煒的說法,這首詩(shī)采用了代言體的形式描寫了女主人公對(duì)情人的思念,所寫內(nèi)容很有可能和作者早年的戀愛經(jīng)歷有關(guān)。
(七)《何滿子》詩(shī)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shí)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這是白居易關(guān)于何滿子其人的描述,何滿子是唐玄宗時(shí)期的歌手,因得罪皇帝,被判以極刑。自此以后《何滿子》遂為悲歌代稱,而何滿子其人也因出色的技藝被眾多詩(shī)人相繼賦詩(shī)。
(八)白居易《山鷓鴣》詩(shī)云:“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fù)啼,啼時(shí)露白風(fēng)凄凄。黃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不緩復(fù)不急,樓上舟中聲暗入。夢(mèng)鄉(xiāng)遷客展轉(zhuǎn)臥,抱兒寡婦彷徨立。山鷓鴣,爾本此鄉(xiāng)鳥,生不辭巢不別群,何苦聲聲啼到曉。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這首詩(shī)中的“苦竹嶺”指的是鷓鴣鳥的老家,白居易借助鷓鴣鳥同樣是“懷南不北”的習(xí)性來抒發(fā)傾訴自己的身處異鄉(xiāng)之苦。
三、形成原因
以教坊曲調(diào)為題或者圍繞其作詩(shī)是當(dāng)時(shí)士大夫文人最擅長(zhǎng)也是最樂于做的,這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背景、曲調(diào)流傳以及士大夫的自覺性需要密切相關(guān)。
(一)社會(huì)背景
《教坊記》中記載了初盛唐時(shí)期的教坊曲名,大約成書與唐代宗寶應(yīng)年間,當(dāng)時(shí)教坊、太常是普遍存在的音樂演奏場(chǎng)所,但是隨著安史之亂的發(fā)生,這些所謂的音樂機(jī)構(gòu)受到大肆破壞,教坊中的樂人、歌妓等音樂人才也都流落人間。因此士大夫文人有更多的機(jī)會(huì)接觸到這些教坊曲調(diào),然后加以創(chuàng)制填詞,形成屬于自己的詩(shī)作流傳于世,同時(shí)這也成為教坊曲調(diào)延續(xù)生命的方法。
(二)士大夫的自覺
唐代的文人士大夫喜愛宴游狎妓是當(dāng)時(shí)的普遍現(xiàn)象,這也就使得詩(shī)歌詠唱成為文人宴席的助興節(jié)目之一。白居易在閑居洛邑時(shí)擔(dān)任一閑職,而且俸祿也很樂觀,這就使得他舉辦或者參加宴游玩樂、詩(shī)歌酬唱沒有后顧之憂。文人的詩(shī)酒風(fēng)流促進(jìn)了以教坊曲為題的詩(shī)歌產(chǎn)生、流傳,一方面為教坊曲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另一方面,詩(shī)人通過詩(shī)歌寄托情感,排遣憂愁。除此之外,士大夫長(zhǎng)期寫作教坊曲詩(shī),可以改變翻新其內(nèi)容,也使得詩(shī)人的詩(shī)風(fēng)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fā)展。
總之,詩(shī)歌與詩(shī)人任何時(shí)候都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通過分析白居易詩(shī)歌中的這八首教坊曲詩(shī),聯(lián)系八個(gè)教坊曲名的本事,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各個(gè)朝代的變遷,加上文人創(chuàng)作的主觀性,教坊曲的內(nèi)涵也在經(jīng)年累月中發(fā)生著改變,但無論怎么變都是從最初的意義中繁衍生發(fā)出來的。
參考文獻(xiàn):
[1]崔令欽.任半塘,箋訂.教坊記箋訂[M]. 北京:中華書局,1962.
[2]郭茂倩.樂府詩(shī)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歐陽(yáng)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921.
[4]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58:18.
[5]王灼.碧雞漫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8:35.
[6]任半塘.唐聲詩(sh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8.
[7]胡震亨.唐音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38.
作者簡(jiǎn)介:高雪雪,遼寧師范大學(xué)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