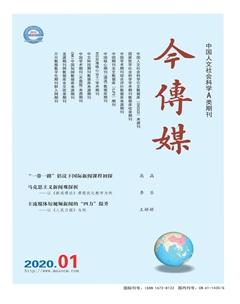從擂臺到明星
周芳 曾榮
摘?要:本文從歷時性的角度對機器人格斗節目進行研究,重點討論其形式、內容、功能、審美等方面的變化。機器人格斗節目的屏幕化”返場”既是智能時代的特色,又是在歷時性視角中不斷更迭變遷的實踐產物。節目從擂臺走向舞臺、從比拼競技到重視演技,受眾也從窄眾起于大眾化,節目的美學呈現也從暴力美學延伸到人文情懷領域。機器人格斗節目在形式和內容上更娛樂化、戲劇化,使節目本身的競技性被其他“看點”覆蓋和消解,其所具有的功能也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從知識科普走向大眾娛樂,其機器人“車庫文化”也逐漸消融為一般意義上的“圍觀”。
關鍵詞:機器人節目;競技消解;功能遷移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20)01-0107-03
機器人格斗節目最早源于國外,國外在這類節目的制作上已達到一個相對成熟的程度,但對中國來說,它還是一種新興的綜藝節目樣態。十多年前,中央電視臺CCTV-7頻道和國內一些地方臺曾引播過BBC的《機器人大擂臺》,并且得到了一定的關注。然而,這樣的節目在中國受眾層面上依然較為“窄化”,當時國內也沒有足夠的經驗去制作類似的節目。
2018年1月8日,國內首檔以機器人格斗競技為題材的綜藝真人秀節目《鐵甲雄心》在浙江衛視播出。同年3月、4月,兩檔機器人競技網絡綜藝節目——《機器人爭霸》和《這!就是鐵甲》在網上熱播,受到了觀眾的廣泛關注。隨著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機器人節目的播出,機器人格斗文化節目逐漸被更多的觀眾接受,節目的融合形式和多元化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機器人競技在中國的發展,同時也引發了更多爭議:機器人節目到底是應該以機器人為核心還是以人為本真,我們又該如何規劃節目中“人”和“機器人”的雙重競爭版圖?
一、從擂臺到舞臺:明星的深度卷入對競技的沖淡
早期的機器人格斗節目沒有明星參與,參賽選手、主持人、觀眾是構成節目的三大主體,機器人選手進行對決則是節目最主要的內容,節目的“擂臺性”十分鮮明。如“亞太區機器人電視大賽”,節目更接近于一個體育賽事的轉播,節目以機器人擂臺為核心,以比賽輸贏晉級為流程,所有的看點均集中在參賽隊伍和機器人格斗本身。
而現在的綜藝大多有明星助陣,這種偏重科技競技的節目,其受眾群本就相對窄化,如若沒有話題點,傳播起來會更困難。因此,很多節目制作方通過邀請明星作為主要參與者或“發起人”,用多重身份來表演和豐富節目的內容。明星的加入能為節目帶來更多流量,由于其自帶的“舞臺屬性”和粉絲基礎,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節目收視率和提高節目話題的點擊率。
明星加入后,節目在制作上必然會為明星單獨劃分出較多內容,這就使節目本身包含的競技性受到了一定的沖擊。觀眾不僅看到機器人選手之間的格斗,也會被明星在節目中的表現,明星之間的沖突或者是明星與選手之間的互動等吸引眼球。在《機器人爭霸》中,明星親手操控格斗機器人,觀眾雖然看到的是操控極為不熟練的嘉賓,但這種以明星為代入的“體驗感”卻滿足了觀眾對機器人操控的“幻想”以及對明星嘉賓實力的好奇。明星的加入使觀眾的注意力從“擂臺”轉向了“舞臺”,從“機器人競技”轉向了“明星”。明星深度參與節目,節目內容的主體和視點就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轉移,其競技性就在無形中被消解。
二、從競技到演技:戲劇化和表演化的成分加重
其實,早在2000年的《博茨大戰》就已經以真人秀的形式在Comedy Central頻道正式播出。《博茨大戰》與《機器人大擂臺》有著鮮明的差異,盡管身為一個專業賽事,但節目卻顯得很“隨意”:邀請了一位無專業基礎的“外行人”當主持;問出一堆“不知所以”的問題;喜劇演員千方百計地利用采訪環節插科打諢……而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在于《博茨大戰》當初的轉播簽約方Comedy Central本身就是一個娛樂臺,以至于在節目定位和制作上就受到了部分限制。后來這一點為《博茨大戰》創始人Gregory詬病,并要求之后的《博茨大戰》一定要按體育賽事的方式來制作。由于《博茨大戰》本身的賽事風格和場地設計原因,雖然燈光效果不如《機器人大擂臺》,但憑借著專業的高水平對抗,《博茨大戰》依然在美國打開了市場。
當前,節目生態競爭殘酷,面對著市場化的壓力,各大媒體也不得不迎合受眾多元化的需求,高收視率和高點擊率成為其兩大追逐目標。隨之而來的,節目中戲劇化情節、翻轉情節增多,以及后期剪輯制造出的懸念效果在節目中頻繁出現。《這!就是鐵甲》里,有著“老狐貍”設定的撒貝寧遭到“打臉”的情節不少;“重度猶豫癥患者”吳尊在選隊員的時候總是搖擺不定,因而錯失選擇良機……“在劇本中將人物角色設定完成之后,明星嘉賓只要根據劇本扮演角色,而無法展現其真實的人物性格”[1] 。此外,節目內容部分也常有“劇本感”:《機器人爭霸》中全場造價最貴的機器人——“電競魔靈”在制造者對其一頓吹捧之后,慘遭對手“黑狼”擊敗,并使其意外著火,節目被迫暫停錄制;節目中多臺格斗機器人也總在比賽開始前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情節似乎像設定好一般,誘導觀眾成為“看戲”的人。“真人秀的核心離不開人,不管是對環境進行選擇,還是對節目規則進行制定,目的都是在于節目更好地進行戲劇性動作”[2] 。可見,在種種戲劇化情節的背后,表演成分已經占據節目大部分時長,早已超過格斗機器人之間對決所需要的時間,節目能夠體現的競技性少之又少。
三、從“機器”到“人”:暴力美學的情懷性弱化
早期的機器人格斗節目形式相對簡單,多為賽事轉播或機器人之間的格斗晉級,機器人節目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形式在當下也會遇到更多挑戰。《鐵甲雄心》作為中國首檔機器人節目是相對保守的,其借鑒并改良了國外成熟機器人競技節目的賽制,在制造機器人階段和對抗階段分別使用真人秀和賽事的形態。《這!就是鐵甲》和《機器人爭霸》的節目也都以戰隊的形式來進行對決,這相當于是在格斗機器人單獨作戰后又組成團隊的形式進行比拼——明星隊長根據隊員的長短優劣來挑選出合適的格斗機器人。
“田忌賽馬”式的節目形態讓人們的關注點從“馬”本身的技能競爭到“人”的謀略競技,節目形態從機器人之間的抗衡也延伸為人與人之間的對決,這背后則是暴力美學向人性情懷的一個“轉場”。早期的機器人格斗節目中西方暴力美學風格鮮明,強調“暴擊”“KO”“勝利”,是一種人類攻擊性本能的釋放。在奧地利動物學家、習性學創始人康羅·洛倫茲看來,人類的“攻擊性比大多數其他的本能更容易找到一個替代物,而求得完全的滿足”[3] ,機器人格斗便是這樣一個替代物。在現代文明中,人類格斗競技無法實現,社會倫理和法律道德層面都不具備可行性,而無生命的機器人的制造和開發很好的替代了暴力實施的對象,鋼鐵擂臺則成為最好的格斗“場域”。機器人競技從本質上說是實現了一種徹底的暴力格斗競技。然而,在綜藝化的機器人格斗節目里,暴力被沖淡,故事的加入、賽場外空間的拓展,風格逐漸“溫情”,鋼鐵的“冰冷”幻化為人的“真情實感”:選手接受采訪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團隊介紹機器人開發過程中的辛酸與不易,明星們互拋懸念、“互抖機靈”,主持人控制全場大方得體……暴力美學被弱化,人的情懷則被強化和提升。
四、從窄眾到大眾:“車庫文化”嬗變為“圍觀”
“車庫文化”是美國創新精神中重要的一環。“車庫文化”最早的發端是汽車發明,而后是汽車改裝和修理,車庫甚至還被用來作為教育子女動手開發興趣的“重要基地”[4],是一個“研究空間”,體現的是勇于創新、敢于吃苦的精神。在美國,誕生于車庫的“作坊”會受人們尊敬,在這種文化背后,車庫這一“場域”被賦予“奇跡”的屬性。
在機器人格斗題材的節目里,通過有限的時間迅速修理機器人并重返賽場,這對受眾來說便是期待“奇跡”的過程。當機器人節目還處于純粹的機器人格斗階段時,機器人的愛好者和創造者是其主要受眾群,暴力美學和“車庫文化”則是節目的核心表征。然而,機器人格斗節目發展至今,它的受眾面不僅是前兩類人,還有明星的粉絲和潛在粉絲,受眾范圍擴大了許多。明星的舞臺、機器人的擂臺、場外的紀實空間、廣告空間……無一不構成了視覺分享領域,既呈現出公共性,又帶有娛樂性,在人與機器人熟悉而又陌生的關系特征中,現場觀眾集聚、屏息、歡呼,屏幕前的“粉絲”“觀眾”見證著節目的進度條在時間里的消亡。“圍觀即參與,分享即表態”[5],此刻的圍觀是具有力量的,他將“車庫文化”中的獨創精神化為信息分享,將奇跡的誕生過程在熒幕前“示人”。“圍觀的力量”此時便是“見證的力量”,即能“ 把信息移動到最能產生影響的地方”[5]。觀眾在這個過程中各取所需,有人看見了技術、有人看見了團隊、有人看見了情懷、有人看見的是明星。“車庫文化”中的私密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見證與圍觀。
五、從科普知識到娛樂互動:功能的遷移與衍變
機器人格斗節目問世之前,除了機器人愛好者,普通大眾對格斗機器人是沒有專業性的知識了解的。當這類賽事被轉播后,節目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它才真正被大眾所認知。節目里介紹了格斗機器人的由來、制作過程、攻擊屬性、賽場的配置等,側重技術知識的科普,如傳感器、自動控制、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圖像識別、路徑規劃……所以在當時,機器人格斗節目最核心的功能便是科普格斗機器人的相關知識,并為機器人研發團隊和愛好者群體提供一個全球性的交流平臺,激勵更多年輕人加入機器人浪潮,開發機器人格斗競技的龐大娛樂及消費市場。
機器人格斗這個項目在國內普及程度沒那么高,認知度低,缺乏大眾層面的關注度,因此在機器人技術方面也沒有體現出更高的賽事水準,如沒有碰撞傳感器、影像識別、紅外感應、激光測距、自主行走,也沒有人工智能,甚至部分機器人沒有類似工業機器人的預設程序,更像裝載了攻擊武器的大型電動“遙控玩具”。此外,明星的加入、真人秀的形式、劇本與臺本都使得機器人格斗節目的傳播功能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遷移。選手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各種拍攝采訪排練上,比賽的重點卻是一場配合主辦方的“秀”,每個隊伍沒日沒夜畫圖趕工做出來的機器人鏡頭數量卻驟減,一個競技性質的節目變成了一個娛樂性質的節目。機器人格斗節目也像更多的綜藝節目一樣充滿了“情懷”,有著令人“潸然淚下”的故事,有著激烈的人與人之間的爭論……而機器人本身所代表的技術性、科技性卻在傳播的版圖中縮小了。
六、結?語
這種從時間到空間,從線下到線上,從直播到錄播,從窄眾到大眾的變遷,機器人格斗節目儼然已經從機器人之間的競技轉化為“田忌賽馬”式的比賽形式,“人”在節目中不僅是真人秀的形式,更是內容上的情節與情懷。在這個時代,機器人格斗節目似乎有著更多的可能性,但也存在著更多潛在的風險:其核心的競技性被消解、“車庫文化”的表征被弱化、暴力美學被減淡、科普功能也逐漸被娛樂互動所取代。
參考文獻:
[1]?劉姣露.網絡自制綜藝節目的內容生產研究[D].海南師范大學,2018.
[2]?房寧.試析電視娛樂真人秀節目主持人角色和功能的轉變[J].電影評介, 2014(21):86-87.
[3]?羅輯,王現強.《鐵甲鋼拳》:后身體暴力時代的格斗競技敘事[J].電影評介,2016(21):51.
[4]?丁大琴.創客及其文化歷史基因探源[J].北京社會科學,2015(8):23-24.
[5]?胡泳.圍觀的力量[N].中國青年報,2010-12-27.
[責任編輯:楊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