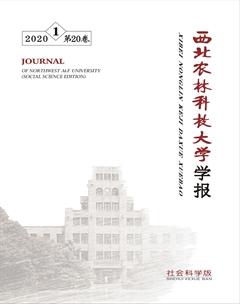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動力與實現機制
李俏 賈春帥
摘?要:推進農村產業融合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而探討以合作社為載體的農村內生性產業融合模式,對于提升農業產出效率、繁榮農村經濟和促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相關政策的梳理發現,合作社依次經歷了初期起步及產業破壁階段、快速發展與農業產業化階段、發展壯大與帶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階段。在具體實踐中,農業多功能開發、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經濟良性循環、跨界經營等需求都對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提供了現實動力,合作社也展現出了資源整合、社會服務和公信力增強等優勢,并探索形成了農業內部技術融合、縱向一體化經營融合、現代農業與旅游業融合、農業生態旅游和文化創意產業融合模式。針對目前合作社所面臨的規模小、資金少、創意不足等問題,建議從鼓勵合作社向綜合和聯合方向發展、改善合作社融資渠道、挖掘當地特色文化等方面著手構建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實現機制。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村產業融合;合作社
中圖分類號:F3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0)01-0033-09
一、問題的緣起
近年來,“三農”形勢逐漸向好,卻也面臨一系列風險與挑戰,以“老人農業、空心農村和失地農民”為主要特征的“新三農”問題日漸突出,農業傳統粗放型生產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后勁不足。對此,黨中央、國務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政策文件,將“農村產業融合”作為促進農業增效、農村繁榮和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而合作社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形式,在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國內許多學者都將“培育和發展農民合作社”作為促進產業融合的必要對策[1-4]。那么為什么合作社能夠帶動農村產業融合,其背后的政策原因是什么?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發展的優勢有哪些?其實踐模式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深化合作社的相關理論,還可為當下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新思路和新經驗。
在經濟學領域,“產業融合”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最早源于20世紀60年代因數字技術出現而導致的產業交叉[5],隨后開始從信息通訊業向其他經濟領域拓展,其驅動力主要來自于管制的放松、技術創新與擴散、市場需求、商業模式創新等[6]。其含義是指因某些技術在一系列產業中的廣泛應用和擴散而出現的創新活動發生過程[7]。然而,作為一種應用于農村經濟領域的新范式,“農村產業融合”則是需要理論挖掘與實踐轉化的新概念。日本學者今村奈良臣最早于1996年就用“六次產業”(1產業+2產業+3產業=6)這一概念來指代農村產業融合現象,他認為發展綜合性農業有利于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和農民收入[8]。在我國,“農村產業融合”區別于“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產業化,是農業產業化在產業層面的擴展與升級[2],是指以農業為依托,將勞動力、資本、技術和資源等生產要素進行產業之間跨界經營配置,使農業與二三產業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協同發展,最終實現延伸農業產業鏈、擴展產業范圍和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9]。
從既有研究成果來看,對于合作社與農村產業融合的關系尚缺乏成型的理論解釋,但目前學界大致形成了如下三類觀點:一是認為合作社是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的主要載體。目前涉及農村產業融合的組織有普通農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非農企業和工商資本、平臺型企業等六類[10],但一體化經營的合作社往往比農民單家獨戶實現產業融合更具資源整合能力[11],比農業企業更能結合當地特色,有利于實現產供銷間的聯合[12]。其作用不僅在于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業產業鏈的延伸,農業多功能的拓展,還可以促進農村新業態的不斷涌現[13-14]。二是認為合作社為實現農村產業融合提供了可借鑒的管理模式。根據法國農業發展經驗,一體化經營的合作社管理模式可以延長農業產業價值鏈,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合作社在法國已發展成為農業和食品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5]。三是認為合作社可通過提供專業化服務構建起農業縱向融合的經營與利益機制,如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進入農業的二三產業就可以直接幫助農民獲得經營農業下游的收入[16],而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同樣也會促進合作社等大批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產生[17]。目前中國農民合作社不僅在數量和質量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18],而且在國內各地都開始出現了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具體實踐。而在國外,日本農協、韓國農協、法國合作社早已在推動農村產業融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5]。
綜上所述,目前學術界有關農村產業融合的研究成果較多,但明確有關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內容的研究則相對較少,而已有關于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研究成果中多集中于對具體實踐現象的描述,而缺乏對于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的動因及其實現機制的學理性分析。據此,文章將緊扣當下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系統梳理改革開放以來相關政策的演進脈絡,分析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動因與優勢,并結合實際案例深入探討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的具體模式與存在問題,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出推進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的實現機制。
二、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的政策演進
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中央政策圍繞“三農”問題,大體經歷了從解放生產力到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再到盤活整個農村經濟的改革方案,并陸續提出了有關合作社發展及其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思路。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系統梳理發現,合作社在帶動農村產業融合方面主要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一)農民專業合作社起步與產業破壁階段(1979-2007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中國得以確立,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勞動生產率得到了顯著提高,但隨之形成的市場機制不僅對農民的資金實力和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形式帶來了全面挑戰。對此,國務院于1993年頒布了《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穩定、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而少數二三產業發達的地方則允許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實行適度的規模經營。在此政策背景下,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始得到初步發展。截至2006年,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數量已超過15萬個,帶動農戶2 363萬戶,占到當時全國農戶總數的9.8%[19],并在一些地方實踐中已經出現了“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的產業經營模式。隨后,2006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第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并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實施。同年農業部開始組織實施“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加工推進行動”,該行動計劃的核心是通過培育壯大龍頭企業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來提高對農戶的帶動力。且在當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的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再次強調要“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為合作社的快速發展以及促進農村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合作社快速發展與產業延伸階段(2008-2014年)
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農民專業合作社興辦農產品加工企業或參股龍頭企業”,開啟了合作社涉及農村產業融合的新局面。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指出,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發展,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從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的角度,將農民專業合作社納入政府貸款擔保公司的服務范圍,“支持有條件的合作社興辦農村資金互助社與農產品加工企業”。在此政策影響下,到2011年底,中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已上升至50.9萬個,其中提供產加銷一體化服務的合作社達26.6萬個,占合作社總數的52.3%,從事購買、倉儲、運銷和加工服務的合作社分別占3.5%、0.8%、3.3%和2.2%[20]。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則再次強調,要繼續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興辦農產品加工企業或參股龍頭企業,并重點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初加工和貯藏設施予以補助。隨后的2013年和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分別提出“鼓勵農民興辦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類型合作社”,同時提出“支持農民合作社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培育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理念。自此,合作社涉足產業延伸的業務更加豐富起來。
(三)合作社壯大與產業融合階段(2015年至今)
從合作社法頒布至2015年,合作社數量已從2006年的15萬家發展為153.1萬家,合作社數量呈10倍增長,并成為農村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織。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并于同年發文鼓勵農民合作社廣泛涉足農產品加工、銷售、鄉村旅游等經營活動,以拓展合作領域和經營內容。在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進一步指出,要繼續推進農村產業融合,扶持農戶發展休閑旅游業合作社,支持合作社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和直供直銷。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要支持農民合作社成為鄉村建設的主要載體。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通過多種形式讓農民合理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則強調:“要支持農民合作社開展農技推廣、土地托管、代耕代種、統防統治、烘干收儲等農業生產性服務。”這些政策文件都體現出國家對拓展合作社功能以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充分肯定,并引領了新時期合作社的發展方向。
通過回溯政策演進過程不難發現,十多年來,中國政府針對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大致經歷了從提高合作社生產的積極性到鼓勵合作社發展縱向一體化、再到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發展過程。中央一號文件始終都將合作社與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問題聯系起來,尤其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在重視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同時也將注意力轉移至農村全面發展中來,通過借助合作社的組織平臺帶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體目標。
三、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動力與優勢
為準確刻畫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動力與優勢,有效區分其融合過程中的形態差異,根據課題組2018年7-10月以及2019年4-5月在湖北、江蘇、河北、河南等地對合作社進行的實地調查,主要選取了江蘇省宜興市豐匯水芹專業合作社、河北省肅寧縣益源種植專業合作社、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社以及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陽山鎮桃源村合作社展開案例分析。
(一)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動力
1.農業多種功能開發需要。農業除了具有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糧油肉蛋奶棉麻園藝等農產品外,還具有很強的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和文化傳承功能[21]。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強調要開發農業多種功能和延長農業產業鏈。但由于農村地區大規模、持續性非農就業趨勢顯著,農戶兼業行為導致農村優質勞動力大量流失,由此加劇了農村經濟的蕭條[22]。因此,要滿足農業多功能的發展需要,單純依靠小農生產是難以實現的,亟需以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揮其專業化、組織化的優勢,在加強農業生產間聯合的同時,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以無錫市惠山區桃源村為例,該村地處陽山省級旅游度假區核心區域,自然環境優越,該村結合當地水蜜桃生產,充分利用當地景觀的獨特性,對自然資源與環境資源進行了有效開發,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產業融合模式。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合作社與陽山鎮桃農協會對該村的農戶進行培訓指導,改變了過去各自種植的局面,由合作社統一對村民進行專業的技術培訓,對桃樹進行選育種植,引導農戶改用最新的農業技術和種植管理方法,提高了陽山水蜜桃的品質與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合作社還在當地文化方面“做文章”,結合當地桃園、古剎、大小陽山、地質公園等生態自然景觀和田園風光,構建了以鄉村旅游、農事體驗、度假休閑為一體的田園綜合商業模式,拓展了農業的多種功能。
2.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需要。家庭不僅是中國人基本的認同和行動單位[23],也是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在傳統農業社會,小農戶生產更多地是為了滿足自身生存及繳納稅賦的需要,而隨著社會發展,農業生產的功能已從滿足基本生存轉移到支持個人及家庭發展方面。面對大市場,小農戶無論在科技素質、文化素質,還是在發展農業生產的思路上都較為弱勢[24],無法自發走上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因此,還需要一個介于農戶和政府之間的組織來整合“原子化”的農戶,“抱團”共同面對大市場風險,研發新品種、學習掌握新的種植技術及現代信息技術。不同于資本下鄉的工商企業,合作社兼具草根性和內生性,社員幾乎都是當地村民,除了可以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還能發揮合作社的社會化服務作用,提高農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拓展農民增收的空間。以江蘇省宜興市豐匯水芹專業合作社為例,該合作社便屬于一個“抱團”的組織,舉合作社全力研發新品種,而后將新品種傳授于普通農戶,并給農戶進行技術示范,滿足了農戶對技術、信息的要求。除此之外,合作社還建立了自有品牌——“陶都”水芹,通過技術研發和專業化種植使得水芹價格從每斤不足1元提高至2~3.5元(調研時當季價格),增加了普通社員的收益。對當地村莊及周邊村莊而言,由于當地水芹種植名聲在外,吸引了大量外來資本投入水芹種植,農戶的土地流轉收入及涉農打工收入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一)農業內部技術融合
這類融合模式因發生在農業內部而主要屬于由于技術革新而導致的產業融合,具體表現為農業技術的革新開發出的替代性或關聯性的技術、工藝和產品通過滲透、擴散融合到其他產業之中,改變原有產業生產的技術方式[31]。以江蘇省宜興市豐匯水芹專業合作社為例,該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目前成員382人,主要的經營方向是水芹種植與加工,水芹種植面積1 800畝,經營輻射面積5 000多畝。在過去水芹是單季作物,每年僅能種植一季,由于產量低、價格低,農戶生產積極性不高,且很難實現水芹種植技術的更新。豐匯水芹專業合作社成立后借助眾多高校的科研技術力量,使水芹種植突破了季節限制,由一年一季變為一年四季皆可種植,但受制于土地肥力和勞動力的因素,當地采用土地輪作的生產方式,每畝地平均約種植3茬,即便如此對水芹種植產業而言也是顯著的技術突破。合作社掌握該技術后將此技術教授于社員,并為社員配發農資、宣傳農業訊息,合作社成為傳播農業技術、傳遞農業政策以及訊息的平臺,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以2018年水芹市場價格為例,春芹能賣到每斤2元,每畝能產出8 000斤;夏芹能賣到3.5元,畝產5 000斤。以當地農戶戶均3畝地為例,全年種植水芹可收入5~6萬元。水芹產量的提高導致市場供應充足,為防止出現產品滯銷,提高水芹的市場價值,合作社又出資購買機器設備,對其進行深加工,制作出各類醬菜產品,進一步提高了水芹的附加值。
(二)縱向一體化經營融合
相關研究表明,合作社在橫向規模擴大的基礎上往往還會向產業鏈上游和下游縱向拓展業務范圍,以分享生產、運輸、加工、銷售等環節的利潤,顯著降低交易成本,通過建立風險分散機制,提高農戶對市場風險、自然風險、金融風險的抵御能力[32],目前縱向一體化經營融合已成為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一種典型模式。以河北省肅寧縣益源種植合作社為例,這一合作社正式注冊于2010年3月,是集特色農產品種植、加工、收購、貯藏、銷售為一體的經濟組織,屬于國家級示范社,它將“種地”和“建廠”聯系到一起,發展縱向一體化經營。首先,合作社對入社農戶進行技術培訓,根據市場需求統一種植特色黑小麥、玉米、黑花生、黑芝麻等作物。其次,合作社把從社員那里收購來的農作物送入合作社加工廠:將黑小麥加工為黑小麥仁、黑小麥粉;玉米加工為玉米油、玉米糝(玉米磨成的碎粒);黑花生加工成黑花生油、黑花生醬;黑芝麻加工為黑芝麻糊、黑芝麻香油、黑芝麻醬等,產品類型豐富,涵蓋高中低三檔。再次,合作社統一使用注冊商標“翔貴”對農產品進行包裝,再上架家樂福等大型超市,最終流入消費者手中。該模式以合作社為載體,較好地將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整合在一起,通過延長產業鏈將收益留在了合作社,并通過分紅返利等形式返還至普通農戶。據該合作社測算,其通過縱向一體化經營融合模式使加入合作社農戶的種植收益每畝增加700元,顯著提高了農戶收益,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實惠。
(三)現代農業與旅游業融合
現代農業與旅游業融合屬于典型的產業跨界融合,由于其效益突出成為當前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重要模式。以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為例,該村在2009年以前十分破敗,村內青壯年大量外出務工,屬于典型的空心村,村莊內留守人員以種植水稻為生,因缺乏有效管理以及生產技術等原因,村民收入較低。后來,郝堂村在區政府、村委及學者李昌平支持下,建立了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社,以合作社為平臺開展村莊內部資金互助。該合作社收益用于村莊內入社老人的分紅,而資金貸給村內有需要的村民,合作社不限制資金使用方向。由于郝堂村地處山區外圍,景色宜人,且距信陽市僅半小時車程,具有良好的旅游業發展潛質。自2011年起,該村整合村內資源,修路建橋,改造水田,發展鄉村旅游。同時,農戶借助合作社提供的互助資金進行農家樂房屋改建、村莊環境改善以及特色農業發展,使現代農業與旅游業同時興盛起來。盡管合作社初建時僅有啟動資金34萬元,但資金互助合作社作為促進該村發展的“發動機”,通過村莊內部資金的流動,使“資金血液”流向村中各個部門,激活了村莊活力,而旅游業的發展又進一步帶動了當地現代農業的發展。藍莓、桑葚、火龍果等生態采摘等形式以及特色農產品如信陽毛尖(茶葉)、板栗、蓮蓬等深受游客歡迎。資金問題的解決使村莊經濟得到了良性循環,使越來越多的資源要素參與進來,游客吃、喝、玩、住、娛產生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與創業機會,吸引外出務工人員重新流回村莊,寂靜的村莊重新變得熱鬧。
(四)農業生態旅游和文化創意產業融合
雖然農業生態旅游和文化創意產業融合是鄉村振興背景下涌現出的一種新業態,但卻表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江蘇無錫市陽山省級旅游度假區核心區域的桃源村,擁有悠久的種桃歷史,由于所在區域地理較為獨特,土質含多種微量元素,特別適宜水蜜桃的生長。該村自1987年開始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將所有水稻田全部改種水蜜桃,目前該村擁有4 000多畝桃林,但是近年來也遭遇了一系列制約發展的問題:如桃樹衰老、農業生產后繼無人、水蜜桃品質下降以及品牌混亂等。2008年年底,為解決此類問題,他們積極培育以合作社為主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雙置換的方式引導村民將土地承包權經營權有序流轉,搞規模化經營與農場化改造。目前該村建有水蜜桃種植類合作社38家,家庭農場9個,并由村委牽頭成立了綜合社,統一使用“太湖陽山”品牌商標,提高了種植收益。除了生產水蜜桃外,當地合作社還深入挖掘特色農副產品,一是與江南大學合作,研發水蜜桃汁,受到市場好評,成為當地有名的“網紅”產品;二是深度開發當地傳統美食,如具有民間特色的大麥餅、陽山團子、糕點等,不僅供給當地消費,還通過電商銷往全國;三是充分利用種養結合的生產優勢,發展生態養殖業,如在桃園里養殖雞鴨等禽類,土雞蛋成為熱銷旅游產品。除了發展生態旅游外,陽山鎮與桃園村共計投入約1 500萬元,對寺舍、大路頭等具有歷史底蘊的古村落進行包裝整治,挖掘當地特色文化,建立了田園創意文化園。在此過程中,合作社不僅積極引導成員創辦農家樂、民宿等項目,協助村民進行品牌推廣,還提供桃子采摘、垂釣等休閑娛樂項目讓游客體驗農事,挖掘了農業的休閑娛樂與文化體驗功能。
五、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的瓶頸與破解策略
從實踐層面上看,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尚處于起步階段,發展還不完善且面臨較多瓶頸問題。(1)經營規模小,發育不充分。雖然當前中國合作社數量龐大,但從發展質量來看,合作社個體發展規模仍然處于初期階段,且“假合作社”“精英俘獲”問題突出[33],這部分發育不充分或者發育畸形的合作社多處于滿足自身存活階段,僅能為社員或自身提供少量的服務,自身發展能力弱,且經營方向單一,管理松散,受制于自身體量,很難開發產業融合項目和發揮合作社的引領作用。(2)資金運轉不暢,融資難度大。從桃源村合作社案例來看,其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合作社自身經營得當,選擇了正確的戰略方向,另一方面也得到了當地鎮、村兩級財政的大力支持及對周邊設施的建設與改造。從產業鏈延伸的角度看,如果合作社要涉足農產品加工、貯藏、運輸、包裝、營銷等環節,需要大量的投資,而一般的小型合作社根本不具備充足的資金儲備,也就難以實現產業的延伸與升級。有數據顯示,全國約有70%的農產品加工企業同時存在長期資金與流動資金缺口,而處于“弱勢聯合”的合作社形勢就更加不容樂觀[34]。此外,目前針對合作社的融資渠道也較為單一,申請難度較大,合作社及農戶不易獲得,這也為合作社帶動農村產業融合帶來了困難。(3)發展休閑農業創意不足。從目前主流的休閑農業模式來看,農家樂、采摘、垂釣等項目已普遍存在,且各地間相互模仿,從宣傳標語到房屋裝飾再到活動形式都缺乏創意,游客往往游覽一次就失去興趣,當地“特產”也是在旅游市場上隨處可見的產品,往往不能吸引游客。在這個過程中,合作社由于缺乏專業的人才來規劃發展方向,具有文化內核和地方特色的休閑農業模式相對匱乏,部分休閑項目與合作社主營業務結合不緊密,甚至服務業態呈現“四不像”狀態,無法達到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預期效果。
對此,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合作社帶動產業融合的能力:(1)要鼓勵支持合作社聯合社與綜合合作社的發展。合作社通過弱者聯合,改變了農民在市場單打獨斗的局面,而合作社間的聯合則進一步提高了農民合作社的抗風險能力與持續發展能力,從而提升了合作社的影響力與帶動能力。另外也要看到,綜合合作社在產業融合中往往因其“綜合性”更易將分散的資源整合,形成農村產業融合一盤棋的局面,發揮最大效用。同時,還要倡導國家在政策上多給予扶持和引導,積極調動廣大農民的參與積極性,通過合作社這一載體更好地帶動農村產業融合,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2)改善合作社的融資渠道。農村三產融合的發展和推廣對合作社人才、資金、技術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此合作社應適時做出相應調整。除了鼓勵合作社間的合作外,一方面應當適當引入外部工商資本與合作社進行合作,將合作社的本土化優勢與工商資本的先進管理、運營、資金、宣傳等優勢結合起來,以讓利換發展;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還可通過財政獎勵等手段引導金融機構為合作社發展提供信貸支持,并鼓勵有條件的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引導其規范發展。(3)積極推進農業與旅游、健康養老以及特色農產品等深度融合,探索農村產業融合新業態。同時開發農村鄉村游要保持鄉土風貌,盡量避免人云亦云引發的同質化競爭,挖掘當地特色文化,增強文化教育尤其是農耕文化教育,將文化融入到鄉村游中,保護農村文化遺產。
參考文獻:
[1]?張義博.農業現代化視野的產業融合互動及其路徑找尋[J].改革,2015(2):98-107.
[2]?蘇毅清,游玉婷,王志剛.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理論探討、現狀分析與對策建議[J].中國軟科學,2016(8):17-28.
[3]?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院和農經司課題組.推進我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問題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6(4):3-28.
[4]?王樂君,寇廣增. 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思考[J]. 農業經濟問題,2017(6):82-88.
[5]?馬健.產業融合理論研究評述[J].經濟學動態,2002(5):78-81.
[6]?Rosenberg Natha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1840-1910[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3(4):414-443.
[8]?崔振東.日本農業的六次產業化及啟示[J].農業經濟,2010(12):6-8.
[9]?馬曉河.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發展[J].中國合作經濟,2015(2):43-44.
[10]?姜長云.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的主要組織形式及其帶動農民增收的效果[J].經濟研究參考,2017(16):3-11.
[11]?張靜,張梅.國外農業合作社的金融支持模式及啟示[J].世界農業,2014(2):17-21.
[12]?徐旭初.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辨析:一個基于國內文獻的討論[J].中國農村觀察,2012(5):2-12.
[13]?李云新,戴紫蕓,丁士軍.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農戶增收效應研究——基于對345個農戶調查的PSM分析[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37-44.
[14]?梁偉軍.交易成本理論視角的現代農業產業融合發展機制研究[J].改革與戰略,2010(10):87-90.
[15]?李玉磊,李華,肖紅波.國外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研究[J].世界農業,2016(6):20-24.
[16]?黃祖輝.在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增加農民收益[J].中國合作經濟,2016(1):23-26.
[17]?蘆千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研究述評[J].農業經濟與管理,2016(4):27-34.
[18]?喬金亮.農業合作社發展三問[J].農村·農業·農民(B版),2018(6):51-52.
[19]?葉琪.建國60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成就及展望[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0):44-48.
[20]?劉穎嫻,郭紅東.資產專用性與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縱向一體化經營[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47-56.
[21]?Ploeg van der J D,Roep D.Multifunctional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Actual Stuation in Europe[C]//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A New Paradigm for Europea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Aldershot:Burlington,VT (Ashgate),2003: 37-54.
[22]?焦源.山東省農業生產效率評價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12):105-110.
[23]?賀雪峰.農民行動邏輯與鄉村治理的區域差異[J].開放時代,2007(1):105-121.
[24]?Duflo E,Kremer M,Robinson J.Nudging Farmers to Use Fertilizer:Theor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6): 2 350-2 390.
[25]?陸岐楠,張崇尚,仇煥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非農勞動力兼業化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影響[J].農業經濟問題,2017(10):27-34.
[26]?楊嬛,陳濤.生產要素整合視角下資本下鄉的路徑轉變——基于山東東平縣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實證研究[J].中州學刊,2015(2):50-55.
[27]?張穎,王禮力,邱凌,等.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責任范疇及其評價[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2):142-150.
[28]?黃祖軍,莊宜倩.轉型期農村精英“差序人格”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61-66.
[29]?潘建成.構建現代農業體系需加強產業融合[EB/OL].[2017-11-20].http://www.cssn.cn/xnc/201711/t20171120_3748630.shtml.
[30]?李俊嶺.我國多功能農業發展研究——基于產業融合的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9(3):4-7.
[31]?王昕坤.產業融合——農業產業化的新內涵[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7(3):303-306.
[32]?張學會,王禮力.農民專業合作社縱向一體化水平測度:模型與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6):37-44.
[33]?鄧衡山,徐志剛,應瑞瑤,等.真正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何在中國難尋?——一個框架性解釋與經驗事實[J].中國農村觀察,2016(4):72-83.
[34]?梁立華.農村地區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動力機制、發展模式及實施策略[J].改革與戰略,2016(8):74-77.
Policies,Motives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s of Cooperative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LI Qiao1, JIA Chunshuai2
(1.School of Law,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214122;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100094,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explore the rural endogenous industry integration model with cooperatives as the carrier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output efficiency,prospering rural economy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Through the combing of policies related to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riven by cooperativ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is paper finds the cooperatives have experienced the initial stage of start-up and industrial break-off,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growth sta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In practice,the needs of multi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h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the virtuous circle of economy,and cross border management all provide real impetus for cooperativ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Cooperatives also show the advantage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social services and credibility,and form the models of agricultural internal technology integration,vertical management integration,moder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agro-ecological tourism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tegration.In view of the issues of small scale,low capital,and insufficient creativity,this paper suggests to start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aspects of encouraging cooperatives to develop in a comprehensive and joint direction,improve the financing channels,and tap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cooperative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