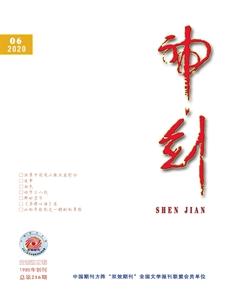生長的短語
張阿泉
前些年,常有機會與巴公共同參與青城書人的宴聚,席間好友贈書題字,得享一夕相晤暢談之趣,十分快慰。近幾年,巴公似乎愈習慣于“宅守”,大家也就隨之失去了很多相互“親聆謦欬”的機會。好在巴公的思考不停、激情不減,靈感與妙悟如山泉般流淌,主打的短語手札仍定期在《北方新報》的相關專欄里曬出來,算是用另一種“筆談”方式持續發散著他“思想的芬芳”。
生于1941年的巴公,雖已進入楓丹晚年,但觀察其活躍涌動的寫作態勢,并無遲暮的一派頹廢,顯示出的反倒是越來越湛醇明澈的“芳華”。我所說的“芳華”,當然是指巴公的精神年齡。近一二十年來他潛心讀書思考,尤其慣以短語方式對復雜人生進行多維度的辨析拷問,這使他的精神年齡始終保持在“芳華”階段,其陸續出版問世的十多本成色扎實的短語集就是明證。而且,這種業已形成個人風格的“巴式短語”,屬于一種“生長的短語”,即隨著生命年輪的遞增而日漸透徹明晰,真可謂把“寸光陰”都淘成了“寸金”,一寸有一寸的開掘,一寸有一寸的生發,一寸有一寸的長進,這是最令人嘆服的。
如今展攤在讀者眼前的書稿《爾雅心語》,乃“芳華”巴公的叉一本新的短語采獲,經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編審王世喜兄悉心打理,呈現出一貫的短語氣質、連貫的睿智風格。小書制式依舊,仍粗線條,分為自然意象、人生況味、心靈境界、修養妙悟、道德審視、哲理思辨、精神家園七輯,視角貌似分門別類,內涵實則混合交叉,難以分清界線。本質上,無論巴公在談論什么,都是在談人,都是對人生真味與意義的感知與追尋,這也是他鐘愛短語寫作的“核心訴求”。
在前幾次為巴公短語集所寫的小序中,我已對“巴式短語”的美學特征做過深入解讀,這里不再贅述。最近翻讀了一本也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藏書《蒙古族諺語》,發現蒙古族格言與其他民族格言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只是表達風格更具有草原色彩而已(譬如“寧按自己的自由喝冷水,別按人家的意志喝奶油”,類似于漢語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當一次鷹,勝于當一輩子烏鴉”,類似于漢語的“寧為雞口,勿為牛后”;“好馬從駒時異群,好漢從幼時異眾”,類似于漢語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想來這也屬于正常現象,其原因約略有二:一是對同一個問題,真理只有一個,只是表述微有區別;二是人同此心,各民族之間感情相近、思理相通,構思與表現手法便多有巧合與偶合。自從巴公側重短語寫作以來,已先后蠶吐出數千條諺語式短語,用前面說的理念來審視,可發現其中同樣有不少“似曾相識”“形異神似”的條目,這既因“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物”,也因“真理總是老生常談”。人性與科技不一樣,科技時時在更替刷新,而人性的變化緩慢遲鈍,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幾無改進提升,故而久遠年代的先哲解剖人生奧秘的經典著作(如古羅馬時期的《沉思錄》、古希臘時期的《愛經》)拿到今天來看仍深具現實意義。通覽新結集于《爾雅心語》所收的這數百條短語,并無稀奇古怪的角度、振聾發聵的力度、萬人空巷的熱度,逐句品來,仍是一些已探討琢磨過許多遍的舊物事、老人情、平常心,而作為已然成熟的“思想者”,巴公恰恰是在“難以下鎬”的俗套話題領域完成了自己“智慧金礦的開掘”。
在《爾雅心語》中,巴公的短語似乎呈現出更為親切誠摯的“筆談”口吻,像好友間的絮語,沒有訓誡,只有傾心而談;同時,又更加善于從司空見慣、熟視無睹、耳熟能詳的角度巧妙發力,用最平實的白話,高難度捕捉一絲一縷“意外”的禪悟與心得,做出一個漂亮的思想“前滾翻”或“后滾翻”。我現從每一輯中“取一瓢飲”,試舉七例:一,“愛大自然,不僅要貼近自然、融入自然,更要師從自然,這才是真正的道法和敬畏”(這句話提醒人們光享受旅行是不夠的,還要虛心向自然學習);二,“書畫,講究‘留白,這是一種藝術境界。人生,其實一樣,也要懂得和學會‘留白,諸如話不說滿,事不做過”(這句話通俗易懂,富含人生機趣,很多人知道卻做不到);三,“孤獨種種,各有不同:當孤獨是一種習性時,即會孤僻;當孤獨是一種品性時,則會慎獨”(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在于“習性”與“品性”的“近義詞辨析”,辨析出了兩者間細微卻巨大的美學差異);四,“只有面對鏡子,才會正視自己;只有擦亮鏡子,才會看清自己”(這句話強調的不是“鏡子”,而是“面對”和“擦亮”這兩個具有遞進關系的動作);五,“誠實,鏡子是我們的榜樣:對丑的,回報以丑,決不掩飾;對美的,回敬以美,決不扭曲”(這句話繼續以“鏡子”為喻體,強調的確實是“鏡子”,它的“誠實”遠超愛撒謊愛吹牛的人類);六,“‘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宋代詩人朱熹的名句,經解讀,它讓我們領悟到兩個成語,一是‘水到渠成,一是‘源遠流長”(這句話殊為靈動機智,對朱熹名句進行升級版點評后,妙悟自在其中矣);七,“一般匠人只會說:朽木不可雕 ;而真正的藝術家,則可以化腐朽為神奇”(這是一句變“朽”為“不朽”的審美開示,意思非常接近日本“以陋為美”的佗寂美學和“以枯為美”的枯山水美學)。
《爾雅心語》雖是一本簡淡小書,卻并不是一本容易讀通透的書,它與之前的其他短語小書一樣,融匯著作者近八十年的人生經驗,當然也需讀者能以豐厚閱歷來對書中的“干貨”進行緩慢的咀嚼消化,若以浮躁之心匆草閱讀這種“鹽巴”一樣的文字,恐只能浮光掠影,品咂不出什么滋味。作家徐遲曾在《瓦爾登湖》一書的譯序開篇說:“你能把你的心安靜下來嗎?如果你的心并沒有安靜下來,我說,你也許最好是把你的心安靜下來,然后你再打開這本書,否則你也許會讀不下去,認為它太濃縮,難讀,艱深,甚至會覺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徐遲先生在1982年對讀者提出的這個要求,現在依然甚至尤其不過時。
“心靜乾坤大,欲少智慧多。”以此來形容“知行合一”的巴公,很是恰切。他的短語寫作源頭是“個人修為”,是其長期淡然物欲、超脫名利、克制內斂的修德生活。巴公的思想遠行還將繼續,他與讀者的“短語之約”也會一路并行,這是他耗費心血奉獻出來的“靈糧”,更是諸多喜愛他作品的讀者之福。大家都知道蘇格拉底說過“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過”,其實蘇格拉底還說過更深刻的另一句“美德即智慧”,意即“美德乃孕育智慧之母體”。巴公既是愛思考人生的人,更是講美德的人,在喧嘩時代里,他發出的聲音如此低頻而又如此清晰,且富于柔韌的穿透力,始終熏染引導著人們向真向善向美而前行,這也是他最值得大家學習與追慕的地方。
小序一篇,聊記拉雜細碎讀感,并再續我與巴公之間難得的“序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