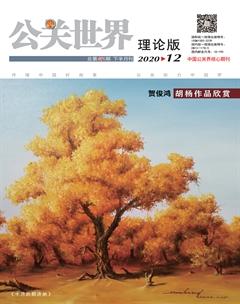大革命時期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
湯佳玉
摘要: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發展離不開共產國際的幫助。共產國際一面指導中國革命,推動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另一面,由于其對中國國情了解的缺乏及一味套用蘇俄模式所引發的弊端,也給中國共產黨帶來無法忘卻的傷痛。因此,正確認識大革命時期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有助于我們總結相關的歷史經驗,為中國共產黨處理黨際關系提供借鑒。
關鍵詞:共產國際 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
共產國際的建立,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其成立之初,共產國際就曾派代表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系,由此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支部。自此,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步發展都可以看見共產國際的身影。大革命時期是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發展的一個承前啟后的特殊階段,這一階段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必然在整個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共產國際的誕生及對中國革命的關注
受第二次工業革命影響,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并要求占據更多的勢力范圍,新舊殖民者的矛盾由此激化,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災難的同時,激化了作為參戰國之一的俄國的國內矛盾。各種矛盾交織的俄國成為“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環節”,革命力量在此匯聚,十月革命由此爆發。
(一)共產國際的創建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之振奮,由此推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波蘭、德國等多個國家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為新的國際組織的成立奠定基礎。面對積極的革命形勢,列寧認為“國際革命愈來愈逼近,俄國有必要建立世界蘇維埃”。
1919年3月,共產國際在列寧的領導下宣告成立。同一時間,初生的蘇維埃俄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國內反動勢力叛亂不斷,帝國主義動用武力干涉,意圖將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于襁褓中。為沖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圈,蘇俄急需尋找國際共產主義的幫助。而此時的歐洲革命也飽受資產階級的殘酷打壓。由此,列寧將視線轉向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首當其沖的便是中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一直在對帝國主義實行積極反抗。于蘇俄而言,在中國存在著“同世界資本主義斗爭的成功機會”。
(二)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的確立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希圖借鑒資本主義的先進之處,救亡圖存。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暴露無疑,十月革命的爆發則昭示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轉而借鑒蘇俄經驗,這與共產國際的東方戰略不謀而合。
1920年,共產國際和俄共(布)派遣維經斯基前往中國,以與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系。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1923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促成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結成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國共合作的確立開拓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使中國革命步入大革命時期。
二、 大革命時期的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休戚相關。一方面,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積極指導,不僅促進了工農運動的發展,而且從人員、物資等多方面給予黨不遺余力的幫助。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指導過程中也存在失誤。共產國際對國共力量的片面性判斷、錯誤地執行三次退讓等原因,給中國革命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也正是由于兩者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共產國際指導過程中的失誤才招致了如此嚴重的結果,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一)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指導
1.促進工農運動蓬勃發展
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不僅積極為工會籌措資金,而且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對中國革命施以援手。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和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五卅運動席卷全國,省港大罷工震驚中外。
工人運動如火如荼開展的同時,農民運動也日益高漲。共產國際的駐華代表不僅幫助中國共產黨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還擔任講習所的教員。講習所的創立不僅為中國農民運動培養了一批主力,而且推動了中國農民運動的發展。
2.為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資金援助
只靠奮發的革命動力是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的。要革命就要進行實際革命活動,而活動的每個過程都需資金支撐。在此情況下,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就尤為重要。1927年,共產國際、聯共(布)等多方提供的資金就高達100萬元,而中國共產黨自行籌備的金額卻僅有3000元。由此可見,在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如僅憑自身籌措的資金是無力支撐起中國革命的。
共產國際的資金援助不僅保障了中國共產黨革命活動的開展,而且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
3.為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培養了一批堅實力量
隨著革命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急需一批政治素養較高、理論知識豐富的黨員干部推動革命工作的開展,培養一批合格的黨員干部就成為黨內亟待解決的問題。
1925年,共產國際創辦了中山大學,中國共產黨遂安排共產黨員赴莫斯科學習。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培養了一批批干部人才:劉少奇、鄧小平、葉挺等人都曾在此學習。
(二)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指導上存在的失誤
1.對國共力量的片面性判斷
大革命初期,共產國際輕視共產黨重視國民黨的苗頭已初見端倪。
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在《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國民黨是中國獨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團體。”而對于中國的工人階級,他們的評價是“他們還不能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共產國際觀察事物的片面性使他們只看到“國民黨是由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工人等多階級聯合的政黨”,看到國民黨內部與工人聯系的部分,忘記在國民黨內部占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缺乏認知。
共產國際于第六次擴大會議召開時提出“只要國民黨實行正確的政策,共產黨就要對國民黨的一切工作進行有力的協助”。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全力輔助國民黨的工作,使國民黨成為真正的人民政黨,此舉相當于把與國民黨同等地位的共產黨置于從屬地位。
2.忽視共產黨的武裝建設,片面援助國民黨
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忽視對共產黨的武裝建設。當時,共產黨想建設一支武裝軍隊,以具備與國民黨抗衡的實力。但共產國際極力壓抑共產黨的軍事活動,卻大力馳援國民黨。共產國際不僅協助國民黨建成黃埔軍校,更將援華的大量物資全用于國民黨的建設。1925至1926年,共產國際援助國民黨的各項軍械總額高達110億元。共產黨曾對此提出質疑,要求建設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鮑羅廷以“此舉易引起國民黨的猜疑,不利統一戰線鞏固”為由,駁回意見。
共產國際單方面援助國民黨的行為,事實上是對共產黨力量的削弱。數量可觀的物資使國民黨的勢力日益壯大,也使共產黨逐步喪失與國民黨爭奪領導地位的能力。
3.三次退讓
統一戰線的原則是既團結又斗爭,以確保它的穩固性。但大革命期間,共產國際為鞏固國共合作,執行片面團結的政策,當國共兩黨發生摩擦時,屢次對國民黨實行退讓。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于廣州召開,會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占據多數代表席位。據周恩來回憶:“在中央執委中,中共黨員占三分之一,我們的政策是多選左派,使左派占優勢。”然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認為“國民黨內部一旦分裂,勢必影響革命局勢”。他以維護統一戰線為由,向國民黨右派讓步。在維經斯基的安排下,陳獨秀與國民黨進行會談,決定國民黨二大延期召開。
鮑羅廷在與加拉罕來往電報中曾提及,黨內討論中執委名單時,關于國民黨中執委中共產黨所占人數雙方曾一度爭執。鮑羅廷表示“中央提出7人,我反對,為的是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終同意最低限額為4人”。鮑羅廷的承諾造成右派勢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
國民黨二大后,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件”,以共產黨私調軍艦、包藏禍心為由,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領事館。
事后,共產黨決意采取強硬態度,陳獨秀派彭述之前往處理相關事宜,卻受到以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訪華團的制止。布勃諾夫憑共產國際賦予其的權利,對中山艦事件進行全權處理。他認為“此次行動只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共產黨人的小規模暴動。是由于我們犯的一些錯誤而復雜化了。”布勃諾夫只看到自身的錯誤而忽視了蔣介石的反動性,他不僅對國民黨的陰謀行徑視而不見,而且為防止蔣介石擺脫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布勃諾夫將與蔣介石不合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嘉山撤職。
中山艦事件后,由于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蔣介石達成了強迫共產黨人退出黃埔軍校的目標,掌控了軍事權力。
共產黨的兩次退讓,使蔣介石攫取權力的欲望更勝。1926年5月,蔣介石以整理國民黨黨務為由,要處理國共兩黨關系。鮑羅廷遵循共產國際要求三次赴約與蔣共商協議,中共中央對此全無所聞。會議召開前夕,中共派張國燾、彭述之作為代表前往出席時,鮑羅廷要求張國燾向國民黨表明支持態度。據張國燾回憶:“鮑羅廷找到我和譚平山,要求我們向蔣表述中共決不會作公開反對之舉。”。次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召開,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提案內容為:加入國民黨高級黨部的共產黨,擔任執委數量不能超總數的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不得由共產黨充任。中共黨員對《整理黨務案》表示反對,但又無力反抗共產國際的指令。正如周恩來所言:“會上,彭述之表示不能接受提案。問他不接受又如何?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在鮑羅廷的操縱下,中共被迫接受提案。《提案》的通過,使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長的共產黨人被免職,國民黨右派分子借機上位。
第三次退讓的結果,使蔣介石繼奪取政權、軍權后,將黨權攥進手心。此舉更是為之后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做了準備。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進行屠戮,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大革命由此遭受失敗。
三、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導致失誤的原因
(一)共產國際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共產黨
共產國際在二大召開時規定:“各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支部,對共產國際的決策必須予以施行”。由此可知,共產國際具有最高的決策權,中國共產黨必然要聽從共產國際的命令。
共產國際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中共的決策指手畫腳。1925年,二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共產國際就越過中共,對中共事務進行自行裁決,確定了“要在內部組織上向國民黨左派作出讓步”等決定。這種越俎代庖的傲慢姿態,貫穿整個大革命的進程。據研究人員統計,自1923年至1927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過122次會議,做出了738個決定。
由此可知,大革命期間,共產國際處于主導地位,即使共產國際提出錯誤的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也必須予以執行。而在此期間,共產國際對蔣介石實行三次讓步,共產黨雖有心抗爭,也無力抗拒。共產國際這種大權在握、強制發出指令的指導方式使中國共產黨無法自主地決定中國內部事務,最終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受重創。
(二)不了解中國國情
制定決策時應從實地出發,因地制宜,但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使決議過程本身就存在問題。
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級關系復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應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決策常常是“決勝千里之外”。這種不從實際出發做出的決策往往存在誤判。譬如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的立場已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共產國際仍認為蔣介石是“左派中派的代表人物”。隨著大革命的深入,革命形勢瞬息萬變,共產國際更需要對斗爭形勢迅速作出判斷,以適應事態發展。然而共產國際對中國情況了解的缺乏,使做出的決策只是“紙上談兵”。例如大革命后期,共產國際發出“五月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通過工農領導人加強國民黨的領導。這些指示具有一定現實意義,但缺乏實際操作性。陳獨秀就曾在接收共產國際指令后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
(三)套用蘇聯的政策模式
共產國際在制定政策時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的成功革命經驗奉為圭臬,以此為依據指導他國實踐。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共產國際并非依據國情,而是對蘇俄的經驗進行照搬照抄。俄國是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所以共產國際認為,中國要先有一個資本主義完全發展的階段,再去推翻這個階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共產國際未意識到中國與俄國的國情千差萬別,將兩者一概而論。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共領導人也認為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與無產階級無關,從而為放棄領導權埋下伏筆。
四、由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得到的歷史啟示
(一)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共產國際從創立之初便強調各國共產黨作為其下的一個下屬支部,需要聽其命令,受其指導,對其下發指令堅決予以執行。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更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睥睨中國共產黨,對中共的工作決策指手畫腳,無視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為了達成鞏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這一目的,共產國際對國民黨接連實行了三次退讓,助長了國民黨右派的囂張氣焰,為大革命失敗埋下禍根,更是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歷史經驗證明,要進行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必須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也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同時還要學會取長補短,吸收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發展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探索屬于本國的社會主義道路
共產國際出于發展共產主義者同盟,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需要,在政策制定、戰略選擇等眾多重大問題上予以中國共產黨積極的指導和幫助,這也和大革命時期理論知識薄弱、革命經驗又十分匱乏的中國共產黨力圖發展壯大的需求相合。但共產國際不應將蘇俄經驗作為刻板的教條,進行一味的照搬照抄。
毛澤東曾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的具體革命實際相聯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指南。我們不應當強行套用統一的策略模式,把他國的勝利經驗奉為圭臬,而應該因地制宜、對癥下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各國發展水平大不相同,經濟和政治狀況更是千差萬別,我們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參考文獻:
[1]列寧.列寧全集[M].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963年版:361—362.
[2]王淇,楊云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21.
[3]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8-119.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613.
[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168-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