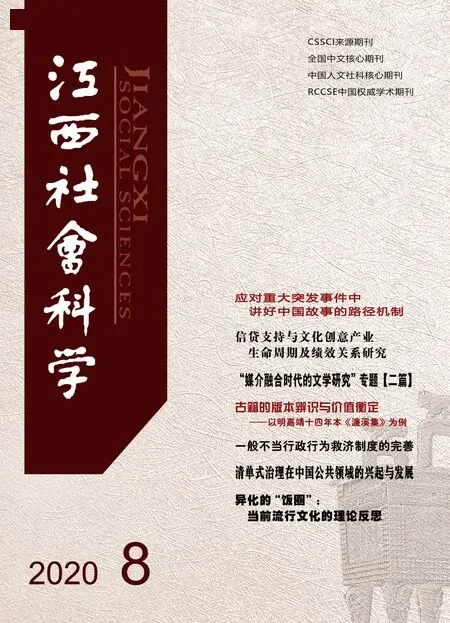媒介融合語境下文學之“危”與“機”
■喬世華
對媒介融合語境下文學命運的思考,離不開媒介這一聚焦點。首先,紙媒文學的衰落趨勢明顯,這與印刷媒介在激烈的媒介競爭中不得不把話語權讓渡給新媒體大有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的終結。其次,普通讀者獲得了更多的文學評判權,其審美趣味得到了專業讀者的尊重,對于重新審視文學經典和認知作家作品具有重要意義。最后,文學的媒介屬性得到凸顯,“媒介文學”得到正名,同時倒逼人們對文學本質問題展開更多有意義的思考。
媒介既是技術,也是訊息,更是動力,其對文學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崛起和壯大就得益于晚清之后中國現代報刊業的快速發展。當我們提到魯迅、郭沫若、茅盾、沈從文、徐志摩、梁實秋、戴望舒、林語堂等閃耀的文藝群星及其作品時,不禁會想到和他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新青年》《語絲》《創造》《小說月報》《申報》《晨報》《大公報》《新月》《現代》《論語》等各種報刊,以及以這些報刊命名的文學社團、流派和獎項。可以說,一部現代文學史就是一部現代媒介史。故此,在媒介融合語境下思考文學的命運問題,現代媒介這“第五要素”亦應作為一個聚焦點。畢竟,“技術,從其起源時刻開始,就與人類本質屬性互相聯系”“人類內在的精神組織特性一旦形成,技術手段就會支持和放大人類的表達能力”。[1](P11)
一、紙媒文學的衰落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2](P135)80年前張愛玲在時代變動、文明交替之時發出的如是感慨,放到今天來看,更像是對文學寫作在媒介融合時代遭到沖擊的精準預言。2000年,美國著名解構主義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在中國作過一場題為“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的演講,其中有關“文學終結”的看法一時引發學界熱議:“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終結。”[3](P132)這是他在對電信業強勢崛起和印刷文明漸次衰落的事實有了足夠考察之后得出的結論。差不多同時期,中國的先鋒小說家馬原也表示“小說已死”,甚而以“博物館藝術”來形容小說,后來還對此有解釋說明:“我說‘小說死了’,是說小說在公眾廣泛接納和閱讀的意義上越來越不重要了”“讀圖永遠比讀字更直接,一個畫面比一部長篇小說更有力”。[4](P55)的確,當人們有了更多或者更好的文化選擇如電影、電視、戲劇、游戲、資訊、網絡以后,為什么一定要把閱讀小說作為不二的選擇?
印刷文明培養了人們閱讀文字的習慣,也構筑了人對文字的敬畏心理:“能夠看到自己的語言持久存在、反復印刷,而且以標準的形式出現,這使人類與語言產生了最深厚的關系。”[5](P47)與此相關聯,文學受重視、對人發生重要影響的案例比比皆是:托爾斯泰被視作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據稱引發了美國南北戰爭;卡遜《寂靜的春天》激起人們對環保問題的強烈關注;魯迅棄醫從文以療救國民;一些青年因為閱讀了高爾基、蔣光慈或者巴金的小說而動念投身革命……類似文學改易人心或改良社會的說辭、案例或許會有夸張之處,但文學導引人精神成長、幫助人認識社會的巨大功用是不必否認的,畢竟文學是人們重要的情感表達場域和宣泄通道,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受萬眾矚目是當然的事情。進而言之,文學能夠如此風生水起,實得益于賦予其安身立命場所的紙媒的發達,得益于紙媒長久以來所匯聚的社會公眾的熱烈目光。不過,當更多新媒體出現并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紓解和分流了紙媒承載思想認知、提供言論表達空間的功能后,紙媒的受關注度也隨之下降,紙媒文學的影響力被削弱,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們不可能一邊讀狄更斯、亨利·詹姆斯 (Henry Janmes) 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一邊看電視或者錄像帶上的電影。”[6](P17)
“媒介融合”的提法很容易讓人只注意到不同媒介之間“相愛”的溫情一面,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相殺”的殘酷一面。其實,即使是在印刷傳播時代,紙媒之間的相互競爭也都是不爭的事實。90年前,當法國文學史家保羅·阿扎爾注意到一些成人唯一的閱讀媒介是報紙而非圖書時,就表達了“對書本的捍衛”的強烈愿望,極力主張培養兒童擁有終身與書本相伴的習慣。[7](P2)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各地報刊上關于“連環圖畫的害處”“連環圖畫為害最烈”“教局會同警廳取締連環圖畫”的新聞報道和“小人書影響小學生甚巨,教育當局亟宜改進”“請當局取締連環圖畫”的呼聲屢見不鮮;拋開其時連環圖畫內容上可能的怪力亂神不說,這當中透出一個很顯然的信息:同為紙媒,連環圖畫比純文字讀物更容易吸引眼球。
至于媒介融合時代電子媒介之間的競爭、電子媒介與紙媒之間的競爭,更是有目共睹。尼爾·波茲曼在寫作《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時,還是電視蒸蒸日上、咄咄逼人而印刷文化步步后退讓出地盤的時代,那時他就注意到把電子革命和圖像革命二者結合起來的電視“代表了一個互不協調、卻對語言和識字有著很強的攻擊力,把原來的理念世界改造成為光速一樣快的畫像和影像的世界”[5](P104-105),因而慨嘆“隨著印刷術影響的減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構成公共事務的領域都要改變其內容,并且用最適用于電視的表達方式去重新定義”[8](P8)。繼電視之后相繼出現并甚囂塵上的網絡、掌上電腦、手機等新媒體發威之時,印刷文明遭遇的困境只會雪上加霜。近十年間國內已經有超過一百家報紙關門歇業,《譯文》《大家》《萬象》《天南》等文學期刊也先后停刊。國外情形同樣不容樂觀:“男人、女人和孩子個人的、排他的‘一書在手,渾然忘憂’讀書行為,讓位于‘環視’和‘環繞音響’這些現代化視聽設備。”[3](P137)俄羅斯最古老的文學刊物《文學報》在最盛時期每期有650萬份發行量,而在今天只有20萬份發行量,其總編盡管相信“報紙不會消亡”,但也還會為數字閱讀正在取代紙媒閱讀而感到無能為力:“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吸引年輕人讀報紙。我每天都乘坐地鐵。記得以前,地鐵上每個人都手持一份報紙,而現在沒有一個人看報,所有人都在看手機。當我看到有年輕人在讀《文學報》的時候,我甚至想給他們點錢,好讓他們繼續下去。我在大學里教新聞學,大學生也不讀報紙,報紙文化已經過去了。”[9]就在2020年春天,有著67年歷史、期發行量曾高達700萬冊的美國《花花公子》雜志亦宣布停刊,并計劃未來向數字媒體轉型。《花花公子》的紙刊“終結”與未來的數字化“新生”,都更像是印刷媒介從話語大權獨攬到把權力讓渡給新媒體的一個縮影。
當人們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通道可以走,閱讀文學作品就自然成為眾多選擇中的一種而非唯一道路。要了解當下世間百態,一張新聞報紙未必就比一部文學作品的信息量少,而可以即時獲取各種渠道消息的手機甚至令報紙、電視、廣播、電腦相形見絀;要消遣娛樂打發時光,閱讀一本小說不見得就比看電影、追肥皂劇觀、電視真人秀節目或刷手機高明多少;要抒發憤懣或喜悅之情,在網絡上發帖子、在公眾號里留言、在微信里發朋友圈,可能要比暗寓褒貶、曲里拐彎的文學表達來得更及時迅速,顯得更透明敞亮。希利斯·米勒正是在看到了紙媒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頹勢后,而發出了“文學終結”的預警,因此其實際指向的是紙媒文學。對于文學本身,希利斯·米勒還是充滿信心的:“文學雖然末日將臨,卻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經受一切歷史變革和技術變革。文學是一切時間、一切地點的一切人類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關于‘文學’的嚴肅反思,都要以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論斷為前提。”[6](P7)只要人類有情感生活與思想表達的需要,則文學當然會伴隨人類命運始終,至多就是表現形態和涵蓋類型會有不同。口語傳播時代里應運而生的說唱文學,并沒有因為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或電子傳播時代的到來就偃旗息鼓,在今天依然強勁地生存著,只是不再獨占鰲頭而已。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最早始于17世紀末的西歐,那時回憶錄、歷史書、書信集、學術論文等都屬于文學范疇之內,把文學只限于詩歌、戲劇和小說屬于更晚近的事情。[6](P8)同樣的,中國今天所認可的“文學”是在20世紀初得自于西方“文學”概念的啟發而逐漸建立起來的,在這之前相當長時間里,“文學”都指的是文獻之學,亦即關于古典文獻的學問,至于今天被我們視作文學之大宗的“小說”,在很長時間里一直都不受待見,要到了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后其地位才得到大幅提升。
回到紙媒文學的話題上來,紙媒文學的危機說到底是人對文字和文學閱讀的危機,而這種危機早就存在,或者表現為對經典著作的盲視和拒斥,或者表現為對影像追逐的熱情勝于文字。而到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媒介融合時代,人對需要走心動腦的文字閱讀的輕慢、對能讓閱讀富有尊嚴與儀式感的紙質媒體以及這背后的龐大文學歷史的冷落,只不過令閱讀危機表現得更嚴重罷了。不過,紙媒文學遠沒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一擊,畢竟其身后有著數百年歷史、已形成相當威權和公信力的印刷文明在為它做背書,更何況媒介融合時代也需要各種類型的媒介爭芳斗艷、多元共生以全方位地滿足不同人群讀、視、聽的需要。即使有一天紙媒黯然退場,也不過意味著文學找到了一個能更好地安頓自身的合適媒介而已,就像當初文學棄繁重的龜甲竹簡不用而選擇了輕便廉價的紙張那樣。
二、讀者地位的提升
與紙媒式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電子媒體的春風得意,互聯網和手機正獨領風騷,已成為當下我國成年國民閱讀中高度依賴的主要電子媒體。“第十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 的相關數據就指出了這樣的閱讀現狀: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Pad閱讀等)的接觸率為79.3%,較2018年的76.2%上升了3.1個百分點;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在12年間保持持續上漲的態勢,從2008年的24.5%,增長到了2019年的79.3%。[10]雖說數字閱讀還不可能完全取代紙媒閱讀,但數字閱讀卻在加速改變著人們的閱讀方式、閱讀內容和閱讀生態,并且賦予了普通讀者更好的閱讀體驗,使之能點贊打賞、暢所欲言,可與作家、評論家、編輯等專業讀者及其他讀者之間展開即時迅速的對話。
在媒介融合時代到來之前,評判作家作品的優劣,往往是專業讀者的事情。普通讀者若是沒有一定的專業訓練,不經過嚴格審核層層篩選,很容易缺席文學裁判。一些文藝評獎活動如“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百花獎”等雖也會向普通讀者敞開意見大門,但最終往往會在專業讀者的操控下定下乾坤。因此,很長一段時期,文學“讀者”的概念實際上是被少數專業讀者構想出來的,即或有時一些批評文章會刻意標注出讀者的“工農兵”“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之類的平民身份,也很可能實際操刀者是某位理論家或權威讀者。也就是說,在紛繁的文學現實面前,普通的大眾讀者通常是沉默的大多數。
而到媒介融合時代,普通讀者可以在網站、留言板、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自媒體等公共空間直抒己見,表達個體的閱讀喜好與訴求,而世界也樂于關注普通讀者的聲音。于是乎,普通讀者不再單向度地被作家、批評家塑造和引導,其同樣也會引導和重塑作家、批評家。譬如,本來一本令編寫者們自鳴得意的圖書早就編排印刷就緒,只待時機成熟推向市場,在聲譽和金錢上賺個盆滿缽滿,孰料在預熱推介過程中遭遇到天南海北讀者一片吐槽聲,這本“書”隨即就胎死腹中、煙消云散。又如網絡文學作家在更新連載作品時會特別關注追更讀者的即時閱讀反應,讀者對后續作品情節走向和人物塑造的建言獻策會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會被作者照單全收,如純潔滴小龍之寫作《深夜書屋》;或者會被作者刻意違逆,如噬紙狂魔之寫作《神臀證道》。夸張一點說,普通讀者對一本書或者書中主人公的命運握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利。當普通讀者發表批評意見的渠道暢通,引領文藝爭鳴、命名文藝現象、為中意作品“打Call”的權利,就不再專屬于專業讀者了,普通讀者亦可置喙。對某個文學獎項評獎是否公正的認知,就某某作家是否有資格得獎的討論,對作家之間筆戰是非的評判,或者對“梨花體”“羊羔體”“烏青體”等詩歌的命名,普通讀者都是最活躍的“吃瓜群眾”。專業讀者不屑不愿不敢也無暇無心關注的文事,普通讀者偏像那橫沖直撞的黑旋風一樣善于也敢于從中尋找到興趣點,雖說沒有專業讀者長篇大論的四平八穩架勢,雖只是三言兩語也未必有什么學理性,卻愛憎分明、快人快語、一針見血,絕不云山霧罩、吞吞吐吐、口蜜腹劍,這種“酷評”給文藝帶來的活力與批評生態格局上的改變,是值得肯定的。
正是因為普通讀者能直陳己見,其與專業讀者在文學見識上的分歧得以浮出水面,而他們之間審美上的罅隙與分裂恰好是值得探究的富有意味的地方。譬如金庸武俠小說、楊紅櫻童書、郭敬明青春文學等,會被相當一部分專業讀者認為去純文學甚遠,會被批得體無完膚,而普通讀者卻對他們的創作愛不釋手,令他們的作品一印再印。又如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張悅然主編的《鯉》等青春文學刊物以及“國民刊物”《讀者》《故事會》都是不會入專業讀者法眼的,但在上萬名網友打分評選出來的“年度文學刊物十強”中,這些刊物與《萌芽》《小說選刊》《收獲》《人民文學》《譯林》《青年文學》等純文學刊物同聚一堂,甚至《最小說》還高居榜首。再如由眾多網友吐槽投票推出的“死活讀不下去的書”排行榜上,《紅樓夢》《百年孤獨》《三國演義》《追憶似水年華》《瓦爾登湖》《水滸傳》《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西游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尤利西斯》 等經典赫然名列前十。類似文學認知分歧在早先就可能存在,只是普通讀者無緣發聲,遂得以長時間被掩蓋,唯有到了媒介融合時代,普通讀者的真實閱讀取向、體驗、意愿和興趣才能得到彰顯,其對既定文學秩序和既有文學經典的“離經叛道”才可能得到公示,文學閱讀和接受的真實圖景才水落石出。在從前,作品經典與否、作家稱職與否,完全由專業讀者來評判,但專業讀者在這當中是否推敲人際關系、能否劍走偏鋒、有無掛一漏萬,這都很難說。但看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被一代又一代專業讀者反復書寫,諸多作家在文學史書中時隱時現,評價時高時低,即可知道專業讀者并不總是目光如炬、慧眼識英才。掌握話語權的人不一定掌握真理,古今中外諸多名家經典初時不被專業讀者理解的例子同樣可以佐證這一點:儒勒·凡爾納的《氣球上的星期五》連續遭到15家出版社退稿;司湯達期待《紅與黑》能在半個世紀或者一個世紀后被人理解;惠特曼《草葉集》常常被文壇大腕們不屑一顧地擲進爐火中;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最開始并不被認為是好作品;陶淵明、杜甫、威廉·布萊克、愛倫·坡、本雅明、卡夫卡等生前文名寂寞……因此,普通讀者的聲音與專業讀者的論斷和衷共濟、此消彼長,可避免其中任一方對某部經典或者某個作家作品評價的一錘定音。畢竟,在文學鑒賞和評判方面,專業讀者并不總是全知全能、大智大慧,普通讀者也并不總是目光狹隘、根基淺薄,普通讀者和專業讀者既可以美美與共,也可以各美其美。因此,如果我們能“兼聽”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的閱讀反饋,則可得“明”,獲得對作家、經典、文學史更清晰、客觀、準確的認知。這該是媒介融合時代之于文學的一大福音。
普通讀者與專業讀者之間出現閱讀分歧很正常,也并非不可調和。專業讀者可幫助普通讀者提高文學修養,普通讀者的閱讀意見也不會對專業讀者毫無助益。事實上,媒介融合時代,普通讀者的閱讀口味與喜好得到了專業讀者的足夠尊重與“遷就”,成為專業讀者衡量經典、評判作家的一個重要參數。到今天,金庸、楊紅櫻、郭敬明的文學作品或者被認證為經典,或者得到研究者的首肯,或者獲主流文學界的青睞——《人民文學》和《收獲》等權威期刊先后刊登郭敬明長篇小說《小時代2.0之虛銅時代》和《臨界·爵跡》,這都是傳統文學勢力適應時代審美風尚變化而向普通讀者“示好”的表現。所以,我們也不必奇怪,麥家那部依舊例該歸入通俗小說之列的《暗算》、金宇澄起于網絡的小說《繁花》先后問鼎茅盾文學獎,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鮑勃·迪倫獲得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當文學評委聞時代之風而動走出象牙塔、正視普通讀者閱讀趣味而適時調整評判標準,自然會有這樣的評獎結果。“新的傳播技術不僅給予我們新的考慮內容,而且給予我們新的思維方式。”[5](P44-45)于是乎,一時代有一時代所認可的文學、所欣賞的作家,一時代也就有一時代所弄潮的讀者、所追逐的風尚。而且,普通讀者的評判會激發專業讀者對“經典”品質或作家資質進行認真探討的熱情,進而活躍學術氣氛,譬如北大教授對“四大名著”不適合孩子閱讀的認定,譬如復旦教授將絕大多數中國古典小說和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列入“不必讀”書單,譬如農民、工人、月嫂等草根寫作者的作家身份認定。沒有普通讀者地位的提升和相應審美訴求的表達,上述“異端”聲音的出現是不可想象的,而這一切都有賴于媒介融合對普通讀者和專業讀者開展對話的有效促成。
三、媒介屬性的凸顯
印刷傳播時代,眾多文學期刊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文學場域即文壇,對此場域表示認同的編輯、作家、評論家等專業讀者形成了文學圈子以及相應的審美標準。值得提及的是,文學期刊當中還有嚴肅與通俗、純正與商業之等級、品質差異,就像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哪怕期發行量超百萬冊、擁躉者眾也還是不權威,某些純文學刊物哪怕只發行幾千幾百冊、門可羅雀也還會是文學高地的標桿,后起之秀唯有在這樣的權威紙媒文學圈子里把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才算登堂入室。但媒介融合時代,作家發表作品的途徑已不再局限于文學期刊這“自古華山一條道”了,寫作者既可以直接出書走市場,也可將作品放到網站或者博客上與人分享,更無須擔心沒有專業讀者來為自己作品買單或喝彩,只需大眾讀者認可,哪怕是孤芳自賞。當然,在抱持傳統觀念的專業讀者看來,承載文學肉身的期刊、圖書和網絡這三種媒介還是有質量等級的參差的:級別最高的是期刊,走市場的圖書等而次之,網絡是最不入流的,即使網絡擁有再多的瀏覽量,即使圖書賣得再好,即使純文學期刊門前冷落車馬稀。2006年發生的“韓白之爭”就很好地證實了文學界存在著的這條“鄙視鏈”。
2005年白燁在文學雜志《長城》上發表《80后的現狀與未來》一文后還無聲無息,但當他轉過年來將該文掛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時,立刻遭到了“80后”的韓寒在新浪博客上的迎頭痛擊,二人間自此所發生的論戰以及后來相繼加入這場“廝殺”的眾多作家評論家們的意見大都是發表在網絡(博客)空間上的。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在媒介融合時代,紙媒(文學期刊)的影響力要遜于新媒體。同時,這場引人矚目的“韓白之爭”實則關乎到了作家、文學的“資格認證”問題。遵循印刷傳播時代文學游戲規則的白燁堅持認為,“80后”作家唯有先在權威紙質文學期刊上亮相,才算真正走上了文壇,否則,就算在出版社出再多的書,都還只是文學“票友”。但在韓寒看來,能在公共媒介上發表文學作品,就都應該被視為作家,而且絕不應該以作品見諸何種媒介——是期刊還是圖書抑或是網絡——來判定質量的高下優劣、作家身份的真偽大小:“每個寫博客的人,都算進入了文壇。”因此,韓白之爭的實質是文學觀念之爭、文學媒介認知之爭。而當現代電子媒介迅速獲取輿論高地并強勢介入文學后,文學的媒介屬性得到了再清楚不過的彰顯,媒介文學被很好地正了“名”。
以網絡文學為例。當其剛剛在網絡上露出尖尖角之時是被視作文學性的網上游戲的,但在今天已然名正言順,有眾多研究者在為建立網絡文學專屬的評價體系而絞盡腦汁。中國網絡文學已被認為堪與美國好萊塢大片、日本動漫和韓劇相媲美,其活力、受關注度、市場占有份額等均非昔比。歷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上網絡作家收入之高令人咋舌,這證實了網絡文學受眾之多;眾多的熱播影視片改編自網絡文學作品,這說明網絡文學影響力之高;在全國性的青年作家會議上網絡作家已經占據了半壁江山,各省市紛紛成立網絡文學作家協會,研究網絡文學的專家學者和機構越來越多,有為選拔優秀網絡文學作品而設立的諸種專門大獎,甚至就連傳統權威文學獎項也對網絡文學網開一面,這些均可以證明網絡文學所受到的重視和禮遇。事實上,如果要獲知中國當代文學的真實景象,也唯有將紙媒文學與網絡文學這兩種媒介屬性不同的文學放在一起考察才足夠客觀全面。可以肯定,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寫作、閱讀、研究格局所造成的強有力沖擊還會繼續,文學版圖的重新繪制勢在必行。這一切不能不讓我們認同如是的判斷:“傳播技術的變化無一例外地產生了三種結果:它們改變了人的興趣結構(人們所考慮的事情),符號的類型(人用以思維的工具)以及社區的本質(思想起源的地方)。”[5](P32-33)
印刷傳播時代,作家是人群當中少數可以在紙媒上擁有話語權力的人,因而會得到“無冕之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等各種加冕,那情形就與從前文言至尊時代把持文壇的書生對只會操持大白話的眾多引車賣漿者流造成威壓之勢一樣。但當媒介技術發展到可以為人的文字表達提供暢通渠道時,則賦予了全民寫作以可能性,每一個人都可以“我手寫我口”,激揚文字指點江山,抒發自己對詩和遠方的向往之情。就像桀驁不馴的韓寒在“韓白之爭”中所公開聲明的那樣:“別文壇不文壇,每個碼字的都是作家,每個作家都是碼字的。”這當然褪掉了籠罩在作家和文學身上的神性光環,有讓作家平民化或文學普泛化的“危險”,但這對促進文學品質的提高不無好處。寫作不再是專業作家的特有權利,人人都擁有了言說的空間、閱讀的意愿和寫作的欲求,文學最廣泛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得以形成。那些頂著“國家一級作家”“獲獎詩人”或作協主席等桂冠的專業寫作者與凡夫俗子比較起來理所應當技高一籌,若是專業作家吟誦出來的詩句被發現不過是用回車鍵分行的大白話、是圍繞著“天上的白云”、超市里的梨來回說的車轱轆話、是“自慰自樂管不住”的打油詩,則他們的身份和寫作當然要遭到普通讀者的質疑與恥笑。換言之,媒介融合時代,以文學為主業的寫作者需要才與位匹配、名與實相副才行,這還意味著文學寫作要郊寒島瘦、字斟句酌,切不可隨意涂鴉、下筆匆匆。
其實,媒介融合時代之于文學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倒逼”人們重新認真思考文學的本質問題。在過去資訊稀缺之時,文學是很好的認識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載體。可是,當無孔不入的媒介攜帶著大量的關于這個世界的新聞資訊鋪天蓋地而來之時,人們會發現,不必借助文學也照樣能夠清晰地認識世界、了解人生,而且很多時候,現實要比文學作品更富有戲劇性更刺激更充滿懸念,生活真相要遠遠超出作家的想象極限,不必添油加醋,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復制現實,我們就可以得到各種意想不到的悲劇、喜劇、正劇、鬧劇、荒誕劇、驚悚劇、懸疑劇、宮斗劇,我們照樣能品出生活百味、參透人心詭譎、讀懂人性復雜。這是廣闊的現實、無邊的生活以及無處不能抵達的媒介給文學帶來的沖擊和挑戰!因此,如果作家依然滿足于對現實的機械拷貝的話,則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文學?文學區別于各種八卦消息、花邊新聞的特質是什么?文學該怎樣處理自己和生活的關系問題才可能不被奇聞怪事所覆蓋和替代?
我們由是可以更進一步思考“何為文學”和“文學何為”這樣既古老又現代的常思常新的嚴肅話題,也許會因此尋找到理解當下文學世界、打開時代生活之門的鑰匙:文學刊物經年累月推出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某些公眾號上宣稱“真實”的博得超高閱讀量的淚目文章,是否都是在瞅準了人們對“真實”和“故事”的雙重閱讀渴望后的虛實難辨的“應需”之作?文學體裁的“三分法”或者“四分法”是不是已經遠遠落后于文學發展的實績而需要理論出新了?某些作家熱衷于動用“魔幻現實主義”或“神實主義”來書寫現實,是否為了避免對現實的機械復制?某篇小說堆積與拼貼了各種社會新聞,是否因為著作者發現自己對世界的想象無論如何也不能跳脫出生活如來佛的掌心?某個困守家中的作家所寫的都市日記引發的究竟有多大代表性和多大價值的激烈爭執,是否意味著人們對“真實”或“典型”的理解歧異?當人工智能寫作成為現實,微軟“小冰”都能編程出讓人似懂非懂的“陽光失了玻璃窗”一類的詩歌時,我們是不是該對現代漢語新詩寫作及評判標準有一個再認識?文學脫胎換骨,文學研究鳳凰涅槃的機會也許就隨之出現。
要知道,在人類傳播活動先后經歷的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和電子傳播幾個時代里,文學都因應著媒介變化而有著不盡相同的表現形態。在口頭傳播時代,口語媒介支撐下的說唱文學當然是寵兒。在文字傳播時代和其后的印刷傳播時代,語言文字構建起的文學大廈則樹立起了自己的威權。到了電子傳播時代,媒介無處不在,報紙、雜志、圖書、廣播、電影、電視、互聯網、手機、移動終端等群歡共舞,文學亦隨著媒介觸須的四處探伸而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延展與變身。既然媒介千變萬化、多種多樣,則依附于媒介之上的文學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必然會隨著所依附的各種媒介而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因為“文學就是一切被標為文學的東西”[6](P22)。因此,除了傳統的紙媒文學外,電影、電視劇、廣播劇(小說)、網絡文學乃至于微博、微信公眾號、APP客戶端等平臺上的段子、文案、說書、短視頻、抖音等,也都盡可以被收納在“文學”之筐內,就譬如那把生活過成一首詩、全球粉絲過億的中國鄉村美食博主李子柒的網絡視頻,就完全可以被認定是“文學”。“是什么推動了世界文學一次又一次的巨變?通常是每當有人對某種簡單的、被貶價為略低一等而不被重視的藝術形式善加利用,令它發生了蛻變。”[11](P7)那么,媒介融合時代是不是已經用它那無形之手暗暗撥轉了人們對文學觀念的認識,文學出現巨變的歷史拐點是否已經或即將到來?遭遇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文學將會因此獲利還是得弊?迎來的會是危機還是機遇?
因是之故,我們不但不會對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學前景感到悲觀,反倒因此發現文學創作的視域無限寬廣、文學研究的天地充滿玄奧。我們應該還記得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對這個世界和有關這個世界的文學書寫的期許:“我很好奇。很想知道出生在網絡、手機、電郵和微博的一代代年輕人將用怎樣的文學去表達這個人人都時刻‘連在網上’、‘社交網絡’侵害到個人隱私的世界。”[12](P61)的確,世界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它的五光十色,時代讓我們意識到有多種多樣的媒介形式和表現手段可資利用,藝術的多種可能性正在向我們敞開,那么,開啟一段值得期待的文學旅程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