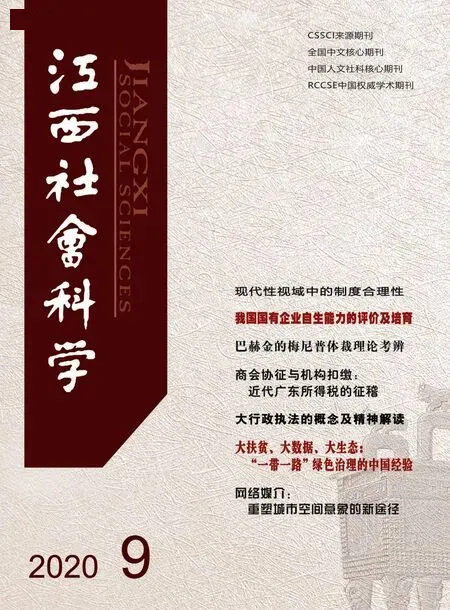現代文學理論在中東歐的興衰
——兼論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
在書寫文學理論與批評史以及文學思想史時,可以采用多個視角,而其中一個就是勾勒出不同學者之間的人際交往圖。研究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這兩位文學理論家之間的關系,從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寬泛語境中探究其關系的轉變,進而將這種轉變置于他們所經歷的政治、文化事件的語境中,可以概述出其結構主義詩學的認識論基礎。這不僅有助于闡述一段友誼的起落,還關乎結構主義的興衰,也可以表明結構主義的源起與中東歐的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
提到中東歐,大多數人會聯想到歐洲中部的一些國家: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波蘭的一部分、匈牙利或奧地利。從地理學角度來看,的確如此。但實際上,中東歐的概念有著一段悠久且豐富的歷史淵源,我們還需記住另一種觀點: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奧匈帝國衰落時,尤其是在1918年,中歐這一概念愈顯重要。一些獨立的甚至是新建立的國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成為中歐這一新概念的發展基石。在語言學、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語境中,中東歐這個概念經常被提及,它是現代文學理論與語言學的一些關鍵概念的發源地:如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及現象學、闡釋學等。20世紀現代文學理論的興衰可以用結構主義的境遇來加以闡明,這種方法的起源還與中東歐的歷史密切相關。除此之外,現代文學理論的興衰還可以用穆卡若夫斯基(1891—1975) 和雅各布森(1896—1982)這兩位文學理論家的一段不平凡的友誼來加以闡述。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討論這些跌宕起伏的歷史事件。
一、結構主義
在捷克文學理論及批評史中,抑或在語言學和美學史上,很難找到一種科學方法能在重要性和接受程度上與結構主義相提并論。在捷克語境中,結構主義的起源、發展與布拉格語言學小組(存在于1926—1948年,1989年后再次復興)是緊密相連的,后者是制定結構主義基本方法論前提和概念范疇的大本營,其成員通常用結構主義的方法系統研究語言、文學或美學。眾所周知,布拉格是俄羅斯形式主義與巴黎結構主義的重要中間節點,布拉格語言學小組對現代語言學、詩學及美學的興起與發展均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馬泰休斯、穆卡若夫斯基、雅各布森、哈弗拉奈克及其他學者的努力下,布拉格語言學小組的研究成果得以進入更廣闊的文化意識中。
雅各布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移民至美國,而布拉格語言學小組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經由他介紹,進入美國語言學及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視野中。20世紀50年代,結構主義學派的中心移至法國,而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是列維-斯特勞斯,他在雅各布森音韻學研究方法的啟發下,開始關注語言的聲學及語義系統結構與其他文化系統結構(如神話故事、親屬結構和宗教儀式)之間的相似性。在法國,結構主義被當作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可普遍適用于任何社會及文化現象。法國理論家在科學、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興趣各不相同,這導致了他們對結構主義概念的理解、結構主義方法的應用及其批評潛能存在巨大差異。例如,社會學家盧西安·戈爾德曼創立了生成結構主義,其他學者則將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結合起來,還有學者聚焦結構主義與詮釋學的關系等。結構主義廣泛流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一些法國文學理論家,如羅蘭·巴爾特、熱拉爾·熱奈特和茨維坦·托多羅夫,他們把結構主義作為文學理論研究、新詩學以及文學理論與批評術語研究的基礎。[1][2]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對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趣達到頂峰。這種理論興趣還逐漸蔓延到北美和整個西歐,并在同一時段達到頂峰。[3]它的影響還波及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家。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結構主義曾在這些國家被禁止過,20世紀60年代得到復興。在捷克斯洛伐克,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揚·穆卡若夫斯基美學研究文集》1966年首次出版,布拉格語言學小組的一些老派結構主義傳統得到延續,并在塞萬卡、揚科維奇、什瓦提克等學者的努力下進一步發展。波蘭建立了結構詩學學派,成員包括格洛文斯基和斯拉文斯基;斯洛伐克創立了尼特拉學派,成員包括米克、波波維奇等人;另外,還成立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符號學和結構學研究中心,包括一些在蘇聯莫斯科大學與塔爾圖大學中成立的研究中心,后者成員包括洛特曼和烏斯賓斯基等。
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學界尤以雅克·德里達和吉爾·德勒茲為代表,對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批評之聲越來越多,這導致結構主義逐漸轉向后結構主義。正是由于這種批判,結構主義在人文學科的通用科學方法論中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和特權地位。20世紀80年代,后結構主義(解構)和文化研究取代了它的地位。
二、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
學界現在無法確切知曉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首次會面的時間和地點。據考證,早在1920年9月,雅各布森已經見到了后來擔任布拉格語言學小組主席的馬泰休斯。1926年10月,布拉格語言學小組成立,而雅各布森與穆卡若夫斯基正式記錄在案的首次會面發生在1920年12月2日。盡管他們兩人代表著不同類型的學者,然而也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對現代藝術、詩歌研究、語言學、詩學、美學、文化及社會問題都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他們都對科學情有獨鐘,并開始了緊密的合作研究,共同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1929年10月,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一屆斯拉夫學者大會上,他們發表了著名的《布拉格語言學小組論綱》,這是一項集體工作,總結了語言學和斯拉夫學研究的現狀,并概述了這些領域新的結構主義—功能主義方法的主要原則。二人合作完成了有關詩歌語言和詩歌作品一節的內容。
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共同參與并合作了很多活動。例如,1930年3月25日,布拉格語言學小組公開集會,其主要目的是紀念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托馬·加里格·馬薩里克的80歲生日。[4][5][6]再如,1932年,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完成了另一學術合作——主題為捷克文學語言與語言文化的系列演講(這些演講后來結集出版,書名為《捷克標準語與語言文化》)。1934年,他們二人的合作達到巔峰,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歷史與地理》,這本書呈現了他們對古捷克詩歌和現代捷克詩歌的研究成果。[7]文學理論家雷納·韋勒克為此書寫作了一篇內容詳細的書評文章,其中說道:
在該書中,兩位作者不僅從新的角度首次展示了捷克詩歌的歷史,還向讀者描繪出了一種新的文學歷史編撰方法,還用其中一節展示了捷克文學的新的歷史風貌……要正確評價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這種變革行為,我們需將其放置在當時捷克文學史的背景中。[8](P437)
韋勒克對他們著作的評價證實了兩人之間的友誼很自然地影響了他們個人關系的性質、他們合作的學術工作及具體的研究成果。
20世紀30年代中期,捷克的這三位著名學者,哈弗拉奈克、穆卡若夫斯基、雅各布森(同為布拉格語言學小組的成員),似乎在學術活動、學術合作和私人關系等方面都密不可分。然而,1938—1939年歐洲發生的政治和歷史事件(法西斯的抬頭)將他們置身于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之中。德國法西斯軍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后,雅各布森被迫于1939年4月經由丹麥、挪威和瑞典移民至美國(1941年)。他們三人之間的交流也被迫中斷長達幾年之久。1945年6月,他們之間的第一批問候電報才得以發出。然而,雅各布森身在美國,穆卡若夫斯基和哈弗拉奈克處在捷克。雅各布森自1941年開始在高等研究自由學院擔任普通語言學教授,同時還在位于紐約的東歐和斯拉夫文獻學和歷史學研究所任斯拉夫語言及文學教授,而穆卡若夫斯基和哈弗拉奈克公開露面的機會都很少,也很難展開學術研究活動。[9][10]穆卡若夫斯基和哈弗拉奈克邀請雅各布森回到捷克,同他們一起在大學任教,但這一想法未能實現。雅各布森推遲了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劃,他很有可能從愛倫堡那里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很快會發生政治巨變,而1948年,捷克共產黨開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執政黨。
三、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結構主義詩學的認識論基礎
盡管在某些具體層面,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的結構詩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稍有不同,他們卻在一些主要原則上觀點一致,這種一致性是他們結構主義及結構詩學研究的至高點。
從他們發表的研究成果、公共演講和大學演講中,從他們合作完成的《布拉格語言學小組論綱》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結構主義詩學的基石已經形成。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雅各布森藝術作品分析的幾個關鍵原則也已形成。[11][12][13][14]
第一個原則是強調藝術作品是一種獨特現象。這一觀點源自俄羅斯形式論學派,他們認為對藝術品的分析不能依靠來自作品外部的任何解釋[15],這一觀點認同穆卡若夫斯基和其他結構主義者的方法,將藝術創作視為一個整體,各個組成部分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第二個原則與這一原則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在20世紀的前20年中,俄羅斯學界研究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除了這些理論源泉外,布拉格結構主義也深受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和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的影響。胡塞爾在1900年出版的《邏輯研究》一書中,探討了部分與整體的關系。[16]而在布拉格語言學小組內部,整體與部分的原則通常表現為將研究對象作為整體來觀察。然而,整體并不是單個組成部分的集合,而是形成一種結構,且每個獨立的組成部分互為關聯。因此,要解讀這些組成部分,只能將其放置在整體之中,分析它們各自的功能與角色,所以,整體的結構是由所有組成部分的功能決定的。這一原則在詩歌分析上尤其具有根本性影響力,它消除了內容與形式之間的界限。穆卡若夫斯基的很多研究都試圖表明構成一部藝術作品形式的所有要素如何影響進而構成了該作品的內容。反之亦然。穆卡若夫斯基在20世紀40年代寫作的幾篇文章中,闡述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他還回應了捷克學者、生物學家布爾雷德克提出的整體論方法。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他已經在德國哲學家的觀點基礎上,形成了自己有關結構和整體的概念,而最為重要的則是現代語言學的概念原則。[11][12]
穆卡若夫斯基提出的第三個重要原則是運動原則,他認為不能將作品理解為一個封閉的、源自本身的整體,在他看來,每個作品都處在不停的發展之中,是整個詩學結構的一部分。創作詩歌所用的語言尤為獨特,因此,在評析詩歌作品時,可以將其放置在一個國家的文學整體中,并參照之前的文學創作。穆卡若夫斯基認為一件藝術作品不屬于某個人,而屬于問世后接納它的那個社會。他承繼了俄羅斯形式論學派的觀點,宣稱打破傳統是發展的驅動力。這是他首次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在與矛盾斗爭的基礎上,理解什么是發展。藝術創作的基礎是違背傳統,只有這樣,它才能通過宣揚傳統而最貼近傳統,這的確是個悖論。總之,文學處在不停運動之中,是一種自發的結構,按照自身發展規律而發展。與此同時,文學類型、詩歌概念等,也處在運動之中。[11][17]
穆卡若夫斯基嚴格遵循的第四個重要原則是要永遠不斷地研究素材,時刻關注素材,即所研究的語言或藝術作品。在他看來,科學研究的職責在于尋找、描述并整理素材。他認為理論作品不能脫離具體的材料。如果一些觀念被視為某些假設,那么自然有必要不斷地證實這些觀念。[18]
第五個原則是將藝術品視為一種符號,藝術是一套符號系統。[18]在1929年出版的《布拉格語言學小組論綱》中,藝術已被視為一套符號結構,重要的是作為符號的藝術本身,而不是它所指涉的對象。將藝術品視為一種符號,這樣可以聚焦其具體特征、復雜的內部構成、不穩定的位置和意義的產生過程,這是藝術家與接受者之間出現的一種符號過程,還能研究它與其他符號的不同。
而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到底有哪些一致觀點?其結構主義的認識論基礎是什么?答案很簡單,是辯證法。他們二人都將辯證法視為連通上述原則的認識論基礎,不僅如此,辯證法還可以幫助理解存在于文學結構中的、進而存在于整個世界中的各種模式。在20世紀40年代的前半段,穆卡若夫斯基尤其認為結構主義和辯證法開始逐步合二為一。
辯證法這一概念出現在布拉格結構主義學者的學術著作中。比如,他們會用它來解釋具體的語言問題、現代藝術的起源與發展、文學結構的運作,并勾勒出藝術與社會的關系等。然而,辯證法也是他們闡述自己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出發點。正是源于這一點,他們的觀點開始偏離結構主義的觀點。依據辯證法,布拉格的學者們開始將結構本身當作一個動態的整體,一個由相互矛盾的部分聯系在一起的統一體。他們將辯證法解釋和理解為一門研究矛盾集合體的學科,成為捕捉運動和過程本質的最合適的工具。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世界不再被視為由一整套事物構成,而是由一整套過程構成的。
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流亡者,尤其是契熱夫斯基和雅各布森,把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帶入布拉格語言小組,這里說的辯證法不僅包括黑格爾的辯證法,還特別包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辯證唯物主義框架內運用的辯證法。[19][20]1934年,穆卡若夫斯基首次出版了運用辯證思維原則的研究成果。在這些著作中,他調整了自己審視俄羅斯形式論學派傳統的立場,尤其是他們所提出的內在發展概念。他承認,不能僅僅從內在的角度來考察語言和藝術的發展,還必須考慮它們的社會層面。布拉格語言學小組開始將語言和藝術視為符號,或者更具體地說視為符號系統,該事實為這種觀點的轉變奠定了基礎。將眼前的現實(語言與藝術)視為一種符號,這要求人們還應關注社會,因為社會也會使用這些符號和整個符號系統。穆卡若夫斯基的辯證法基于黑格爾發展觀念,并不涉及世界的發展,而是關注邏輯、關注思維形式的發展。他還從列寧的《哲學筆記》中獲得啟發。[19]
盡管穆卡若夫斯基最初意識到辯證法能夠解釋發展變化是與黑格爾哲學有關,但他并不接受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他認為唯心主義辯證法基于否定,而否定會導致慣性。這可以用正題、反題和合題來舉例說明(盡管這不是黑格爾舉出的直接例子)。穆卡若夫斯基認為(雅各布森也贊同此觀點),合題是沒有運動的、無生命的整體,而現實、世界是在不停運動中的。生命就是變化與發展。世界(思維也是如此)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因此世界不能是靜止的。
我們若將辯證思維應用于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就能夠識別個體的發展機制與整體的發展機制。如果矛盾的趨勢不再在構成整體的各個體部分之間運作,那么,整體就開始以和諧的形式出現,即“開始瓦解”。整體(結構)是(而且必須是)在不斷運動中的。
四、關系破裂
1939年4月,雅各布森在離開捷克斯洛伐克時,曾把自己的一袋手稿留給穆卡若夫斯基,托他代為看管。1948年,他希望穆卡若夫斯基能把手稿交還與他。也就是在這一時段二人之間的關系出現了裂縫。
雅各布森寫了幾封信給穆卡若夫斯基,但均未收到回應。而雅各布森此時正焦急地等著使用這批手稿。因為沒有直接收到穆卡若夫斯基的回復,他轉而向哈弗拉奈克和其他朋友尋求幫助,哈弗拉奈克的確幫了大忙,最終雅各布森也妥善地收到了這批手稿。問題看似解決,但此事在很長時間內為雅各布森與穆卡若夫斯基的關系籠罩上了一層陰影。尤其在雅各布森這一方,他無法理解穆卡若夫斯基為何無動于衷,這令他頗有些心存怨恨。我們只能認為穆卡若夫斯基保持沉默且不愿回應,自有苦衷。雅各布森對穆卡若夫斯基的不滿則很快在他對穆卡若夫斯基研究中的嚴苛批評與指責中可見一斑,20世紀40年代末,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多集中在馬列文學理論和美學。[21][22][23]這些新作與之前那些純粹結構主義研究的共同特性在于它們的辯證發展視角。
雅各布森分別在1957年、1968年和1969年訪問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國際會議,這樣他們就有機會見面,當面消除兩人間的誤解和戰后出現的各種“喧嘩”之聲。而他們的確也見面了,這從留存下來的照片中就能看到。他們之后關系怎樣?很不幸,我們沒有更多的史料記載。但是,間接證據表明,雖然他們再也沒能像30年代那樣成為親密朋友,但仍然保持著友誼——至少是本著合作和學術認可的精神。例如,雅各布森在與克里斯蒂娜·潑墨斯卡合著的《對話錄》中將穆卡若夫斯基看作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最能給人啟發的學者,尤其是處理不同種類的藝術與特定藝術作品的符號學之間的異同時。[14]
當然,我們也可以不考慮這部書寫作的背景,獨立評估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的學術成就。然而,只有勾勒出廣泛的背景以及各種不同的形式和變化,我們才能理解他們工作的實際意義和范疇。他們的詩學著作在捷克文論史和批評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印記。[13][24][25]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在廣泛的語言、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背景下,沿著這一邏輯軌跡完成。
最后一件可以用來揭示他們關系的檔案是雅各布森1971年為祝福穆卡若夫斯基80歲生日而發的電報:“祝福我親愛的朋友、世界知名的學者。羅曼。”[26]雅各布森雖沒有給予穆卡若夫斯基1951年發表的公開自我批評高度評價[27],但很明顯,他一直非常欣賞穆卡若夫斯基和他的工作,而穆卡若夫斯基對雅各布森的態度也是如此。
五、結語
對穆卡若夫斯基與雅各布森友誼的起起伏伏,外部環境和政治形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結構主義也經歷了這些,而現在的情形又怎樣呢?顯然,從文學理論發展的表層來看,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基本術語和理論假說(尤其是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的結構主義詩學)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結構主義目前正在從好幾個領域(包括文學理論與批評)獲得了一種新的、不斷更新的形式,這一事實也證明了它的生命力。[10]
從上述對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發展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沒有一個通用的理論能夠包含所有可能的變量和文學研究方法,而且這些也不會僅僅由一個學派來完成。毋庸置疑,文學術語也是如此。盡管存在差別,不同的結構主義概念都處在文學理論和批評研究之中,它們卻有著共同的且可以互為比較的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對文學的系統(有條理的)且理性的批評方法,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具體符號,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它的個體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