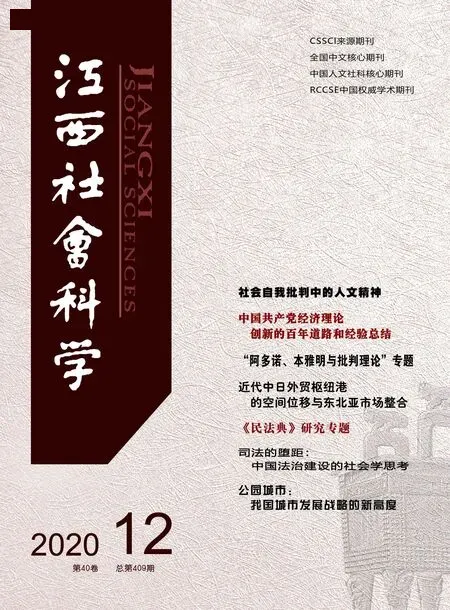從民事單行法到《民法典》:守成與創新
我國《民法典》的編纂是對民事單行法進行“揚棄”的過程。我國民事立法雖受潘德克頓觀念影響而繼受以德國為主的大陸法系的立法體例,但基于歷史慣性、社會現實、體系因應、倫理觀念等原因,我國《民法典》的立法體例、物權主體、合同效力、人格權利類型、親等制度、繼承順位及多數人侵權制度等明顯具有守成的一面;而社會變革、交易保護、政策調整、價值協調等因素則決定民法典各編在權利體系、交易與擔保規則、未成年利益保護與財產分配、權利保障與責任承擔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創新。本次民法典編纂的守成與創新,相當程度上系基于我國實踐經驗,其實用主義的立法態度值得肯定,亦將成為我國社會發展之佐證。
自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編纂民法典”、2015年初重啟民法典編纂工作以來,經過立法機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本文其他法律均照此使用簡稱)在2020年5月28日經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在5年多時間里,民法典編纂遵循“兩步走”的工作思路,以各單行法為基礎,總結吸收改革開放40余年來民事立法和實踐經驗,先后起草民法總則和民法典各分編,最終形成了七編制的法典結構。《民法典》的頒布實施,改變了原有民事法律分散狀態的立法格局,包括《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婚姻法》《繼承法》等在內的一批民事單行法及司法解釋亦將廢止。相對于上述民事單行法,《民法典》在體系及內容上既有守成,又有創新。本文從具體制度之變動入手進行比較分析,以窺《民法典》編纂之得失。
一、從《民法通則》到總則編
根據“兩步走”的立法規劃,《民法總則》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實施,后略作修改成為《民法典》總則編。相對于《民法通則》,《民法典》總則編一方面基于歷史慣性繼續秉持民商合一立法體例,沿用“序編”結構,凸顯“權利-義務-責任”之主線,另一方面在具體制度上,吸收40余年來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完善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法律行為等規范,以求因應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
(一)立法體例的繼受
總則編對《民法通則》的繼受,主要表現在立法體例方面:在與商法的關系上繼續堅持民商合一體例;在章節結構上遵循“權利-義務-責任”的邏輯線索。
我國民商合一體例的正式確立,始于《民法通則》的制定。當時大多數學者認為,民法應調整橫向的經濟關系與人身關系,經濟關系既包括公民之間的財產關系,也包括經濟組織與國家之間的財產關系。[1](P109)這種觀點使《民法通則》尤其是其中的法人制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無論相較于頒布之前的《經濟合同法》《繼承法》,還是之后的《合伙企業法》《公司法》等民商事法律,《民法通則》都始終處于基本法地位。2002年民法草案及《民法典》總則編繼續堅持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其典型特征,體現在總則編中的主體制度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類型的商主體,除最典型的“營利法人”外,還包括“特別法人”中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本應作為商個人的“個體工商戶”,以及“非法人組織”中的商合伙。總則編第三章第二節“營利法人”也是以《公司法》為藍本進行抽象,其中部分內容如第84條對關聯關系的規制、第85條關于違反法人章程的決議內容可撤銷的規定,與《公司法》第21條、第22條第2款相同。而第一節“一般規定”中的第71條,也將“公司法律的有關規定”直接作為引致規范。不過,雖然總則編對民商合一的堅持系基于歷史慣性的守成,但構建于潘德克頓體例之上的民商合一,卻是“世界范圍內的最新一次嘗試”[2]。
除民商合一體例外,總則編“權利-義務-責任”結構也是《民法通則》的產物。與《德國民法典》總則編相比,“民事權利”處于我國民法典總則編的中心位置,其他章節則圍繞“民事權利”對權利主體、權利實現方式及權利保護進行規定。但與《民法通則》及2002年民法草案有所不同的是,總則編將權利客體嵌入了“民事權利”一章。雖然《德國民法典》對“物和動物”以專章規定,但亦不免被批評為“一般化嘗試失敗的典型”[3](P26)。事實上,僅有物和智力成果能夠界定權利的支配范圍,大多數情況下,對于客體的爭議卻并不影響權利本身的承認和權利內容的認識。就總則編來說,避開有爭議的非財產權利客體,僅對具有范圍界定意義、理論上無爭議的物和智力成果進行規定是明智的。[4]另外,由于數據、網絡虛擬財產及個人信息存在關于權利本身的爭議,對其從客體的角度進行規定,能夠使“民事權利”一章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能夠解決特殊民事權利的保護問題。而總則編“民事責任”一章,系直接源于《民法通則》,這種規定方式可溯源至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民法典,其中第八章第176條至第187條規定了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尤其是第179條仍以列舉方式規定了民事責任承擔方式。從體系上看,總則編雖承襲《民法通則》之規定,卻與其作用不同。《合同法》制定后,《民法通則》統一民事責任立場已難以維持。因此,總則編“民事責任”的統一規定,并不等于對違法行為的統一救濟,立足“權利-義務-責任”體系,在總則部分規定統一民事責任更具有形式意義,“民事責任”而非“民事權利保護”之名也屬應然選擇。
(二)具體制度的創新
總則編在延續《民法通則》基本結構的情況下,進一步完善若干具體制度,主要創新之處有如下幾點。
1.優化民法淵源。在《民法總則》頒布之前,《民法通則》第6條將民法法源確定為“法律”與“國家政策”,但在運行過程中,“國家政策”作為裁判依據存在較多問題。一方面,《民法通則》第6條中“國家政策”的層級與范圍并無統一的明確規定;另一方面,各地法院在適用國家政策時對法律行為的效力判定亦存在不同的標準。因此,《民法總則》制定過程中對《民法通則》第6條進行優化,將“法律”之外的法源限定為“不違背公序良俗的習慣”。此種做法符合各國民法典通例,并且能夠為民商合一體例下商事習慣的適用提供空間。但總則編對法律淵源的優化并不徹底,由于將法理排除在民法法源之外,僅有“法律”及“習慣”的做法會導致適用法源時缺乏必要的彈性。即便我國存在以法律條文對法律原則進行確認的慣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此種缺漏,但亦不利于民法法源與法律解釋的軟化。
2.重構主體類型。《民法通則》對主體類型采“二元制”結構,分為自然人與法人。由于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及其他服務機構的存在與發展,《民法通則》的此種規定已不合時宜。[5]在個人獨資企業突破了傳統大陸法系法人概念外延之后,傳統法人概念已僅具形式意義。總則編延續《民法通則》責任獨立性的標準,將組織體劃分為法人與非法人組織,一方面能夠避免概念內涵變動所帶來的混亂,另一方面也符合民事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的發展趨勢。另外,由于我國采民商合一立法體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的三元制結構同樣能與商法中商個人、商法人與商合伙的主體劃分形成對應關系,從而對商法起到較好的統領作用。
3.豐富權利體系。相對于《民法通則》,總則編增加了第109條作為人格權的一般規定,從而為自然人人格權的擴展留下了空間;第110條增加身體權作為自然人人格權的內容,對人格權體系進行補全。除此之外,總則編對于《民法通則》權利體系最大的突破,是首次將個人信息及數據的保護納入“民事權利”一章。第111條對個人信息保護進行單獨規定,從形式上完成了其與隱私權的區分,為進一步制定具體規則提供可能;第127條對數據、虛擬財產的規定,也是對信息社會和網絡時代的回應。與其他權利的規定方式不同,總則編對于個人信息、數據及虛擬財產,未能以權利確認的方式進行規定,而是從客體的角度規定保護,從而回避了權利性質的爭議問題。
4.完善行為規則。《民法通則》受蘇聯民法影響而構建的法律行為制度頗受學界詬病。一方面,堅持民事法律行為合法性的要求造成概念上的矛盾;另一方面,無效法律行為的范圍過于寬泛,效力劃分不盡合理。[6]相較《民法通則》,總則編將原有9條的法律行為制度充實至28條,其進步在于:(1)恢復傳統法律行為概念,摒棄蘇聯民法中法律行為合法性的要求,重新以意思表示作為法律行為的核心要件;(2) 完善意思表示實施與解釋規則,以意思表示為基礎增設決議行為;(3)重構法律行為效力規則,包括增加第146條通謀虛偽表示規則、第149條第三人欺詐規則,改變“二元制”的表意瑕疵體例而刪除可變更法律行為,通過第151條合并乘人之危與顯失公平情形,并限縮無效法律行為的范圍。[7]但法律行為效力規則仍存在較大的完善余地,如在效力評價體系上應進一步對法律行為的有效與生效進行區分,增加真意保留、戲謔表示規則,完善錯誤類型,將限制行為能力人實施的單方行為規定為無效,補充規定法律行為無效時的轉換規則等。[8]
5.改進時效制度。我國立法機關對待取得時效與訴訟時效的態度截然不同。盡管學界普遍主張設立取得時效制度,但卻一直未被立法機關采納。在訴訟時效問題上,總則編對其效力由“勝訴權消滅主義”轉向“抗辯權發生主義”的態度值得肯定。另外,總則編明確了訴訟時效客體為請求權,并以列舉方式排除若干絕對權請求權的適用。從理論上說,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具有持續性,如果適用訴訟時效,容易導致訴訟時效不斷重復計算;而返還原物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這一問題,我國理論與實務界的主流意見采“否定說”,但我國并未如瑞士或德國民法采“否定說”或“有限肯定說”,而是借鑒我國臺灣地區較有影響力的“區別說”,其目的主要在于與物權變動規則相適應并考慮第三人信賴利益的保護,但此種創新之效果尚有待檢驗。另外,第196條對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請求權的列舉排除并不徹底。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系為維護人格圓滿狀態而設,不宜適用訴訟時效;基于倫理要求,離婚請求權、扶養請求權等基于身份關系所生請求權也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即便前者依據人格權編第995條可以被解釋為“依法不適用訴訟時效的其他請求權”,但后者卻屬于法律漏洞,因此只能根據第1001條“參照適用”第995條關于人格權請求權訴訟時效的特殊規定。
二、從《物權法》到物權編
我國的不動產物權的制度基礎是土地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這一基本國情決定物權編的立法原則與內容,尤其是有關土地物權的規定,與傳統大陸法系物權制度存在區別,某些物權主體與變動程序的特殊性也將繼續存在。與此相反,我國物權編雖繼受了大陸法系的立法技術,但并未嚴格遵循傳統大陸法系“動產-不動產”二元體系,在某些方面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
(一)物權編對《物權法》的繼受
首先,物權變動采取混合模式。從物權變動模式來看,我國《物權法》在物權變動上采取以公示要件主義為原則,以公示對抗主義為例外,兼采“合同生效”規則,此種物權變動模式過于繁雜而招致批評。雖然學界就物權變動模式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9],但均主張對物權變動模式進行統一和簡化[10]。登記對抗主義需在個案中考慮所有權人與第三人的利益平衡,因此不動產宜統一以登記作為生效要件。但物權編仍對上述物權變動模式完全繼受:公示要件主義原則,包括第209條不動產登記與第224條動產交付;公示對抗主義,包括第225條特殊動產的物權設立,第396條動產浮動抵押,第335條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互換、轉讓及第374條地役權的設立等;“合同生效”規則適用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立。上述物權變動方式未必契合土地流轉的市場化趨勢,也不能有效防止發包方隨意解除合同終止土地承包經營權。另外,對于處分行為與負擔行為的關系等關鍵問題,雖然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原因與結果的區分即為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區分[11],但物權編仍繼續采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對這些問題予以回避。
其次,平等保護與區分規定共存。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對所有權編體系結構存在“一元論”與“三分法”的爭議。“一元論”主張對所有權主體“一體承認,平等保護”,并認為“三分法”存在立法技術和立法倫理上的缺陷。[12]但更多的學者認為,“三分法”與“動產—不動產”二元劃分性質相同,只是一種法技術的處理方式[13],并不包含對物權主體價值序列上的評價[14]。因此,物權編第207條在物權主體上繼續采用國家、集體、私人的“三分法”表述方式。在物權平等保護已成為共識的前提下,繼續采用“三分法”不應被理解為對物權平等保護原則的否定,而是對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客觀存在的照應和銜接,物權編通則有必要對此作出形式上的宣示性區分。另外,物權編第五章雖以“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命名,但實質內容主要是有關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客體范圍和利用方式(程序)的特殊規定,在關系平等保護原則的物權變動與物權保護方面,二者相較于私人所有權并不存在獨立的規范體系。從現實的角度考慮,我國土地使用權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之上,如果不對國家、集體、私人所有權進行區分,他物權制度將無法設立,因此物權編繼續堅持符合制度現實的“三分法”設計值得肯定。
再次,維持城鄉二元分立格局。由于國家所有與集體所有的所有制結構,我國土地制度也呈現出城鄉二元分立格局。在土地所有權上,物權編仍然堅守城市與農村土地分屬國家與集體所有的原則,城鎮建設仍需通過征收集體所有土地來完成;在用益物權的種類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區分依然存在。由于宅基地使用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較強的福利性質,也使農村土地用益物權采取與城市土地使用權不同的取得與流轉方式;在建設用地使用權內部,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存在也使城鄉二元格局進一步分化。另外,土地制度的二元格局使農村住房與城市住房的所有權實現方式存在差異,農村住房并未完全實現商品化,因此其流轉與抵押功能受到限制。事實上,我國市場化改革始于農村,本已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將農民從集體中脫離出來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但將發展重心轉移至城市后,農村發展相對滯后,土地要素也被政府施以行政性控制,從而導致上述二元分立格局長期存在。雖然中央提出建立城鄉建設用地統一市場的改革目標,但在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出臺之前,城鄉分立格局仍然具有堅實的憲法依據和現實基礎。[15]
最后,抵押權客體兼容。在傳統大陸法系國家,由于各國動產物權與不動產物權二元結構涇渭分明,抵押權很難適用于動產,其功能由所有權保留與讓與擔保代替。《物權法》制定之后,將一般抵押權的范圍擴大至動產,便無設立讓與擔保之必要,僅需解禁流質條款以簡化動產抵押權實現程序。但抵押權客體范圍擴大至動產也會帶來一些結構問題: 動產擔保物權均著眼于自身規則,又無統一登記制度,會導致動產擔保物權規則的分散;同以登記為公示方式,動產抵押的制度便利也會使權利質權虛化。物權編繼續沿用此項做法,同時對擔保物權制度進行改造,說明了立法技術的可選擇性:通過第404條確立“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取消《物權法》第191條“抵押物轉讓須經抵押權人同意”的要求,為動產抵押適用善意取得提供可能,解決動產抵押與善意取得的銜接問題;第401條亦不再嚴格恪守流押無效原則以簡化動產抵押實現程序;通過第424條、439條、446條等準用條款的設置,簡化擔保物權的共同性規則,以消解原有的制度困境。
(二)物權編對《物權法》的創新
1.添附入典。《物權法》未規定添附制度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者認為遵循添附規則可能會導致裁判不公。但從比較法來看,各國民法典大都確立了添附制度。物權編(第322條)規定了添附之物所有權的確定方法,即依“約定”“法定”及“發揮物之效用,保護無過錯當事人”原則確定。但第322條并未按照學界所達成的共識進行規定,而是深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86條影響,僅解決了形式意義上的有無問題,制度本身仍存在較大缺憾。添附作為非基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方式,本身具有強行法的性質,其適用并不存在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因此“依約定確定”本身不能為添附制度兼容。依添附制度確定物之歸屬應為物權編的任務,“依照法律規定”又將導致該制度效用的落空。添附物之歸屬,在附合與混合情形通常應根據物之“主要成分”確定,不能確定的則歸所有權人共有;于加工之情形宜采“加工主義”為原則,“材料主義”為例外,而非以“發揮物之效用”為標準。[16]對權利人之保護,亦不宜以“過錯”為依據,而應以“善意”作為判斷原則,在有過錯但為善意情況下,仍應優先保護善意添附人利益。不過,添附在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本屬動產所有權的取得方式,我國添附制度的特色在于將添附適用范圍擴大到“物”,從而包含了不動產。
2.增設居住權和土地經營權。物權編在用益物權方面的進步,主要在于用益物權權利類型的增補,包括居住權與土地經營權。《物權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中曾對居住權進行過專章規定,但后來的《物權法》中卻沒有確立居住權制度。物權編編纂時,對居住權的設立也存在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態度。反對者認為房屋租賃及建筑物區分所有權已足以起到保障作用,將居住權引入會導致“水土不服”。[17]居住權的設立取決于我國社會情勢的變遷和特定人群的住房需求。在羅馬法中,居住權就其本質而言屬人役權,且具有無償性。物權編二審稿曾堅守這一做法,但受到學者的批評[18],因此第368條雖堅持居住權的無償性,但亦不排除當事人之間另設特約[19]。物權編居住權的設立方式,包括合同及遺囑(遺贈)設立均屬意定居住權,而對于依身份關系產生的法定居住權卻未置一詞。由于法定居住權被排除在權利體系之外,其他各編如婚姻家庭編亦難以對其進行具體規定,因配偶在繼承順位上并不具有優先性,會弱化對配偶生存利益的保護。就土地經營權而言,作為“三權分置”的政策落實和法律表達,目的在于解決承包地的流轉問題。第339條規定了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方式,應包括但不限于轉讓、入股、出租;對土地經營權的初次轉讓對象并未設身份限制,堅持經營權流轉平等性的態度值得肯定。但物權編對《土地承包法》第46條土地經營權的再流轉仍須經承包方“書面同意”這一條件并未加以改變,土地經營權之定性亦未明確。在土地經營權變動模式上,第341條采登記對抗主義,不僅有利于靈活設立土地經營權并降低成本,同時能夠提供完善的風險防范機制。
3.完善擔保物權規則。從物權編對《物權法》的變動幅度來看,除所有權與用益物權制度上“補缺”之外,主要在于擔保物權規則的變動。為落實“三權分置”的土地政策,第399條刪除了耕地性質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的規定,以配合第339條放活土地經營權;第404條將抵押動產買受人保護與動產浮動抵押脫鉤,借鑒《美國統一商法典》等域外規定而確立一般性的“正常經營買受人規則”,明確了動產抵押權與動產買受人之間的權利順位。在商事動產買賣中,不可能要求買受人對標的物上之負擔一一查詢,故上述規則也符合交易活動的經濟規律與動產抵押善意取得的基本原理。在抵押權追及效力問題上,物權編刪除了《物權法》第191條“抵押權人同意”規則。但有觀點認為,第406條在承認抵押權追及效力的情況下,會與第404條“正常經營規則”發生沖突,從而造成體系違和。事實上,由“經營活動”的條件限制可以看出,第404條適用范圍應限于商事領域,解釋論上抵押權追及效力對于普通民事交易仍有約束余地。另外,第415條明確了抵押權與質權的清償順序,按照登記與交付時間先后判斷,值得肯定。但第415條卻忽視了擔保物權人的善意因素對擔保物權優先效力的影響:先抵后質及同時抵押、質押之情形,動產抵押登記僅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惡意第三人仍應受未登記之在先抵押權的約束;先質后抵之情形,質權人未經出質人同意將質物抵押給第三人,第三人應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優于質權的抵押權。除此之外,擔保物權變動最大的內容是第416條借鑒《美國統一商法典》新設的“超級優先權”,其直接對傳統擔保物權順位構成沖擊,學界對此持謹慎態度。[20]但我國不存在所有權保留登記制度,在企業設定浮動抵押權后,企業的投資人對價金設定的所有權保留作為無公示擔保物權將劣后于該浮動抵押權,此時企業找不到辦法設定一項優于該浮動抵押權的擔保物權,其融資渠道將會消失。因此,“超級優先權”的設立,能夠解決同為價金擔保物權的所有權保留所不能解決的融資問題。
三、從《合同法》到合同編
雖然在編纂過程中條文數量被不斷壓縮,但合同編的條文數量仍然保持在民法典條文總數的一半左右。合同編的守成主要表現在,在堅持民商合一理念的前提下,對合同效力規則與原有典型合同類型予以保留;合同編的創新則在于為承擔債法功能和適應經濟發展所做的調整。
(一)合同編對《合同法》的吸收
合同編立法必須注意與民法總則及其他各編內容上的協調,因此《合同法》中“合同的效力”一章的許多內容將被《民法總則》吸收,合同編通則立法也就面臨兩難問題:或刪繁就簡以滿足體系的抽象性,或保留內容以維持總則的周延性。[21]編纂過程中,有學者提出刪除第三章以避免規范重復。[22]但我國并不存在嚴格按照《德國民法典》進行高度抽象的立法傳統,如果將合同效力完全交由《民法總則》第六章解決,在缺乏債法總則的情況下既無法實現抽象的層次化,又破壞了總則規制合同發生過程的完整性。因此,合同編保留了“合同的效力”一章,但同時卻未對第三人利益合同、無權處分、未生效合同、合同聯立等《民法總則》第六章未涉及的問題進行回應。
除通則部分外,分則合同類型部分對《合同法》的繼受同樣明顯。合同編對《合同法》典型合同類型全部繼受,且仍未遵循大陸法系“有償-無償”的立法思路,而是繼續以有償合同為規制重點。合同類型仍按照標的轉移型、加工定做型、服務提供型及技術合同的思路進行劃分。在內容上繼續將買賣合同標的限制在實物買賣;仍然拒絕規定除借款合同外的消費借貸合同與使用借貸合同;相較于承攬合同,對建設工程合同及運輸合同進行單章規定;第十章“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第十七章“承攬合同”、第二十二章“倉儲合同”、第二十五章“行紀合同”幾乎完全繼受自《合同法》相應章節的內容。在體例上,合同編也繼續堅持民商合一理念,如第501條保密義務仍然保留了《合同法》第43條中的“商業秘密”;繼續納入行紀、保理等商事合同;保證合同仍未區分民事與商事保證,而將未約定或約定不明時的保證方式統一規定為一般保證。
(二)合同編對《合同法》的調整
第一,債法總則的賦能。合同與侵權責任獨立成編之后,形式意義上的債法總則不復存在,合同編以《合同法》總則為基礎進行結構調整和規范添補,以使其實質上發揮債法總則的功能:合同編采納了立法過程中的學者建議,借鑒《歐洲合同法原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等經驗,將選擇之債、按份之債、連帶之債等納入其中,以補強缺失的債法總則領域內“債的種類”及“多數人之債”的規定;另外,通過合同的適用范圍(第464條第2款)、非典型合同的適用(第467條)及非合同之債的適用(第468條)三個層次準用規范設計,來滿足取消債法總則所帶來的規范配置方面的要求。
第二,典型合同的增添。相較《合同法》,合同編新增了四類典型合同,分別是保證合同、物業服務合同、保理合同和合伙合同。保證合同在《合同法》起草過程中曾被列入,之后又被刪除,擔保物權歸入物權編后,定金與保證合同納入民法典便成為必然選擇。但保證合同的調整范圍僅限于作為從合同的保證合同,并采納學界意見吸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獨立保函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規范獨立保證。對物業服務合同的規定,則主要是為了彌補《物業管理條例》之不足,從私法層面進行權利設計,其修改了《物業管理條例》中僅允許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服務的單一模式,進一步明確物業服務人的信息公布義務,并規范業主單方解除權的行使。保理合同則為拓寬融資渠道而設[23],主要參照《國際保理通則》《保理示范法》,并吸收了《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關于審理前海自貿區保理合同糾紛案件的裁判指引》等規范。就合伙合同而言,域外民法典多在合同類型中設有合伙合同,其雖在《合同法》征求意見稿中出現過,但因《合伙企業法》的制定被刪除。根據合伙的雙重屬性,有必要對合伙企業與合伙合同分而置之。[24]
第三,制度缺失的填補。《合同編》吸收了司法解釋的若干規定,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預約合同、懸賞廣告、情勢變更等制度,以彌補相關法律規則的缺失。在合同編之前,我國通過司法解釋已承認預約合同的效力,但因僅限于買賣合同解釋而無法普遍適用。從比較法而言,立法對預約保持沉默是較為常見的做法[25],但合同編將其提升至“合同的訂立”一章,以第495條規定填補相關規則的缺失。而對于懸賞廣告的規定,首見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3條,但其并未消弭理論上對于懸賞廣告性質屬于合同抑或單方行為的爭議,從第499條的表述來看,更傾向于承認原本缺失的單方允諾制度。對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規定的情勢變更制度,合同編一審稿最初進行規定時將不可抗力作為情勢變更的條件,事實上混淆了不可抗力與情勢變更的適用范圍,其后第533條根據學界意見進行了區分處理。[26]
第四,具體規則的完善。合同編對具體規則的完善,主要集中于合同的履行。第514條至521條規定了金錢之債履行貨幣的確定、選擇之債的選擇權移屬制度及選擇不能、連帶債權的內部關系及連帶債務的涉他效力等規則,彌補了《合同法》的漏洞;第522條確立了真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明確承認了第三人的履行請求權和違約責任請求權。另外,在合同保全領域,第552條確立了債務加入規則。有學者認為,該條款遺漏了債權人與第三人達成債務承擔協議的情形,且此種情況下應賦予債務人異議權。[27]但筆者認為,債權人與第三人達成協議后,債務人若窮盡手段仍無履行能力而提出異議,實屬異議權濫用;若有履行能力則只需債務到期積極履行,便可阻止第三人享有追償權,因此實無異議權設置之必要。
四、從人格賦權到人格權編
人格權編以六章內容形成人格權權利類型基本結構,對人格權主體、保護模式及權利體系作出規定,其中人格權主體與權利類型劃分方面呈現出更多的保留,而進步主要體現在權利保護模式與具體權利體系方面。
(一)人格權編的守成
一方面,人格權編的守成體現在有關人格權主體的規范上。人格權編第一章“一般規定”及第五章“名譽權和榮譽權”中,凡涉及人格權主體的規范均表述為“民事主體”,而第二章“生命健康權”、第三章中的姓名權、第四章“肖像權”、第六章“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的主體被限定為自然人,第三章中名稱權則專屬于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盡管有學者認為,法人的人格權無精神利益,其實質為財產權[28],但法人享有某些人格權已成為我國主流學說。《民法通則》第99、101、102條均承認法人人格權,因此人格權編關于權利主體的區分規定也符合我國民事立法的一貫立場。
另一方面,在人格權類型體系方面,人格權編相較于《民法通則》中的人格權類型并無重大突破。就人格權類型劃分來看,國內主要有以下代表性學說:(1)將人格權劃分為物質性人格權與精神性人格權,精神性人格權又被分為標表型人格權、自由型人格權和尊嚴型人格權[29](P142-158);(2)保障自然人自然存在的人格權與保障自然人社會存在的人格權[30](P315);(3)人身完整、人格標識、人格尊嚴與人格自由[31](P93);(4)人格內在要素與人格外在要素,前者又可劃分為安全、自由、尊嚴三個方面[32]。因此,人格權編總體上雖遵循“同類聚合”的立法思路,在第二章、第三章及第五章中對同類具體人格權進行統合,但仍有商榷余地。另外,對于榮譽權的性質究竟為人格權、身份權,抑或并非獨立的權利,學界一直存在爭議。[33]人格權編與《民法通則》所持立場相同,將榮譽權作為獨立的權利加以規定。但人格權應為人的自然生產與社會生存所必需的權利,而榮譽權由公權力授予,并非私主體所必須;榮譽需具有一定范圍的公開性,榮譽感亦不過是基于外部評價而產生的心理上的滿足。因此,域外國家通常將榮譽納入名譽權項下,而非作為獨立的民事權利。
(二)人格權編的進步
首先,人格權編突破了原有人格權保護規范分類列舉的保護方式,構建了“從具體到一般”的人格權保護模式。在民法層面,具有代表性的人格權的保護模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法國基于自然權利觀的概括保護模式,雖不在法定意義上規定人格權,但卻要維護更高的人格,通過概括性的侵權條款實現。其二是德國基于法定權利觀的列舉保護模式,通過列舉方式設置若干人格權類型并予以侵權法保護。[34](P266-268)我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所構建的人格權保護模式同樣為列舉保護模式。雖然德國法學界又創設了人格權保護的一般條款,但需以突破人格權法乃至私法范疇為前提。人格權編在私法層面構建了“從具體到一般”的人格權保護模式,在組織體人格權采法定主義原則的同時,承認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所發展的其他人格權,較好地實現了人格權的周延保護與人格利益之平衡。
其次,人格權編豐富了人格權權利體系,擴大了人格權的具體保護范圍。我國民事單行法所創設的人格權權利體系,并不包含傳統人格權中的隱私權和身體權,雖然《侵權責任法》第2條曾將隱私權納入保護范圍,但嚴格來說其并非設權性規范,人格權編對隱私權的正面確認應屬首次。而基于傳統倫理觀念,身體一直被確定為消極利益而非積極權利,因此相較于通過《侵權責任法》“升格”的隱私權,身體權卻一直以人格法益的形式存在。現代倫理觀念的轉變和身體支配屬性的顯化,要求人格權編對身體利益的規范由消極防御轉向積極賦能,身體權納入人格權體系亦順理成章。但人格權編將榮譽作為獨立的人格要素進行賦權卻殊有爭議。榮譽系公權力授予,人格權編第1031條對于榮譽侵害方式,其中剝奪與記載錯誤以及對應的救濟途徑,如恢復榮譽與更正,應屬行政法調整范疇,私法未必可以作為公法行為變更的依據;而詆毀、貶損實屬社會評價的降低,應屬于名譽權的射程范圍。
再次,人格權編的亮點之一在于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學界對于個人信息的性質,存在“法益說”[35]、“財產權說”[36]、“人格權說”[37]與“公法權利說”[38]。從民法典規范來看,雖然第111條的位置處于列舉的人格權與人身權利之間,但個人信息卻始終未被冠以權利之名,依體系解釋方法認定對其享有人格法益更為恰當。基于個人信息的可利用性與財產價值,人格權編將其與隱私權而非姓名權、肖像權等標表型人格權合并規定的做法也有待深論。
最后,人格權編完善了具體的人格權保護規范,增強法律規則的可操作性。以健康權為例,第1004條明確了健康權的內容,包括生理健康與心理健康;第1005條則規定了救助義務,但第1005條“法定救助義務”本應屬公法范疇,是否會造成規范重復尚存疑義[33](P9);另從肖像權來看,第1018條第2款充分揭示了肖像權“可識別性”“外部形象”等特征,第1019條與1020條從消極權能與積極利用兩方面對肖像權進行周延保護。通過第1023條準用條款的設置,將對外部符號保護由肖像延伸至姓名與聲音,形成較為完善的人格標識保護規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格權編第996條首次承認的違約精神損害賠償,將精神損害納入違約損害賠償范圍,是對損害賠償制度的一大突破。但本條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違約損害賠償制度在體系上應被納入合同編的違約責任部分而非規定在人格權編;“人格權”的條件限制使其適用范圍過于狹窄,應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擴張。
五、從《婚姻法》到婚姻家庭編
傳統大陸法系中,婚姻關系一直都是民法調整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薩維尼提出的法律關系學說更奠定了包括親屬法在內的潘德克頓五編制結構。但我國受“婚姻并非契約”理念及《蘇俄民法典》的影響,自1950年起便形成親屬法單獨立法的格局。本次民法典的制定,在形式上實現了親屬法的回歸,婚姻家庭編的內容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優化。但基于歷史和政策原因,本編較其他各編而言仍帶有更多的單行法色彩。
(一)立法風格的延續
婚姻家庭編對蘇聯民法觀念清除得并不徹底,在立法技術和內容上繼續以婚姻及其延伸關系為規制重心。在婚姻家庭編制定過程中,“婚姻法”之名已不合時宜。在繼受蘇聯民法之前,我國一直沿用調整范圍更廣的大陸法系“親屬編”稱謂,故有觀點認為改稱“親屬”為宜。[39]但根據學界主流意見,“婚姻家庭”足以反映本編調整對象。①[40]基于“婚姻家庭立法的傳承性與連續性”[41]的要求,以及我國民眾的理解程度,稱“婚姻家庭編”較為合適。在調整范圍上,婚姻家庭編拒絕規定事實婚姻、同居關系等類家庭關系;基于時間順序,沿用了“結婚-家庭關系-離婚”這一以婚姻為中心的立法結構,使家庭關系淪為婚姻關系之附庸,與以親子及親屬制度為規制重點的立法趨勢相悖;而“收養”作為擬制血親,卻被簡單地置于婚姻家庭編最后一章,導致其與“家庭關系”割裂開來,法律匯編痕跡明顯。除此之外,上述按照婚姻狀態變化進行章節劃分的立法技術也對本編內容產生了溢出效應。一方面,婚姻家庭編僅規定了親子關系和親權(第1058條、第1068條),但卻未規定監護。《民法通則》之所以在主體部分規定監護制度,是為了彌補《婚姻法》不包含監護制度的立法漏洞。但在婚姻家庭編對親子關系進行規定后,總則編繼續采用廣義監護制度不僅會造成內容分離,而且會造成規范重復(第26條)。另一方面,我國習慣以“代”作為劃分親等的計算方法,但按照學界意見較之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方法不甚合理。[42]由于婚姻家庭編立足于婚姻關系的狀態,而非整體上的親屬制度,因此在“一般規定”中也并未按照上述意見規定親等的有關內容。除婚姻、家庭及收養關系的法律原則外,只有第1045條作為親屬制度的共同性規則,吸收了相關司法解釋,將配偶和二等直系及旁系血親納入近親屬范圍。
(二)婚姻規則的改良
1.穩定婚姻家庭關系,強化家庭保障功能。現代親屬法立法理念已逐漸由“家庭主義”轉向“個人主義”,具體表現為國家放松了對婚姻家庭關系的介入,而給予個人更多的行為自由。但這一趨勢在婚姻家庭編中表現得并不明顯,反而出現了通過規范加強“再家庭化”的趨勢。第1043條首次以倡導性規范規定家庭美德與優良家風,以回應中央加強家庭文明建設的精神;第1047條順應國家政策也刪除了鼓勵晚婚晚育的規定。上述政策體現在制度上,主要在于離婚間隔期限的延長。第1077條為解決我國登記離婚程序過于簡略、離婚率較高的問題,增設30日離婚冷靜期,但第1077條應明確離婚冷靜期僅適用于協議離婚,并就家暴、虐待、遺棄等情形設置除外規定;第1079條則明確規定應當準予離婚的前提條件為“分居滿一年”,變相延長了《民事訴訟法》第124條第7項中六個月內不予受理的間隔期限。延長離婚期限的制度初衷,在于穩定婚姻家庭關系,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但離婚率較高的社會因素非常復雜,恐難僅憑民法上微觀的權利制度取得離婚率降低的宏觀效果;人為地延長離婚期限,明顯存在“法律家父主義”思維傾向,不僅有違反離婚自由的嫌疑,更難以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除此之外,婚姻家庭編也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家庭的社會保障功能。通過擴張撫養費的給付范圍(第1071條)、對提供幫助方設置限制性條件(第1090條)以及增加收養人數(第1098條),進而發揮家庭的“社會穩定器”功能。
2.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婚姻家庭編在未成年人利益保護方面確認了兩項原則:一是第1058條確認的共同親權原則,夫妻雙方對未成年子女平等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二是第1084條規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則,撫養權的歸屬應當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子女八周歲之后應當尊重其真實意愿。第1041條、第1093條分別將《婚姻法》保護的主體范圍與收養對象由兒童改為未成年人,保護主體更加明確;第1044條調整了有利于被收養人原則,增加“禁止以收養名義買賣未成年人”;第1102條被收養人的保護也不再限于女性。上述措施加強了對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護力度,符合“親子中心主義”的立法趨勢。[43]
3.財產分配與債務負擔更加公平合理。婚姻家庭編仍然實行婚后共同所得制為法定財產制,第1062條在規定方式上延續《婚姻法》第17條“概括-列舉”方式,增加了勞務報酬及投資收益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在夫妻共同債務方面,我國最初采取基于“共同生活”的推定規則,但所列舉的兩種除外情形往往難以得到證明:第三人在借款時往往不愿意約定為個人債務;而我國又不存在夫妻財產登記制度,要求配偶證明第三人知情顯然強人所難。因此第1064條吸收了實踐經驗,規定“共債共簽”“事后追認”以及家庭日常生活所負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第1066條離婚財產分割也刪除了“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表述,不再以優先保護債權人利益作為夫妻共同債務的處理原則。另外,婚姻家庭編在財產分配上更加注重保護無過錯方利益。第1054條增加了婚姻效力瑕疵情形下無過錯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第1087條離婚財產分割也明確了照顧無過錯方權益原則。
4.塑造與保障身份權利。其一是保證婚姻的自我決定權利。第1051條規定“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之情形,婚姻效力由無效改為可撤銷,同時確立關于重大疾病的告知義務,是否通過撤銷之訴否認婚姻效力由當事人自主決定;第1069條擴大了子女不得干涉父母的婚姻范圍,以保證父母離婚自由。其二是新增家事代理權。第1060條肯定了夫妻一方實施家事代理行為的效力,符合善意第三人對家事行為的信賴預期。其三是補充確認親子關系的權利。第1073條允許當事人有異議時向人民法院請求確認親子關系,彌補了《婚姻法》規定之不足,有利于化解糾紛和明確親子權益。
六、從《繼承法》到繼承編
在制定民法典所依據的各單行法中,《繼承法》 及其司法解釋頒布時間最早且至今未經過修訂,這固然體現了我國《繼承法》“運行良好”[1](P402),但并不意味著無需改進。為適應社會變化情況,繼承編一方面考慮了原有的繼承習慣,另一方面也對繼承規則進行適當修正。
(一)繼承順位的固守
繼承編對《繼承法》的保留主要體現于法定繼承制度。在繼承編制定過程中,對法定繼承順序存在較大爭議。《繼承法》中法定繼承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其一,法定繼承人范圍過于狹窄,排除了子女以外的直系血親及兄弟姐妹的子女,不利于遺產的傳承和充分利用;其二,配偶的順序被固定在第一順位,區別于國外立法例中配偶不設固定順位而與不同順位繼承人一同繼承的做法,可能導致子女以外的直系血親難以分得遺產;其三,《繼承法》將父母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的做法也有待商榷,容易導致遺產經父母繼承后流向旁系血親,而使家庭內部成員少分遺產;其四,喪偶女兒、喪偶女婿即使盡了贍養義務,其作為第一順位法定繼承人也不符合繼承慣例;其五,《繼承法》中代位繼承采“代表權說”而非“固有權說”,導致當繼承人喪失繼承權時,其子女難以通過代位繼承獲得遺產。在上述問題中,繼承編通過對代位繼承制度進行修正,將子女以外的直系血親及兄弟姐妹的子女納入法定繼承范圍(第1128條),也承認了代位繼承人系基于自身權利代位繼承(第1152條)。善盡贍養義務的喪偶女兒、喪偶女婿作為法定繼承人雖與各國通例不符,但卻較為符合我國的社會習俗和繼承習慣,因此被繼承編保留也無可厚非。對于法定繼承順位問題,盡管學界普遍主張修改,但繼承編仍然沿襲《繼承法》之規定。
(二)繼承規范的補益
繼承編對《繼承法》的修正主要集中于遺囑繼承制度和遺產處理兩個方面。對遺囑繼承制度修正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擴大本人意思自治,盡量尊重被繼承人的意愿,其具體內容包括:首先,擴張寬宥制度范圍。第1125條新設寬宥制度,將原有可以得到寬宥的范圍擴大至“偽造、篡改、隱匿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及“欺詐、脅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礙被繼承人設立、變更或者撤回遺囑,情節嚴重”的情況。另外,在第1125條故意殺害被繼承人或殺害其他繼承人的行為中,犯罪中止符合“確有悔改表現”的限制性條件,故也可在未來考慮將上述兩種行為的犯罪中止情況納入寬宥制度范圍。[44]其次,優化遺囑方式和效力。通過增加遺囑信托的遺產處分方式(第1133條)、錄像遺囑(第1137條)、遺囑撤回擬制條款(第1142條),并廢除公證遺囑的優先效力,以實現被繼承人意思自治范圍與形式的擴張。遺產處理規則的優化目的在于充分利用遺產: 為做到權利義務相對應,第1144條限縮了未履行所附義務情形下取消接受遺產的范圍;第1160條將收歸國有遺產用途限定在公益事業。最后,繼承編對遺產處理的重要突破是設置遺產管理人制度,對遺產管理人的產生、指定、職責、民事責任及報酬請求權均作出詳細規定。
七、從《侵權責任法》到侵權責任編
侵權責任編的內容在各編中變動較大,這與侵權法本身的目標價值相關。侵權法的基本價值在于協調自由與安全的緊張關系,但自由與安全之間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保持動態平衡,侵權責任編所有制度與規則的變動均圍繞這一目標展開。
(一)侵權編對《侵權責任法》的繼受
侵權責任編在數人侵權規則與飼養動物損害責任方面基本保留了《侵權責任法》的內容。在動物飼養責任中,主要變動在于第1246條中補充了動物飼養人、管理人侵權責任減輕情形。學界爭議主要在于數人侵權規則。對此,我國采德國模式,對要件及法律后果均作出規定。第1170條共同危險行為仍未按照學界意見,允許行為人通過證明其行為與損害結果無因果關系而免責。[45]對第1172條“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責任承擔方式,筆者認為仍應堅守按份責任的觀點。②[46]正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直接結合”與“間接結合”難以確定,因此才有了共同侵權行為與第1172條的區分。在平均責任兜底的情況下,如果行為人認為承擔份額過高,也將具有更大的積極性通過舉證來減輕責任,從而有利于查清事實。
(二)侵權責任編對《侵權責任法》的優化
1.債法屬性的回歸。立足于“大侵權”模式,《侵權責任法》第二章規定的“責任構成與責任承擔”,尚屬廣義的賠償法理念。民法典制定之初,就有觀點認為應借鑒德國、奧地利立法經驗建立完整的損害賠償體系。[47]由于我國不存在債法總則編,因此并未就損害賠償的共性規則作出規定,違約與侵權損害賠償規則亦被分而置之,但立法理念已開始轉向狹義的賠償法理念。《民法典》通過第118條將侵權行為規定為債權的發生原因,淡化了侵權之債與侵權責任的區分。侵權責任編最終回歸英美法系的債法救濟模式,將承擔侵權責任的基本方式確定為損害賠償。盡管第1167條保留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三種預防性侵權責任,但僅作為損害賠償的補充,無法構成對其債法性質的挑戰。
2.歸責原則的明確。侵權責任編通過第1165條與1166條消弭了學界對于歸責原則的爭議。學界對《侵權責任法》中的歸責原則存在三種看法:其一認為侵權法本身堅持過錯與無過錯的二元歸責原則;其二認為侵權法歸責原則為過錯、無過錯和過錯推定原則;其三認為侵權法以過錯和無過錯為原則,公平責任為補充,嚴格責任為例外。[48]但過錯推定屬于過錯原則中對證明責任的特殊規定,并非獨立的歸責原則;侵權法對歸責原則的規定應置于責任承擔方式之前,而非損害賠償之后。公平責任的性質屬于損失分擔方式而非歸責原則,適用范圍也過于狹窄;傳統大陸法系所堅持的二元歸責原則也能夠實現對歸責原則的周延劃分。
3.抗辯事由的補正。《侵權責任法》在第三章規定了六類免責或減責事由,但抗辯事由規定并不全面,自助行為、受害人自甘風險、依法行使權利等典型抗辯事由均未予以規定。侵權責任編第1176條與1177條新增了自甘風險與自助行為作為抗辯事由,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侵權責任編并未規定執行公務、行使權利與受害人同意三類免責事由;而自助行為則應納入到總則編中,而非僅作為侵權行為的免責事由進行規定。
4.特殊侵權規則的完善。首先侵權責任編增加了有關責任人對第三人追償權的規定,包括第1191條用人單位向工作人員追償;第1192條接受勞務一方向提供勞務及第三人追償;第1198條經營者、管理者或組織者向第三人追償以及第1201條教育機構向第三人追償。其次補充了一些各侵權領域的典型規則,如網絡侵權中的反通知規則(第1196條)、機動車交通事故侵權中的好意同乘規則(第1217條)、生態環境侵權人的修復義務(第1234條)以及高空拋物中國家機關的調查義務、管理人的安全保障義務(第1254條)等。
總之,民法典頒布后,我國將進入后法典時代,民法學界的主要任務也將由立法論逐漸轉向條文適用研究。雖然眾多單行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終將退出歷史舞臺,但其對我國民法思維的塑造和權利意識的啟蒙意義重大,民法典及其配套的司法解釋實施之前,這些民事立法仍然不失其價值。在潘德克頓法學觀念的深刻影響下,我國所持法律政策,雖不免大量擷取歐陸立法例,但對民商合一體例、物權主體三分等契合中國社會現實的法律制度,仍應“保持成法而不失墜”;對保護人格權利、增強交易預期等順應世界潮流的立法資源,亦應“與時俱進以致其新”。無論如何,本次法典編纂未再系統照搬他國經驗,對各編所進行的改造,相當程度系基于我國實踐所得,其實用主義的立法態度值得肯定。本次民法典得以順利通過,亦將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進步之佐證。
注釋:
①在王利明及徐國棟主編的民法典草案中,均稱“婚姻家庭編”。
②張新寶認為應按照域外立法例采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