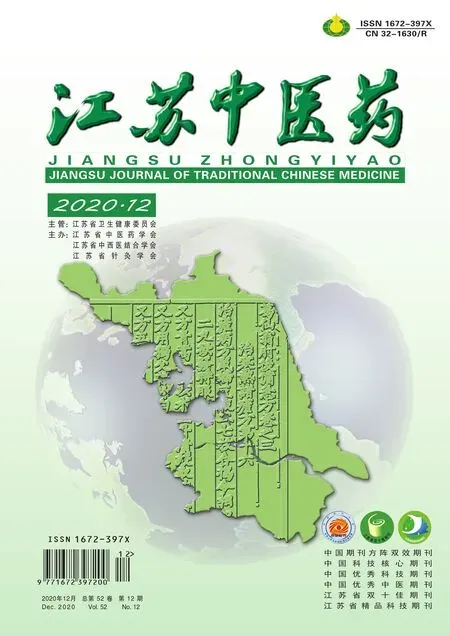黃慶田以肺系整體觀念指導哮喘診療的經驗
張 磊
(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濟南250355)
指導:黃慶田
支氣管哮喘屬中醫學“哮病”范疇,其病位在肺。而以肺為核心的肺系還包括鼻、咽喉、皮毛、大腸等,都和哮喘的發生發展有密切關系,對哮喘的診斷和治療有重要意義。整體觀念是中醫學的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強調人體自身的統一性和完整性,同時又認識到人和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環境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且不可分割的整體。
吾師黃慶田主任醫師是山東省名中醫藥專家,善于以肺系整體觀念指導支氣管哮喘的診斷和治療,現總結如下。
1 鼻為肺之竅,治哮應肺鼻同治
鼻為肺之外竅,鼻生理功能的正常,有賴于肺氣的和暢。《嚴氏濟生方·鼻門》在分析鼻塞流涕諸癥的原因時曰:“此皆肺臟不調,邪氣蘊結于鼻,清道壅塞而然也。”可見,鼻病的成因主要是肺臟功能失調所致,鼻部癥狀與肺的功能狀態密切相關。黃師認為,哮喘患者如見噴嚏、鼻塞、鼻癢、流涕等癥狀,不論是否出現喉中哮鳴,均提示肺臟受邪,進一步發展可致肺氣上逆而咳喘。同時,可根據鼻涕之清濁、鼻腔黏膜之色澤來辨別哮喘證之寒熱。
現代醫學提出了“同一氣道、同一疾病”的觀點[1],認為慢性鼻-鼻竇炎和支氣管哮喘有非常密切的關系[2]。研究表明,46%以上的過敏性鼻炎患者伴發支氣管哮喘[3],約80%的哮喘患者并發過敏性鼻炎,約20%的慢性鼻-鼻竇炎患者并發哮喘[4]。同時,慢性鼻-鼻竇炎伴支氣管哮喘患者,經過積極干預鼻部疾病,可明顯改善患者支氣管哮喘癥狀[5]。可見,使鼻竅通暢也是控制哮喘的重要手段。因此,黃師在哮喘的治療過程中,重視“肺鼻同治”[6],適當選用細辛、辛夷、蒼耳子、藿香等藥物以宣通鼻竅。挾風配伍荊芥、防風;熱象明顯酌加桑白皮、黃芩、龍膽草、石膏等清熱瀉火之品。
2 咽喉為肺胃之門戶,平喘當通利咽喉
《靈樞·憂恚無言》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可見,咽喉上連口鼻,下通肺胃,主司飲食、呼吸和發聲。分而言之,喉為肺之系,又為肺之門戶;咽為胃之系,又為胃之門戶。合而言之,哮喘發作可伴隨咽癢、咽干、咽痛、咽部異物感、頻繁清嗓、聲音嘶啞等咽喉部位癥狀,這主要是外邪侵襲咽喉,痰阻氣道,肺氣不利所致。
臨證中,黃師指出哮喘患者雖咽喉部位癥狀明顯,但其局部黏膜色澤多蒼白而潤,熱象不顯,少數患者可見黏膜紅腫,多為胃火內熾之象。針對咽喉不利這一重要病機,哮喘發作時,在宣肺平喘、降氣化痰的基礎上要適當選用射干、僵蠶、薄荷、牛蒡子等以通利咽喉。若熱象顯著,則伍以石膏、大黃等清熱瀉火利咽,如果熱象不顯,不可因其咽干、咽痛而擅用寒涼。
3 皮毛為肺之合,祛邪首重解表
《素問·六節藏象論》曰:“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可見,肺與皮毛在生理上關系密切。現代醫學從胚胎學角度認為,皮膚和肺都是由外胚層發育而來,皮膚發展為復層扁平上皮,而肺則發展為單層扁平上皮,肺內4億個肺泡好像是體表皮膚向體內凹陷的部分,以此來完成氣體的交換以及熱量和水分的散發[7]。這和中醫學對肺和皮毛關系的認識契合。
《素問·咳論》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類經·十五卷·傷寒》曰:“寒之中人,必先皮毛,皮毛者肺之合,故在外則有寒栗鼻塞等證,在內則有喘咳短氣等證。”可見,肺和皮毛在病理上相互影響,皮毛是外邪侵襲,誘發肺系疾病的重要途徑,而哮喘的發作亦和外邪襲表關系密切。
因此,黃師在哮喘的治療中尤其重視“肺病治皮”的理念[8]。急性發作期,注重解表劑的應用,方選麻黃湯、小青龍湯等,使邪氣從表而解,則哮喘得平;慢性持續期,重視補肺氣以實衛表,同時配伍少量祛風散邪之品,方選玉屏風散加減,以預防哮喘反復發作。
4 肺與大腸相表里,急危不忘攻下
《靈樞·本輸》曰:“肺合大腸”,認為肺與大腸通過經脈的互相絡屬而構成表里關系。而從現代醫學胚胎發育的角度看,肺、氣管與腸的結構來源是相同的[9],這也為“肺與大腸相表里”提供了現代醫學的依據。肺與大腸不僅在生理上相互依存,在病理上也相互影響,《靈樞·四時氣》曰:“腹中常鳴,氣上沖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可見,若大腸腑氣不通,則可影響肺之宣發肅降,而產生胸滿、喘息等癥狀。《讀醫隨筆·卷三·論喘》曰:“大便久秘,腸中濁氣上蒸于肺,以致升降不利,呼吸短促”,認為大便秘結可以誘發和加重哮喘發作癥狀。當然,肺腸同病時,并非僅表現為便秘,亦有表現為泄瀉者,如《黃帝內經素問集注·痹論》曰:“大腸為肺之腑而主大便,邪痹于大腸,故上則為氣喘爭。”
黃師鑒于肺與大腸在生理和病理上的密切聯系,臨證中,針對哮喘合并大便異常的患者,重視肺腸同治,便秘者配伍行氣導滯之枳實、厚樸、萊菔子、檳榔、大黃等,腑氣通則肺氣平復。特別是對于哮喘發作之急危重癥而伴大便秘結者,急用大承氣湯口服或灌腸,可收立竿見影之功效。而伴泄瀉者,新發以祛邪化滯為法,久病者重視健脾固腸。
5 典型病案
吳某某,女,71歲。2019年11月27日初診。
主訴:反復咳喘30余年,加重6 d。近30年反復發作咳嗽、喘息,伴哮鳴,受涼和刺激性氣味可誘發。初起多于秋冬季發作,近10年無明顯季節性。近5年吸入布地奈德福莫特羅,320 μg/次,每日2次。平素能緩慢步行。6 d前患者受涼后出現咳嗽、哮鳴,咳白色泡沫痰,夜間較重,不能平臥,惡寒輕,無發熱。近3 d在當地衛生室靜脈滴注阿奇霉素、地塞米松等藥物,癥狀不減。今晨患者喘憋加重,嘔吐,伴煩躁、譫語,急診轉入我科。患者形體肥胖、面紅唇紫,腹部膨隆,神昏、譫語,喘息、哮鳴,全身汗出,大便7 d未行。舌質紅、苔黃燥,脈滑數。診斷為哮病(陽明腑實證)。患者病情急危,宗大承氣湯意,急予芒硝30 g,于500 mL溫水中溶解灌腸,排出硬糞球約10余枚,后排出軟便若干,患者喘憋逐漸減輕,神志轉清。后經中西藥物治療10 d,好轉出院。
按語:本案為老年女性患者,哮喘病史較長。此次急性發作,初則因外感風寒之邪,擾動痰飲之宿根,痰阻氣道而喘;后則因風寒入里化熱,引起陽明腑實證,熱擾神明則神昏、譫語,氣機不暢則喘憋進一步加重。《靈樞·病本》曰:“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因此急當通腑泄熱,熱去則神清,腑通則氣機通暢而喘平。本案通腑泄熱法治療哮喘急危重癥,充分體現了肺系整體觀念對哮喘診療的指導意義。當然,臨證中不可僅僅拘泥于局部之肺系整體觀念,還要重視人體之整體性以及自然界和社會環境對人體的影響,才能更全面地指導哮喘診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