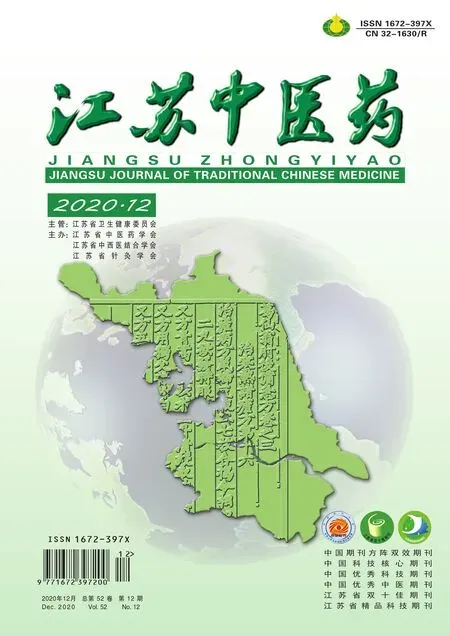從“疫邪”致病特點淺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恢復期的調 治 要 點
施榮偉 谷 雨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南京21002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于2019年末暴發,至今尚未完全控制,嚴重威脅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同時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預防及治療新冠肺炎的西醫特效藥物。中醫藥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中指出,要在醫療救治工作中積極發揮中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結合,促進醫療救治以取得良好效果。目前,國內的疫情早已獲得有效的控制,前期有大量患者經過積極治療后痊愈出院,但其中仍有部分人群伴有長期的臟器功能損傷,或乏力、睡眠障礙及其他精神癥狀。因此,對新冠肺炎患者恢復期的調治以及痊愈后的遠期康復治療顯得尤為重要。
1 強調恢復肺脾功能
新冠肺炎初起以發熱為主癥,具有廣泛流行性及傳染性。《素問·刺法論》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當屬“溫疫”范疇。吳又可所著《溫疫論》是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一部瘟疫學專著,書中對“疫邪”發病的病機及臨證論治做了詳細的闡述。吳氏認為,疫邪多起病于上焦,直犯于脾,即“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于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手冊》[2]闡釋本病病機為“疫毒外侵,肺經受邪,正氣虧虛”,病性為“濕、熱、毒、虛、瘀”,肺為首當其沖的受邪臟腑;患者肺氣大傷,后期肺氣虧虛難復,不能貫通心脈而通達周身,則見氣短乏力,故補益肺氣乃本病瘥后調治重點。同時“疫邪”可直犯于脾,脾胃運化失司,中焦阻滯,危重期可見腹痛、吐瀉,而病后恢復期由于穢毒之邪久居中焦,脾胃功能難復,則出現納呆、痞滿、便溏不爽等癥,此時當重點調治脾胃,宜用健脾和胃之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亦強調恢復期對于肺脾氣虛證的治療,正如《難經·十四難》中云:“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脾者,調其飲食……此治損之法也。”根據疫邪病理性質的不同,病后調治措施也當有所側重。肺為嬌臟,喜潤惡燥,清虛而處高位,不耐寒熱,熱毒疫邪最易耗氣傷陰,氣虛則宣降失職,陰虛則不能清潤,導致肺氣上逆,發為咳喘。甘潤可使肺氣自降,清肅之令得行,因此恢復期可予補肺湯益氣固表、沙參麥冬湯益氣養陰等,藥物多用沙參、麥冬、西洋參、蘆根等甘潤之品,平素飲食宜忌辛辣刺激,可予銀耳、百合、蓮藕、杏仁等熬粥或燉梨湯、鴨肉湯等以滋養肺陰。如感受濕毒疫邪,濕困中焦,脾失運化,恢復期可予參苓白術散、六君子湯等平補中焦,并清淡飲食為主,防止過食肥甘厚膩以滋膩礙胃,平時可進食山藥、薏苡仁、茯苓、芡實等藥膳以健脾益氣祛濕。
2 重視調養臟腑氣血
吳氏《溫疫論》謂:“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繼而傷血,繼而傷肉,繼而傷筋,繼而傷骨。邪毒既退,始而復氣,繼而復血,繼而復肉,繼而復筋,繼而復骨。”疫疬侵入人體后往往迅速充斥表里、內外,彌漫三焦,造成多臟腑、多組織的廣泛損害,心、肝、脾、胃、腸、心包等皆可受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根據尸檢及組織病理觀察發現:新冠肺炎病變主要在于不同程度的肺實變,見漿液、纖維蛋白滲出物,肺泡隔血管充血、水腫,肺組織出血、壞死、纖維化;同時累及心、肝、腎、食管、胃和腸管等變形、壞死;主要破壞免疫系統[1]。疫邪暴戾猖獗,自口鼻而入,或燔熾陽明,或直達膜原,或內攻臟腑,或熱毒內陷,病理性質總屬濕、熱、毒、虛、瘀夾雜互結。早期疫邪熾盛,趁虛深入,病變可波及多個臟腑,導致變證四起,危象畢現。大病之后邪氣過盛,臟氣受損,故恢復期及遠期康復當以調補氣血為要。五臟之傷,不外乎氣、血、陰、陽,氣血同源,陰陽互根。氣虛不能生血,血虛無以生氣。氣虛者,日久陽氣漸衰;血虛者,日久耗傷陰液。陽損日久,累及于陰;陰虛日久,陽氣無依。本病恢復期則常出現陰液耗傷、脾胃虛弱、心神失養、熱竄經絡等表現,故在病后調補臟腑氣血,有利于元氣的恢復。
同時還要根據疫邪的病理性質,兼顧平衡陰陽。筆者在本次疫情期間作為遠程會診專家參與了黃石義診服務,有相當數量的痊愈患者,在恢復期出現活動后胸悶干咳、口燥咽干的情況,證屬肺陰不足,治以麥門冬湯或沙參麥冬湯以補養肺陰;另有一些患者存在氣短乏力、心慌汗出、夜寐不安的情況,予炙甘草湯合生脈飲以補養心之氣陰,收效均良好。可見“疫邪”常耗傷陰血,恢復期當以甘涼濡潤之劑滋養陰液,如《溫疫論》云:“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郁,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為火,陰血每為熱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陰血未復……凡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榮湯。”也有少部分患者病后長期出現倦怠嗜臥、形寒肢冷等后遺癥,多因感受寒濕疫邪致脾陽受損、中陽不展,或直中心包使心陽不振,又因腎陽為人身之元陽,故心脾之陽虛日久常累及于腎,出現心腎陽虛或脾腎陽虛的癥狀,筆者以附子理中丸合真武湯溫陽散寒,防陽氣不復而遺留痼疾。然臨床用藥時當注意配伍,考慮到陰陽互根相資,不可一味妄投寒涼或溫燥。《景岳全書》曰:“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善補陰者,必于陽中求陰,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當宗其意。
3 注重寧心安神以暢情志
“疫邪”暴虐,傳變迅速,染之其人多死。新冠肺炎患者身心健康均受損,疫情期間除了情緒的郁結不暢,還有對疾病的焦慮與恐懼,以及對預后的擔憂與親朋好友患病甚至離世所致的悲傷等情緒變化。情志不遂,則伴發郁證,而郁證會進一步加重臟腑氣機郁滯,如《素問·舉痛論》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新冠肺炎恢復期的調治應注意酌加疏肝理氣、調暢情志之品,防止出現“因病致郁—因郁致病”的惡性循環。此外,歸結情志對臟腑功能的影響,還包括“憂傷肺”“思傷脾”“恐傷腎”。《諸病源候論》述:“結氣病者,憂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故結于內。”過度悲傷可使肺氣抑郁,久則耗傷肺氣,而致氣短乏力。思慮過多則中焦郁結、脾失建運,久則出現神疲乏力、納差、泄瀉等脾氣虧虛、脾陽不足之證。恐傷腎主要體現在對腎中精氣的損傷,可見骨痿、小便頻多失禁、動輒氣喘等包括腎氣不固、腎不納氣之證。因此,在病后調治中需結合患者主要的情緒表現與具體證候以明確病變臟腑,處方用藥時需有所側重。此外,睡眠障礙也是情志失常的伴隨癥狀,其病機總屬陰不入陽,神不守舍。疫邪所著,正氣被傷,邪氣鴟張,周身之陽氣被困遏,營衛運行之機阻滯,陰陽失交,導致不寐。同時熱毒疫邪更兼熱傷血絡,使機體呈現陰虛之候,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心神不寧,也是不寐的主要病機。不寐與郁證又互為因果,導致疲乏,降低患者恢復的信心,甚至影響遠期的生存質量。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推動一身血液運行,心血不足則心神失養而見精神恍惚、失眠多夢,故而在本病恢復期的調治中,還應當重視配合寧心安神、潛陽育陰之法,方選酸棗仁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等,并從心理疏導、調整生活習慣等多方面進行針對性干預。
4 講究三因制宜并預防復感
4.1 因人制宜 患者年齡、體質等差異,對預后都有一定影響。如《溫疫論》云:“蓋老年榮衛枯澀,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浡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幼兒氣血未充,臟腑嬌嫩,老人生機減退,氣血虧虛,故病后調治多以補益為主,且用藥時間宜長,甚至可給予藥膳長期調補。而青壯年氣血旺盛,病后臟腑功能易于恢復,恢復期疫邪清除較快,短期調補即可。患者體質也有強弱與寒熱之偏,對偏于陽盛、陰虛之體或感受熱毒疫邪者,恢復期應多用甘涼濡潤之劑以滋養陰液;偏于陽虛、陰盛之體或感受寒濕疫邪者,恢復期當以溫補為要,以復陽氣。通常體質強壯之人,恢復期無需長期調補;體質瘦弱,平素易感者,當大補氣血,以清其余邪。
4.2 因時制宜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時間較長,于我國境內始于秋末,貫穿整個冬季,歷經來年春夏,至今全球范圍仍不斷新增大量感染者。而四季氣候不同,疫邪發病季節各異,則易夾雜不同的病邪,故患者病后調補應適應四季氣候的特點。如夏季雨水較多,濕氣盛,常兼濕邪。如患者臨床表現伴有肢體沉重、嘔惡腹脹、納呆、苔厚而膩等,后期調補當重視利水化濕;同時濕邪久羈,易防礙陽氣蒸騰,應根據實際情況酌加少許溫陽之品,以利一身之氣機。深秋以及春冬季節,氣候寒冷,陰盛陽衰,人體腠理致密,陽氣斂藏于內,故易兼寒邪。誠如《溫疫論》所說:“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為病最重。”恢復期調補應以溫陽散寒為主,氣血方得融合,不至病情反復。《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所列新冠肺炎的證型中,夾雜濕邪較多,包括寒濕、濕熱、濕毒等,濕性黏滯不易去除,后期更當健運中焦,以化濕邪。
4.3 因地制宜 地區診療方案表明,湖北地區新冠肺炎患者證素特點為濕、熱、毒、虛,武漢周邊地區患者證素特點為溫、熱、毒、瘀,南方沿海地區患者證素特點為濕、熱、毒;北方地區患者的證素特點為寒、熱、濕、瘀。可見,除了濕與熱為相同證候,其他證素需因地制宜[3]。如北方及西北甚至高原地區,氣候寒冷、干燥少雨,疫邪致病常兼夾寒邪、燥邪,恢復期調補當投以溫潤之劑,切不可予辛溫大燥之品。南方炎熱多雨、氣候潮濕的地區,多為濕邪、熱邪致病,恢復期當以健脾化濕、益氣養陰為主。根據患者具體情況,也可加用艾灸、拔罐以散寒除濕,配合針刺以健運中焦,以及運用八段錦、五禽戲等運動療法以加速患者康復,提高遠期生活質量[4-5]。
4.4 預防復感 《溫疫論》中提到:“所謂溫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鳥棲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疫邪傷人后,如調養不當,易出現勞復、食復、自復。所謂勞復多因“元氣未復,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動……前證復起”。“若因飲食所傷者,或吞酸作噯,或心腹滿悶而加熱者”,名為食復。若無故病情反復者,“以伏邪未盡”,即為自復。由此可見,感染疫邪后,稍有不慎,患者易出現病情反復。恢復期的自我調治方面當靜養為主,注意避風寒,少疲累,逐漸增加飲食、適當運動以提高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