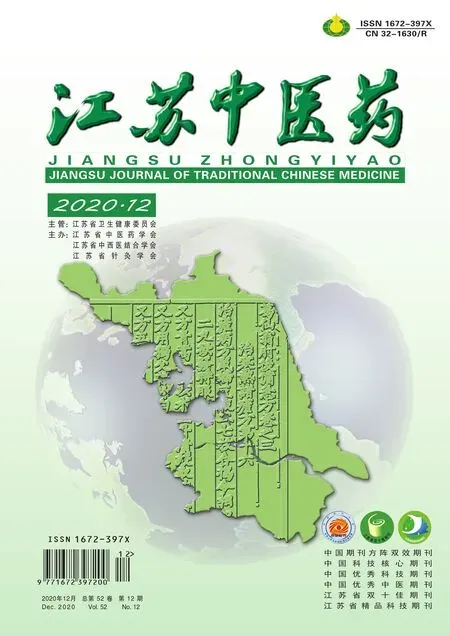基于名醫醫案探討收斂藥在急性腹瀉中的應用
陳保伶 張北平
(1.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廣東廣州510405;2.廣東省中醫院,廣東廣州510000)
泄瀉是一種常見的疾病,相當于現代醫學的急慢性腸炎、胃腸功能紊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腸結核等,按照病程區分,可分為急性腹瀉與慢性腹泄。急性腹瀉即暴瀉,又稱“暴泄”“洞泄”,指大便如洪水直注而下。暴瀉常因飲食不潔、外感濕熱、寒濕之邪等引起,病性多屬實。因實邪為患,其用藥多以祛邪為主。一般認為收斂藥性味酸澀,會使邪氣停聚臟腑,使邪無出路,有“閉門留寇”之虞,故不主張在急性腹瀉中應用。然而,急性腹瀉起病急,病勢竣猛,若暴瀉無度,則可能出現口舌干燥、眼窩凹陷、尿少、四肢厥冷等陰竭陽脫的癥狀,甚至可危及生命。近現代某些名老中醫在治療急性腹瀉時,不拘泥于“初瀉祛邪,久瀉固澀”之說,而根據病情需要大膽靈活使用收斂藥物,亦收效甚捷,現基于名醫醫案探討收斂藥在急性腹瀉中的應用如下。
1 經典醫案及分析
1.1 金邵文醫案[1]當代兒科名家金邵文曾診治一位患兒,暴瀉3 d,日行6~7次,大便青綠夾黏液,兼見身熱不揚,舌質紅、苔中白。考慮濕熱夾積。然泄瀉勢不可止,患兒年幼體弱,恐有陰竭陽脫之虞。故予清熱燥濕、健脾行氣,兼以收斂止瀉。處方:蘇梗6 g,淡干姜3 g,煨木香3 g,白術1 g,制川樸3 g,川連1.5 g,地榆10 g,馬齒莧10 g,訶子皮10 g,砂仁殼3 g,山楂炭10 g。藥物寒熱相佐,標本同治。此案金老以干姜、黃連辛開苦降,配合地榆、馬齒莧清熱解毒;蘇梗、木香、白術、砂仁殼等行氣燥濕以治其本;訶子皮、山楂炭澀腸收斂止瀉,直折其暴瀉之勢。尤其妙在山楂炭既有消積治本之功,又可取炭類收斂止瀉之效。
又診治一位兩個半月大患兒,泄瀉2 d,日行10數次,黃色水樣便,量多,身熱不揚。舌質紅、苔中白。據其癥考慮濕邪壅盛,雖“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但小兒疾病發展迅速,若純滲淡利濕,則有氣隨陰脫之弊,故佐以訶子皮、石榴皮、山楂炭固腸止瀉,防患于未然。處方:雞蘇散30 g,煅木香3 g,淡芩炭6 g,川連1.5 g,茯苓10 g,山楂炭10 g,炒麥芽10 g,訶子皮10 g,石榴皮10 g,生甘草3 g。2劑基本痊愈,予七味白術散1劑善后。此案在對證清熱利濕基礎上以山楂炭、訶子皮、石榴皮收斂止瀉,祛邪與收斂并用,收效迅速,且無斂邪之弊。石榴皮為藥食同源之品,具有澀腸止瀉之功,且藥性平和,尤其適用于小兒稚陰稚陽之體。
1.2 王仲奇醫案[2]近代名醫王仲奇,數代業醫且一生行醫40余年,醫術精湛。曾診治一名高年患者,因飲食不當而泄瀉數日,并有肛門墜脹,輕微大便失禁感,其脈弦緩而滑。考慮老者精血衰弱,正氣不足,腹瀉過度而損及脾腎陽氣,導致脾不升清,氣虛下陷,故肛門作墜。腎主封藏,司二便,年高腎氣不足,瀉下無度傷脾及腎,封藏失司,二便不固,故可見輕微失禁。泄瀉雖源于飲食不節,但因年高體弱,病機由實轉虛。王老以升陽健脾、澀腸止瀉為法,予方藥:于術一錢二分,蒸白芍二錢,炒肉果一錢,煨禹余糧三錢,青防風一錢,六神曲三錢,炒茯苓三錢,罌粟殼錢半,益智仁八分,炒谷芽四錢。二診癥狀已改善,惟大便未成形、口舌干燥,脈弦緩而滑。予方藥:于術一錢二分,蒸白芍二錢,炒益智仁八分,茯苓三錢,肉果八分,煨青防風八分,炙黑苡仁三錢,炒罌粟殼錢半,宣木瓜一錢,橘紅衣一錢,荷葉三錢(米炒),金釵斛二錢。在補脾腎、升清陽、消積滯的基礎上,配伍肉豆蔻、益智仁、禹余糧、罌粟殼等溫中澀腸止瀉,防微杜漸,避免瀉下過度導致陰竭陽脫,標本同治,故獲良效。
1.3 熊繼柏醫案[3]國醫大師熊繼柏曾診治一位青年農民,患者在酷暑季節操持農活,因口渴遂飲2碗生水,隨即出現腹痛、上吐下瀉,暈倒田間。醫生先予十滴水、藿香正氣水,后予針劑注射、服藥,但無好轉。急尋熊老診治時,癥見冷汗淋漓,兩目、腹部深陷,聲低息微,口張氣短,時時嘔逆,大便失禁,泄水不止。查舌淡白,診脈微細無力。雖知其病起外感暑熱,內傷寒濕,但暴吐暴瀉,謂之“上爭下奪”,傷津耗氣,患者已見惡候,危在旦夕。因此,不可拘泥于“初瀉祛邪,久瀉固澀”,眼下當急止吐瀉以存陰救陽。據其諸癥,熊老擬第一方:烏梅30 g,干姜15 g。第二方:高麗參30 g,黑附片60 g,炙甘草15 g。后續予附子理中湯合生脈散治之。吐瀉均止后乃擬參苓白術散。方中干姜溫中止嘔,回陽救逆;配伍烏梅生津存陰,固腸止瀉,既可回陽救陰,又可吐瀉并止,作為開路先鋒,力挽狂瀾,再以參附、生脈、參苓白術之類固其根本,使得患者轉危為安。
2 收斂藥在急性腹瀉中的應用指征
分析以上名家醫案,可總結急性腹瀉配伍收斂藥的應用指征如下:(1)瀉下量、次頗多,或吐瀉并作,氣津過度丟失,應酌情使用收斂藥。中醫學認為津能載氣,陰陽互根,陽氣可隨陰津脫失,甚者形成陰竭陽脫的危候。(2)小兒、老人等體質偏弱患者,當酌情使用收斂藥。小兒臟腑“兩有余而三不足”,脾常不足,脾胃運化能力不足,而泄瀉之本無不在脾胃;小兒具有“易虛易實”的生理特點,病情轉變迅速,若見陰傷之證,可預防性佐以收斂藥。老人陰陽氣血偏弱,暴瀉過度容易由實轉虛,出現陰竭陽脫等變證。酌情佐以收斂藥,可顧護正氣,以防變證蜂起。(3)收斂藥必須與對證藥配合使用,上述案例應用收斂藥后均無出現邪氣留戀之象,原因在于祛邪收斂并用。或淡滲利濕,或清熱燥濕,或消食導滯,或溫化寒濕等,使得實邪得清,正氣可顧。如此根據虛實程度,調整祛邪、收斂的藥物比例,則無閉門留寇之虞。
收斂藥物大多性味酸澀,但具有寒熱補瀉等不同。急性腹瀉多由濕熱、寒濕、食積引起,而患者體質偏向也會產生相應的虛實轉化,需根據辨證合理搭配收斂藥。(1)濕熱泄瀉:適宜選用藥性平和之收斂藥,如石榴皮、訶子;若陰傷突出,可選用烏梅、五味子、石榴皮等固澀生津之品。(2)寒濕泄瀉:寒邪傷陽,可能出現精神萎靡、肢冷氣短等氣隨津脫之變證。在滲淡利濕、溫陽健脾的基礎上,適宜選用辛溫酸澀之品,如赤石脂、肉豆蔻、五味子、伏龍肝等。(3)食積泄瀉:適宜選用尚可消食導滯的收斂藥,如山楂炭、烏梅等,既可消食化積治其本,又可收斂止瀉治其標,起到標本兼治之效。(4)老者、小兒等素體不足之人,瀉下無度最易傷及脾腎,需兼顧扶正收斂。若其人素體脾虛,暴瀉當酌情加入蓮子、芡實、伏龍肝等,若其人肝腎不足,暴瀉容易導致下元不固,應佐以山茱萸、赤石脂、肉豆蔻、五味子等。若出現陰竭陽脫危重癥,當以龍骨、牡蠣斂陰潛陽。此外,罌粟殼澀腸止瀉作用最強,如嚴重暴瀉急當存陰時,無論何種證型均可應用,中病即止。
3 收斂藥的現代藥理研究
急性腹瀉相當于現代急性腸炎、過敏性結腸炎、腸功能紊亂等疾病,多因細菌、病毒感染而致。因胃腸道活動亢進、水液代謝異常導致腹瀉,腸黏膜炎癥損傷、胃腸平滑肌痙攣等導致腹痛。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收斂藥可有效抑制腸道病原體,產生抑菌、抗病毒的作用,如烏梅、五味子、石榴皮、肉豆蔻等;或調節胃腸道平滑肌活動,從而解痙止痛、止瀉,防止水電解質紊亂,如五味子、罌粟殼等;或修復、保護胃腸道黏膜,如赤石脂、禹余糧等。根據文獻報道:烏梅、石榴皮具有抑菌、抗病毒、治療腹瀉、痢疾的作用[4-5];五味子具有抑制多種腸道致病菌、抑制胃腸平滑肌亢進活動的作用[6];肉豆蔻具有抗菌抗炎、止瀉的作用[7];赤石脂可吸收消化道內的有毒物質及產物,保護創面。
4 病案舉隅
胡某,女,1歲4個月。2019年11月14日初診。
主訴:發熱伴腹瀉3 d。患兒3 d前開始出現發熱,體溫波動于38.5 ℃上下,每日解泡沫水狀便2~3次,大便色黃,氣味臭穢。刻下:汗多,口氣臭穢,哭鬧較多,胃納欠佳,睡眠欠安,小便調。舌紅苔黃根部厚膩,指紋色紫。辨證:濕熱蘊結,飲食積滯;治法:清熱祛濕,消食導滯;予葛根芩連湯加減。處方:
葛根 15 g,黃連 6 g,黃芩 6 g,鹽車前子 9 g,火炭母 9 g,布渣葉 9 g,炒麥芽 9 g,炒谷芽 9 g,神曲 6 g。3劑,日1劑,水煎,分2服。
二診(11月18日):患兒體溫下降,哭鬧煩躁緩解,日解水狀大便10余次,色黃。舌紅苔薄黃根部稍膩,指紋色紫。辨證治法同前,考慮患兒年幼體弱,瀉下過多,恐有氣陰欲脫之虞,在前方基礎上加山楂炭6 g、石榴皮6 g、赤石脂9 g(先煎),3劑,水煎服。服藥后第1天泄瀉減至3次,量較前減少,第2天已無泄瀉,第3天諸癥悉除,后續以調理脾胃收功。
按:濕熱夾積,蘊結腸腑,下注魄門,故患兒發熱、瀉下臭穢。一診以葛根芩連湯化裁清熱利濕,消滯止瀉。服藥后熱減,積滯濕濁尚有留戀,但瀉下過度恐有脫證之虞,故二診在原方基礎上佐以山楂炭、石榴皮、赤石脂以消積化滯、澀腸止瀉,標本兼治,癥狀大減。此案于辨證用藥基礎上配合收斂藥,故無斂邪之弊,且收效甚捷。
5 小結
急性腹瀉危急癥多發生于小兒或老人等體質偏弱人群中。小兒為稚陰稚陽之體,病情傳變迅速,易虛易實;年高者大多元氣不足、精血虧虛,不耐暴瀉耗氣傷陰。臨證中患者若出現精神萎靡、口渴甚、皮膚干燥、眼窩凹陷、淚液少,舌干少津、少苔或苔剝脫等,為陰液重耗之危象。中醫認為,“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機”,津液的盛衰直接影響疾病的預后。故對于暴瀉過度或暴瀉危急癥,尤其屬體質虛弱者,應在辨證用藥基礎上佐以對證的收斂藥,既可顧護陰液,避免出現陰竭陽亡等惡候,又無“閉門留寇”之弊,可大大提高療效,臨床應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