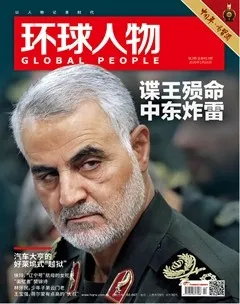“面壁者”樊錦詩
陳娟

樊錦詩在敦煌。(孫志軍/攝)

1938年生于北京。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畢業后到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歷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院長,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研究館員,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近日出版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1962年初,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故事的主人公叫尚達,在巴黎學了10年油畫,偶然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看到一部名為《敦煌石窟圖錄》的畫冊,為之震撼,之后毅然回國,奔赴敦煌,投身莫高窟的保護、臨摹和研究,歷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直守在那里。尚達的原型就是常書鴻先生,1943年到敦煌,次年創辦敦煌藝術研究所。當時,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讀大三的樊錦詩一口氣讀完了這個故事,被先生對藝術的忠誠、對事業的執著深深打動,也對敦煌充滿向往。
那年8月,樊錦詩愿望成真——系里安排她去敦煌實習。這是她第一次去敦煌,一路上都在暢想,想象風度翩翩的常書鴻先生,想象如世外桃源般的敦煌。可一下車就傻了眼,眼前的常先生穿一身洗舊了的“干部服”,一雙布鞋,戴一副眼鏡,“一個鼎鼎大名的藝術家怎會這么土!”那里的生活更是想象不到的艱苦,住破廟泥屋,沒電沒水,上個廁所都要跑很遠。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洞窟里那些壁畫和彩塑。整整一個星期,人稱“活字典”的史葦湘先生帶著他們幾個北大學生,攀緣著被積沙掩埋的崖壁,一個洞窟一個洞窟地看過去。從北涼、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從伏羲、女媧到力士、飛天。樊錦詩至今還記得第一次進洞窟時的情景,“洞中的溫度遠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氣從地層蔓延上來。然而看著洞窟四壁色彩斑斕的壁畫,我就忘記了寒冷”。 那一年,她24歲,是一個朝氣蓬勃、對未來充滿遐想的青年學子。
沒有料到,正是這次實習改變了她的命運——此后的人生都與敦煌連在一起。第二年,樊錦詩畢業,被分配到敦煌工作。當時的她雖有些不情愿,但還是背起大包,戴著草帽,坐火車、轉汽車,歷經三天三夜,回到敦煌。這一去就再也沒有離開。
一晃57年過去,樊錦詩依然是初到敦煌時的短發,只是青絲變華發。在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的發布會上,她一出現就被人團團圍住,瘦小的身軀被淹沒在人群中,只能偶爾飄出一兩句話語,有些粗有些硬,明顯被西北風沙打磨過。輪到她發言,她躬著背走上臺,一開場就說:“我的經歷很簡單,出生在北京,上海長大,北大求學,到敦煌工作。”之后的故事,便是她與敦煌大半生的糾葛。
常書鴻點名就要樊錦詩
敦煌研究院是一片灰色平房,兩層樓高,孤零零地矗立在戈壁灘上。它與莫高窟隔著一條宕泉河,宕泉河畔有一片墓地,安葬著常書鴻、段文杰等莫高窟人。每天下午5時20分,最后一班旅游車載著游客離開莫高窟。除了研究院,方圓20里內就沒有人煙了。
幾乎每一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都會被人問一個同樣的問題:當初為何選擇來偏遠而荒涼的敦煌?

1965年,樊錦詩與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

1964年,樊錦詩(左)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敦煌研究院供圖)

莫高窟第61窟東壁北側。(孫志軍 / 攝)

2004年8月,樊錦詩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現場。(敦煌研究院供圖)

2004年5月,樊錦詩在454窟調查壁畫題記。
“那還有啥可說的呢?一個有事業心和責任感的女大學生,碰上一個思想純粹的年代,最終的結果就是扛起鋪蓋卷兒,義無反顧地上路。”樊錦詩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其實最初敦煌并不是她的理想選擇,自己只是服從分配——1963年,她從北大畢業那一年,時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向北大考古系申請推薦畢業生到敦煌工作,點名就要樊錦詩。
畢業分配結果宣布時,樊錦詩猶豫不決。“1962年的那次實習,給我留下了心理陰影。”她說。敦煌晝夜溫差大,氣候干燥,她從小在上海長大,根本無法適應。“嚴重的水土不服,加上營養跟不上,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經常到三四點鐘就醒了。”還有一次半夜房頂掉老鼠,把她嚇個半死,暗暗發誓:“這地方我再也不來了……”
但真正面臨抉擇時,樊錦詩又和許多年輕的大學生一樣,天真而堅定——只要是國家需要,就愿意無條件地服從。“我轉念一想,說不定這就是天意。作為一個考古學生,其實在潛意識里,我還是非常喜歡敦煌的。”
樊錦詩念念不忘的是敦煌那些美麗的壁畫和造像。“這些洞窟最初是誰建的?壁畫是什么人畫的?她又是怎樣湮沒在了歷史的記憶中……都在向我傳遞著一種強烈的信息,這里充滿著奧秘,我想要去探究它的謎底。”
支撐樊錦詩去敦煌的,還有一個美好的希望——學校承諾,三四年后會分配新的考古專業畢業生來敦煌,她就可以離開,去武漢和愛人彭金章團聚。彭金章是他們班的生活委員,在學校時對樊錦詩格外照顧,給她占座,送她手絹、家鄉土特產,一來二去兩人確定戀愛關系。畢業分配,彭金章的去向是武漢大學。分別時,樊錦詩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誰也沒想到,這一分就是23年。直到1986年,彭金章調到敦煌研究院,夫婦二人都在敦煌扎下了根。
畢業離校前,發生了一件令樊錦詩難忘的事。
有一天,蘇秉琦先生突然派人找她,將她叫到在北大朗潤園的住處。蘇先生當時任北大歷史學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與夏鼐先生齊名的考古學界泰斗。一進門,樊錦詩忐忑不安,蘇先生給她沖了一杯咖啡,說:“你去的是敦煌。將來你要編寫考古報告,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必須得好好搞。”
在那一刻,她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重任——完成對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
“我有好幾次想離開敦煌”
樊錦詩很小的時候就對考古充滿遐想,這和父親有很大關聯。
父親畢業于清華大學,是個工程師,雖學的是理工科,但熱愛古典藝術和文化,從小給孩子們講歷史故事,教他們背《古文觀止》。受父親影響,樊錦詩中學時就常常逛博物館,看文物學歷史,知道許多精美文物都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1958年,她考上北大歷史系,偶然聽到學長們講考古,覺得很神秘,“能夠飽讀詩書,還能游遍名山大川,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于是,她就成了一名考古專業的學生。
當時,北大考古專業是新中國首個考古專業,云集了一批頂尖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如周一良、田余慶、蘇秉琦、宿白等先生。宿白先生是樊錦詩的授業老師,也是對她人生影響極大的一位先生。
宿白畢業于北大歷史系,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的開創者。他做學問很認真,有一次,期末提交論文,樊錦詩本打算隨便寫一寫,交差了事。沒想到先生逐頁批閱,一條一條意見清清楚楚地寫在一張臺歷紙上,然后拿給她說:“你回去好好修改吧。”樊錦詩很羞愧,此后做學問、做人做事,都認認真真、腳踏實地。
到研究所后,樊錦詩牢記蘇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的囑托,第一項工作就是和其他幾位同事一起撰寫敦煌第一部考古調查報告。她加入到 “面壁者”的隊伍中去,每天睜開眼就往洞窟里鉆,跟著先生們爬“蜈蚣梯”——一根繩子直上直下吊著,沿繩一左一右插著腳蹬子。每次爬她都心驚膽戰,在梯子上左搖右晃。
“我把所有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在洞窟里。”樊錦詩說。剛到敦煌,一不工作她就胡思亂想,想上海、想北京、想愛人,有一種巨大的孤獨感和失落感,“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郁的深淵,有好幾次都想離開”。
為了抗拒這個深淵,她學著遺忘,將姐姐送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她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板的泥地,習慣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板,習慣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后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繼續睡。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所有的孤獨和不快全都忘了。“慢慢地離不開敦煌,安下心來,心無旁騖地守護它。”
3年后,考古報告草稿初成,但“文革”來了,研究工作被迫中斷。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編寫石窟考古報告工作才又提上日程,只是限于技術人員的缺乏,始終難有推進。1998年,樊錦詩從前任院長段文杰手中接過重擔,成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如此一來行政工作又占去了她大部分時間。
沒時間搞專業,樊錦詩就想辦法一點一點擠。2000年前后,她拿著考古報告的部分草稿給宿白先生看,先生直截了當地問她:“你怎么現在才想起寫考古報告?你是為了樹碑立傳吧?”聽了老師的話,她哭笑不得,內心很委屈。先生這么說是有原因的,因為那段時間他經常在電視里看到樊錦詩。他是在提醒樊錦詩:不要老在電視里晃來晃去,要專心致志于自己的考古研究。
樊錦詩被先生“敲”醒了,再把心思收回到考古上。經過多年反復探討、研究、修改,2011年,終于完成并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也算了卻了一樁心愿,但只是開了一個頭。敦煌一共735座洞窟,更繁重漫長的工作還在后頭。”
讓敦煌消失得慢一點
735座洞窟,樊錦詩能說出每一尊佛像的來歷、每一幅壁畫的年代、每一個石窟需要修復的問題。“每一個洞窟都有病。”她說,所以保護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2009年8月,樊錦詩在第85窟指導敦煌石窟壁畫數字化工作。(孫志軍 / 攝)

莫高窟第158窟。每當煩悶時,樊錦詩就來到這個洞窟看一看。
“文革”十年動亂結束不久,樊錦詩被任命為敦煌研究所副所長。上任不久,她就開始做莫高窟的“科學記錄檔案”——為每一個窟編制一本檔案,包括平面圖、剖面圖以及照片、文字等詳細信息。
做檔案的過程中,需要查找過去的老資料。敦煌最早的照片,來自1908年的冒險家斯坦因,以及后來的伯希和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敦煌研究院也留下了數萬張照片。兩下一對比,樊錦詩吃了一驚,“同樣的洞窟、同樣的文物的照片,現在見到的彩塑和壁畫等,或退化,或模糊,或丟失”。那一刻,她發現了敦煌的脆弱、易逝,“那些懷抱琵琶的飛天和斑斕的佛國世界,遲早會消失。人類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讓消失的過程慢一點”。
有一陣子,樊錦詩總在做夢,夢到墻體上的壁畫一塊塊地剝落,“難道我們就眼睜睜地看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敦煌石窟藝術逐漸消亡嗎?”問題一直縈繞著她,走路吃飯睡覺都在琢磨,但總也無解。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樊錦詩到北京出差,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人在電腦上給她展示圖片。她忍不住就問:“那你關機后,剛才顯示的圖片不就沒了嗎?”對方回答:“不會!因為轉化成數字圖像后,它就可以永遠保存下去。”她茅塞頓開:壁畫也可以數字化保存。
后來,這一構想得到甘肅省科委的支持,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開始了壁畫數字化的試驗。“盡管我們在山溝里,但我們從來都是開拓進取,不墨守成規的。”
此后,敦煌便行走在數字化的道路上。1993年,敦煌研究院開始嘗試用計算機技術重組壁畫信息;2006年,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成立,專門從事研發石窟文物數字化;2014年,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建成,游客可以在這里觀看球幕電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這些年,越來越多的游客被莫高窟的神秘和美麗吸引。隨之而來的是,它也被裹挾到旅游開發的大潮中,遇到了市場開發和保護的矛盾。
1998年,樊錦詩接任院長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當時,全國掀起“打造跨地區旅游上市公司”熱潮,有關部門要將莫高窟捆綁上市。“敦煌是國家的遺產、人類的遺產,決不能拿去做買賣。”為此,她四處奔走,甚至對當時的相關主管部門領導說:如果敦煌也捆綁上市,文物局就關門吧,我這個院長的帽子也不要了。就這樣,她硬是把壓力頂了回去。
“擔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縮。”時至今日,再談起當年,樊錦詩仍很堅決,“敦煌研究要做什么?就是完整、真實地保護她的信息,把她的價值傳給子孫后代。如果沒好好挖掘文物的價值就讓企業來開發,那我就是罪人。”
“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誰”
在敦煌堅守近60年,樊錦詩覺得自己最對不住的就是丈夫和孩子。
1968年,她生下大兒子,產假一休完就上班。孩子沒人看,只好把他捆在襁褓里,臨走之前喂飽,中途再回來喂一次奶。有一次,她下班回宿舍,發現孩子從床上滾了下來,臉上沾滿了地上的煤渣,心疼得直哭。最終,她和彭金章一商量,把孩子送到丈夫河北老家的姐姐那里。后來,老二也由這個姑姑帶大。
一家四口真正團聚,是在彭金章調到敦煌后。樊錦詩忙于工作,照顧孩子的重擔就落在了丈夫身上。“我能守在敦煌,離不開老彭的理解和支持。”樊錦詩說。
當年,她一頭撲在敦煌考古時,彭金章也肩負重任,在武漢大學創立了考古系。兩人面臨的現實問題是:誰去誰那里?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開始了——武漢大學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以禮相待”,也到武漢大學要人3次。結果雙方“不歡而散”。后來,還是彭金章妥協,做起了“敦煌女婿”。
彭金章來到敦煌后,研究所就交給他兩塊“硬骨頭”,其中之一是研究被當時學術界稱為“敦煌荒漠”的北區洞窟。“洞窟積塵都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發掘完一個洞窟后,他就成了泥人,眉毛和眼睛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換幾個,都是黑的。”樊錦詩回憶。8年里,彭金章用篩子幾乎篩遍了北區的每一寸沙土,挖掘出大量珍貴文物,證實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構成,從而使有編號記錄的洞窟由492個增至735個。
樊錦詩今年82歲了,仍住在莫高窟,做研究、撰寫考古報告,只是身邊沒有了愛人彭金章——2017年他因病去世。
她一生不喜名譽,談及個人成就,她說“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誰?那不是我的榮譽,那是敦煌的榮譽。”她也不追逐物質和金錢,生活簡樸,可以稱得上是“摳門”。任院長時,她每次出差盡可能獨自一人,為的是省差旅費。而且只要去北京出差,就住在景山公園后的一個地下室招待所,連那里的服務員都認識她,稱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級別最高的名人”。
在敦煌,每當苦悶和煩惱時,樊錦詩都喜歡去第158窟看一看。第158窟內的佛床上,臥著莫高窟最大的釋迦牟尼佛涅槃像。臥佛像頭向南,足向北,右脅而臥,面向東。1200多年來,始終從容不迫、寧靜坦然地面對著朝圣者。一走進這里,她的心就格外寧靜,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靈安頓的地方,如果心靈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猶如生活在漫漫長夜中。敦煌就是我心之歸處。”
樊錦詩1938年生于北京。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畢業后到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歷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院長,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研究館員,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近日出版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