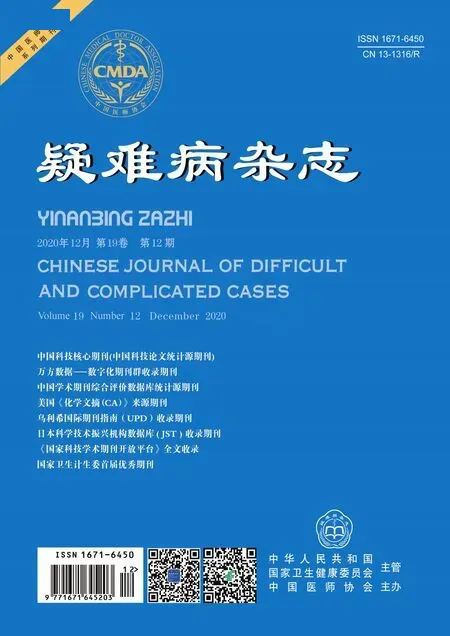細胞自噬在Th2型氣道炎性反應中的作用與研究進展
何昱沁,續珊綜述 陳始明審校
細胞自噬又稱細胞自我消化,是一種機體依賴溶酶體降解過多蛋白質及衰老、損壞的細胞器,以此實現機體物質的再循環、維持細胞代謝平衡及內穩態的過程[1]。自噬廣泛存在于真核細胞中。其在進化上高度保守,參與細胞內多種重要功能的調節,包括細胞生長、分化、存活、衰老及免疫反應。自噬異常與多種疾病的發生相關,如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病變、代謝相關性疾病及免疫性疾病等。
過敏性疾病又稱變態反應性疾病,指機體接觸致敏物質后引起的某一組織、器官甚至全身過度反應的疾病。Th2型炎性反應是導致過敏性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以Th2型細胞反應亢進為特點。近年來全世界范圍內Th2型炎性反應導致的相關疾病尤其是氣道炎性反應如支氣管哮喘、變應性鼻炎、嗜酸粒細胞性慢性鼻竇炎的發生呈明顯上升趨勢[2-4],已經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造成沉重的社會負擔。深入研究Th2型氣道炎性反應的發生機制并開辟新的靶向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表明,細胞自噬在Th2型氣道炎性反應中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現就自噬與支氣管哮喘、變應性鼻炎及嗜酸粒細胞性慢性鼻竇炎等Th2型氣道炎性反應的關系作一總結,以期能從細胞自噬角度深入認識Th2型氣道炎性反應發生發展規律并開辟新的靶向治療策略。
1 細胞自噬概述
1953年,De Duve C首次將細胞質物質遞送到溶酶體以降解的過程定義為“自噬”,自此人們開始對自噬在各種生物學過程發揮的作用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5]。自噬即自體吞噬,是細胞的一種程序性死亡方式,區別于Ⅰ型程序性死亡——凋亡,被稱為Ⅱ型程序性死亡。mTOR激酶是一種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也是自噬的關鍵負調控因子,可抑制自噬,調節細胞生長、增殖和蛋白質合成[6]。mTOR激酶作為能量和營養狀態的感受器,能感受細胞的多種變化信號從而加強或降低自噬的發生水平。經典通路如PI3K/Akt和MAPK/Erk1/2信號可通過激活mTOR通路抑制自噬,而AMPK和p53信號可通過抑制mTOR通路促進自噬[6]。
目前已經發現30多種自噬相關基因(autophagy-related gene,ATG)[5,7],它們編碼的蛋白分子調控著整個細胞自噬過程 (包括自噬體的形成及自噬體捕獲受損的細胞器和生物大分子的過程)。在某些病理條件如低氧、饑餓狀態或病原微生物入侵時,mTOR激酶活性受到抑制,其對自噬起始復合物(由ULK、FIP200、ATG101、ATG13構成)的抑制作用得以解除,隨后自噬起始復合物遷移至帶有ATG14和VMP1蛋白的新生吞噬膜。ATG14在ULK1/2的作用下磷酸化,并招募Beclin-1蛋白(又稱為ATG6)以及Vps34/15蛋白,以形成Ⅲ型磷脂酰肌醇三磷酸激酶(Beclin-1-PI3KC3),從而參與招募細胞質中含3-磷酸磷脂酰肌醇結合域的ATG蛋白復合體,其形成的ATG12-ATG5和LC3-Ⅱ(ATG8-Ⅱ)復合物可控制自噬體的形成,其中LC3-Ⅱ是檢測自噬變化的標志性蛋白,其含量多少與自噬活性高低密切相關[5]。細胞自噬通過降解自身受損細胞器及大分子物質產生的氨基酸和小分子物質被重新利用,從而實現胞內物質循環和內環境平衡,為細胞存活提供一種可能的保護機制。然而,當自噬活性過于強大時,其對胞內蛋白的無節制降解則會誘發細胞死亡。
大量研究表明,自噬與免疫系統及炎性反應之間有密切關聯,可影響內源性抗原提呈,并調控免疫細胞的分化、成熟及功能。Th2型氣道炎性反應如支氣管哮喘、變應性鼻炎、嗜酸粒細胞性慢性鼻竇炎的發病主要基于免疫系統的失調,因此,深入探討自噬異常在Th2型氣道炎性反應發病中的作用,將有助于加深對該類疾病的認識和防治研究。
2 自噬與支氣管哮喘
支氣管哮喘是由多種細胞和細胞組分參與的氣道慢性炎性疾病,臨床表現主要為突發性喘息、氣促、胸悶、咳嗽,多在夜間發生。全球至少有3億支氣管哮喘患者,且呈逐年上升趨勢[8]。Th1/Th2介導的免疫失衡是支氣管哮喘氣道炎性反應的主要機制,機體產生大量的IL-4、IL-5、IL-13等炎性因子可加劇肺部感染,促進嗜酸性粒細胞大量浸潤、黏液過度分泌及氣道高反應性[9-11]。
針對自噬基因與支氣管哮喘關系的研究發現,ATG5的單核苷酸基因多態性(SNP)rs12212740與哮喘患者的肺功能和氣道重塑具有顯著相關性[12],推測支氣管哮喘的遺傳傾向受自噬通路ATG5的SNP等位基因影響。臨床研究表明,自噬標志物LC3-Ⅱ在支氣管哮喘患者痰液的中性粒細胞、成纖維細胞、T淋巴細胞及外周血中性粒細胞、嗜酸性粒細胞(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s, PBEs)、單核細胞中高表達,在支氣管哮喘患者支氣管上皮細胞(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s,HBECs)、氣道平滑肌(airway smooth muscle, ASM)、肺嗜酸性粒細胞中也檢測到自噬通路相關蛋白Beclin-1、LC3b、ATG5的表達較對照組明顯升高[11, 13-17]。此外,哮喘急性發作期患者鼻黏膜上皮細胞中ATG5 mRNA的表達顯著上升[18]。IL-5、IL-13等也可加重支氣管哮喘患者氣道上皮細胞(airway epithelial cells,AECs)自噬水平而促進氣道炎性反應[10-11]。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DC)自噬相關基因ATG5特異性敲除或Beclin單倍體均可導致DC細胞MHC Ⅱ類和固有細胞因子(IL-6、TNF、IL-1β等)的表達降低、功能受損,導致支氣管哮喘模型小鼠肺部炎性反應加重[19-20]。可見,DC細胞的正常自噬對其功能發揮至關重要,對肺部炎性反應是保護性因素。而ATG5-Cko(CD19+B細胞ATG5基因特異性敲除)小鼠經OVA致敏后,其支氣管哮喘癥狀及肺部炎性反應與對照組相比均顯著減輕,Th2型細胞因子IL-4和IL-13表達水平也顯著降低[9]。中性粒細胞、胸腺細胞的自噬對支氣管哮喘同樣是促進因素[13,21]。以上研究表明自噬對支氣管哮喘病理機制調節作用具有雙重效應及細胞依賴性。
IL-5可以增加重度哮喘(severe asthma,SA)患者PBEs中的自噬水平[11]。哮喘模型也發現,小鼠鼻黏膜特異性敲除自噬相關基因ATG5后其氣道高反應顯著減輕,嗜酸性粒細胞浸潤狀況及IL-5表達明顯下降而Th2炎性反應減輕[17]。這些研究均提示自噬通過嗜酸性粒細胞參與難治性哮喘的發病機制。IL-13可以促進氣道杯狀細胞的形成,通過激活自噬誘導氣道上皮細胞分泌黏液[10]。難治性哮喘個體中,ATG5的基因表達與氣道Ⅴ型膠原纖維(COL5A1)的含量呈正相關[22];卵泡抑素樣1(FSTL1)可通過激活自噬誘導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和氣道重塑[23]。這些研究說明自噬還可通過促進氣道上皮細胞分泌黏液、氣道重塑加重支氣管哮喘癥狀。
研究表明,中藥平喘寧湯可通過抑制氣道自噬體的形成來有效緩解氣道炎性反應[24]。CD46可以誘導自噬并減少氧化應激介導的呼吸道上皮細胞凋亡[25]。這些研究結果提示深入研究自噬在支氣管哮喘發病中的作用有望為其提供更精準、有效的靶向治療。
3 自噬與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指機體接觸過敏原后主要由IgE介導的Ⅰ型超敏反應,是由肥大細胞、嗜酸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等多種細胞和炎性介質參與的鼻黏膜慢性非感染性炎性疾病[26]。AR的臨床表現主要為陣發性噴嚏、清水樣鼻涕、鼻癢和鼻塞,可伴有眼癢、眼紅等眼部癥狀[27]。與支氣管哮喘發病機制類似,AR發病主要是Th1/Th2介導的免疫失衡,原本占優勢的Th1免疫反應,轉變為Th2細胞免疫反應占主導。
臨床研究表明,AR患者氣道自噬體及自噬相關蛋白Beclin-1、LC3-Ⅱ蛋白表達較正常對照組顯著升高,并且Beclin-1、LC3-Ⅱ水平與Ⅲ型膠原沉積及患者總體癥狀嚴重度評分(VAS)呈正相關[28],提示自噬在AR炎性反應及氣道重塑中發揮重要作用。體外研究發現,PM2.5可顯著上調鼻黏膜上皮細胞LC3-Ⅱ蛋白表達,促進自噬體形成,從而誘發炎性因子如IL-6、IL-8及TNF-α分泌,采用ATG5-siRNA和Beclin-1-siRNA下調細胞自噬水平可顯著緩解炎性因子的表達[29-30],提示PM2.5通過上調細胞自噬水平促進鼻黏膜上皮炎性因子的合成與釋放,導致鼻黏膜局部炎性反應加重。AR患者中自噬相關基因Beclin-1和p62的表達水平可以為預測其后期是否發展為慢性鼻—鼻竇炎伴鼻息肉(CRSwNP)提供臨床參考。動物實驗表明,TNF-α單克隆抗體可通過抑制自噬水平而改善AR小鼠的鼻部癥狀及炎性指標[31]。目前對自噬在過敏性鼻炎發病中的作用研究尚不深入,其確切作用機制仍需深入探討。
4 自噬與慢性鼻竇炎
慢性鼻竇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大約影響全球百分之十的人口,對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影響,每年可產生數十億美元的醫療費用[32]。根據是否伴發鼻息肉(nasalpolyp,NP),CRS分為CRS伴NP(CRSwNP)和CRS不伴NP(CRSsNP)[33]。在歐美國家,CRSwNP多是以Th2型炎性反應為主的嗜酸粒細胞炎性反應,而CRSsNP則多以非Th2型炎性反應為主[33]。
目前自噬與CRS的關系結論不一,Chen等[34]研究表明,在CRSwNP患者息肉組織中自噬標志物LC3表達較正常對照組顯著下降,自噬與鼻息肉的形成呈顯著負相關。然而也有研究表明,CRSwNP息肉組織中自噬體的形成及自噬相關蛋白(LC3B-Ⅱ、ATG、Beclin-1)的表達較正常組顯著增高[35]。體內試驗表明,鼻息肉成纖維細胞(nasal polyp fibroblasts,NPF)中去乙酰化酶6(sirtuin 6,SIRT6)表達降低,而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和自噬相關蛋白Beclin-1表達增強。進一步細胞實驗證實,過表達SIRT6通過抑制無氧糖酵解而抑制自噬[36],提示低氧誘導了CRSwNP中自噬的發生。脂多糖(LPS)是CRS中最常見的致病因素之一,可通過AMPK-mTOR及Toll樣受體4(TLR4)介導的信號通路誘導人鼻黏膜上皮細胞自噬的產生[37]。
在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human neutrophil elastase,HNE)誘導的CRS中,特異性沉默人鼻黏膜上皮細胞自噬相關基因ATG5的表達后,其黏蛋白MUC5AC的分泌顯著減少,提示自噬還參與CRS氣道重塑過程[38]。Choi等[39]通過ECRS基因敲除小鼠(特異性敲除髓樣細胞自噬相關基因ATG7的表達)模型發現,髓樣細胞ATG7-/-基因敲除鼠嗜酸性粒細胞浸潤情況、上皮細胞異常增生及黏液分泌明顯加重,Th2炎性因子及炎性介質PGD2表達顯著上調,進一步體外研究發現,耗竭自噬缺陷的巨噬細胞后,嗜酸性粒細胞炎性反應及PGD2表達則顯著下調。這些研究提示髓樣細胞尤其是巨噬細胞的自噬在嗜酸性粒細胞炎性反應及CRS病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臨床研究也表明,甲潑尼龍作用后,息肉組織中自噬相關基因LC3-B及蛋白表達上調,p62表達下調,自噬水平升高,說明甲潑尼龍能夠通過上調息肉組織的自噬水平來治療鼻息肉[40]。以上研究共同表明自噬可能是治療CRS嗜酸性粒細胞炎性反應的重要靶標。
5 自噬與其他Th2型氣道炎性反應
自噬通路相關蛋白LC3B-Ⅱ、ATG4、ATG5、ATG12和ATG7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肺組織的表達明顯高于非COPD患者[41]。穩定期COPD患者存在Th1淋巴細胞功能亢進,而急性加重期Th1/Th2平衡有向Th2漂移的特點[42]。目前有許多關于自噬與COPD的研究,但均著重于穩定期,急性期是一個空白,有待進一步研究。Cabrera等[43]發現,過敏性肺炎(hypersensitivity pneumonitis, HP)患者肺中巨噬細胞和上皮細胞LC3B、p62和酶ATG4B高表達,中性粒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和內皮細胞中的ATG5和ATG7染色陽性。
6 展望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自噬與Th2型氣道炎性反應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但由于自噬調節過程非常復雜與精細,其至今仍然是廣受研究者關注和不斷探索的熱點領域之一。近年來有一些特異性新型自噬調節劑在免疫調節、腫瘤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嘗試,這些數據為自噬調節劑在氣道過敏性疾病中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參考和實踐基礎,未來有望從自噬角度開發出一些靶向防治氣道過敏性疾病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