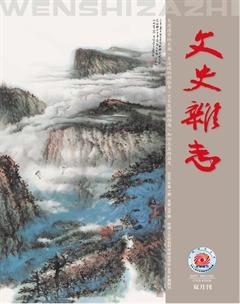略說漢代的巴蜀農業
袁檣


在戰國晚期秦蜀守李冰主持建成都江堰之前,雖然巴蜀的農業已經有所發展,但是在成都平原上的農田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數廣種薄收。都江堰把奔騰不羈的岷江水引來,立即在廣袤的原野上掀起了墾種農田的熱潮。很陜,獲得水利滋潤的田畝,竟然超過了100萬畝;每到秋收,豐收的喜悅便洋溢在田間地頭、百姓心頭。巨大的農業效益,為秦始皇統一天下,乃至后來楚漢相爭劉邦的勝利、漢初的戰略穩定,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撐。東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欲請諸葛亮出山輔助。在諸葛亮為劉備分析天下形勢的《隆中對》中,諸葛亮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業。”(《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東漢建安時期(公元196年-219年)的益州治今成都市,轄地比今四川及重慶要大。因此,可以說這是歷史上關于稱四川為“天府”的第一次記載,更為重要的是它出自尚在南陽躬耕的作為一介布衣的諸葛亮之口。這說明當時關于蜀中經濟形勢遠優過關中的觀點,已經形成并有了傳播。
過了一百余年,東晉著名史學家常璩在《華陽國志·蜀志》中則明白寫道:“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一天下謂之‘天府也。”“陸海”“天府”這兩頂標舉物產富饒、倉廩充實的華麗桂冠,便遷轉易主,最終落地西蜀。
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崇州市)人,他對家鄉的愛是真誠的、熱烈的,而他的文筆則是認真的、理性的。他為后人留下了一部最早的、比較完整的地方志——《華陽國志》。在那里面,他忠實地記錄了李冰治水的歷史偉績,說都江堰的功勞不止是灌溉蜀、廣漢、犍為三郡的農田,還使岷江上游砍伐的竹木,也能順水漂流,直到成都集散,“功省用饒”;同時,引水樞紐還有分洪減災效應,故被時人記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李冰治水的另一個意義是“穿二江(郫江、檢江)成都之中”,“以行舟船”,促進了長江沿線的物資交流與人文交匯,實現了西蜀與全國的戰略對接和融合,使岷江成為古代蜀人沖出四川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今天的川人之所以將李冰納入“四川十大歷史名人”之列(居次席),原因即在于此。
在東漢之前,“天府之國(土)”的美譽原本是為關中平原享用的;但到了東漢班固寫《西都賦》,已在說關中“郊野之富,號日近蜀”。它的潛臺詞是說當時蜀地之富已超過關中。不少史書對兩漢時期的巴蜀之富都有描述。如班固《漢書·地理志下》便徑直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焚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兇年憂,俗不愁苦。”《后漢書·公孫述列傳》載李熊復說公孫述,更盛稱:“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在東漢人物眼中的巴蜀,之所以一躍而為天下富庶之區,不用說當緣于李冰所修都江堰在兩百余年間的強大功用;除此之外,還有蜀地于鐵工具的普遍使用、耕作技術的普遍提高等原因。
漢代的巴蜀地區,特別是成都平原的水稻種植廣泛推行精耕細作的先進技術。在彭山、新都、宜賓、合江等地的東漢墓中,出土過一種陶水田模型,呈長方形,中有溝渠,渠中養魚。兩邊是稻田,田中密布秧窩。這說明那時已很注重多種經營、綜合利用。從四川各地漢墓所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來看,漢代巴蜀的農民已經掌握了設埂、分區、供水、排水等技術。稻田一般分為若干小區,有供水口和排水口。這不單是為了操作、管理的方便,更重要的是能使每塊面積的秧窩都能承受相等的水位。那時的農民已擁有施肥、除草、收獲等方面的豐富經驗。
漢代四川的氣候與現在相比,氣溫略高,雨水充足,適宜種植水稻。所以四川農業自漢代起就以水田種植為主,除種水稻外,還種芋等。漢代巴蜀農民在水利建設方面主動性較強,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項:一是充分利用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二是挖蓄水塘,貯存雨水;三是鑿井,取用地下水。
由于水利的興修、鐵器的廣泛使用和耕作技術的進步,使得蜀地的農作物產量達到比較高的水平。《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漢晉間“綿與雒(今綿竹、廣漢一帶)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換算成今天公制,這大約相當于畝產390-580公斤,達到全國的先進水平。西晉左思《蜀都賦》描繪魏晉間成都平原的風光:“溝渠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米莫莫”。
漢晉時的巴蜀地區已然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漢朝常調巴蜀的糧食賑濟災荒。按《漢書》的說法,漢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高帝紀上》)。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秋九月,又下詔:“今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武帝紀》)
巴蜀地區的園藝業、畜牧業及養魚、養蜂等副業也很發達。《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蜀郡有“桑漆麻纻之饒”,“其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不僅有桑蠶絲綢、茶葉美酒,而且柑橘的生產尤為著名。左思《蜀都賦》說“戶有橘柚之園”,這說的是柑橘種植的普遍。西漢朝廷甚至在巴蜀特設橘官,專門管理柑橘生產。南安(今樂山)的黃柑橘(即今廣柑)“大如升,色蒼黃”,是有名的特產。《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說:“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文中橘首列蜀地,足見其在全國影響很大。《華陽國志·蜀志》總結兩漢蜀地經濟說:“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在以后差不多兩千年的歲月里,四川一直是全國重要的商品糧油和生豬等主要農副產品生產基地,也是歷代中央王朝重要的庫糧和賦稅來源地。